纪念|华年与碎影:黄蜀芹生前最后一次访谈
【编者按】
著名导演黄蜀芹于2022年4月21日在沪逝世,享年83岁。
本文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川,于2013年对导演黄蜀芹的采访,以下系采访全文,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石川和黄蜀芹
受访:黄蜀芹、郑大圣(黄蜀芹之子)
访问:石川
时间:2013年3月3日下午
地点:上海徐家汇黄蜀芹寓所
一
石川(以下简称“石”):黄导,好久不见了。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黄蜀芹(以下简称“黄”):不好,不灵了。
石:您今天气色看上去很不错。
黄:那是假的。
郑大圣(以下简称“郑”):她现在体质还可以,只是偶尔会有点晕眩,短期记忆不太好,最近一两天的事记不住。但以前的事,比如她拍片的事情,或者看过的电影、电视剧,都能记住,反应也比较快。
石:哦?黄导现在还看电影吗?
黄:在电视上看。
(郑:主要在家里看电视,影院我也带她去,但没那么多了。)
石:老朋友还常来家里聊聊天吗?
黄:不来了,我已经不在这个圈子里了。
石:那是您比较超脱。
黄:我不在了,他们都还在。聊不起来了,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石:黄导,您还记得吗?2007年夏天我找您聊过一次,是关于给谢晋作副导演的事,那时候谢导还健在。
黄:对,我给谢晋做过两三次副导演。
石:是两次。一次是《啊!摇篮》,一次是《天云山传奇》。
黄:是这两部。拍《摇篮》的时候,我的任务是给他看驴。(笑)
石:这个上次您讲过,石晓华负责看孩子,您负责看驴。
黄:我是最没用的。(笑)
石:您还讲过,谢导让你们把军装上的金属纽扣全部换掉。他说,八路军军装上怎么会有金属扣,瞎搞,要换掉。你们只好连夜把纽扣全部拆掉,重新来过。
黄:是,谢晋很重视这个,很要细节,他这个人是很严格的。
石:后来您自己独立拍片,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吧?
黄:我拍片也是谢晋他们推荐的。
石:您是说《当代人》?
黄:是,《当代人》。那是部命题作文,别人都不要拍,才叫我去的。

《当代人》海报
石:这是潇湘厂的,不是上影的片子。他们厂创作力量不够,来向上影借人,老厂长徐桑楚就推荐您去了。
黄:对,徐桑楚,老厂长。他这个人看起来挺凶的,平时很严肃,不随便说笑。他让我去拍,我就去了。
石:我听老厂长讲过,说让谁去好呢?一线导演不能去,自己的片子都拍不完,就让年轻人去吧。但又要找一个比较成熟,能独立工作的。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您。他说,这样一举两得:既帮兄弟厂解决了困难,又为本厂培养了新生力量,何乐而不为。是不是这样?
黄:是。我觉得徐桑楚他早就想好了。厂里工宣队不让去,他就跟他们绕啊绕的,把工宣队绕糊涂了,就放我去了。
(郑:那时候没有工宣队了吧?都1983年、1984年了,已经是党委了,没有革委会,也没有工宣队了。主要是轮不到你们拍戏,老导演都没戏拍,你们就更轮不上了。)
石:当时派黄导您去,是因为老厂长觉得您完全可以独立拍片了。此前,您在《天云山传奇》剧组里,实际上已经有过执行导演的经验了。
黄:《天云山》我是副导演。
石:您是副导演,但有些场面是您在现场指挥拍的。比如,县师范里的几场戏。
黄:对,是在安徽(青阳县)。《天云山》比《摇篮》参与多一点。《摇篮》主要是站在边上看别人怎么拍。
石:到《当代人》,就完全独立了。
黄:拍这戏的时候是大热天,在广西柳州,热得要命,我都晕倒过3次。
石:您是拼命三郎。
黄:那时候只要有戏拍就好,管他什么呢。心里着急,巴不得有戏拍。已经浪费了很长时间,不想再浪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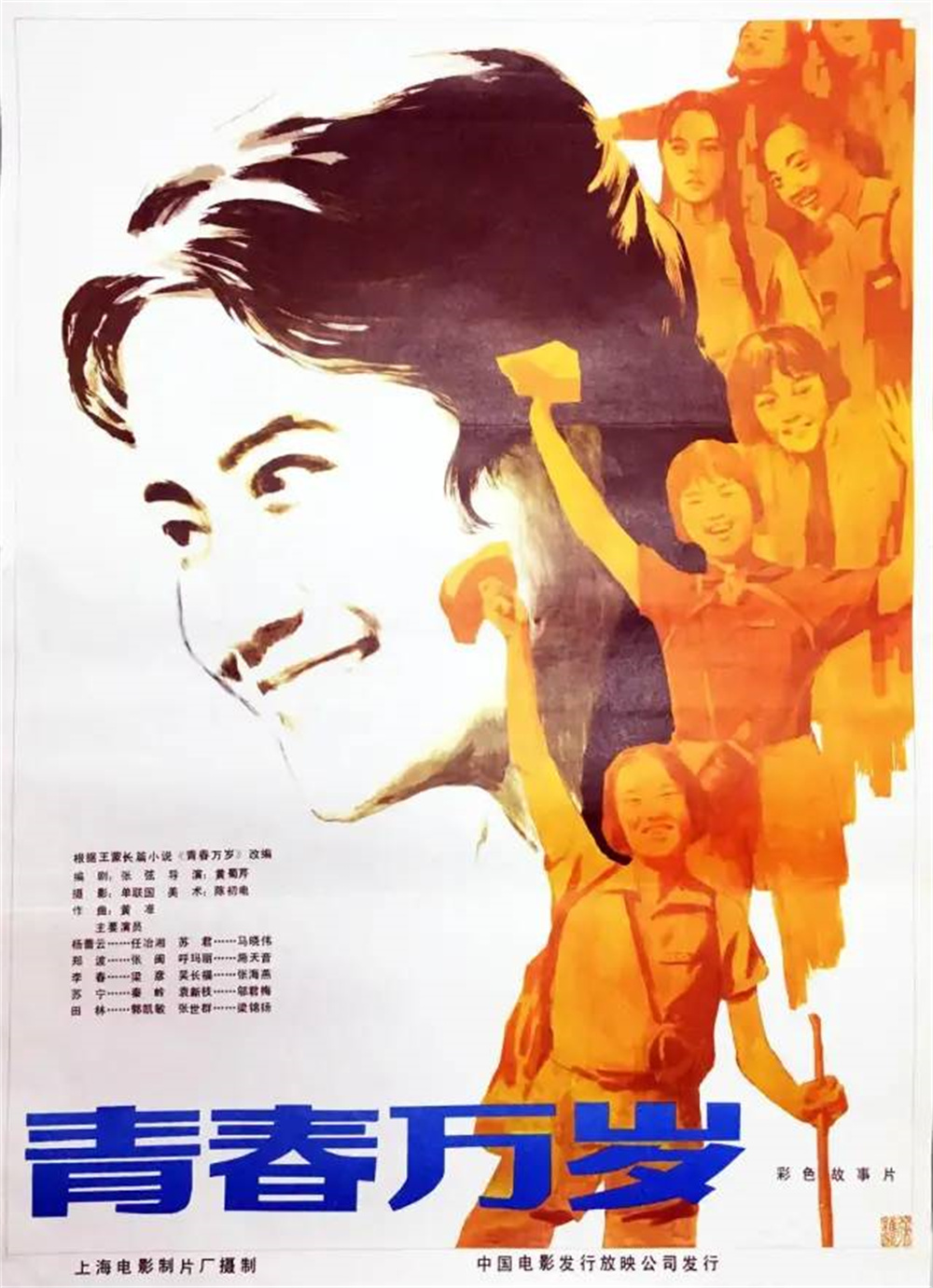
《青春万岁》海报
石:《当代人》以后,您又拍了《青春万岁》。这两个片子您更喜欢哪一部?
黄:喜欢《青春万岁》。《当代人》是他们看我没戏拍,才给我的。这样蛮好,蛮公平的。我也奇怪,那么多人排队等着呢,怎么会轮到我头上?还感到很意外。
石:能有这样的机会,也难得,您应该感到高兴吧?
黄:高兴,但也挺哆嗦的,万一弄不好怎么办?怕拍砸了。这东西不好弄,但我又能怎么样,总比没戏拍强。
石:你是说这部戏比较概念化?
黄:不是我最喜欢的,特别想拍的那种。
石:国营厂的时候,大家都和您有一样的心态。自己愿不愿意是一码事,厂里给不给机会是另一码事。那时候是靠厂里分配任务,分到你头上,你才有戏拍。
黄:是。分配任务的人也会犯嘀咕,分得对不对,公平不公平。也有找错人的,戏拍砸了,领导要骂娘。就怕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石: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戏,哪怕是自己不太喜欢的,也要认真去拍,也要拍得一丝不苟。
黄: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什么事都不争不吵。事情来了,人家都往前拱,我是往后缩。和别人不闹矛盾。拍成了,是运气好。你要说什么出类拔萃,我觉得我们都算不上。
石:运气好有时候也能碰上自己喜欢的题材,像《青春万岁》,拍这部戏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黄:王蒙的小说,写女中的,我中学就是在女中念的。
石:片子里的生活,是不是和您自己的高中生活很像?
黄:我们就一群小丫头,在操场上跑啊、跑啊,挺爱疯的。
(郑:她跟我说过,上中学以前,她性格比较闷,不大爱说话。学校里有很多男生横冲直撞。高中是女中,没有男生了,女孩子在一起比较融洽,才开朗了。)
黄:男生是故意来撞的啊,我总缩在别人后面。很怕看见男生。他们是成心来撞你的。
石:所以您对《青春万岁》特别有共鸣。您还记得是怎么得到这个剧本的吗?
黄:是文学部一个人(王士祯)弄来的。领导上让我拍,我就拍。
石:您对剧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黄:剧本忘记了,王蒙小说以前就读过,谢晋拿给我的,很喜欢,反复看了好几遍。
石:当时有人反对这篇小说,说干嘛把五十年代写得这么美好?
黄:那个时候的人就是那样,很幼稚,傻傻的。(笑)
石:是不是有人觉得这部小说比较“左”?
黄:没什么“左”不“左”的,那时候的人就那样。一群小丫头片子,什么都不懂,就爱疯,能把这种味道拍出来就不错了。
石:当时拍这部片子情况您能说一下吗?比如说,外景地是在哪儿?
黄:王蒙小说写的是北方,和上海这边的女中不一样。我们到北京去拍外景,室内景都是在上海拍的。
(郑:学校的外景是在松江二中。)
黄:那个操场是松江二中的。松江二中那时候看上去蛮像北京的。上海的学校都小小的,松江二中很大。我就怕这些学生说话带上海口音,上海女孩说不出北京话那种味道。拍完以后,又重新找了一群女孩子来给她们配音。
二
石:拍完《青春万岁》以后,您又拍了《童年的朋友》。拍《青春万岁》我能理解,因为里面有您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记忆。可拍《童年的朋友》又是为什么呢?延安的生活,毕竟和您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创作这部影片呢?
黄:也是厂里的任务。
石:剧本里有什么特别东西打动了您?
黄:没觉得剧本有什么特别。延安、小八路,这些东西怎么拍,我也不知道。上大学的时候,班里有几个干部子弟,他们有这样的背景。我没有,不太了解。我们就去陕北采景,看到黄土高原、窑洞,就全傻了,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要重新去理解它。
石:那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黄:延安比较正宗,那时候的上海总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石:您意思是想说两个地方的文化差异吗?
黄:对。地域对我倒不算什么。我也喜欢北方,特别迷新疆、西藏。那时候年轻,喜欢往外跑,背了个小包就出门了,买火车票都不花钱,大家挤在一块。
石:您是说“文革”初期,您和郑长符老师一起到新疆“串连”的事?
黄:就是。我中学时候看过新疆歌舞,就很迷新疆。他说我们去新疆吧,我说好,就跟他一起去了。反正没包袱,想干啥就干啥。
石:后来拍《啊!摇篮》的时候,又去了陕西、山西一带,您喜欢那边吗?
黄:其实我更接近北方,我对上海反而不适应,不是人家想的那样。
石: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黄:我父亲是广东人,但他是在天津长大的。长大后又到英国念书,回国以后才到上海工作。对上海这地方,我们还是属于从远处看的那种人。
石:可您在上海那么多年,说上海话,喝黄浦江的水……
黄:我们家兄弟姐妹都是说上海话的,只有我爹妈说普通话,也不是很纯正,带一点天津口音。家里生活习惯也是北方的。
石:天津话您会说吗?
黄:我不会,大圣会。他小时候说天津话,把我都说哭了。
石:啊?为什么会哭?
黄:他小时候在天津长大,后来把他接回上海,他说话我都听不懂。我就哭,这还是我儿子吗?我儿子怎么会是这样?哭了好些日子,特别伤心。(笑)
石:所以您内心对北方有一种特殊感情?
黄:小时候在上海上小学,别的同学都穿很漂亮的小洋装,我们姐妹穿的是北方的小棉袍。那间学校是一家贵族学校,别的孩子都是有钱人家出身。
石: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土?
黄:有那么一点。我爸把我们送到这间学校念书,是想让我们接受西式教育。
石:大圣去年拍了两部天津的戏,一部叫《天津闲人》,一部叫《危城》。
黄:是啊,我看的时候就学说那种话,“嘛呀,嘛呀,你说嘛呀?”,好玩死了。
石:您这说的不是很地道吗?
黄:毕竟家里都是天津人嘛。
石:大圣这两部片子您喜欢吗?
黄:看《天津闲人》的时候,觉得大圣有幽默感了,这个不错。以前拍的东西都太严肃。
石: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童年的朋友》。我看过您以前一篇访谈,您在这部片子中开始有意识追求视觉造型,特别强调要把陕北自然环境的视觉风格表现出来。
黄:陕北就是那样,黄土高原啊、黄河啊,就是那种风格。能把这种感觉拍出来就对了。
石:那您觉得自己拍出这种感觉来了吗?
黄:不好说,马马虎虎吧。(笑)
石:《童年的朋友》以后,您又拍了《跨国界行动》。当时我们看过,都很吃惊,心想黄蜀芹怎么会去拍这样一部片子,又有惊险,又有动作。那时候是商业片大潮嘛,大家都去拍商业片,当时有种说法叫“娱乐片”,尽是武打、枪战、动作什么的。
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拍这个片子,别人叫我拍,我就拍了。
石:是不是那个时候厂里亏损,经济压力比较大,让你们年轻导演多拍些卖座片,为厂里分忧?
黄:当时这片子就很卖座,大光明门口,黄牛票,炒到十块钱一张。
石:十块?当时一张电影票才多少钱?顶多几毛钱吧?
黄:还是有很多人排队买票,上座挺好的。别人来告诉我,当时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石:但您本人并不特别喜欢这种打打杀杀的片子对吗?
黄:不喜欢,我是属于那种忒胆小,凡事往后缩的人,不喜欢和别人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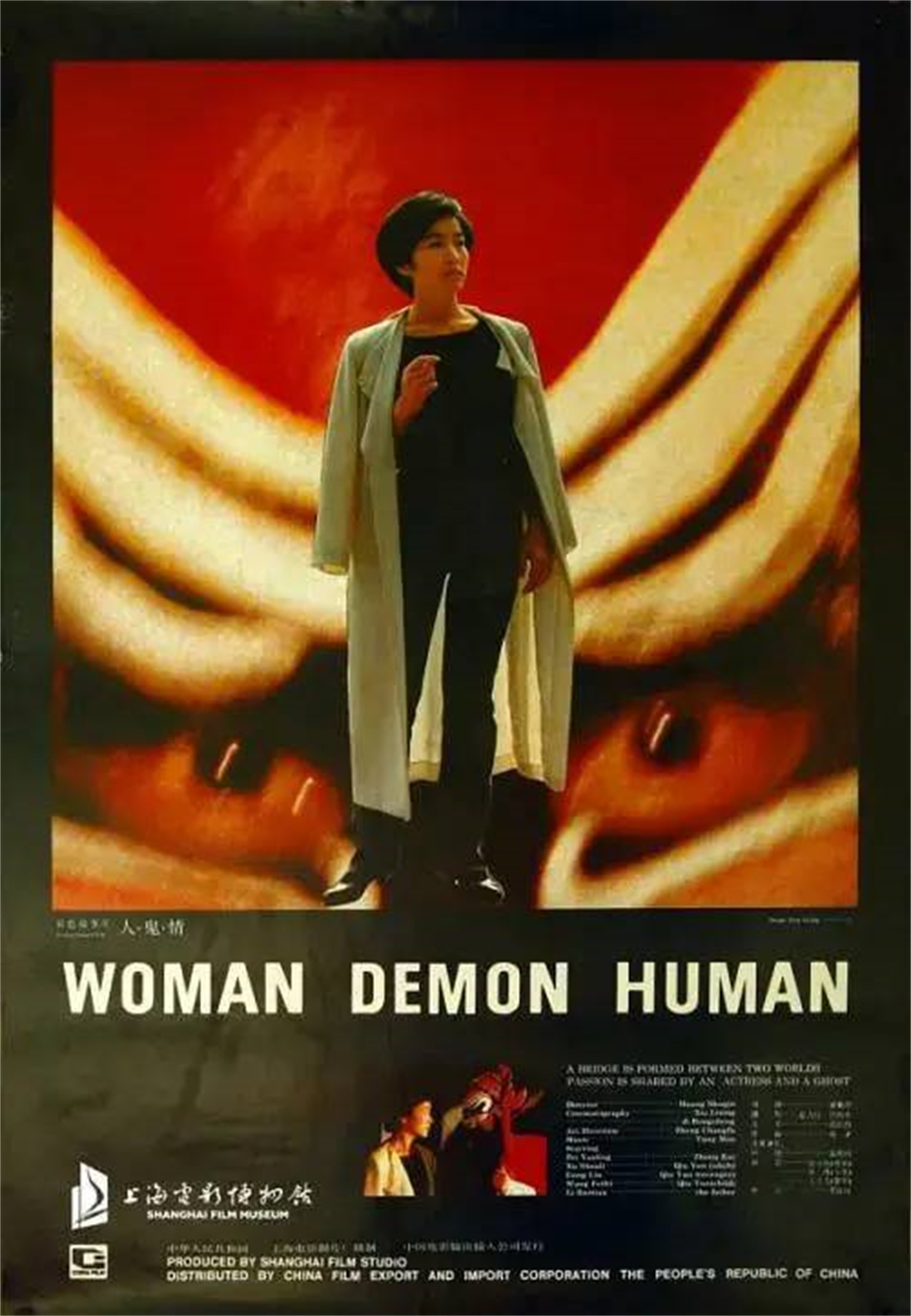
《人鬼情》海报
石:所以,拿《跨国界行动》和后面一部《人鬼情》相比,您更喜欢《人鬼情》?
黄:是,《人鬼情》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石:为什么呢?
黄:我喜欢裴艳玲演的那个戏,一个女人演个大男人,画个大花脸,穿着厚底靴,真的很受震动,觉得她太了不起了。
石:我看到过您那时候的一张照片。您扮上了戏妆,是您自己化的吗?
黄:不是,他们给弄的,我不会化。(笑)
(郑:其实我妈不太懂戏,我们家真正懂戏的是我爸。)
石:这我听说过,他平时自己还会唱。
黄:是哼,他那不叫唱。喜欢哼,没词儿的,哼什么我也听不出来。
石:您会哼吗?
黄:我不会。(笑)
石:拍《人鬼情》的时候,您没跟裴艳玲学两句?
黄:学两句?(笑)我不行的,特笨,学不会。
石:您太谦虚了。您不是很小的时候就演过电影吗?《不了情》,您还记得吗?
黄:电影跟戏曲完全是两码事。
石:《不了情》您还记得吗?您在里面演刘琼的女儿,一个穿得漂漂亮亮的小女孩。
黄:嗯,那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导演是桑弧。演的时候就不高兴啦,他们骗我去的。小时候不懂事,老给大人找别扭。
石:人家小孩都觉得拍电影好玩,您不觉得好玩吗?
黄:本来觉得好玩,就跟他们去了。演了之后就觉得不对了,不是原来想的那样,就傻了,开始往回缩。
石:我记得有一场戏,您病了,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今天看也还蛮像那么回事的。
黄:像个倒霉蛋儿,闭着眼睛,想逃避。人家桑弧那时候是个年轻导演,刚开始拍片,就碰上我这种屁孩子,不听话,闹别扭,他就倒了霉了。
石:不是挺好的吗?至少今天还能在银幕上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黄:他们骗我去的。说你愿不愿意拍戏?要愿意,就跟我们去吃好吃的。要不要?要!就这样被骗走了。(笑)
石:后来好吃的吃着了吗?
黄:吃了吧。也就客串一下,哪知道什么是拍电影?
石:就这一次?后来还拍过吗?
黄:(摇头)这一次就吓死了,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以后就再也不敢了。
(郑:《不了情》的编剧是张爱玲。)
石:是啊,大作家。
黄:那时候,我一个小不点,懂个什么?
石:怎么着也算和刘琼、陈燕燕这样的大牌明星拍过戏,您喜欢他们吗?
黄:他们都挺好的,老逗我玩。我那时候都不会笑,一天到晚撅着嘴,尽闹别扭。我就当不了演员。
石:那考大学的时候,您为什么还考电影学院呢?
黄:后来懂事了,到电影学院都20岁了,总归懂得点道理了,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喜欢的。
石:这不正好说明,您心里还是喜欢电影的吗?
黄:是喜欢,但不是表演。我就没报表演系。再不愿走小孩子那会儿走过的路了。
石:电影学院的生活还记得吗?老师、同学,您对哪些人印象比较深呢?
黄:读书那会,电影学院也是个新学校。课本是苏联那套,表演课也要上,心里特害怕。
石:那您碰到排小品怎么办?
黄:那个是不上银幕的,胶片紧张,不给你们浪费钱,只是在舞台上演。
石:您都演过什么角色?
黄:我就一跑龙套的,尽演群众了。我们班那会儿,表演最好的是郭宝昌,他演北京“爷们儿”,特别有劲。他人也好,但是呢,还是被阶级斗争给耽搁了。
石:您曾说过,《大宅门》是他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就想拍的。他就是为了想把自己家里的事拍成电影才来考电影学院的。
黄:他那时候已经开始弄这个剧本了,后来草稿丢了,又从头开始写。
石:您自己有什么特别想拍的东西吗?
黄:我那会儿就总觉得自己特笨,话也不会说,还要演小品,真的够呛。
石:您说的可跟其他人对您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我听说,有一回你班同学问班主任田风老师,说咱班同学以后谁能变成大导演,田风老师说,黄蜀芹。
黄:这个我可不知道,是他们后来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田风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大学念了五年,我就整天低着头,一点自信也没有。
石:你讲过这段,我看过您的一篇访谈,上面说起过这事。
黄:是吗?那也是听他们说的。
石:您跟老师和同学关系相处得好吗?
黄:一般,不好不坏。我就不愿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但学校开会都要去。郭宝昌他们那帮子“北京爷们儿”,出身不好,一开会就要给人抓辫子。
石:那您的出身算好还是不好?
黄:中等吧,知识分子,不是工农兵,也不是资产阶级。那时候抓反动学生,郭宝昌就被抓了。可能是他出身不好吧,礼拜天总让外地来的同学去他家吃饭,像个小首领一样,就说他是反动学生。
石:电影学院毕业以后,分到上影厂,那之后拍过什么东西吗?
黄:没有。回上海以后就是下乡,搞四清,接下来就“文革”。尽瞎折腾了。
石:那时候除了搞四清,调查别人,干过农活吗?
黄:干过,在上海郊区的菜地。人家都是蹲在地里干活,我蹲不下去,宁可跪着也不愿蹲。腿上没力气。
石:心里觉得委屈吗?
黄:不委屈。到底还年轻啊,跟现在比起来,欲望少,想想也没什么了不起。
石:体力上呢?吃得消吗?
黄:就是不会蹲,跪在地上,腿麻了就站起来挪挪。
石:您当时的心态,是不是比一般人更好些?
黄:还可以吧,要不然你又能怎么样?
石:不拍戏,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黄:也没有,不让拍戏,咱就结婚、生孩子,做自己的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三
(郑:刚才石川问您,当时您有没有特别想拍的戏?)
黄:没想过。
石:我听说您“文革”结束后,有段时间想拍《杨开慧》。为了这部戏,您还到湖南做过实地考察和走访。
(郑:《杨开慧》这事我还记得,应该在《当代人》之前。当时你们看了许多杨开慧的书信。但后来没拍成。)
石:什么原因没拍成呢?
黄:太复杂,很多东西不是以前想的那么简单,没法拍。
(郑:她还有个想拍的,一个捡垃圾的老太太,捡了很多孩子,把他们养大的那个,名字都取好了,叫《垃圾千金》,最后也没拍成。)
黄:那个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老太太,自己都吃不饱,却从马路上捡回很多孩子,把他们养大。我当时看到这个,觉得很震动。但别人都说不好,“新中国”怎么可以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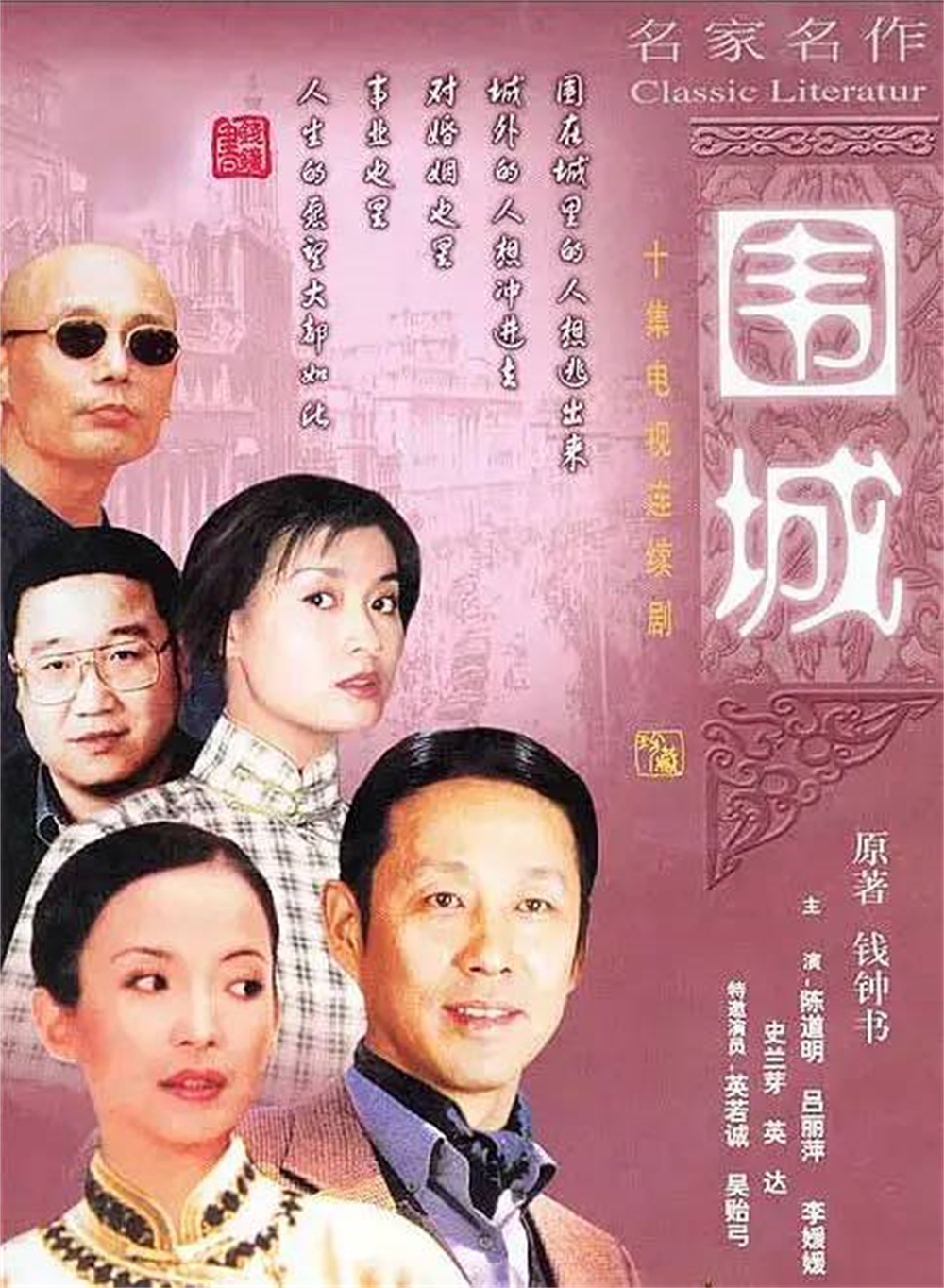
《围城》海报
石:这个应该是1990年代初的事情,已经拍完《围城》了吧?
(郑:是的,他们剧本写好了,景也看好了。我记得当时我爸是美工,摄影是王小列。)
黄:你看,他记得比我清楚多了。(笑)
(郑:您说别人不认可,其实是民政部门有明确的书面意见。报纸上那个报道好像是在江苏还是浙江?你们当时去了两次,一次是采访老太太,一次是去看景。最后,这个片子的外景地确定在湖南、江西那一片。)
石:那老太太收养了多少个孩子?
黄:有多少个?不记得了。
(郑:您跟我说过,当时老太太身边就有十来个孩子。你们去采访她的时候,还碰到有个已经长大的孩子闹早恋,想结婚,弄得老太太很头疼。结果这孩子恋爱出问题了,就吞钥匙想自杀。是个女孩子,喜欢搜集各种各样的钥匙,挂在胸前,有一大把。因为她自己没有家,就去捡别人的钥匙,好像要去开自己家门上的锁。碰到那时候正好是青春期,跟一个一起长大的男孩谈朋友,一会好,一会吵,一会又好了,一会又吵。她自杀就为这事。你们那会儿管这个女孩叫“钥匙女”。)
石:那孩子当时多大?
黄:那时候正上中学,十五六岁的样子。
石:为什么当时民政部门会有不同意见?
黄:他们的意思,你什么不好拍,干嘛偏要去拍个叫花子?
石:可这种题材也不一定是抹黑啊,也能拍得很正面,比如从讴歌母性的角度。
黄:我们也不想拍得惨兮兮的,也想尽可能拍乐呵一点。可这个题材就不让碰。没办法,当导演有时真挺难的。
石:这片子打算找谁来演呢?
黄:演员还没定。
石:这个老太太的戏没拍成,后来《嗨,佛兰克》又是个老太太,方青卓演的,两部片子之间有关系吗?
黄:就是因为《垃圾千金》没拍成,才拍了《弗兰克》。
石:可《嗨,弗兰克》是2001年的,两部戏中间隔了将近十年。
黄:《弗兰克》筹备就用了五六年,最后成了,还是蛮开心的。

《童年的朋友》海报
石:您大概是什么时候知道《围城》这部小说的?
黄:是别人推荐给我的。在黄河边拍《童年的朋友》。那阵子黄河边上真挺热闹。黄河那边是《黄土地》那个组,我们在榆林这边。因为演员时间的问题,我们这边有两天拍不了戏,没事干,我就去了趟县城。孙雄飞给我拍电报,说你应该看看《围城》。我就掉头去了趟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一看,钱钟书是谁?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作者啊?结果,在那个小地方看了《围城》。知识分子味道很重的一部小说,感觉很吃惊。啊?!我们还有这样的小说?讲的东西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都不一样。
石:我是上大学那会儿看,跟您感觉完全一样,也不知道钱钟书是谁,但特别喜欢这部小说。后来在报上看到您要拍《围城》,我们就特别期待。
黄:当时让我拍,我就哆嗦。这能行吗?我能拍吗?一点自信都没有。
石:我们知道《围城》要拍电视剧,第一反应就是,钱钟书的语言很传神,要是拍成电视剧,书里有很多旁观者的叙述和描写、比喻该怎么办?后来您是用画外音来解决的,我们都觉得很精彩,保留了原作的韵味。
黄:对,那个最好是洋嗓子,特意去请毕克配音。
(郑:《围城》应该是毕克留下的最后的配音作品了。)
石:我去过上虞春晖中学,那是谢晋的母校。抗战刚开始的时候,谢晋在那里念过一个学期。校园里有一片老校舍,那里就是《围城》三闾大学的外景地。
黄:你去过?
石:去过两次,我清清楚楚记得电视剧里有场戏,陈道明在教师宿舍二楼过道上洗衣服,孙柔嘉上来和他搭讪……那个水斗今天都还在。
黄:《围城》一共10集,我们拍了100天,10天一集。
(郑:真羡慕你们那会儿,要搁现在,怎么可能10天一集?)
石:我很好奇,一部电视剧怎么能找来这么多大腕?连英若诚、吴贻弓、沙叶新……都出场了。
黄:都觉得这戏特好玩,一叫他们,都来了。拍的时候也很开心。常常是,一场戏拍完,大伙就给自己鼓掌。剧组里,大伙相处得不错,没有谁给别人使绊子,捉弄人的。
石:英若诚曾当过文化部副部长,也算是个大官儿,但在《围城》里只演了个小角色。
黄:他以前也是演小人物,《茶馆》里的刘麻子就是他演的。
石:《围城》里他演高松年,三闾大学的校长。
黄:鬼头鬼脑一老头。
石:里面最逗的还有俩人,一个是葛优,一个是李天济。那个李天济,“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哈!以前我们有个校长就这样。
黄:(笑)李天济本来就是特好玩的一个人,见得人就说笑话,逗乐子。
石:您是怎么想到用葛优来演李梅亭的?那时候他应该名气还不算很大吧?
(郑:《顽主》是他演的,但真正火起来,应该是《编辑部的故事》,老百姓开始都知道他了。)
黄:葛优那时候就鬼里鬼气的,人特别瘦,看上去就特逗。
石:《围城》很完整,很细致,里面每个小角色也都很有趣。
黄:像个人,说人话,不说鬼话。
石:从观众上讲,知识分子一般比较喜欢《围城》,一般观众更喜欢您的《孽债》。
黄:我本来以为没人会看《围城》,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怕,这么学究气的东西怎么弄法?后来发现,只要老老实实把故事拍出来也不错。
石:这两部电视剧您自己更喜欢哪个?
黄:我喜欢《围城》。
(郑:《孽债》同期声是上海话的还是普通话?)
黄:上海话,普通话是后来配的。
石:这个黄导以前说过,比如刚开头的时候,那群孩子从云南来上海,人生地不熟,听不懂上海话。扮演父母的演员都说上海话,那些小演员本身就是云南的,他们原本就听不懂上海话。大人一张嘴,小孩们就懵了,听不明白。这样,他们和父母之间,和这座城市之间的隔膜感就出来了。
黄:拍的时候他们就老是问,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什么?听不懂大人的台词,他们心里也蛮害怕的。
……
石:今天差不多了吧?黄导您也说了大半天了,累了吧?
黄:不累,挺好玩的。
(郑:谢谢你来看她,今天她和你聊得挺开心的,说了这么多。)
石:黄导您要保重,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
黄:开心,人傻了就天天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