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原读书会2015年由毛尖、朱康、罗萌、丁雄飞、黄锐杰发起,致力于绍介最新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研读最新的当代文学作品。我们认为,文学文本是各种因素生产或转化出的一种全新形态,因此更需要关注文本的物质属性,强调文学形式的三方链接:修辞生成、历史语境呈现及其读者接受。
本文系莽原读书会2019年7月活动的文字整理稿,刊发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十期,原标题为“连续性的韵律:在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布尔乔亚’”,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布尔乔亚文化死了
毛尖: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莫莱蒂和《布尔乔亚》,一会请朱康来主持。我先跟各位通报一下我们读书会的成果。最近已经出版和即将推出的“远读”译丛(朱康、丁雄飞、罗萌主编)有下列几种:伊格尔顿的《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D. A. 米勒的《简·奥斯丁,或风格的秘密》、南希·阿姆斯特朗的《小说如何思考:个人主义的限度》,以及莫莱蒂的《布尔乔亚: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另外,莫莱蒂的《现代史诗》《远读》《欧洲小说地图集》中译本,也在陆续翻译中。我们读书会关注莫莱蒂由来已久。用《长安十二时辰》中徐宾的说法,莫莱蒂也有一套“大案牍术”,“远读”大数据,和伊格尔顿、杰姆逊一起,成为当代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三位节点人物。可惜莫莱蒂在中国译介太少,所以我们立志补白,尤其“远读”还特别适合教学,它让我们去关注那些比文本小得多或大得多的单位,比如装置、主题、文类、体系,藉此,远读让我们和文本拉开距离,通过串联形式单位来解释文学史的规律,理解整个文学体系。
《布尔乔亚》我们都读过,现在朱康完成了全书翻译,待会先请他谈。就我个人而言,莫莱蒂的远读法,他的关键词抓取,对关键词的精准辨析和历史勾连,都特别具有示范价值。

朱康:《布尔乔亚》是莫莱蒂出版于2013年的著作,原书全名为“The Bourgeois: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命名,通过一个冒号的隔离与连接,莫莱蒂既界定了自己的写作立场——“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同时又明确了自己的写作主题——“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布尔乔亚”。而这个Between,不仅意味着区分,更意味着关联甚至综合:作为文学史家的莫莱蒂立足于历史中的文学,通过叙述文学中的历史,再现历史中的布尔乔亚;或者反过来,通过再现文学中的布尔乔亚,叙述布尔乔亚的历史。
在莫莱蒂的母语意大利语中,历史与故事是同一个词语:storia。叙述布尔乔亚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在叙述布尔乔亚的故事。《布尔乔亚》正文共五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序曲,交代布尔乔亚在十八世纪的自我理解,第二到五章是全书的主干,展现布尔乔亚在十九世纪的命运:它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经历了上升与妥协,当发展并转移至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带,它经历了挫折与自我批判。
十九世纪是一个布尔乔亚的世纪,但在这一世纪,如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布尔乔亚经验》中所说,布尔乔亚一词在英语、法语、德语之间存在着表达与分类的混乱。将《布尔乔亚经验》与《布尔乔亚》对比可以看出,莫莱蒂触及而又绕过了这一混乱的氛围,树立了一个理想型——“资产的布尔乔亚”与“文化的布尔乔亚”的融合形象。两个布尔乔亚的融合召唤着布尔乔亚的上升,但随后布尔乔亚就面临着其文化与资产之间的失衡。在十九世纪中叶,布尔乔亚建立了有力的社会控制,但其文化没有建立有力的阶级认同,其成员反倒屈服于旧贵族文化的霸权。到十九世纪末以后,“资本主义胜利了,布尔乔亚文化死了”。

毛尖:朱康说的两个布尔乔亚形象,揭示的布尔乔亚文化之死,都很有意义。我在看莫莱蒂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布尔乔亚一旦被放在“中间”,就无法承担世界道路的责任。我的问题是,如果那个能承担世界道路之责的布尔乔亚确实死了,是不是已借尸还魂在中产阶级身上?或者,换个问法,我们今天依然到处看到听到的布尔乔亚是什么,中产阶级又是什么?
朱康:中文里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词语,在当下,它一般被用来与the middle class对应,不时也被用作bourgeois的译词。而在英语中,这两个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平行使用。
十七世纪末bourgeois从法语进入英语,十八世纪末the middle class(es)在英语中出现。在彼得·盖伊的追溯里,英国人抗拒前者而偏爱后者,因为前者作为外来词具有时尚的性质,后者作为本土词带有严肃而理性的尊重。在雷蒙·威廉斯的考察里,the middle class曾经作为bourgeois的翻译词提供了后者在十九世纪前的大部分意涵,但这一从封建社会里上层、中层、下层的区分里起源的概念,在布尔乔亚成为上层统治阶级后,无法再成为bourgeois的替代者。
莫莱蒂将the middle class的兴起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布尔乔亚的品格:它喜欢隐藏真实身份,the middle class是它的面具;一是社会的需要:社会因工业增长而两极分化,渴望一条连接富人和穷人的纽带。这两方面都使the middle class有一种内在的模糊性。相对于bourgeois这个包含都市世界意识的概念,the middle class更像是描述性词语,它指向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位置,而各层次之间构成的是一个可流动的连续体。
的确,那个能承担世界道路之责的布尔乔亚死了。但不是整个布尔乔亚死了。莫莱蒂说:“资本主义胜利了,布尔乔亚文化死了。”而这也就是说:文化的布尔乔亚死了,资产的布尔乔亚还在;或者说:布尔乔亚死了,资产阶级还在。它无法在中产阶级身上借尸还魂,因为中产阶级作为布尔乔亚的伪装或发明,本身就是布尔乔亚文化死亡的产物。事实上,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布尔乔亚,只能是那个资产的布尔乔亚,而人们所谈论的中产阶级,不过就是布尔乔亚发明出来的作为纽带的阶级,或者用布尔乔亚自身的分层化的说法:小布尔乔亚。
黄锐杰:莫莱蒂讨论布尔乔亚文化之死的时候征引了1932年托马斯·曼的《歌德——布尔乔亚时代的代表》演说。托马斯·曼指出,歌德代表的布尔乔亚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唯个性论的时代”,歌德的全人理想滋养着这一时代,一战后这一理想“失落”(lost)了。莫莱蒂“补刀”指出“布尔乔亚的失落”的另一面恰恰是资本主义的胜利:经由两次世界大战,布尔乔亚最终放弃了对霸权(hegemony)的追求,转而隐匿于“中产阶级”的政治神话之中,大众的合意(consensus)取代霸权,商品又主宰着合意。

莫莱蒂没有接着马斯·曼讨论布尔乔亚文化的出路,实际上托马斯·曼乐观地设想了一个“后布尔乔亚的世界”:个体不再重要,只有全部的人才能使人性完美,布尔乔亚性将“进入世界共体性,进入共产主义性”。这还是从“文化”入手。1934年的桑巴特——莫莱蒂认为“将资本主义和布尔乔亚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的人——则已经设想了一套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将歌德的文化民族引向政治民族的解决方式。他在《德意志社会主义》中设想由德意志民族性出发,破除建基于“奢侈”的宫廷模式之上的主权,施行全面计划经济。不幸的是,两人的主张很快就为纳粹的声浪吞没。

桑巴特的《德意志社会主义》1934年出版,同年便由杨树人先生译出,这是一次“布尔乔亚”理论旅行的过程。这书在抗战爆发前译出,既是对政治民族的召唤,也是面向未来的劝诫。
丁雄飞:“布尔乔亚”的理论旅行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布尔乔亚》第四章讨论了十九世纪末欧洲半边缘地区的布尔乔亚,那再往东到其时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呢?“bourgeois”最早在日语中被译为“资本家”“富豪”。1904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日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其创造了专门的译名“绅士”(复数作“绅士阀”),1908年《天义》所载、译自日文的中文《宣言》第一章采纳了这个译名(刘师培在为“绅士阀”作的注里已经用到了“资本阶级”“中级市民”等词)。1919年的日译本《宣言》把bourgeois译为“有产者”(复数作“有产者阶级”),即被李大钊引入中文。1920年,陈独秀等人开始使用“资产阶级”。再后来就有了毛泽东对于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农、手工业主、知识分子、小商人等)的区分。从绅士阀到资产阶级,正如从平民到无产阶级:语言不断革命。
从上述翻译史不难发现,“资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批判对象被引入中国的。近代中国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有小布尔乔亚文化,但大都集中在租界,是少数、局部的存在,尚没有形成中国的布尔乔亚社会和布尔乔亚领导权。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观念,不仅是为了“阶级分析”和符合“历史规律”,更是为了超越这一观念:彼时茅盾和朱自清虽然持有不同的小资产阶级观,但都认为无产阶级必然胜利,小资产阶级必然没落。

布尔乔亚风格,布尔乔亚文体
朱康:莫莱蒂仿佛的确是把《布尔乔亚》当作故事来写的,甚至是当作长篇小说来写的,因为他为这部著作设置了一个主人公。不过这主人公却不是布尔乔亚。布尔乔亚仅是他的这部著作的主题(subject),根据他在最后一章所强调的,“散文(prose)才是本书唯一的、真正的主人公(hero)”。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散文是典型的布尔乔亚style——(生活)风格/文体,对于布尔乔亚来说,散文既是一种再现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正如莫莱蒂的“布尔乔亚”是“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布尔乔亚”,他的“散文”是在存在与再现之间的散文,而布尔乔亚的“在历史与文学之间”严格对应着散文的“在存在与再现之间”。
散文,prose,它的形容词,prosaic,意思是散文体的,平凡的、乏味的。当莫莱蒂将散文放在存在与再现之间,也就是放在the prosaic与the prose之间。莫莱蒂在导论里说他“是在style里而不是在故事里寻找布尔乔亚的”,进而又说“所谓style,主要指两件事情:散文与关键词”。全书除导论外共五章三十节,有六节以“散文”为题,七节在讨论关键词。在“散文”这一标题之下,莫莱蒂描述了散文的连续性、精确性、生产性、中立性等等品质;而他所选取的关键词,都是“有用的”“效率”“舒适的”等等这些普通用词,这些关键词归结起来就是prosaic——散文性的。这些关于“散文”的章节对应着对世界的“再现”——文体意义上的散文的再现,这些关键词指向的都是“在世界中存在”——风格意义上的散文性的存在。在这里看出莫莱蒂这一著作的体系性的构造:历史与文学、存在与再现、the prosaic(风格)与the prose(文体),相互对应。而正如他所说的“文学”是历史中的文学,他所说的“再现”是存在中的再现,他所说的“散文”是散文性的生活风格中的散文。例如,他借助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讨论“有用的”这一生活风格的关键词,结论却是:这部长篇小说是“笛福给予布尔乔亚‘心态’的伟大贡献:作为有用性的风格的散文”。
罗萌:读《布尔乔亚》的过程中,我常常会联想到另一部在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小说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著作: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二者在年代和所涉作品方面具有相关性,当然,区别也非常明显。首先,《布尔乔亚》含括的地理范围是整个欧洲,突显“文学地图”的意味;更主要的区别是方法论上的,《小说的兴起》采取传统做法,选择若干重要作家进行论述,而《布尔乔亚》从“关键词”入手,一定程度缩减了个别作家的重要性。

这两部研究关于一些关键概念的阐发同样体现出差异化,非常有意思。比如针对“现实主义”。瓦特认为,十八世纪以后成为小说主流的现实主义,起源于一种观念,即“个人通过知觉可以发现真理”,也就是说,强调的是经验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个人主义是其认识论前提。具体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背离传统,内容来自真实经验,而不是神话、历史、传说或先前的文学作品。一言以蔽之,根据瓦特的解释,小说的现实性,和小说的“独创性”,是相互绑定的。
莫莱蒂寻求的是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双线并进”关系。因此,“现实主义”在他这里,超越了文学概念的范畴。书中有这样的论断:布尔乔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的阶级。那么,布尔乔亚是如何演绎现实主义的?莫莱蒂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它的现实性表现在,它曾经充分实现去魅,迫使社会直面自身的真相,然后和现实妥协。这进而引出了莫莱蒂和瓦特的不同走向:莫莱蒂在精细加工、追求准确的布尔乔亚散文中看到的是一种“客观的‘非个人性’”,一种“去人化”的倾向。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自由间接引语的诠释:这种文体中的“第三者声音”并非对“主观视角”的保留,而是体现了相对客观化的、为社会所接受的声音,“它是一项社会化的技巧,而不是一项个人性的技巧”。它代表的是普通智识群体,传达资产阶级“共同意见”。这样一来,自由间接引语反而成了“说服个人”/“使个人妥协”的方式;这种技巧使得小说在摆脱了显性“说教”形式之后,反而成为更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毛尖:莫莱蒂对自由间接引语的阐释真是漂亮,他另一个做得特别漂亮的是,对鲁滨孙的解读。莫莱蒂发现,作为故事行动中心的鲁滨孙,每一次行动都延伸出下一个行动,“砍枝条”后发现可以“晾晒”它们,然后发现可以“编篮子”,再发现可以“编大篮筐”,可以“不用袋子装谷物”。每行两三个动词,被编得跟篮子一样,笛福的句子,没有跳过任何一个步骤,就像黑格尔所说的“散文的心智”(prosaic mind),它们通过“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这样的范畴来理解世界”。莫莱蒂认为,这就是工具理性的第一个化身,是投向布尔乔亚“心态”的第一束目光,本质上,鲁滨孙就是工作的第一代主人,他告别非理性的前现代状态,成为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始祖。

回头看莫莱蒂的写法,他对关键词的选取,也颇有鲁滨孙精神,从“有用的”,到“效率”,到“舒适”,就像笛福的叙事流,一个行为,在语法上完成,在叙事上开放,莫莱蒂的第一关键词,向第二关键词开放,如此生生不息,构成“连续性的韵律”。在对过去行为的不断更新中,布尔乔亚,或者说,莫莱蒂,获得以前进为导向的语法和精神,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加冕,持续不断地自我证成,并在“精神的生产性”面前,为自己开出分叉的两条道路。
朱康:的确如毛老师所说,莫莱蒂的写作,同笛福的写作一样,都颇有鲁滨孙精神,有着布尔乔亚式的“散文的心智”。莫莱蒂送给鲁滨孙的那个称号——a working master,也可以送给笛福,甚至送给他自己,他们都是“工作的主人”,或者说是工作的大师。写作,更具体地说,散文写作是一种工作。在莫莱蒂看来,“不对工作做直接的思考而去想象散文的媒介是不可能的”,这种“语言的工作”“体现了布尔乔亚活动的某些最为典型的特征”。也因此,作为《布尔乔亚》主人公的散文,又被莫莱蒂称为“布尔乔亚散文”,“辛劳的散文”(laborious prose)。
辛劳的散文,这样的命名体现了一种写作的伦理学,一种散文的文体学,同时也召唤着一种长篇小说(Novel)的文类学,虽然文类这一概念在《布尔乔亚》中并不是焦点。“连续性的韵律”,这是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论散文一节的标题。随后弗莱谈论了“特定的连续形式(散文体虚构作品)”,其中第一类形式就是长篇小说,其特点是以稳定的社会作为框架描写人物的性格,其人物都是带着社会面具的角色。莫莱蒂没有借用弗莱对于“特定的连续形式”的讨论,在弗莱对“连续性的韵律”的阐述之后,他接续的是卢卡奇《小说理论》里的判断:为了适应世界的异质性,长篇小说需要以严密的、无韵律的散文为媒介,来赋予异质性以形式。这就是“主观的再生产”,是“精神的生产性”。而正是在对世界的适应之中,世界的合理化的逻辑渗透在长篇小说的韵律之中,它要求长篇小说摆脱偏误与模糊,由此,长篇小说的写作,不能依赖天赋,而只能是训练的产物。莫莱蒂借用福楼拜对自己的《包法利夫人》的评价来概括整个十九世纪长篇小说的特征:耐心远胜过天分,工作多于才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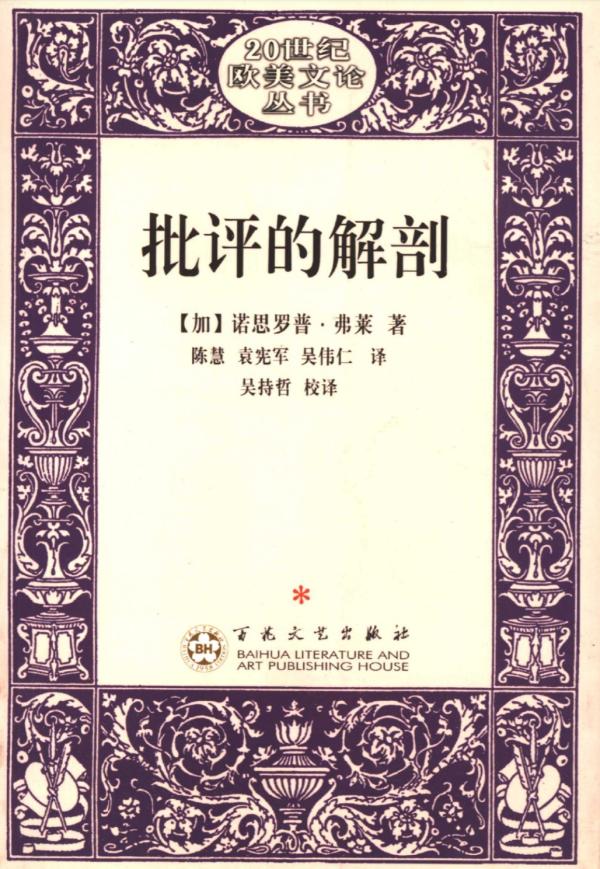

丁雄飞:如朱老师所说,散文是散文性的生活风格中散文,作为一种再现世界的方式,它可以是小说的文类,也可以是电影的类型。莫莱蒂最近比较了二战后的两大电影类型——西部电影和黑色电影。在他看来,西部片里杀伐明确,总是由对根本冲突的发现所致,而黑色电影里的谋杀,则是一系列基于片刻利益而不断变化的联盟中的一个环节。因此,黑色电影中,多种叙事力量在繁殖:这可以上溯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伟大的都市小说,甚者,上溯到黑格尔对于公民或市民社会的描述:市民社会里的个体总是把他人化约为实现自己特殊目的的手段。这便是所谓“世界的散文”(the prose of the world)。换言之,市民社会充满了中介(mediation),在这里,利用他人,是一个远胜于如西部片那样消灭他人的策略。于是,黑色电影的叙事结构可以不断膨胀,因为总能在情节“中间”加点什么。而这个有限的世界也不再制造英雄:西部片需要英雄来填补国家缺席产生的空白,但在黑色电影里,没有人担心社会制度不稳,一切越轨行为都是局部的。不但如此:不同于1930年代黑帮电影里的狂妄大盗,黑色电影里的散文性头脑更关心准确性和清晰度,行凶之前务必检查推演,确保万无一失。当然,鉴于市民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最安全的谋杀,便是出钱让一个陌生人去杀另一个陌生人。

布尔乔亚在中国
罗萌:研究界常说近代中国不存在较为稳定的布尔乔亚/市民阶级,但同时,在文化文学研究中,又不断征引(类)布尔乔亚概念。这方面可能和《布尔乔亚》一书形成某种有趣的对照:书的主线是,资产阶级首先掌握了经济权力,并创造出自己的美学,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化,反而日益丧失文化领导权。中国研究在借鉴一系列“布尔乔亚”术语的时候,反复强调经济意义上的布尔乔亚不存在,但针对文化问题的引用却是不间断且较为自信的。当然,并不是说,在欠缺经济布尔乔亚的前提下,讨论文化布尔乔亚是一种空中楼阁。而且,在近代中国的文学现象中,确实可以发现和《布尔乔亚》中描述的风格特征非常相似的东西,这里面的原因可以是多重的:比如以报刊为载体的大众阅读市场的形成,比如西方文学的引介和影响。陈平原提过中国传统小说重“布局”不重“描写”,最初译入外国文学时,也以译出“布局”为主。所以当时的很多译作,都更倾向于“译述”甚至“节译”。而准确的细节描写的大量生产,和对西方文学理解的深入是有关的。在中国近现代小说转型中,细节描写的加强是重要变化,曲折中和《布尔乔亚》里谈到的十八世纪欧洲小说的变化产生了对应关系。
《布尔乔亚》没有涉及对读者大众(尤其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的阅读大众)的讨论,如果加入的话,或许可以和作者关于布尔乔亚现实主义的“非个人性”的论断直接挂钩。而由“填充物”(filler)所引起的叙事减速本身也是清末民初小说转型的一大特点,看看《海上花列传》就知道了。《海上花列传》是第一部通过报刊连载的长篇小说,以往对小说中大量日常细节铺陈的解释,往往从适应连载形式的角度出发,如果结合莫莱蒂的一系列见解(比如“严肃”、人与物的关联、非个人性等),应该会有助于生成进一步的阐发。

黄锐杰:这种晚清的“布尔乔亚”“描写”到了“五四”时期进化为了一种理论上的自觉。像雄飞说的,“五四”之后,知识界开始以“资产阶级”对译“bourgeois”,凸显了布尔乔亚的经济涵义,但这一翻译恰恰是为了超越布尔乔亚的经济面向。以巴金为例,巴金1933年出版《家》的时候,后记中点明自己写的是“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的家庭”的历史,但书中的高家完全不像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还是一个传统的大家族。这与1933年这一后“五四”时代有关。这时大革命思潮兴起,阶级话语迅速流行。这时候使用“资产阶级”一词,许多时候已经偏离西方的原始语境。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用法,其着眼点并非当下的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新阐释和再创造。因此即使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巴金等还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一阐释模式。不过,这同时也是“大革命”失败的时代,巴金写《家》,是要由“大革命”的“政治”回到“五四”的“伦理”以重建信仰。在“五四”叙事中用“资产阶级的家庭”指称高家,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时代错位。然而,这一做法必然造成“政治”与“伦理”间的错位。因为到了1930年代,“政治”的问题已经不可能仅仅依靠“伦理”的方式得到解决,这是巴金等一批“五四”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面临的困境。

丁雄飞: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布尔乔亚。而在文学想象上,没有哪个当代中国作家能像王安忆那样,把如此巨量的精力投注在(上海)市民身上。从1993年的《“文革”轶事》到2018年《考工记》,王安忆反复书写着市民的“小世界”。《长恨歌》的最后一句话说,“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这便是王安忆在九十年代的乌托邦(或者说意识形态):呼唤出新一代市民阶级。在她彼时的作品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中间的理想——处在“奢侈”和“贫贱”之间的“富足”。体现这一理想的,首先是作为中间阶级、处于经济和“政治”的中流状态的市民阶级,其次是市民阶级身处其中的某种中间城市形态。如果说上海的消费空间是城市文明的极端形态,农村是前城市/文明的形态,对于王安忆,一个理想完满的城市便是在二者之间,它可以是小镇(《长恨歌》里的邬桥)、小城市(《长恨歌》里的苏州、《启蒙时代》里的宁波),也可以是上海的中间生活空间(《富萍》里的扬帮棚户区、《长恨歌》的平安里)——“富足”是其基本限定。然而类似于莫莱蒂在《布尔乔亚》最后指出的,十九世纪诚实的布尔乔亚终不敌二十世纪诡计多端的金融投机者,我们从王安忆晚近十年的小说里亦能读到:老上海市民在新上海人——金融阶级面前节节败退。


毛尖:《布尔乔亚》导论中说,布尔乔亚产生于某个“在中间”的地方,但中间性恰恰是布尔乔亚需要克服的东西。鲁滨孙出生在英格兰现代早期的“中间状态”里,但他拒绝接受父亲把这一状态理解为“世间最好状态”的观念,用一生来克服这种状态。今天,在“中产阶级”到处替换“布尔乔亚”的世界,虽然已经无法唤回布尔乔亚的往日精气神,但重提“中间性”的危害,却似乎有必要,包括小丁讲的,王安忆这十年的小说,从一个侧面说,也可算是给十九世纪样态的布尔乔亚唱的挽歌。而这些年,很多国产文艺也很愿意表现“小资情调”和“布尔乔亚”,但是,在对大小布尔乔亚进行形象、情感和伦理进行造型的时候,却完全没有历史脉络,有时金融资本家有时小业主,有时貌似文化的布尔乔亚有时江湖野狐禅,同时,在相关评论中,他们获得同一个名称,中产阶级。中间性对布尔乔亚的历史伤害已经有一百多年,但在今天是最令人绝望的,因为中间性已经成了布尔乔亚的墓志铭,所以,重新梳理布尔乔亚的脉络,也算是一次初心钩沉。
朱康:确如毛老师所说,重新梳理布尔乔亚的脉络,初心钩沉,目的并不在布尔乔亚自身,而在“已经无法唤回”的情况下去辨认它的“往日精气神”,即借助历史中的布尔乔亚,审视现实境况中的世界道路与世界道路的责任。在历史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布尔乔亚从克服中间状态的英雄姿态退回到披上“中产阶级外衣”,化用马克斯·韦伯那个著名的隐喻,命运注定了这外衣将变成一只铁笼——世界道路责任的铁笼。这不仅是中产阶级的中间性的危害问题,这是整个布尔乔亚的结构性的矛盾问题:资产与文化之间的失衡。正是在这里,在我们的座谈的结尾,可以并有必要重温《布尔乔亚》的结尾,在那里,莫莱蒂传达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留给今日世界的持久不衰的训谕”:“面对资本主义的自大,承认布尔乔亚现实主义的无能。”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