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之后,统治法国数百年的波旁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迎来的却是法国近现代最动荡不安的世纪。在君主制与共和制轮番登场之际,知识分子选择发声,在议院中成立党派,成为大臣甚至是政府首脑。正是他们对自由的坚持使19世纪末的法国成了欧洲最平等的社会。在法国大革命230周年之际,新经典·文汇出版社出版了法国著名史学家、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在这本书中,维诺克选取了活跃于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中著名的、非著名的一批作家、政论家、艺术家,透过他们的生活、情感、思想来呈现19世纪的自由史。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本书的译者之一、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吕一民,请他谈谈大革命前后这些为着“自由”奔走呼告的“知识分子”群体。

澎湃新闻:“知识分子”,“诞生”于19、20世纪之交,“终结”于20世纪晚期。想请您谈谈这个“诞生”与“终结”是如何发生的?
吕一民:这里的“诞生”是加双引号的,主要是指法文里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首次出现于19世纪行将结束时在法国爆发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今年恰逢巴黎和会召开与《凡尔赛和约》签订100周年,当年代表法国参会的那位个性极强,有点咄咄逼人的“老虎总理”克雷孟梭因而再次引起不少人的关注。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的是,正是这位克雷孟梭,曾在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1898年1月13日,是他在自己主编的《震旦报》上发表左拉就德雷福斯案件写给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时,给这封公开信加了个富有挑战性并被载入史册的通栏标题:“我控诉(J’accuse)!”;其次,在1月23日,在不少将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已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在一起,但“知识分子”一词却还没有问世时,也正是这位因以“我控诉!”的通栏标题发表左拉的公开信而使《震旦报》和他本人进一步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焦点的克雷孟梭,提笔写出“来自各个地方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看法而汇集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征兆吗?”这句话的时候,出人意料地把“intellectual”这一形容词作为名词来使用,并有斜体加以凸显。“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此后,这一词不断地被公众所接受,而且逐渐地流行了开来。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学者一般还认为,“知识分子”一词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法国社会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
至于所谓的“终结”,则与80年代初期法国知识界的两大巨星萨特、阿隆相继谢世后,法国知识分子在社会舞台上一度远不如20世纪早期和中期那样活跃,显得有点消沉,甚至过于“沉默”有关。这一现象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一时间,许多报刊在谈到知识分子时开始频频使用“危机”、“衰落”,甚至“终结”等词语来形容法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与此同时,法国知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对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角色定位与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例如,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其刚创办不久的《争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们究竟能干什么?》的文章。而曾对现代知识的转变和“后现代社会”有过深入研究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世界报》上发文参与相关论战时,竟然为自己的文章取了一个很吸引眼球的标题:《知识分子的坟墓》。上述现象,归根结底,实际上反映了曾在此前,尤其是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辉煌的30年”风光无限过后,法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或曰身份焦虑。
在此还需补充一点,不无吊诡的是,20世纪晚期起一度在法国史学当中成为“显学”的史学分支——知识分子史的勃兴,实际上也与这种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或曰身份焦虑密切相关。而在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勃兴过程中,推动最力,成果最多的当推本书作者米歇尔·维诺克,以及他在巴黎政治学院的同事,曾任法国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历史评论》主编的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澎湃新闻:您在序言中说《自由的声音》这本书是知识分子的“史前史”——所谓“史前”是基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出现而言的——我想请教您的是:在“史前”阶段活跃着的知识分子群体与进入历史叙述阶段、被定义后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异同吗?序言中说19世纪的知识分子与18、20世纪的有区别,那么这个“区别”是什么造成的?
吕一民:这个问题很大,三言两语还真说不清楚。长话短说,我想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是都属于既有公共关怀,同时亦乐于、勇于“介入”的知识人。对此,请允许我倒过来举例,先谈20世纪。
二战结束伊始,在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支持下,萨特就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创办了《现代》杂志。他在创刊号上不仅发表了《争取倾向性文学》一文,而且公开提出:文学必须具有倾向性,必须干预生活。应当说,他不仅是这样说,而且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因而他本人的名字后来也一直跟“介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在《自由的声音》一书中涉及的那个时段,即19世纪的那些法国文人学士们,在“介入”方面也同样可圈可点。事实上,《自由的声音》的副标题,如果要死抠法语字眼,或者用法语来说若要mot à mot地来翻译的话,该译为:19世纪的介入(型)作家。至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在“介入”方面的表现,我想我只需简单提一下伏尔泰在“卡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就颇能说明问题了。
至于这三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那就更复杂了。要用短短的几句话厘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在维诺克在《自由的声音》的导言里曾对此略有阐释,不妨一看。我个人以为,如果非要好好探究这一问题的话,还需要特别关注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其须面对的处境各异、分属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在各自时期首先面临的任务以及需要承担的角色问题。当然,这里也涉及到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究竟多大?能够凭借或利用的资本(这里首先是文化资本)、平台、媒介等等到底如何?
此外,我还觉得18世纪、19世纪、20世纪之类的划分过于宽泛,前两个世纪暂且不论,仅就20世纪而言,法国知识界在二战前后就大不一样;即便是战后时期,“辉煌的30年”期间和过后也大不一样。如果说萨特在创办《现代》杂志时其地位有如“教主”,那么,在诺拉等人创办《争鸣》杂志时,情况已大不相同。以至于80年代初期,诺拉在创刊不久的《争鸣》发表的《知识分子们究竟能干什么?》一文中宣称,权威人士型的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了。即便像福柯那样拥有极高声望的知识分子,其身上已不再具有神职人员般的光环。知识分子正在强力地被世俗化,其作为先知的特征已不复存在。有意思的是,诺拉在这里还特意提到了这一点,即“科学方面的投资已使他(指相关知识分子——编者)被淹没在一个巨大的由科研团体和科研经费等编织成的网络之中。”
毋庸置疑,由于种种变化的出现,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角色定位和“介入”方式势必也得随之调整。作为搞历史的人,我对一位法国同行,我在10多年前翻译的一本译著《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的作者皮埃尔·罗桑瓦龙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和表现特别欣赏。罗桑瓦龙是当今法国最著名的政治史专家。作为法兰西学院近现代政治史讲席教授的他,还是时下在法国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颇为引人瞩目的政治概念史的领军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罗桑瓦龙曾多次强调“政治概念史”也是一种“介入的”史学,而他目前的抱负,就是沿着基佐、基内和托克维尔等伟大历史学家的足迹,分析民主的探索与实验、冲突与争论,以促进人们对当代的理解。罗桑瓦龙表示,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研究和对当代最棘手最迫切的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让历史成为现时的“活动实验室”。他认为,只有借助于这种“过去和现在的不断对话”,人们才能认识创制社会的过程,才能全面地理解当代社会。为此,他还引用年鉴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经典话语——“对现时的不理解,必然肇始于对过去的无知。”——来鞭策自己。在罗桑瓦龙看来,政治概念史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同时创造“理解的工具和现实介入的手段”。在一次访谈中,罗桑瓦龙更是明确表达了成为一个“介入型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强烈的介入意识并没有让罗桑瓦龙丧失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求真品质。罗桑瓦龙表示,他反对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把个人的倾向与激情投射到历史研究上去。罗桑瓦龙认为,政治概念史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介入模式,从此以后,介入与否的标准不再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只取决于其学术研究的内容与性质。罗桑瓦龙指出,除了普通的政治斗争或矢志于捍卫某些价值与乌托邦外,通过清楚地阐明人们在当前面临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知识也能变成“一种行动模式”。所以,政治概念史的优点在于它能很好地兼顾公民的介入需要和历史学家的求真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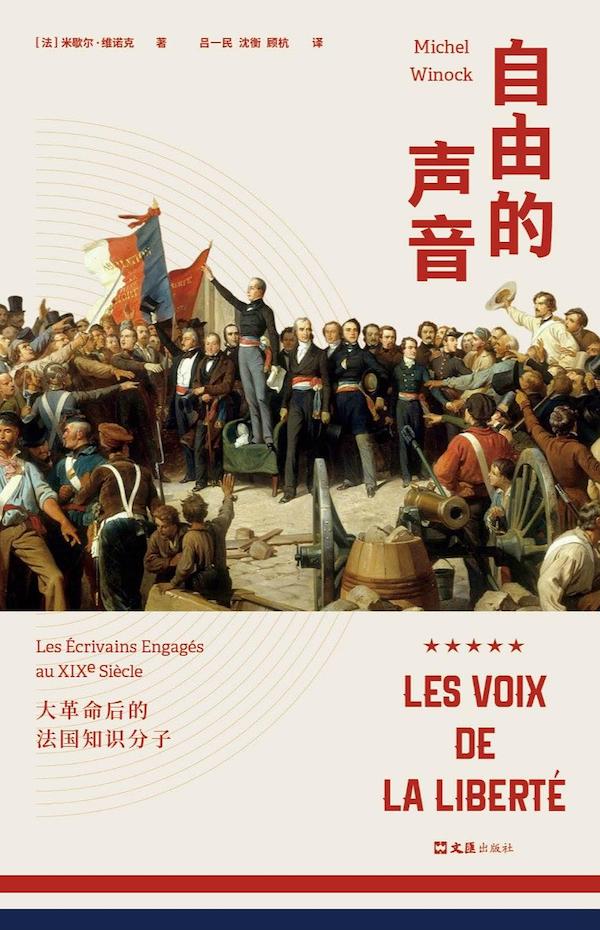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维诺克有一本书叫《美好年代》,我想到了伍迪·艾伦的一部电影——《午夜巴黎》,故事里男主角午夜时分不断地穿越到不同年代的巴黎,在那里见到了那个年代的名流,毕加索、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等,这些名流在派对中讨论他们认为的“黄金时代”——在当下那个时代的人眼中,黄金时代总不是时下的,总是过去的某个时段。我感兴趣的是,在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中,“知识分子”是一个群体概念,这个群体既有代际的差异,在同一代中也有各种差异——像这本书中谈到的人物很多是中国读者不熟悉的,您是不是能举例讲讲,不同个体的知识分子眼中的、所谓的“美好年代”(“黄金时代”),以及这个“美好时代”与其个人生命之间的关系?
吕一民: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事实上,我在浙大给本科生开题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通识核心课程时,也会在讲到“美好年代”这段历史时提及这部影片。看过这部片子的人都知道,它所玩的套路讲白了就是“穿越”,“穿越”,再“穿越”。生活在当下的男主人公,一位好莱坞的年轻编剧在从美国来到巴黎时,心心念念的是海明威等人所生活的20年代的巴黎,结果在午夜时分,鬼使神差地坐上一辆神奇的马车,相继“穿越”到20年代甚至更早的年代,由此和海明威等人也有过亲密接触,结果发现,那些知识名流们在派对中讨论他们认为的“黄金时代”时,总是将“黄金时代”定格于已经过去的某个时段。这种套路简单归简单,但应该说,也还是不乏令人深思的地方。
您在明确“知识分子”是一个群体概念的同时能意识到这个群体虽有代际的差异,在同一代中也有各种差异,这一点很好。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史研究中,从“代层”角度进行审视一直是至关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例如,西里奈利曾在1988年在其国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的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和巴黎高师的学员》。事实也确实如此,处于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例如,在两次大战之间成长的知识分子,和在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在1968年5月风暴发生时尚属热血青年的知识分子,肯定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诚如您所说的那样,同一代知识分子也绝非铁板一块,由于家庭出身、求学经历、社交网络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肯定也有很多不同。为此,我们得尽量同时注意到其共性和特性。就此而言,西里奈利聚焦于同为巴黎高师毕业生,且有同窗之谊的萨特与阿隆的名著《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值得一看。
至于不同个体的知识分子眼中的所谓的“黄金时代”,也确实只能因人而异。例如,对于萨特来说,他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现代》杂志之初肯定是能让其觉得颇好的时期,以至于他在创刊号的导言中这样写道:“过去也许有过更好的时代,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是属于我们的。”毋庸讳言,他这样写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和底气的:最初出版时乏人问津的《存在与虚无》突然成了畅销书,一版再版;为了能与他这位新的大师握上一次手或谈上几句话,他的仰慕者们自愿在《现代》编辑部门口排起了长队;就连他和波伏娃经常去的花神咖啡馆亦成了其追捧者们喜欢光顾之地。一言以蔽之,萨特当时在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完全就像是一个“教主”。不无象征意义的是,有人将紧邻“花神”、“双偶”等令人心向往之的咖啡馆的地标性建筑——著名的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称为“萨特大教堂”。
顺便补充一点,正如西里奈利教授等法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创办《现代》对萨特扩大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说,在当时,创办杂志是意欲占据知识界霸主地位的知识分子非做不可的一件事情,因为杂志能使他成为一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能帮助他向别人灌输自己的思想。不过,我还想在此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对于《自由的声音》第4章提及的贝朗瑞来说,他所处的复辟王朝时期似乎要更好,因为那时新闻自由在法国仍还有待争取,报纸也还是寻常人家亦不是太容易拥有的“奢侈品”,更由于大多数人尚不能识文断字,遂使得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政治歌曲(谣)得以更受欢迎,并因此而获得了“法兰西精神的代言人”之类的诸多美誉。而对于不仅口才好,风度佳,而且还颜值高的贝尔纳-亨利·列维,亦即经常在媒体中仅用BHL来指称的这位当今法国媒体知识分子“第一人”来说,能让自己有机会经常在荧屏中抛头露面的电视时代,显然才是他所期待的时代。
澎湃新闻:今年是法国大革命230年,提到这个历史事件,其中的关键词就是启蒙、自由、人权……这本书讨论的是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主标题也是“自由的声音”。维诺克在“导言”一篇的结尾说:“我们将穿越到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是绝望的世纪,但这一世纪的思想成果依然是我们不可剥夺的遗产。”那么,回望历史,我们怎么看待作为历史遗产的自由原则?
吕一民:法国大革命当然是值得肯定和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法国大革命史早就是国内外史学界的“显学”之一,研究者颇多,论著汗牛充栋,关于其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我就不多说了。我在此只想提及的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确立的目标很高,步子又迈得过大,因而在革命风暴过后的法国,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有待重建、修复或“补课”的地方很多。细心的读者会不难发现,维诺克在这本书中曾如是写道:“自从路易十六人头落地之后,法国在8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9次政权更替,这些疯狂的更替最终以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终”。而在这一不乏腥风血雨的过程中,《自由的声音》中涉及的不少人,包括在去世时得以享有“至高荣誉”的雨果等的表现不仅值得肯定,而且令人敬重。
不过,我觉得此书实际上还需要再补写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早年曾是著名政治记者和历史学家的梯也尔。此人在复辟王朝时期,特别是1830年7月革命爆发时的表现不仅可圈可点,更是勇气可嘉。例如,当执迷不悟的波旁复辟王朝当局悍然颁布《七月敕令》时,时为《国民报》创办者的梯也尔不仅以编辑部的名义草拟了书面抗议,还对在场者慷慨陈词道:“你们知道,抗议书下会摆着颗颗人头。好,交出我的”,并第一个在抗议书上签名。说到这里,我会不由得想到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毋庸置疑,在我们现在通常作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开端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写下“我控诉!”的左拉充满浩然正气,值得我们为他的勇气拍手叫好。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时,此时的左拉实际上心里也很清楚,即便根据相关法律,自己大不了就坐几天牢,被罚点款,绝对不用担心会掉脑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法国,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中,在自由、民主方面走在最前列,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而这一切的取得,与《自由的声音》里的男女主人公们显示出来的才识、情怀,乃至勇气何尝没有关系呢?
关于自由,我们都知道那句很有名的话,Freedom is not free.但我们实际上也应该知道,人们现在已经在享有的一些自由和民主权利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值得敬重的前人们努力争取、不懈奋斗的结果。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代法国一位集政治家和女权主义斗士于一身,以非凡人格力量深受国人爱戴的杰出女性西蒙娜·薇依。出生于犹太人家庭的薇依,早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二战后投身政坛,曾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在这一过程中,她始终致力于“为最弱势群体争取权益而进行正义而必要的斗争”。其中包括她在1974年顶住保守派压力推动立法,促成女性堕胎合法化。2017年7月1日,薇依在去世一年后正式入葬先贤祠。法国政府在先贤祠广场举行了仪式,马克龙亲自发表讲话,向这位杰出女性表示敬意。当时,我因为就住在附近,所以特意走过去观看这一场景,印象很深,而且已经很感动。晚上看电视时,我又发现,有不少如今已年纪一把,但当年也年轻过的女性,在接受采访时极动感情,一再表示对薇依心存感激。说实话,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时,触动很大,不由得想到,人们当今在理所当然地享有的许多权利,实际上都是与一些人在过去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法国如此,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上面的这一小插曲让我更加觉得,我们得铭记包括这本书中写到的一些人在内的中外先贤、先烈们的功绩,常怀感恩之心。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自由的声音》译者序的末尾特意引了维诺克写的一段话,并指出“毋庸讳言,这一提醒绝非仅仅对法国读者具有必要性,对中国读者亦同样有用”。
澎湃新闻:《自由的声音》在法国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历史著作,维诺克在作为学者之前,也从事过记者、编辑的工作。我想他本身就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接棒者。想请您谈谈,这个传统在法国社会的影响。
吕一民:《自由的声音》不仅在法国叫好又叫座,令我不无欣慰的是,中文版也跟着沾光,问世后表现不俗,5月初问世后,不仅在6月份就迎来第三次印刷。在豆瓣上的评分也长期高于9分。维诺克在当今法国堪称是名列前茅的既高产又高质的历史学家,他关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那本名著《知识分子的世纪》,影响力也不在《自由的声音》之下。可以说,他的很多书在得到学界好评的同时在图书市场上的表现也都相当好。因而,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出过袖珍本,或者说口袋本。这一切,不仅和他在巴黎政治学院任教前做过记者、编辑工作大有关系,也和他在任教之余,始终和出版界、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多有关系。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与他具有公共关怀,并希望借助相关平台或媒介实现自己抱负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认同您刚才的提法,说他本身就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接棒者。
至于这个传统在法国社会的影响,那可以说的就实在是太多了。例如,维诺克在先后对20世纪、19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进行总体研究前,曾对至今仍在法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刊物《精神》杂志做过出色的个案研究。巧的是,我在10多年前比较熟悉的一位法国的“中国通”,曾任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科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的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杜明(Jean-Luc Domenach),他的父亲让-玛丽·多梅纳克曾负责过《精神》杂志的编辑工作。杜明先生告诉我,当年他们家经常有知识界名流光顾。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父亲曾和米歇尔·福柯,以及因首先谴责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而名噪一时的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盖一起,联手创办了致力于在法国开展监狱改革运动的组织——“监狱情况报道小组”。
在这一点,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表现也很突出。以其独特而深刻的研究蜚声学界的他后来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一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在1995年法国发生规模空前的大罢工时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且还在此前几年就致力于对社会疾苦的调查研究,主编出版了《世界的苦难》一书。这部厚达千页的著作问世后,立刻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并在当时的法国激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公众对于不平等、种族歧视、社会凝聚力等问题的大讨论。毫不夸张地说,此书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一次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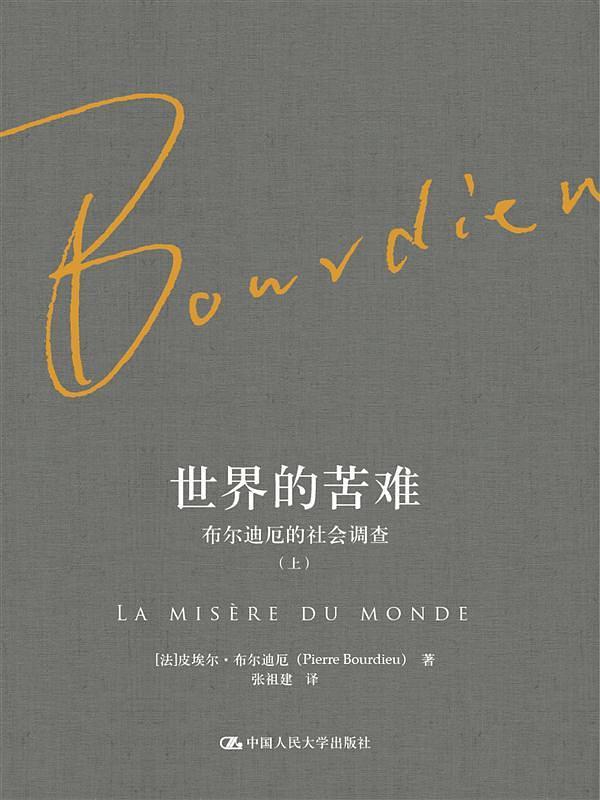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