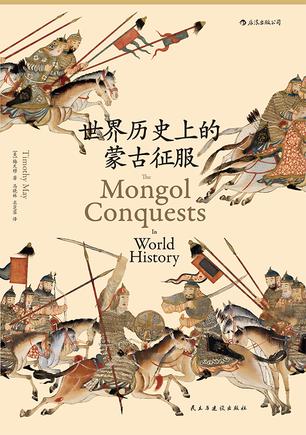梅天穆(Timothy May),美国北乔治亚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蒙古帝国史及军事史的世界级权威学者,除了《蒙古战争艺术》《蒙古的文化与习俗》等专著外,《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是近年来蒙古帝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新作。
作者在世界史与全球史的视野下,重点描绘了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以及蒙古各汗国陆续崩解后,一个新的欧亚世界的产生过程。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动下,东西方之间开始了互相交流的过程,在“蒙古治世”之下孕育出了崭新的欧亚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过去被视为毁灭文明世界的蛮族形象得到了修正。
在《世界历史的蒙古征服》中,梅天穆用详实的资料与晓畅的叙述告诉读者,游牧民族军事上独特性到底在哪里、火器到底能不能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以及游牧民族的军事战略在何等意义上影响了以后、乃至坦克时代的现代战争。这些洞见与一般读者的常识大相径庭。以下选摘内容由澎湃新闻经后浪出版公司授权发布。
蒙古弓骑兵是怎么在攻城战中变得无坚不摧的?
成吉思汗的崛起为草原军事带来了一场革命,他引入了严格的训练和新式的战术,创建了怯薛军校制度,并采用十进制的组织形式。他改善了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草原战略,使蒙古人在范围极广的战线上都能在战术、战略及行动等各个层面上保持常胜不败。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军事革命影响了其后几个世纪的军事发展。
蒙古的战争艺术基于一个简单的要素——弓骑兵。弓骑兵的基本装备是双曲复合弓,拥有惊人的穿透力和射程。它的射程超过300米,不过通常用于较短距离的战斗,一般是150米以内。这种弓射出的箭大概可以轻松射穿锁子甲以及其他护甲。受过良好训练的蒙古战士以 3 ~ 5 匹马相配合,可以轻松地发动一场战胜敌人的死亡之战。蒙古战士大多装备轻型护甲,但他们的护甲是以皮革或金属制成的薄甲,较锁子甲更善于防箭。尽管骑兵是自古就有的,但在将马的机动性与弓箭的火力相结合这一方面,蒙古人是最为精熟的。
蒙古战士主要是轻装弓骑兵,并将草原上的战术推向极致,例如包围战术和佯退战术。这些战术将他们的弓箭技巧和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使他们能够保持在敌人武器射程之外。像其他的草原军队一样,蒙古人逐渐接近敌人,在弓箭射程内发动进攻,通常只有在敌人阵型散乱或变弱的决定性时刻,才直接与敌人近距离交锋。通过这些战术,他们不需要依靠人数优势,而是凭借机动性、火力和计策赢得胜利。
蒙古人也将箭雨与游击战术相结合。蒙古人称游击战术为“失兀赤”(shi’uchi),与欧洲15至16世纪战争中的半回转战术(caracole)类似。蒙古军队向敌阵派出多波战士,每一波都在冲锋的同时射箭,并在与敌军接触之前退却,回转至己方阵线。他们射出最后的箭矢并退却时,距离敌军约40~50米。这段距离足够他们的箭矢穿透敌人的护甲,同时也足以使他们避开敌人的反冲锋。他们更换马匹,保证坐骑精神饱满。该战术常常与其他作战行动配合使用。
两面包抄是草原上的一种传统战术,这种战术来源于蒙古的“捏儿格”(nerge),意思是“围猎”。战士们排成环形,包围猎物,逐渐向中心收缩,密集聚拢,使敌人插翅难逃。蒙古人并不总是需要大量部队来完成这种战术。他们的弓箭技巧与机动性,使其即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也仍然能包围敌人。但凡一有时机,蒙古人就会施展捏儿格来包围敌人。一旦蒙古侦查兵与敌人接触,主力部队就会尽其所能地延展阵线,以与敌军侧翼交叠。有时阵线延展数里,才将敌军包围。包围圈逐渐收紧,向中心聚拢。随着小规模冲突的出现,侦察兵便不间断地向蒙古指挥官们传递情报。
他们也将捏儿格用作侵略战的一部分,见于蒙古与罗斯诸公国的战争中。1237年蒙古人攻陷弗拉基米尔城之后,派出诸万户以捏儿格的形式攻略各个城镇与要塞,包围圈长达数百英里,并逐渐收紧。有时他们会故意在捏儿格中留出空隙,明显是让敌人由此逃走,但这实际上是陷阱。敌人在仓皇逃走的过程中难以维持纪律,经常抛弃武器以便逃得更快。蒙古人正是用这种战术,在1241年的穆希之战中击败了匈牙利人。
攻城战原本是蒙古人的弱项,但他们学得很快,随着他们将技师编入军队,攻城战很快便成了他们的强项。这些技师有的是征召而来的,有的则是自愿的。尽管蒙古人中便有技师,但是从整个蒙古帝国的范围而言,蒙古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穆斯林和汉人技师,他们能够掌握和制造大炮以及其他攻城器械。抛石机不仅用于攻城战,偶尔也出现在阵地战中,例如在俄罗斯和欧洲的战役。
心理战向来是蒙古人的强项,使用颇为频繁。蒙古人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比攻城更加有效,如果遇到抵抗便会屠城。屠城并不是肆虐嗜血,而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战术,能达到多个目的,既可以防止蒙古战线后方的叛乱,也有助于扩大宣传,并在军队的规模上造成误导。他们利用间谍和幸存者传播谣言,将他们的残暴宣扬到极致,使其他地方的民众产生恐惧从而主动投降,而不是负隅顽抗。
这些战术使他们成了一支高效而致命的军队,在战略和行动的层面上,他们成为现代社会到来之前的无敌军旅。他们使用高度机动性的战略。蒙古马的力量和速度都不如其他军队,但它们的耐久力是无可匹敌的。而且,蒙古人能够获得无穷无尽的马匹。蒙古战士平均每人拥有 3 ~ 5 匹马,即使其中一匹坐骑疲乏或死亡,也仍能保持机动性。机动性使蒙古人造就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战争风格,直到20世纪机动车辆应用于军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对许多人而言,蒙古人不是一种军队,而是大自然的力量、上帝的惩罚与《启示录》中的末日之兆。蒙古人的敌人们面对着无法抵抗的死亡与毁灭,拼命寻找抵挡蒙古人的办法。有些人成功了,但大多数人都失败了。蒙古人改变和影响了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战争方式。
火器能够战胜蒙古铁骑吗?
蒙古侵袭日本,导致日本武士参加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本质改变。在蒙古袭来之前,日本武士主要是与单个敌人近身交战,考验个人的武艺。而蒙古人是不打近身战的,而是使用大规模部队,集中火力消灭敌人的兵团。一名武士面对的不是单个敌人,而是一支部队。即使是最好的剑士,也绝对无法以寡敌众。直到武士转而采用部队战术之后,他们才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最显著的变化还是火药武器的出现。学术界已经确证,火药是在中国发明的,蒙古人首次接触火药是在攻打金朝时。在《武经总要》于1044年成书时,火药武器已经投入使用了。早在10世纪时,火药武器(炸弹的一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投入使用了,因为火药本身发明于 9 世纪。在宋代,火药的制造方法一直是一个严防死守的秘密,但到12世纪,像火枪(最初是一根发射火焰的竹筒,后来被绑在长矛上)这样的火药武器在宋朝的武器库中便已十分常见了。12世纪时出现了火箭,但是由于准确度很差而效果有限。不论是燃烧型还是爆炸型的火药,都是威慑性的武器,而蒙古人找到了发挥火药优势的方法。
尽管火药的传播与蒙古的崛起和蒙古治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我们并不清楚蒙古人自身是否对传播火药做出了贡献。有些历史学家宣称蒙古人使用了火药武器,即抛石机所抛掷的炸弹,用于中东战场(可能也用于东欧战场)。不幸的是,没有确切的文献或考古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鉴于蒙古人几乎没有遇到过他们不喜欢的武器,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们找到了安全运输火药的方法,便会将火药带到他们在中国以外的武器库中。
不过这仍然只是推测。杰克威泽弗德提到了蒙古人使用火药,认为火药的使用十分普遍,但他没有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依克提达尔罕(Iqtidar Khan)深信蒙古人在西征时使用过火药武器,并引用了波斯文史料中的数条记载。但他也承认,这些记载中的武器既可以翻译为火药武器,也可以翻译为一种更为传统的武器,比如燃油。依克提达尔罕还指出,火药传入印度是蒙古人的功劳,因为德里苏丹国在1290年已经使用火药了。这个观点似是而非,因为有证据表明,中亚在13世纪下半叶已经使用火药了,至少是用作烟花。
许多推测都来自这一事实,即13世纪50年代旭烈兀征伐中东时有1,000名中国技师随军。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蒙古人在攻打阿剌木忒或者巴格达时使用了火药弹。
在中国以外(甚至在中国)需要火药武器吗?在中国,火药武器是现成的。但它们有效吗?也许吧。不过,它们并没能阻挡蒙古人征服汉地的脚步。在对付土筑堡垒方面,霹雳弹当然比牵引式抛石机发射的石头更有效。正如前文所述,配重式抛石机在中国出现以后,此前坚不可摧的城市都陷落了—而这种情况在拥有火药武器的条件下也没有发生。在中国以外,配重式抛石机取代了牵引式抛石机,可以发射更重的炮弹,更为迅速地摧毁城墙。合列卜的防御工事在抛石机集中投弹 5 天后便被破坏了。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蒙古征服东亚的战争中,可燃性火器也发挥了作用。而蒙古人一到中东就获得了燃油。他们控制了木干平原,距离油田很近,那里自古代以来便有石油涌出地面。当然,可燃性火器是易于制造的,但燃油是除“希腊火”之外最有效的武器,而后者的制法在几个世纪前便已失传。综上所述,蒙古人未必需要火药武器来攻打防御工事。他们就地取材,制造炮弹和攻城器械,即使将邻近地区的石头全部移走,也并未导致他们无材可用。
众所周知,蒙古帝国是火药知识的首要传播者,或者是通过在战争中使用而直接传播,或者只是因为大多数重要贸易路线都从帝国疆域中穿过。欧洲不太可能直接从蒙古人那里获得关于火药的知识,但我们知道,欧洲直到蒙古入侵之后才出现火药。很可能是穿行蒙古帝国的商人们,也许甚至就是马可波罗一家,将火药的制法带回了欧洲。当然,这最终让欧洲在1500年以后成为世界的主宰。1266年,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20—1292)在《大著作》一书中记载了一种火药的制法。众所周知,培根与曾到蒙古旅行的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相识。尽管《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并未提及火药,但他是否有可能发现了这一“秘密”,或者他的同伴中有人将火药带回了欧洲呢?我们不禁推测,柏朗嘉宾是一名间谍,因为他的使命中含有间谍成分。他应该被解雇,因为他没有将火药写进报告中,而他的工作包括提出如何与蒙古人作战的建议,他显然愿意做任何事来遏止蒙古的威胁。只要他有火药的制法,他一定会毫不犹疑地交给某个能用到它的人,而这个人不太可能是方济各会士培根。另一方面,鲁布鲁克去蒙古主要是为了传教。也许他在一个领域失败了,而在另一个领域却成功了。
无论如何,火药武器在一些地区逐渐普及,但是与草原地带接壤的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在与草原游牧民族接壤的国家,火药武器的发展较为落后。直到它们的首要军事目标转向定居国家以后,火器技术才有了进步。到17世纪末,野战炮兵军团的机动性变得更强,因而可以为装备火绳枪的步兵提供支持。加农炮可以轻易地打乱草原骑兵的阵型,射程也比复合弓更远。直到这时,草原战争作为战争的主宰形式才衰落了,但这并不是说,游牧民族没有尝试建立他们自己的野战炮兵。在清朝的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与卫拉特的噶尔丹汗(1678—1697年在位)交战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清朝使用耶稣会士制造的加农炮,卫拉特则使用瑞典路德会士制造的加农炮,发生于1696年的这场战役将会决定谁是最强有力的佛教统治者。此外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加农炮不是用马车运载的(因为在穿过草原时会损坏),而是由骆驼驮运的,骆驼身上披着皮甲以防御箭矢和小型火器。最终,拥有更完善后勤补给的清朝获得了胜利。
“坦克:现代的蒙古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战场的堑壕战导致尸横遍野,机械化战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蒙古式战争得到了重估。随着坦克和飞机的发明,其机动性可以使蒙古式的快速移动与深入突击的战术复活。英国军官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提出了坦克与机械化步兵组合的概念,这一组合可以独立行动,作为大部队的前锋。这一机动性突击部队能够切断敌人的通讯与补给线,使敌军陷入瘫痪。就像蒙古人所做的那样,使敌军只有反应的能力,而无进攻的可能。李德哈特正确地解释了蒙古的战术,却忽视了蒙古战略中的一个核心目的是消灭战场上的敌人。不过,李德哈特可能目睹过“一战”时期堑壕战中的死伤枕藉,想要避免战争中的大量伤亡。
李德哈特借鉴了蒙古式战争风格,强调机动性与火力,最终实现为英国第一个实验性的坦克旅。这支部队在实际战斗中的成功,以及李德哈特在其《揭秘伟大的指挥官们》一书中关于成吉思汗和速不台的章节,影响了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他在1935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美军中进行相似的开发。麦克阿瑟建议研究蒙古战争以备日后借鉴,但是他的建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受到重视。他的继任者十分保守,既没有他的眼界,也没有办法在当时的美军中贯彻这一计划。“二战”结束后,李德哈特继续鼓吹发展坦克,并借鉴蒙古式战略,呼吁以轻型坦克的快捷与重型坦克的火力相配合,以获得进攻的速度与机动性。
另一位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J. F. C. Fuller)也将坦克视为现代的“蒙古人”,并且提倡使用自行火炮。与李德哈特不同的是,他还强调空对地打击。尽管蒙古式战术得到了推广,不过李德哈特和富勒的想法起初在西方军队中并没有实现。然而在遥远的东方,有人在英国人之前就将相似但又明显不同的想法付诸实践,法国和美国军队在发展了一些实验性部队之后开始实现这些想法。
“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的“闪电战”策略与蒙古式的战争艺术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并非出于偶然。闪电战的发明部分源于1923年的《拉巴洛条约》之后德国从苏联获取的情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Nikolayevich Tukhachevsky,1893—1937)的行动信条是强调“使用飞机推进,以快速移动的坦克纵队相配合”。在这一观点之下,苏联认为战争是“长时间占领并保持进攻”,这也被称为“纵深作战”。这一观点植根于草原战争在俄国和苏联的学院中长久的军事影响。在西方,李德哈特和富勒对战争概念的重整没有成功,而图哈切夫斯基则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体系。无论如何,他们的策略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源于蒙古体系。
苏联的纵深作战理论与蒙古人的目标相同,都是牵制敌人使其无法集中兵力,迫使敌人反应但无法发动进攻。因此,在图哈切夫斯基和伏龙芝(Mikhail Vasilyevich Frunze,1885—1925)两位元帅发展出的纵深作战理论的基础上,到1937年,苏联拥有了一支理论和战术意义上的蒙古军。斯大林保卫苏联每一寸领土的策略,与当年花剌子模帝国的统治者摩诃末很相似,而德国国防军则扮演了蒙古人的角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德军透支了自身实力,而朱可夫(Georgii K. Zhukov)元帅接手了红军的指挥权,他曾在1939年的哈拉哈河(位于今蒙古国)战役中成功地使用纵深战术以及其他蒙古式战术大败日军。
直到那时,德国国防军的闪电战一直主宰着欧洲战场。受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新理论的影响,德国也出现了独立的进攻部队。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两位将军在为闪电战设计军队方面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塞克特组建了防卫军,即在“一战”之后和国防军建立之前的德军。他认识到这支军队的规模较小,便重点发展其灵活性。为此,他训练次级军官,使之能够迅速承担指挥任务,以防其长官死亡或指挥不力。因此,如果将军死了,一名少校应该能够有效地指挥其属下部队。后来,这种做法扩展到了未经正式任命的军官,他们也能承担起自己部队中的指挥重任。尽管这种观念有可能是基于拿破仑的做法,即每个士兵都带着将军的权杖,意味着军队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升到最高等级,然而其前身则是蒙古人的领导方法。
蒙古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在塞克特的战略中更加明显。在《拉巴洛条约》签订之前,他于1921年写道:“在未来战争中,重要的是使用相对小型但高度精良的机动部队,并与飞机相互配合。”塞克特是在经历了“一战”并听取了防卫军中下属的意见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战”后德国的裁军,与波兰的敌对,以及苏联红军渐渐显露出的威胁,也让他相信如果德国遭到入侵,一支静态的、只有防守意识的军队是会失败的。像其他军事理论家一样,他渴望避免“一战”时期的静态战争,并且与苏联一样注重机动性,以此震慑敌军,迫使其做出反应。而且,进攻的目的是在敌人反击之前将其消灭。这对于德国东部边境尤其适用。从本质上说,他必须以机动性替代数量,因为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处于裁军状态。有趣的是,塞克特也将传统的骑兵(尽管装备了机枪和卡宾枪)编入了他的军队,用于游击战和其他战略。
古德里安是塞克特的下属,他研究了富勒、李德哈特以及吉法德马特尔(Giffard LeQuesne Martel)等人的著作,他们都强调以坦克作为进攻武器,以其他部队(炮兵、步兵或者空中火力)为掩护,而非相反。古德里安像他们所有人一样重视坦克的发展,相信它们会将机动性带回战场。如前文所论,富勒和李德哈特都深受蒙古的影响,因而古德里安至少是间接地受了蒙古的影响。他将这些观点放进了德国的“闪电战”中,不过,塞克特所奠定的基础以及与苏联之间的交流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