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沈洋:《三十而已》里的育儿烦恼真实吗?
在最近的热播剧《三十而已》中,女主角顾佳忍气吞声,只为了给儿子申请一个私立幼儿园名额的情节,让观众得以窥见国内一线城市中产阶层育儿焦虑的一角。
剧中申请幼儿园时,父母要参与英文面试以及拿到校董推荐信的桥段可能超出了不少人的日常经验,不过,这些电视剧里的情节有现实基础吗?为什么大家如此重视孩子的教育?我们找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副教授沈洋,她最近刚刚为14个月的女儿报上了“亲子班”,对申请私立幼儿园的过程颇有些心得。
沈洋曾经对育儿焦虑的大环境持较强的批判态度,她也表示自己的女儿“健康快乐”就好。但现在,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也开始“阶段性焦虑”了。
作为学者,沈洋“以自己为方法”, 一边深度参与女儿的教育和照料,一边把研究目光转向了上海职场妈妈这个高学历的中产女性群体。她的研究发现,可能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上海二胎妈妈的工作率非常高,超过了80%。并且,在二胎妈妈的高工作率背后,她们依然是家务和育儿劳动的主力军。

沈洋
「对话」
育儿焦虑链
澎湃新闻:在你的研究中被访者应该都是中产阶层吧?关于“中产”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
沈洋:主要还是根据收入跟教育程度,他们的家庭年收入是税后20万到170万。我的26个受访人中只有1个在上海没房,其他都是有房的。当然,这也跟她们自我认知有关,她们也觉得自己是中产。
澎湃新闻:关于《三十而已》中的顾佳,她算中产阶层吗?
沈洋:我觉得顾佳是新贵阶层了。不过,她给儿子找幼儿园的情景确实反映了育儿焦虑的大环境,尤其是择校焦虑的问题。

在幼儿园的面试中,顾佳向老师阐述自己家的育儿心得。
澎湃新闻:《三十而已》里,顾佳对孩子的规划有代表性吗?
沈洋:如果顾佳真实地生活在上海,她的孩子以后很有可能走非高考路线。她给孩子设计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先进嘉宝亲子班,再读嘉宝幼儿园,毕业之后进包校,然后初中或高中去美国或者英国读私校,最后成功申请到美国常春藤或英国G5。
到底走高考路线还是非高考?去公立还是私立学校?目前,国内一线大城市中产的选择太多了,有的家庭觉得从亲子班到高中要环环相扣,错过一环就很难接上另外一环,那么家长就很焦虑。
澎湃新闻:公共政策方面,有没有针对这种焦虑做一些事情?
沈洋:比如上海从2018年开始“公民同招”,从2020年开始民办学校又需要摇号,国家扶持公立的信号很明显。我是比较支持国家这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它的目标是减少家长和学生的学业压力。
澎湃新闻:为什么现在国内一线城市的这些家长这么热衷于孩子的教育?是因为教育回报率很高吗?
沈洋: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回报率都很高(教育资源差异也大)。之所以这样“鸡娃”其实还是因为能看到回报。比如有一些投行,他们只招清北复交的学生。另外,选择什么样的教育轨迹也是强化自己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
二胎妈妈,为什么要工作?
澎湃新闻:我们谈到了孩子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参与到竞争中去了,并且亲子班也是工作日入读,那么,双职工家庭很难有时间带孩子去参加?这个工作最后由谁来承担呢?
沈洋:据我了解的,几家口碑最好的亲子班,都需要在工作日入读,一周两到三次。
这种制度设计对双职工家庭不友好。我们面试的时候,园方也表示最好还是父母陪伴(而不要靠老人和保姆)。因此,只有工作灵活的家长或者有一方全职在家的家庭才有可能去读这种亲子班,而这通常是妈妈陪伴。根据陈蓉老师(上海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的调研,15%左右的母亲工作时间灵活,或者工作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掌握的,还有11.5%的是全职妈妈,加起来就百分之二十几,可能就是这样一部分的工作时间可以自己掌握的妈妈才能带孩子去读亲子班。
澎湃新闻:上海在职的二胎妈妈是很大的一个群体?
沈洋:让我惊讶的一点研究发现是,上海二胎妈妈的工作率还是很高的:有超过80%的二胎妈妈从事有偿工作。陈蓉和周海旺老师(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都做过二胎生育行为的研究,陈老师发现,只有11.5%的二胎妈妈没有收入,大多数其实都在工作,尽管有些女性的工作是灵活的。这是基于上海两三千份问卷的定量的数据,在全世界来说,上海妈妈的工作率都是在前列的。
澎湃新闻:是不是因为上海的生活成本比较高,养育孩子的成本也非常高,父亲的收入不能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才需要母亲外出工作?
沈洋:我的大多数被访家庭,其实父亲一个人的收入也是可以支撑的。我们也都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老公的收入可以支撑全家开销,你们会不会成为全职妈妈?她们都说不会。
因为她们觉得女性要独立自主,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有的女性生完孩子之后辞职了,休息了半年到一年,但后来还是继续工作了,她们有危机感,一个是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离开她们,而且很多高学历女性想要自我实现,他们也追求社会身份。
澎湃新闻:你论文中提到了两个术语,“母职惩罚”与“父职红利”,为什么成为母亲会被“惩罚”,成为父亲却得到“红利”?
沈洋:学术界对“母职惩罚”的定义是:由于生育导致职业中断或者工作时间减少,降低母亲的收入。即使她们继续全职工作,雇主也可能会认为母亲能力更弱,投入工作的精力更少,使得女性的晋升机会相对更少。
而相对的“父职红利”,指的是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通常会更努力地投入工作,获取更多人力资本与收入,减少家务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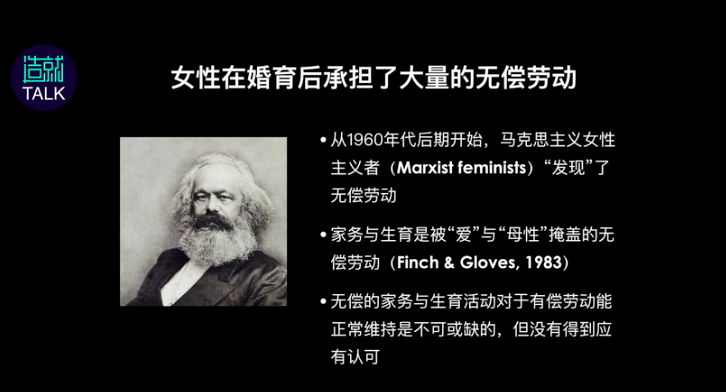

沈洋在“造就talk”的演讲PPT截屏图
澎湃新闻:既然女性工作率这么高,为什么你在造就talk的演讲,呼吁男性更多参与育儿还会引起巨大争议?
沈洋:有的人带着成见;有的人没看演讲,看了标题就直接留言说,丈夫要外出工作。留言者可能没意识到,我们的被访者也都是工作着的高学历女性啊,但是她们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务与育儿劳动。
我的论文里,26个家庭中,父亲能平分育儿的只有3个,大多数都是做的从零到三分之一不等。这还是女性自己的评判。
不少被访者说,虽然她们的丈夫只承担了三分之一的育儿劳动,但是她们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这是因为社会对男性的期待值太低了,整体上,社会与家庭对父亲并没有育儿上的期待。
另外,具体的育儿分工也是性别化的,比如说丈夫大都是那种陪孩子玩的享受型的工作,而妈妈承担了大部分“屎尿屁”的工作。
澎湃新闻:在你的小家庭中,是怎样协调工作、家务与育儿劳动的?
沈洋:我和我丈夫都是大学老师,大家的工作时间也比较灵活,育儿与家务劳动都是基本上平分的。这种平分不仅包括传统的分工,还包括“认知劳动”等隐形劳动。男性在家庭中是可以做很多的,比如我们家每天买菜都是我先生买。其实“买菜”就是一种“认知劳动”,需要很操心地考虑每天要买什么。但是在孩子的东西上面我操心比较多,比如,我会花很长时间考虑奶粉的牌子等,做很多功课,然后让老公及时补货。
谈到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在挑婴儿车问题上,我可能看了有半年,这可能是中了资本主义的毒(哈哈),因为资本的介入使商品越来越细分,其实并没有这么多的区别。我觉得一旦在性价比、轻便、好看等因素中权衡,我就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比较当中——这也是“认知劳动”的一个细节的例子,它通常是无形的。我的做法就是“邀功”,让伴侣看到我的付出,让对方理解这也是一种劳动。
但不得不提的是,我们做得并不算多,家里绝大多数的家务和育儿劳动都是我们雇佣的育婴师做的。
澎湃新闻:在一般家庭中还有什么劳动是被隐藏的呢?
沈洋:我会觉得,收入管理其实也涉及了大量的认知劳动,可能这是丈夫不想做的琐碎的事情,所以交给妻子。
澎湃新闻:这难道不是说明妻子的权力吗?
沈洋:家里的钱都由妻子来管,并不能反映妻子在家里的权力与地位高,也并不能代表性别平等。
如果是我来看的话,权力大小要看重要决定的最终决策权在谁那里,比如说买房子到底是买在哪里?如果双方都是本地人,那么房子靠谁家近?如果这些女性都可以做决定的话,我觉得算是权力的一种体现。如果只是说把钱放在女方那里,然后付水电煤这些琐碎的事,这反而增加了女性的认知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