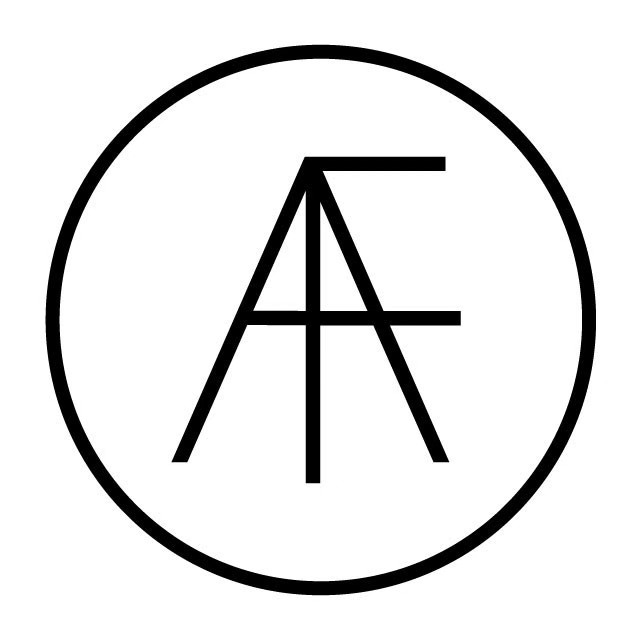作为“范式”的透视法

© Jean Dubuffet
作为“范式”的透视法
——达弥施与思辨艺术史的研究纲领
文 | 姜宇辉
《十月》杂志2015年秋季号以达弥施(Hubert Damisch)和杜布菲(Jean Dubuffet)为主题,不仅完整刊载了两人20多年间的通信(1961—1985),更是同时收录了达弥施曾撰写过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研究杜布菲的专论。由此不仅令读者全面领略这两位当代法国艺术界和艺术史界传奇人物间的命运纠葛(曾历经10年的争吵,但最终冰释前嫌),更为关键的是,这些珍贵的书信和研究资料为我们重新定位、理解达弥施那些往往深奥晦涩的艺术史“思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背景。选择思辨这个主题,不仅因为达弥施自己明确将其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透视法起源》(OP)这一巨著中],更是因为它在哲学意味上与晚近的思辨实在论运动产生了颇有可观的联系。在哲学发展的这个新背景之下,或许亦可对达弥施的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开放性潜能进行更具启示性的挖掘和揭示。

《十月》杂志第154期
一、 思辨方法的发端:“物”的导向
将达弥施的艺术史研究与思辨实在论这个前沿性思潮关联在一起,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早在达弥施研究杜布菲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让·杜布菲,抑或世界之辨读》(Jean Dubuffet,ou la. lecture clu monde, 1962)中,物—导向(object-oriented)的研究方法已经极为明显。此种导向固然一方面受到他的哲学导师、法国著名现象学大师梅洛庞蒂的影响[他后期明确从“主体—身体(corps)”转向“世界—肉身(chair)”],但杜布菲的绘画创作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亦不可被低估。正如达弥施在文中鲜明指出的,在杜布菲那里的一对看似针锋相对的主题[“人化”(humanizing)与“去人化”(inhumanizing)]正是引导他展开研究的核心线索。
在这篇经典之作的开篇,达弥施即明确强调,杜布菲的创作始于反学院、反传统(包括早已沦为传统的先锋派)、甚至反文化的极端叛逆立场,呼吁艺术应该回归“常人”(common man)。杜布菲将此种艺术界定为art brut(原生艺术),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则多少带着贬抑的口吻将其称作“原始绘画”,认为“他们有意识地追求写实,与他们组织画面的无能(除了装饰性地将各个部分凑合在一起外,他们一无所能)之间的矛盾,恰好使他们的艺术变得毫无风格可言”。而达弥施看来并不认同格林伯格这番有些草率的断语。基于扎实的前期研究,尤其是结合杜布菲自己的所谓“形而上学”的背景,达弥施试图对格林伯格的批驳进行回应。

© Jean Dubuffet
之所以杜布菲的画面组织会看似“凑合在一起”,正是因为他更为强调“偶然”(chance)力量的介入。这里的偶然并非主观随意的结果,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在创作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清除人的主体意志和观念的介入,从而复归于“莫测的客观运动过程(unpredictable objective processes)”。在看似无组织的、杂乱无章的表面之下,实际上凸显的是物质力量自身的“深层意义”(deeper meaning)。这里确实不再有任何足以清晰辨认的艺术史传统上的类型化“风格”,甚至也逐渐剥离了艺术家个体的风格,但却尤其呈现出“自然过程”(natural processes)的运动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的心灵重新探寻到介入的可能性,只不过,这回它不再是自然秩序的立法者,也不再致力于通过认知模式来表征世界,而更是退守到一种相对谦逊的地位,去“发现”(而非发明)自然过程本身的秩序、去摹写此种运动所留下的种种复杂诗意的“痕迹”。
然而,如此一种复归自然的运动亦会令人产生另一种误导性的假象,似乎杜布菲想要探寻的无非是近代哲学中(如笛卡尔、洛克)在初性/次性之间所做的区分:在“主观”感受的表象之幕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客观的”物质力量。但杜布菲的真正目的却当然不在于坚执现象/物自体式的分裂,他曾明确批驳了“隐藏世界”(behindworlds)这样的观念,强调“在事物之后,图像之下,唯有基底”(ground)。而这里的“ground”既非表象之后的隐藏本质,亦非单纯是传统透视法空间中的基准地平,而更应该在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始基”(substratum)。但为何要唤醒一种看似早已过时的古老自然哲学?当然是因为其中仍然蕴藏着巨大的思想潜能。这一点尤其应参考谢林→海德格尔→皮埃尔·阿多这一思想脉络中对“自然”(phusis)的重新省思。
阿多在名作《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中围绕“面纱”这一核心隐喻清晰梳理了“从自然的秘密到存在的神秘”的转变过程,对于理解杜布菲的创作理念颇有参考价值。起初“自然的秘密观念总是预设了可见的、显现的现象与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不可见者之间的对立”。但到了浪漫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歌德那里,则试图回归更为原始的“希腊意义上的phusis,或者从内部到外部的成形努力。换言之,“它并不隐藏什么,而是在揭示……如果伊西斯没有面纱,那是因为她完全就是形态,即完全是面纱”。这一源远流长的思想脉络在杜布菲的画作之中重新焕发生机:自然的成型运动(formation)更是进一步落实为具体的、由以突破传统绘画框架的创作手法,即达弥施重点论及的所谓“大地之墙”(Wall of Soil),或“垂直竖起的大地”(the ground rises vertically)。大地从水平向垂直的转换并非单纯是空间的位移、及由此相应带来的视角/视线的变化,而更是在绘画创作乃至本体论领域导致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
一方面,“直立的大地”(the erection of the ground)既是物质基底(the bottom of things)的涌现,同时又对应着传统绘画形式的解体(the dissolution of the forms),进而“无形”(formlessness)(亦即巴塔耶所说的“informe”)将成为绘画的新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直立的大地并非仅仅是主观视角的转换(从水平到垂直),而更是意味着对人类—主体的有限视角的根本性超越,或者说,既是从有限向着无限的开敞,又是从人的视角转向物的视角(从“以我观物”转向“以物观物”)的本体论转换。
从上述两个要点来看,虽然杜布菲的创作手法没有波洛克的滴画那般来得惊心动魄,但垂直竖立的大地与平铺的画布一样,都是借由物质力量的凸显而对传统绘画形式所进行的最为釜底抽薪的极端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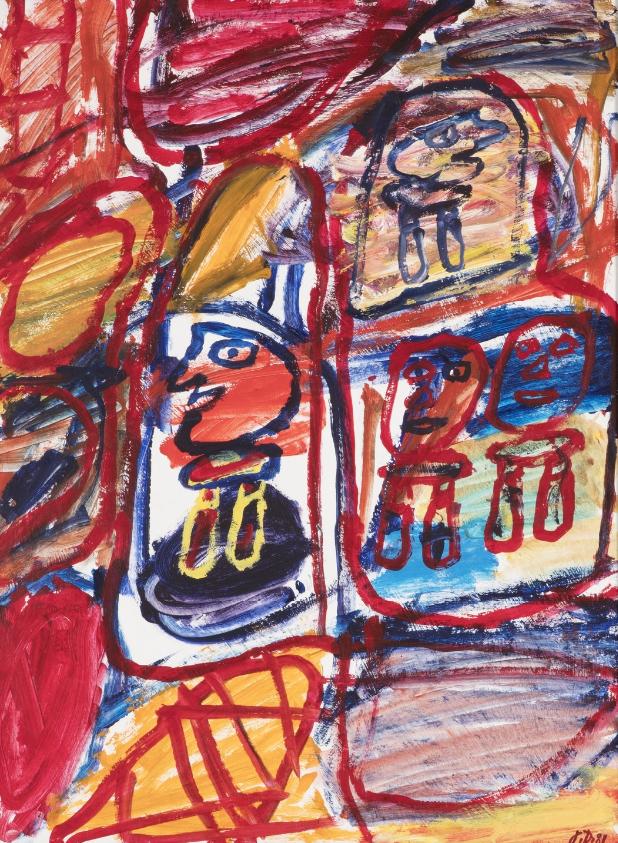
© Jean Dubuffet
二、 透视法作为“范式”
一般都会认为达弥施的最重要著作《透视法起源》(下简称OP)是回应之前《云的理论》中的难题,即云在透视法的几何空间中的那种看似格格不入的边缘或异质的特性。但若回归他的艺术史研究的真正起点,结合他对杜布菲画作的深刻理解,我们会发现其实云的问题只是他用以突破透视法这一典型而牢固的传统绘画“形式”的一个生动历史案例而已。既然形式的解体和大地基底的涌现本是合二为一的运动,由此在OP中,他不仅要将在更为广大的历史情境中来理解透视法的复杂丰富的面貌,更是要从根本上敞开物的基底这一真正朝向无限的超越维度。
也唯有从这个初始动机出发,才能真正理解OP中所深刻阐发的“思辨”的艺术史研究方法。“思辨”这个说法在前言的起始段落就明确出现[透视法作为一个“高度思辨(éminement spéculative)的主题”],看似突兀,但却点出了其研究的主旨,即着重于哲学问题的探索、而非单纯的历史脉络的梳理。正是“思辨”的视角与方法使得达弥施的这本巨著在早已汗牛充栋的关于透视法的历史研究作品中脱颖而出。这首先也就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历史”及“起源”的真正含义“如果有历史,那又是关于什么的历史?”。达弥施明确区分了两种对待起源的态度。一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经验性起源(origine empirique)”,即按照历史事件的顺序,一步步描述透视法的起源、发展、最终逐步消亡的线性过程。此种编年史式描述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将透视法仅仅视作西方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没有意识到:一方面,透视法本身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均质的形式框架(“prototype”或“modèle”),相反,它已经是不同差异要素的聚合(绘画,建筑,几何等等),也正是因此,达弥施非常恰当地(借用福柯的用语)将其称作“透视装置”(dispositif perspectif);另一方面,从“起源”本身的角度来看,透视法远非仅仅是一个早已过时的历史事件,相反,它的创造性的生成潜能(“productrice d'effets”)远远超越了单纯时代的限制。
由此达弥施进一步指出,他所意谓的“起源”(origine)正是在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下简称《起源》)的意义上指向形式和理念“外衣”之下的那个活生生的感觉直观之源”:“回归无定形的感知世界(retour au monde perceptive amorphe)……正如胡塞尔所构想的哲学所希望实现的”。胡塞尔的这篇短文经由德里达的阐发,确实对OP全书的构思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胡塞尔关于“大地”(Earth)作为“开放的无限的未知事物的地平线”的说法又与不断“成型”的大地基底形成了极为明确的呼应。关于这些要点,将于下节展开。我们先回到达弥施的思辨方法。

© Jean Dubuffet
如何摆脱进化论的影响,研究透视法的“另一种历史”呢?达弥施援用“范式”(paradigme)来界定自己的独特研究进路。通常都会将这个概念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结合在一起,达弥施当然也不会忘记提及这个重要来源,但他同时明确指出自己对范式的理解与库恩的科学史研究有着根本差异达。首先,库恩明确将范式与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联系在一起,因而更为强调范式的“规范性”和“调控性”,而达弥施则显然更为关注范式的开放性、多元性和生产性,倒是更为接近阿多诺的“星丛”(constellation)。其次,在库恩所界定的范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之中,虽然第二点亦为范式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但科学革命这个核心理念仍然导致一个明显的结论,即旧范式在被新范式取代之后将会彻底“失效”(obsolete),而这又与达弥施所强调的范式所具有的“本原”性的创生力量背道而驰。
即便如此,达弥施对范式的此种创生力量的阐释却并不充分。即便他非常敏锐地将透视法视作一种典型的范式来进行考察,但此种做法背后的理由却从未得到充分解说。他似乎始终在具体和普遍这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透视法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现象,因而必须首先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进行细致描述(代表性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手法);另一方面,他又往往倾向将透视法视作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结构”,它并不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作为一种弥散性、衍生性的思想模式(autant de modèles pour la pensée)。看似达弥施非常想在这两极之间寻找关联,因为他曾明确指出,透视法并非一种抽象的代码(code),而是如语言一般总是需要在具体的情境之中得以实现(“un ici ou là”)。但透视法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本来就错综复杂(《云的理论》,第三章),因而单纯援引语言的结构特征来进行解释显然并不充分,甚至会进而导致一系列更为棘手的难题。
就此而言,有必要参考阿甘本在《什么是范式?》(What Is a Paradigm?)这一经典论文中的思想史梳理来展开进一步的论证。阿甘本首先就指出,其实库恩的范式理论包含着两个要点:一是规范性功能,二则是“范例”(a single element … serves as a common example)的关键作用。通常我们仅关注到第一个方面,而未意识到,其实正是第二个方面才真正揭示了范式的独特的创造性本原。鉴于这个要点恰好可以补充达弥施论证中的缺失环节,因而有必要稍加详述。阿甘本将“范式作为范例”这一基本原理回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将范式作为不同于演绎和归纳的第三种“悖论性的运动”:归纳是从具体到普遍,演绎是从普遍到具体,而范式则极为不同,它是从具体到具体。后来康德所提出的反思性判断力恰好可以作为范式运作的典型体现:它始终运作于具体性的平面之上,并不试图以一种预设的普遍法则来对具体进行规定或协调。范式始终是以范例为中心展开辐射的“力场”,通过类比(analogy)的关系将越来越多样而异质的具体要素凝聚为一个强度性的聚合体。此种“并置”(placing alongside)与“汇聚”(conjoining together)的作用既呼应着“范式”的词源学意义,但同时更为突出的是范式本身所指向的“本体论特征”(ontological character)。范式并非单纯是一种思维的模式(主体—客体之间的联系),相反,它从根本上指向的是万物之间的根本性的关联方式。
唯有基于这个极为关键的本体论基础,我们方可揭示出仅仅隐含在OP的字里行间的深意,进而真正领会“透视法作为范式”这一核心命题的启示能量。透视法首先是作为“范例”,无论是在布鲁内莱斯基那里,还是在笛沙格(Girard Desargues)或阿尔贝蒂那里,透视法的提出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建筑、几何、绘画),而透视法的运用都有着极为鲜明的特殊性。这里当然不存在一套统一的、足以作为“规范科学”的透视法规则。后人对透视法的发挥也往往是源自这些差异的源头,令这些看似具体而分散的“范例”不断弥散出“范式”的力场,进而将极为不同的领域的创造实践凝聚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弥施亦将范式与潘诺夫斯基的“象征形式”(Symbolic Form)区分开来。虽然后者的《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是当代研究透视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但“象征形式”这个借自卡西尔的概念作为一种贯穿于不同文化领域之中的总体性(totality)“语法”,显然与在具体性层次上拓展其力场的范式有着明显差异。

© Jean Dubuffet
三、 “思辨”方法及其运用:作为无限“界域”的大地
但阿甘本对范式的本体论地位的启示也伴随着史蒂文斯的诗行戛然而止。由此,有必要再度回归达弥施的文本,沿着这个启示性方向来探寻进一步的线索。这即是达弥施清晰点出的“范式”这个词的更为古老的词源意义,即展现、展示、指示(montrer、exhiber、indiquer)。即它作为一种基本的操作方法,最终旨在揭示所研究对象的本质和真实存在。在后文,达弥施甚至将这一点作为OP全书研究的终极主旨:“在它起源之际,透视法正如几何学,更关注的是事物本身、而非作为物之容器(réceptacle)的空间。”这些清晰的界定既明确肯定了透视法范式的本体论地位(物—导向),更是在这个基础上将此种具体的操作方法称为“démonstration”。这首先是因为“démonstration”这个词在法语中兼有论证、示范、展示等意,与“范式”的复杂丰富的含义颇为吻合。
进而,从词源上来看,“démonstration”与“思辨”之间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甚至达弥施在书中多处都将两者并称。“démonstration”源自“di-mostratio”,原本“意指一种复制、复现的重复过程,主要依靠镜子来实现(le miroir est l’agent)”。而“思辨(spéculation)”一词亦是源自拉丁语speculum,正是镜子之意。镜子在透视法的发展过程中占据极为关键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如布鲁内莱斯基这样的透视法的早期发明者本身就大量运用镜子来辅助自己的测量和创作;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镜子并非仅仅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在中世纪的时候它指向“神显(divine revelation)”,而在透视法兴起之后,它则最终旨在揭示事物自身的显现。这些词源学和思想史的背景既再度令我们清晰领会了作为基本“范式”的“展示”—“思辨”方法所共同指向的本体论基础,更是明确界定了此种达弥施从透视法的历史研究中所提炼出的原创性方法的真正内涵:它既是“证明/证实”(verification),同时又是“展示”。换言之,“‘真’之效应(l’effet de vérité)”,这才是“思辨”方法的终极旨归。诚如当时的画家在运用镜子的时候,并非仅将镜像作为一种缺乏实体的幻象(illusion)抑或营造视觉特效的伎俩(trompe l’oeil),而更是旨在展现/展示事物本身的真实特性和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弥施在书中多次援引弗雷格在《意义和指称》中的一个经典案例,即复杂多样的镜像最终所指向(dénotation)的始终是同一对象。
作为证明和展示的思辨方法足以作为透视法范式在本体论方向的最为明确而有力的推进、实现途径。一句话,对“真”的揭示,这正是达弥施之所以运用思辨方法来对透视法历史进行研究的真正意图所在:“这就意味着,一种对于‘真’的追求已然开始发挥作用,而艺术有史以来第一次为真之显现提供了场所。”不过,鉴于“真(vérité)”是一个过于含混、易于引发误解的概念,达弥施随后明确将自己的“真”之概念界定为“超越的(transcendental)”,并由此与神学和自然主义的真理观相区分。神学否认物质世界本身的真实性,将真理归于超越的彼岸。自然主义(尤以英国经验论为代表)虽然肯定外部世界的真实性,但仅仅局限于感觉经验的层次〔主观与客观的相符、一致(adequation)上来理解此种真实,而没有看到物本身更指向着逾越感觉范围的敞开界域。显然,达弥施这里所说的“超越的”立场更接近胡塞尔的现象学(《危机》),而决非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我所理解的对一切现象的先验的观念论是这样一种学说概念,依据它我们就把一切现象全都看作单纯的表象,而不是看作自在之物本身”:他虽然亦强调主观的建构(证明),但最终意在“展示”“被感知物的自身实体(la substance même du percu)”。借用他早在杜布菲的研究论文中所提出的重要概念,思辨方法所要揭示的超越之真并非先天的主观形式,而恰恰是物自身的“基底”(sol/ ground)。
而“sol/ ground”这个概念也恰恰是达弥施自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中挖掘出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根据胡塞尔,感知经验的始基(fonds primitif)构成了所有理论和实践生活的基底(sol)”。就此而言,OP与早期的杜布菲研究实在是一脉相承。可以恰当地说:借助现象学的缜密思索、落实于对透视法的历史缕析,最早由杜布菲所激发的艺术史灵感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就透视法的研究而言,在胡塞尔那里与“基底”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horizon(界域)”显然更具有相关性“纯粹可见性,就是——再度援引胡塞尔——‘一个基底和一个界域的统一体’”,因为两者同样都聚焦于无限性这个根本问题之上。
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需回溯到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对深度感知这个近代认识论中的核心难题的论述。诚如贝克莱在《视觉新论》的第二节中就明确指出的:“我想人人都承认距离本身是不能直接为人所见的,因为距离既是以其一端对着眼的一条直线,因此,它只能在眼底上投入一点。”面对这个难题,贝莱克以心理联想为解决手段,而笛卡尔则以几何光学的方式加以解释。看似透视法应该被归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解决方案,因为它试图以几何学的方式来理解视觉经验的本质结构。但若回归透视法作为“思辨”之“范式”,我们理应将它的作用领域放回到原初的感觉经验,并且不再仅仅将其视作主观的视觉模式,而更是从根本上令其指向物本身的展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对界域这个概念的阐述成功地克服了经验论/唯理论的对立。诚如佩吉·罗尔斯(Peg Raws)所言,胡塞尔在《起源》和《危机》之中对几何学的“起源”所进行的思索真正将几何学从一个纯粹形式的抽象系统带回到“动态的具身活动(dynamic embodiments),由此重新描绘了美学、空间与感觉主体的联系”。正是基于这个重要背景,我们方得以对透视法的“范式”作用进行恰当解释。
实际上,界域早自胡塞尔现象学的发端之处就是一个重要概念。比如在《观念1》中进行“现象学基本考察”的伊始,他就明确指出无限敞开的界域是日常感知经验的本质特征:“现时被知觉的东西……被不确定现实的被模糊意识到的边缘域部分地穿越和部分地环绕着……我的不确定环境是无限的。这个模糊的、永远也不会完全确定的边缘域必然存在着”。由此亦清晰显示出作为范式的透视空间的特征:一方面,透视空间的无限性并非单纯的几何形式的同质拓展(从眼睛出发向无限远处的地平线延伸的视线),相反,它指向的是明确的感知范域的模糊边缘,它划定的是可见/不可见之间的动态边界;另一方面,界域必然体现出超越具体的、特殊的视角(perspective)的趋向,它最终指向的是不同个体所共享的同一世界,是最为广大的世界时空的总体。界域的此种特征在《起源》中更为明确地与大地关联在一起,从而尤其体现出与达弥施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六章中,德里达将这条隐含线索的启示性力量充分展现出来。他首先指出:胡塞尔最终意在将“理念化自然”回溯至“前文化的纯粹自然(la pre nature pré-culturelle)”,而真正能够对此种纯粹自然起到最初的“例证”作用的要素(l’élément exemplaire)正是大地(la terre):“大地本身作为最普遍、最客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要素,恰恰成为全部感性对象的第一个质料。”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几何学的原初源头恰恰指向着“地球—学(géo-logie)”。只不过这里的“地球”不再仅仅是一个天文学研究的天体对象,而是作为“一切可能经验的无限视域”的“原初大地(le sol originaire)”。由此德里达明确将“大地(sol)”和“界域(horizon)”关联在一起。而经由这番文本诠释,我们也终于领会,作为范式的透视法确实最终指向着空间的无限维度,但此种无限并非单纯理性的范畴、亦非数学/几何意义上无限趋近的“极限”,而是从根本上指向物自身的不确定的、模糊的敞开边缘,并最终指向大地这个终极“界域”。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所说的“原初大地”与达弥施自杜布菲的创作中所着力阐发的“大地之墙”又是何其相通。
在OP的文本之中,同样也存在着如此将大地和界域结合在一起的“范例”,那即是居于全书显著位置(第三部分的绝大部分篇幅)的对于三幅与透视法相关的代表性画作的讨论:15世纪(传为建筑师和画家的)Fra Carnavale所作的《理想之城》(Ideal City)[因现保存于巴尔的摩,因而在OP中被称作巴尔的摩图版(Baltimore panel)],以及其他两幅主题乃至巴尔的摩风格皆相似的作品[因保存地点的不同,在OP中分别被称作乌尔比诺图版(Urbino panel)和柏林图版(Berlin panel)]。选择这三幅作品进行集中细致的研讨,首先当然是因为透视法的发端与建筑空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比如布鲁内莱斯基对透视法的重要研究就是源自对佛罗伦萨洗礼堂(The Baptistery of Florence)的空间结构所进行的原创性透析。其次,更为重要的缘由在于这些作品看似与达弥施的思辨方法所要进行的“展示”性操作更为贴合。因为若单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技法、主题等等),它们皆乏善可陈。但它们确有与众不同之处,即它们都并非仅仅是运用透视法的绘画(Peindre en perspective),而更是以“透视法本身”(la perspective)为主题的作品。换言之,它们皆意在以“透视”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来展示透视法自身。这一点或许是受到福柯对《宫娥》的经典研究的巨大影响。OP开篇就提及了福柯这一重要参考背景,而在全书的最后部分又重新回到对于《宫娥》的透视空间的细致讨论。这都是因为与《理想之城》的三幅主题及变奏相似(“透视之透视”),《宫娥》也是绘画史上极为罕见的以“表象”结构本身为主题的作品(“表象之表象”)。
这些当然亦是OP中的重要线索,但达弥施对这三幅作品的分析最终更意在围绕界域的不确定的开放性(无限性)来“展示”三者之间的差异性张力。具体的对比分析集中于第十四章,达弥施从空间层次(niveau)、地砖网格(quadrillage)等方面进行了五重比照,其中对三者的透视空间之差异的阐释明显占据核心地位:乌尔比诺图版的透视空间是封闭的,没影点位于沿着广场中央穿越过庙门的没影线上;巴尔的摩图版的透视空间是半开放的,没影点位于穿越凯旋门的背景之处;柏林图版的透视空间则是全然开放的,它的没影点被抛向无限开放的水域(renvoyé à l'horizon)。如果说在前两幅作品中,透视法仍然被限定在明确的空间规划之中,那么,在第三幅中,正是在无限开敞的界域的背景之下,透视法本身成为主题得以“展示”。在第十六章中,达弥施又重新从界域的封闭和开放的角度阐释了三者之中更为复杂的透视形态:乌尔比诺图版的没影点看似被限定于寺庙之内,但寺庙两旁的道路又显示出一种不确定的纵深;巴尔多摩图版的透视空间则是断裂的,凯旋门之前的广场作为前景与凯旋门之后的远景明显将空间区隔成了两段,而背后的城墙和瞭望塔又将此种含混性推向极致,因为它“既是开敞又是封闭”;而柏林图版始终是最为特别的,因为它最为戏剧性地展现了界域的无限开敞:地砖的垂直相交的网格恰似一个铺展开的扇面,而其中心则指向那片开放的水域;虽然整幅画面可以被视作沿着广场的水平边缘以平行的方式不断向远处层级推进,但这种连续的运动却在水面之处被骤然断裂;远处虽然有浅淡的山影,但完全不像巴尔的摩图版那般指向着半封闭的空间背景,而是如倪瓒的三段式构图般,最终只是更为戏剧性地衬托出无限开放的水域:“目之所及,唯有水,水,水。”(马基雅维利语)
四、 结语:天与地,从“升起的大地”到“宇宙心智学”
实际上,达弥施的这番论述与《云的理论》中对透视法的看似悖论性的架构的揭示亦是一脉相承。此种悖论尤其体现于天与地的分化之中,“同一个画面里区分出两个世界,每个世界又有它不同的风格法则”:地上的风景遵循着严格的透视法的线性空间秩序,而与之相对,没有明确边缘轮廓的天空则只能是“雾一般的”,充满含混和不确定的样态。但其实天与地在传统透视法空间中的分裂和对立并非仅仅体现为表现手法或风格的对立,而更是涉及透视法的空间体系自身的封闭/开放的双重性:之所以地面的景物能够被限定于一个(相对)明确的空间秩序之中,正是因为它同时在边缘之处“开向一个没有地平线的深度,拓出一个‘线外的空间’”。换言之,不可见的、不确定的无限界域正是可见的景物得以被表现、被呈现的真正的本体论前提和背景。只不过,这个无限的界域可能并不像胡塞尔所设想的那般仅仅指向“原初的大地”,而更是指向一个更为广大的界域,即天空。正如在柏林图版之中,开放的水域渐与无限辽远的天宇融合在一起。天空这个向度同样在OP之中被重点提及(第二章),虽然只有简短的讨论,但却直接导向思辨方法的提出。作为透视空间中的不连续的、异质的、进而对透视技法来说是“未受掌控、甚至难以掌控的终极界域,天空确实最为适合作为“展示”的对象。由此,在早期的杜布菲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地之墙”这个物—导向的本体论基础在透视法范式中得到深化和拓展,进一步指向了天空这个最为开放的无限界域。
实际上,在《让·杜布菲,抑或世界之辨读》和OP之中,达弥施都谈及了俯瞰的空间视角(aerial view)。虽然只是暗示的线索,但已经包含着对透视法范式进行创造性拓展的重要启示。首先,这个空间的视角既不同于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已经着力批判的笛卡尔式理性主义所追寻的那种超越的“上帝的视角”,亦不同于歌德式的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俯视的目光与宇宙遨游”的想象(皮埃尔·阿多,《别忘记生活》,第2章),但更不同于太空摄影或谷歌地图这样借助高科技手段所摄取的全景“图像”。根据前文的缕述和达弥施的重要启示,此种空间的视角(由地向天的开敞)必须要在透视法空间自身的边界之处去探寻,是要通过细致的“思辨”步骤方可能被真实地“展示”。诚如卡斯滕·哈里斯在研究透视法历史的经典之作《无限与视角》中所提示的“视角原理”:“要把一个视角作为一个视角来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超越了它,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我们只能把从那个视角向我们显示的内容理解成某种东西的一种视角性显现,而这种东西不能如其本身地显示自己。”
这段话与达弥施的思辨研究法在主旨上颇为相通,因为它既肯定了透视法的物—导向的本体特征,亦同时强调了无限敞开的界域在理解透视法中的本质性地位。只不过,与达弥施在细致的思辨考察中洞察透视法空间体系的开放边界的进路有所不同,哈里斯选择以回归神学/神秘的方式(库萨的尼古拉,埃克哈特)来最终通达无限界域。即便我们并不认同此种神秘主义路向,但他通过布鲁门伯格的“宇宙心智学”所提及的一个重要思索仍然与达弥施的主旨形成呼应。布鲁门伯格曾说自己是“被宇宙航行学留在家里的人”,由此警示我们不要迷失在无限的空间之中,而是仍然要在其中探寻到“家”的归属感。这同样是在强调着有限空间和无限界域之间的内在的、不可分隔的关联。埃杰顿在全书最后提及了一个惊人的天文学案例,即在透视法技术的辅助之下,科学家们在太空之中洞察到了“爱因斯坦十字”这样震撼的图景。这当然既是艺术与科学的联姻,但同时又是人与宇宙之间的终极融汇。
* 本文选自沈语冰主编的《种植我们的花园:当代艺术理论研究》,
感谢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标题:《作为“范式”的透视法 | 姜宇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