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揶揄又加强了小说阅读对女性的危险影响
【编者按】
在《现代性的性别》一书中作者将文化历史和文化理论相结合,聚焦于19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怀旧、消费、女性书写、大众化的崇高、进化、革命和变态等概念进行了检视。她从比较和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对来自英语、法语和德语传统的大量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涉及社会学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颓废文学、政论文章和演讲、性学话语,以及通俗情感小说等多个领域,分析的男性和女性作家包括齐美尔、左拉、萨克-马索克、王尔德、拉希尔德、玛丽·科雷利和奥利芙·施赖纳等。本文摘编自书中对《包法利夫人》的相关解读,由澎湃新闻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女性阅读习惯被认为缺乏批判性,过度情绪化,这种非难当然由来已久。18世纪就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小说作为一种专写浪漫爱情的文类开始流行,这让人们很担心小说对容易受感染的女性读者造成的影响。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描述的相互对立但又具有辩证联系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出现,关于女性阅读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变得日益低廉和高效,具有读写能力的人越来越多,阅读的公众群体不断扩大,这些都使得通俗小说越来越受欢迎。与此同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深奥的信念和创作实践,使自己尽量远离这种粗俗低下、哗众取宠的新型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划分,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性别潜文本(subtext);“文化价值的再度男性化”就发生在19世纪晚期,这段时期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作家,他们崇尚的是一种疏离的、不重感情的美学立场,它显然被认为比通俗小说中的女性感伤主义更加高级。
爱玛·包法利对购物的疯狂,象征性地表现了她未获满足的欲望,虽然这显然与我之前的讨论相关,但现在我想稍微改变一下话题,思考一下消费和阅读之间的关系。从经济意义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与其他大规模生产的物品一样,文学也日益融入了商品文化,它的生产和流通不可避免地受到利润动机的驱使。但令人惊讶的是,文学消费总是从经济领域隐秘地转换到象征领域,消费不仅仅是指买卖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易,而且指向一系列关于大众读者的看法,将读者当成不加批判地消极接受文学作品的受众。换句话说,“消费”一词的贬义被运用到审美范畴内,以维护文学价值和文化权威的等级观。生产高于消费的二元论早已经存在,它被用来区分需要智力劳动的高雅艺术,以及追究盲目快乐和逃避主义的流行小说。
“消费”一本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探究了一些关于消费的内涵,它们与嘴巴和性虐有关,涉及并入和毁灭的幻想。这些比喻反复出现在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评论中,如拉里·里格斯(Larry Riggs)的这句话:“从修道院里老佣人对冒险小说‘大快朵颐’(她也鼓励女孩子们读),到爱玛对时尚杂志的‘饕餮’,再到她最后吞服的砒霜,这些事件就像是一次次宴席,可以说《包法利夫人》就是关于包法利式消费的个案研究。”如此一来,文学被简化为食物之事;阅读成为一种饮食方式。这不是里格斯的一家之言,比如利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也指出了爱玛对浪漫小说的“暴饮暴食”。令人惊叹的是,口嘴比喻被如此频繁地用来描述阅读的过程,尽管有时候这些比喻可能只适用于某一类读者。如贾尼丝·拉德韦(Janice Radway)所指出的那样,经常使用这类比喻的主要是那些流行小说的批评者,他们从消化、归并、吸收这些生物过程中提取比喻,将非智性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文化实践贬低为对本能需求的近乎机械式的满足。
我引用的都是当代批评家对《包法利夫人》的批评,而不是对福楼拜本人的批评。然而,我并非要质疑这些言论的准确性——相反,它们很好地传达了爱玛对文学的感受——我要质疑的,其实是他们对福楼拜作品中嵌入的意识形态的不假思索的认可。人们对爱玛·包法利这个女人存在着一个批评的传统,除了个别真知灼见之外,大多数读者对她的反应是想拥有她,或者是鄙夷她,再或是让她去性别化,这些阐释说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力,人们习惯于将文学性定义为女性为代表的商品文化的反面。拉里·里格斯所说的爱玛“极度功利的浪漫主义”,就很好地概括了这种审美的固有假设。这种说法看上去充满悖论:浪漫主义中唯心主义的、精神化的冲动似乎与讲究实际、崇尚使用价值的社会观念截然相反。然而,正是这种唯心主义和工具性的矛盾结合,以及这种渴望超验和市井旮旯的结合,才使爱玛·包法利成为热爱阅读的女性的原型。
爱玛文学品味中的浪漫主义元素是显而易见的。她喜欢文学中的乌托邦和理想主义,将之视为逃遁到美好世界的方式。作为一个外省医生的妻子,她寻求着那些与她平凡生活有着天壤之别的新奇场景,她渴望一种浪漫的崇高,渴望夸张的情感和过度的激情。福楼拜对她少女时期读的书做了一番冰冷的描述。“书里讲的总是恋爱的故事,多情的男女,逼得走投无路、在孤零零的亭子里晕倒的贵妇人,每到一个驿站都要遭到毒害的马车夫,每一页都疲于奔命的马匹,阴暗的树林,内心的骚动,发不完的誓言,剪不断的呜咽,流不尽的泪,亲不完的吻,月下的小船,林中的夜莺,情郎勇敢得像狮子,温柔得像羔羊,人品好得不能再好,衣着总是无懈可击,哭起来却又热泪盈眶。”
这里,通俗罗曼司中的那些过度夸张的桥段被作者加以反讽,表现为一系列的常规故事的重复;通过将叙事变成一张张清单列表,叙事者显然将戏剧冲突和情节中那些诱人的元素削弱了,并使之变得荒诞。作者没有呈现一个有意义的有机整体,而是让碎片化的文本变成随意并置的语义单元,在各种不同地点无休止地重复讲述。这些充满异域感和逃离色彩的刻板情景,构成了成年爱玛的幻想基础,她试图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转换成罗曼蒂克爱情的文学密码,从而使自己的生活获得意义。然而,爱玛忘记了这些故事根本就是屡见不鲜;对她而言,这些情节体现了绝对的、理想的充盈,衬托出现实的匮乏。“爱玛试着搞懂书中的至福、激情、狂喜这些词到底在生活中是什么意思,对她来说,它们在书本里显得是那么美妙。”
虽然一些评论家认为,爱玛所选择的糟糕读物显然是现代大众市场上那些情爱小说的鼻祖,但也有评论家不那么武断地评价她的阅读,而是认为她对于超越的欲望其实并无别的释放渠道。因此,贝尔萨尼指出,爱玛的阅读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精神化冲动”,而埃里克·甘斯(Eric Gans)则指出,在福楼拜笔下那个无限平庸的世界里,“爱玛的渴望是唯一可能的超越形式,是唯一可能的宗教”。这些观点与最近兴起的对大众文学的辩护一脉相承,批评家开始看到这些作品中的乌托邦元素,认为即使最平庸的作品也绝不仅仅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和,它们也可以是一种抵抗,表达了对现状的拒绝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爱玛身陷贫瘠而狭隘的环境中,她的性别决定了她没有什么社会选择权,所以只能通过所阅读的文本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正如罗斯玛丽·劳埃德(Rosemary Lloyd)所指出的,这些文本实际上比批评家想的更为多样化,它们包括巴尔扎克,沃尔特·司各特,欧仁·苏的作品,还包括各种不知名的大众情爱小说、版画和女性杂志。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当然不是爱玛读了什么,而是她怎么读;她对文本的消费有效地消除了文本之间的一切美学差异。就这个意义而言,与其说《包法利夫人》是关于小说本身的负面影响的,不如说是关于特定阅读方式的危险的。正如前面引文所指出的,爱玛将小说提炼成一系列随机的场景,一连串不相关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它们既是高度具体的——如潟湖、瑞士小屋、苏格兰小屋——也是充满暗示的。卡拉·彼得森(Carla Peterson)指出,她的阅读是一种不断分裂文本,使之碎片化的过程,文学作品被简化为孤立的情节碎片和可供模仿的范例。通过将丰富的语义和神秘的充盈归结于一些去语境化的、自由漂浮的形象,爱玛不可思议地预见了20世纪大众传媒文化的样态和时尚生活的营销形式,它们和“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理论描述的如出一辙。
换言之,福楼拜不希望读者以爱玛的那种方式来读他写的小说。如果作者试图通过细腻的组合和精巧的晦涩风格来阻断读者的期待,爱玛反过来又通过否定文学形式的中介权威,将风格转化为内容。她只求字面意思,只考虑自己的兴趣,只寻找她能认同的奇特意象。审美价值被降格为情感的使用价值;文学仅仅是一种激发情感和情色的手段。爱玛不顾一切地想要摆脱外省无聊生活的束缚,于是去书中寻找那些描绘浪漫诱人的生活的文字,去找她的生活中极度缺乏的东西。“她订阅了一份妇女杂志《花篮》,还订了一份《沙龙仙女》,她如饥似渴、一字不落地读关于剧场首演、赛马、社交晚会的报道……她研究欧仁·苏描写的室内装饰;她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的小说,在幻想中寻求个人欲望的满足。”
因此,爱玛对审美超越性的渴望在小说中只是相对的,因为它与女性情感和感官冲动之间是未经中介的关系;她向往的崇高是感伤化的,而非丰碑化的。当爱玛年轻时表现出对宗教象征物的兴趣时,这个母题就已经有明显体现了,其特点是不能区分复杂的精神渴望与肤浅的感官享乐。福楼拜写道:“她爱教堂是为了教堂的鲜花,爱音乐是为了浪漫的歌词,爱文学是为了文学迸发的激情,她用这种性格去对抗信仰的神秘性,因为这样就能对抗与她的秉性格格不入的清规戒律。”功利性地利用文化形式去满足眼前的主观需求,这成了爱玛性格的标志:“她要求事物必须投其所好;凡是不能立刻满足她心灵需要的,她都认为没有用处——她多愁善感,而不倾心于艺术,她寻求的是主观的情,而不是客观的景。”如纳撒尼尔·温(Nathaniel Wing)所言,爱玛不仅是“资产阶级情感”的象征,也是女性情感的象征,关于利润和功用的词汇常常和情动与感伤同时出现,这颇能说明问题。因此,爱玛的浪漫被刻画成一种堕落的浪漫,根植于眼前的情感渴望和肉体欲望,没有实现精神层面自我超越的动力。就像爱玛年轻时喜欢教堂是因为鲜花,她对文学的兴趣也仅仅因为它“迸发的激情”。
这里暗示的隐含评判标准,正是康德关于非功利性审美的理想,它将审美判断置于所有功利计算和感官冲动之外。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本身,与特定主体的偶然欲望和需要毫不相干。在福楼拜的文学理念中,可窥见康德的这一思想,福楼拜疯狂崇拜的是作家的冷静(impassibilité)、作品的清晰和风格的完美,他梦想有朝一日写出“一本关于空无的书”。这种将艺术与生活完全割裂的观点,当然一直颇受争议,因为艺术家和作家尝试恢复艺术在伦理和政治上的目的性。然而,福楼拜笔下独特的女性气质,其实是一种对使用价值的审美,它的基础是感官兴趣,而非认知。之所以要打破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和人性(尽管现实主义美学是这么想的),而是为了在文本提供的欢愉中进一步丢失自我。
在爱玛去鲁昂歌剧院看《拉美莫尔的露琪亚》(Lucia di Lammermoor)的那段描写中,作者想探究的是女人对情感认同的易感性,以及在激情中的自我放纵。爱玛立刻将自己与女主人的命运做了对比,这使她忧伤地反思自身存在的悲剧性和局限性。她试图保持超然冷静,但很快就被演出冲昏了头脑,她把男演员与他扮演的角色混为一谈,把她在情人身上未能获得满足的浪漫渴望都投射到男主角身上。“她真想扑到他的怀抱里,寻求他的力量保护,就像他是爱情的化身一样。她要对他说,要对他喊:‘带我走!把我带走!让我们走吧!我朝思暮想的,都是你!’”爱玛把自己投射到文本中,只是为了能在文本中放纵自己,让欲望之海淹埋身份的界限。她愈发疯狂的情色欲望,既是关于性爱的,又是关于文本的,体现了一种不成熟的渴望,渴望将自己与真实和虚构的他者融合在一起。
这样的情节暗示女人对艺术的反应是出于自恋症:女人是典型的幼稚型读者,不具备区分文本和生活的能力。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这一点,例如在龚古尔兄弟的杂志上有如下这段话:“今晚,公主说:‘我只喜欢自己能成为女主角的小说。’这是个完美的例子,说明了女人是如何评价小说的。”因为女性读者无法实现想象和思想的跨越去欣赏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她们把文本当成镜子,在镜子里她们同时发现并确认了自己的主体性。爱玛·包法利分不清现实和虚构,她成了那些梦想成为爱情故事女主角的现代读者的原型。女人渴望成为或者认同再现的对象,因而打破了真正的审美沉思应保持的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感。
当然,在把《包法利夫人》解读为一种特殊的女性意识形态的症候时,我也可能会受到一种指责,即我对小说的读法是和爱玛一样的,我在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暴露出的,要么是故意为之的盲目,要么是无意识的愚蠢。许多批评家认为,福楼拜的小说似乎在谴责爱玛的粗俗和自恋,但实际上它包含众多的镜渊,消解了它所似乎宣称的主张。福楼拜对女性气质的认同是矛盾的,这可以从他的书信及叙述视角的不确定性上体现出来,这也进一步支持了前述观点。然而,认同(identification)并不是自动地否定施虐狂式的距离化(distantiation),而可能实际上加强了这种距离化。尽管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所言,福楼拜的小说中共情与反讽确实同时存在,但一个女性主义读者可能更容易注意到反讽,而非共情,尤其是当小说中的叙述者对爱玛的阅读方式做出相对确凿的评价时。
此外,这些论点往往不只是在(无懈可击地)说文本具有多重含义。相反,它们反复强调《包法利夫人》拒绝屈从于任何一种可辨的意识形态立场,这又以可预见的方式物化了艺术作品的光晕。当然,这部小说的审美意识形态就是这么一种主张,即福楼拜的创作代表的是真正的现代性,而爱玛的阅读是幼稚的。有些评论家声称福楼拜的小说颠覆了这种差异性,因为作品承认了它与批判对象的共谋,但这样一来只是在更高层次上强化了这种对立;小说的这种自我意识本身现在成为一把真实文学性的标尺,用于区分《包法利夫人》和那些教条主义的、意义单一的文本。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认为,这些争论并不仅仅是关于所讨论的文本的,它们也是“在虔诚地实践学科的自证性,显示出文学批评这个学科有其独特性和自主性,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不断地把能指提到所指之上,不断地把复杂的形式提到(女性化的)琐碎内容之上,这样就能为文学的专业化进行辩护,从而进一步巩固文学的正典和特定的阅读实践方式。
女性化消费美学的幽灵正是要否定文学行业的专业化地位。女性读者将文学作为自我陶醉和自我放纵的手段,否定了文学的自主性,打破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文本之间的界限。对文本的象征式消费就好比对物品的实在享用,比如食物;文本也是为了满足食欲,它会融入人体,也会被耗尽。不加评判地吞食小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危险现象,因为它否定了文学物品的自主性;因为女性缺少对作品艺术光晕的敬意,所以她们的欲望瓦解了既定文化形式之间的差异和分化,由此否定了审美的独特性及价值。因此,爱玛的阅读可能会破坏福楼拜本人的个人和社会身份的基础。
这种强迫性的阅读反过来会引起女性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女性读者受书上文字的诱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因为她们无法去模仿她们甘之如饴的小说情节。因此,评论家们指出,爱玛的欲望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和“阳刚之气”,因为她想把她真正的爱人利昂改变成她梦想中的理想英雄。浪漫小说给女人灌输了夸张而不切实际的想法,她们因此可能去寻求将之付诸实现。于是,《包法利夫人》再次揶揄但同时加强了关于小说对女性危险影响的悠久传统。詹恩·马特洛克(Jann Matlock)最近对法国女性的阅读历史进行了深入调查。他发现:“妻子对巴尔扎克、欧仁·苏、大仲马、苏利耶(Soulié)、乔治·桑小说中的激情描写和戏剧场景上了瘾,于是欲望开始折磨她——她又反过来折磨不能满足她的那个男人。长篇小说(romanfeuilleton)让她觉得生活了无生趣,厌恶女性职责,变得不切实际。她将变成“火炉边的疯女人”,‘那种邪恶文学作品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夸张’让她冲昏了头脑。更糟糕的是,她开始按照她读的那些小说去生活。”
人们认为女性气质具有“反分化”的冲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总是把女性和现代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女人不能区分艺术和生活”,“她们混淆了美学和色情”,这些说法在日益广泛的消费文化中得到了普及,而日常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现在都已浸淫在消费文化中,并被其文本化。女性无法保持审美距离,这在她们对小说的贪婪消费中得到了体现,从而使她们对市场营销传播的虚幻承诺和迷人形象毫无招架之力。最后,她们对浪漫爱情故事的阅读偏好,使她们成为消费文化的理想对象,因为消费文化的驱动力正是源自模糊的渴望和无法满足的欲望,源自不断缩小真实愉悦和想象性愉悦之间差异的努力。
因此,尽管女人的欲望是来自情感和身体的需要,但这种欲望并没有被看作社会规范之外真实的力比多欲望空间。相反,她们缺乏距离感和自律性,这只会让她们更容易接受商品文化中流通的那些间接形象;她们的渴望是不真实的,只是对他者欲望的复制。现代消费的经济逻辑鼓励人们将情感和情色投入商品中,以加强商品的救赎力量,而小说中大量复制的浪漫爱情意象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那种光鲜的富贵生活的诱惑力。所以,浪漫爱情与金钱、感情与经济看上去似乎截然不同,但在女性想象中它们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福楼拜这样描述他的女主人公:“她被欲望冲昏了头脑,误以为感官的奢侈享受就是心灵的真正快乐,举止的高雅就是感情的细腻。”《包法利夫人》暗示的是,女人读书的情景——这原本是女人私密自我的一般再现——实际上却象征着现代性中欲望主体性的社会生产。这种归因于女人身上的浪漫化的感伤欲望,并不是历史上过时的情感结构的残余,而是现代消费文化运作中的关键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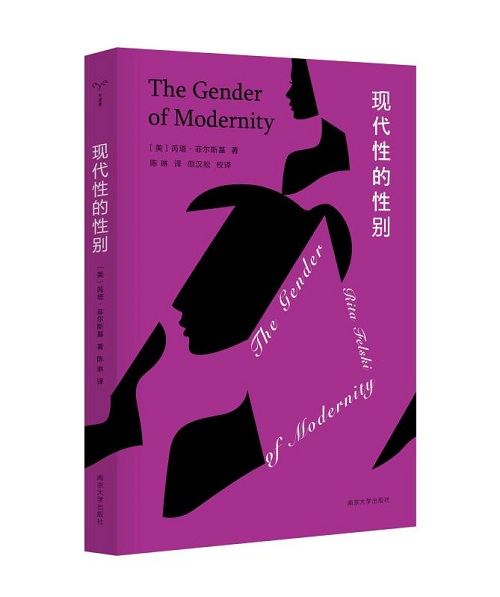
《现代性的性别》,[美]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著,陈琳译,但汉松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