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佛大学社百年史看大学出版的道路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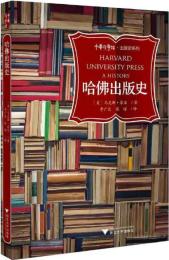
母体大学:相向合力的“父子关系”
在1913年前筹建哈佛大学出版社时,当时的洛威尔校长就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出版学者作品的大学出版社,一所伟大的学校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哈佛大学对出版社的定位是“出版学者作品,传播大学思想”。纵观全书,无论是出版社的选题方向、作者选择,还是管理人选、资金支持、办社条件,都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尽管在哈佛大学社的发展中,经常遇到因财务亏损、库存积压等问题,或因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机,而使学校对出版社曾产生嫌隙甚至是想放弃。但一路走来,出版社还是离不开母体学校的重视和财务的支持,离不开受哈佛精神感召下校友的关心和支持。正是哈佛大学的光环成就了哈佛出版社的声望。
从1947年起担任哈佛出版社社长达20年之久的威尔逊曾提出,大学出版社应是大学的事业,其首要职责是服务于母体大学。哈佛大学出版社通过自己的学术出版,极大地提升了哈佛大学的学术影响力,也推动哈佛大学的学科建设。如1940年代出版的费正清和赖世和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丛书”,推动了哈佛文理学院战后四大外国研究中心的建立。这正是大学与出版社水乳交融,相互促进的生动写照。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这种“父子关系”,决定了出版社没有理由不加强与学校的依托关系。
学术出版:大学出版的“出版自信”
哈佛大学在1913~1914年目录中是这样描述成立出版社这件事:“哈佛大学出版社首先是为了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而创立的。它旨在通过广泛发行全世界最重要学者作品来推动知识进步。它还通过印刷大量系列出版物来帮助及时传播原创的研究成果。但是,它并没有计划与商业出版社竞争,因为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出版发行有利可图的书籍。”
《哈佛出版史》最有说服力的,是从一位亲历者眼中,告诉我们哈佛出版人在征途上所遇到的坎坷。本书介绍哈佛出版社前三任社长时,指出“他们三位的任期非常相似,但每一任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生机勃勃,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感觉;第二部分则是机构遭遇外力的打击,也暴露了内在的缺陷。在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社财务问题恶化,大学当局转而开始敌视出版社”。
在困难面前,哈佛出版社人首先是坚定信念。第三任社长马龙对他的使命的本质非常清楚,他坚持“学术出版社在选择选题时应该更加严格,不仅要出于财务考虑,而且要出于学术理由”。其次,他鼓励出版“解读学术并向更广泛的读者展示学术成果的书,不管这些书是大是小”,就是让哈佛的出版物拥有更多的读者。第三,马龙把哈佛大学出版社视为一个知识和教育机构,而把印刷厂定位为服务机构。他开始对印刷厂这个令他一直头疼,并因为它使学校各院系对出版社产生敌意的机构进行改革。第四就是大刀阔斧地改组理事会和引进优秀的编辑人才。
最为突出的是哈佛出版社坚持质量第一、品牌至上的学术出版价值,坚持走出校园,广纳一流学者,不向作者个人寻求资助。他们坚信,“以尽可能多地出版好的学术著作为存在目的的大学出版社是不会破产的”。历史也证明他们执着追梦的价值。这种执着的精神令人钦佩。
盈利抉择:品牌换取生存空间
哈佛出版社是典型的“小而优,小而精”的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前60年,总出书数仅有约4800种。即使在鼎盛的1971年,职工人数为140名,当年出版新书数是163种。这样的出书规模确实属于小型出版社。在《哈佛出版史》中,有一句话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在商业出版社,一本书的成败一般在第一年就显而易见了。当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学术畅销书时,成效可能会通过几十年内小幅增长的累积而显现,以此证明其持久的价值。”
哈佛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具有全球性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不胜枚举,如“美国外交政策丛书”“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亚当斯档案”等等。但学术著作“叫好不叫座”的现象确是不争的事实。经典之作《存在巨链》《经理人的职能》,出版于1938年,到了46年之后的1984年,销量超过10万册。这虽然已经是了不起的了,但只要稍了解出版社的生存规律,以这样的出书数量和销售数量,出版社的亏损是很自然的。面对亏损的哈佛出版社呼吁“不要简单地将哈佛大学出版社视为商业实体”,校长也只是说了一句:“如果大学财力紧张到一定程度,出版社的亏损必将伤及学校的其他教育项目。”
财务上经常出现的窘境,令出版社的掌门人愤愤不平。第三任社长马龙在辞职函中写道:“评估我的工作的主要标准与适用大学学术部门的截然不同。处于这样一个位置,我无法高兴,因为我无意领导一个近似商业机构的组织。但我相信,在过去的七年里,出版社的学术和文化水准明显提升了,出版社对学术事业服务更有效了,哈佛大学出版社无愧于哈佛大学的声誉。”第六任的卡罗尔社长的观点是:“出版人的作用是保护和发展文化,投入的精力和才能无法完全转化为重复性的流程。这种运作不能被一般的成本会计所接受,知识的维度无法转换成财务报表的一行。”
为了解决经费上的困难,哈佛出版社曾接受了几笔作者的出版资助。如艾米·凯利的书稿《阿基坦的埃莉诺和四个国王》。哈佛出版社在1948年收到书稿时并不感兴趣,但作者拿出2500美元的现金资助,使得本书得以出版,并成为畅销书。哈佛出版社管理者对这种作者个人资助的行为极为反对,最终的结论认为“这是很坏的东西,危险的东西”。但资助仍为一种正当的经济来源,资助者主要是一些团体。
争议印刷厂:与“功臣”的悲欢离合
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13年,但他却希望说自己已有300年的历史。那是因为早在1640年哈佛就拥有并运行着英属北美殖民地第一台印刷机。到了1802年,这家印刷厂还以“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名义开展业务。哈佛大学在考虑建立出版社时,对比当时纷纷成立出版社的大学,令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拥有“能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相媲美的印刷厂,认为这是哈佛的机会”。可以说哈佛的印刷厂对哈佛出版社的建立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1913年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应是1872年诞生的哈佛印刷所的延伸之物,就像书中所说:“发生在1913年的事件更像是点燃了一盏煤气灯,而不是擦亮一根火柴。”事实上,在1920年代,“是印刷所的收入让出版社存活下来”。
印刷与出版的概念至今仍在许多民众心中存在着混淆。这说明印刷与出版是密不可分的两个行业。本书详尽介绍哈佛印刷厂从被学校引为自豪到产生敌意、最终离去的过程,彰显出时代发展的必然。
本书在介绍印刷厂的兴衰过程中,留下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如早期哈佛印刷厂在制作图书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形成了“印刷不仅是一种生意,更是一种艺术”的管理理念。哈佛印刷厂印制的图书在1920年代被评为“国内印制和设计界首屈一指”。哈佛出版社1922年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对学术界以外产生深刻影响的图书中,就有关于排版艺术的重量级作品《印刷字体:历史、形式与使用》,50多年一直在重印,被称为“印刷人的圣经”。而哈佛出版社当年用印刷字体和铅板制作的许多平面设计,其风格古朴典雅,已成为哈佛版图书封面厚重的历史符号并得以延续。
更为生动的故事是,哈佛印刷厂的校对员为出版社的图书质量提升起到重要的作用,“图书印刷厂的校对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所做的远不止是改正印刷工的排字错误。他们都对写作本身更为关注,也会向作者提出更多的问题。学术‘校对员’有时有很高的声誉。”“在19世纪,校对与润色作者的文字都是印刷者的技能,他们有详尽的体例手册作为指导。”到了20世纪,书稿的编辑工作大多从印刷厂转到出版办公室,但哈佛出版社还坚持设立专门的校对室。这也成为印刷厂留给出版社的贡献。
编辑素养:作品的幕后艺术
编辑的专业素养和学术功底是实现出版社目标的保障。哈佛出版社的编辑追求“把好书做得更好”,坚持高标准,对重要作者也不惧怕。编辑需要经常参加学术讲座活动,从中获取选题的信息。编辑对于书稿是否出版只有建议权,最终的决定交由理事会决定。但在决定出版之后,他们对书稿要承担比一般商业出版社更多的责任,“他们直接与作者打交道,并掌控从书稿接受到成书送达之间的书稿所经历的所有阶段”。“编辑是一门艺术,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要充足的同理心。通过同理心,编辑才能够理解作者想说什么,并充分把握作者风格特质的精髓。对图书未来读者的同理心更为重要,因为编辑必须具备通过读者的眼睛来看事物的能力。”“优秀的书稿编辑不易觅得,也不易培训。他们究竟在编辑过程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应该花多长时间,这些都是颇有争议而又神秘的问题,有时会让作者甚至是出版人感到不解。”我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编辑的学术功底、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交往能力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作者对出版社编辑是怎么看的,这其实也是我在工作中十分感兴趣的事。基辛格在《论中国》的序言中评价出版社编辑的一段话,我觉得基本可以代表作者期望与编辑达成关系的概括。他说:“与出版社合作是一段令人愉快的经历。编辑随叫随到,眼光独到,从不添乱,让人乐于与之相处。他们有熟练编辑加工,细致高效的文字校对能力,虽然年轻,但丝毫不畏惧我这个作者,还毫无保留地对我的政治观点发表看法。我甚至有些盼望看到页边空白处编辑的一贯锐利,偶尔甚至是尖刻的评论。他们孜孜不倦,感觉敏锐,给我帮了大忙。”
哈佛出版社的许多编辑故事,读后觉得很有收获。如他们很早就提出组稿对象不止于本校教师著作,要走出“象牙塔”,把目光投向其他著名的学者。为了用心努力提升形象,他们在1948年起在哈佛广场开了一间展示厅,展示自己的学术出版物;1959年起,出版社开始了每年宴请记者的惯例,以结交广大学者和记者;1965年开始发行月度通讯《博览群书》,宣传自己的新书,获得很多读者的关注。1960年代,面对书稿越来越多的情况,编辑部的职能进行重构,出现了“组稿编辑和书稿编辑”。
哈佛大学出版社并没有关于出版教材的明确策略。1950年,经过投票决议,哈佛大学出版社不成立教材部门,一般不考虑出版用于大中小学课程的教材,不进入竞争激烈、使用量大、利润丰厚的来源于二手材料的教材市场;但不排除可以出版商业出版公司不会出版的,但被学院或大学采用作为深入讲授的文本的教材或图书。这些故事都体现了哈佛出版社对学术出版心无旁骛的专注。
对比哈佛出版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与哈佛出版社基本是一致的,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大学出版社在母体大学中的地位、功能和评价方面,中国大学出版社常觉得自己是“又要打鸣又要下蛋的‘神鸡’”而倍感委屈,而哈佛出版人也感叹:“出版社是大学不太明确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尤其是经过转企改制后的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坚持学术出版和保证盈利能力,在适度多元化发展问题上,经常会顾此失彼。大学出版社究竟是“非营利性学术组织”,还是在市场中拼杀的企业,至今仍是常谈常新的话题。
2005年,我随中国大学出版社访问美国,实际了解到美国大学出版社普遍对学术出版保持着执着的坚守,其严谨的学术出版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但其经营活动也都遇到困难,尤其是信息时代纸质图书销售量的下降,更加剧了他们的困境。相反,他们对中国大学出版社的管理者在学术理想和财务困扰问题上“长袖善舞”的经营活力感到钦佩。我们或许可以掩卷沉思,在大学出版社追逐学术出版的目标上,在壮大自身经济实力方面,我们也有“中国特色”和“道路自信”的成功实践,这些值得我们去研究。
出版优秀学术著作的使命,这是所有大学出版人追求的梦想。但现实的人间烟火,使我们不可能成为超越时代的“神仙”。那些生存的窘境,在商言商的现实,都在撩动我们的事业基石,但也在呼唤我们寻找那座灯塔。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他山之石,可以坚定我们的信念,可以成为我们走出困境的参照。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出版社原社长)
本文为中华读书报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留言。欢迎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原标题:《从哈佛大学社百年史看大学出版的道路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