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厂”到我的杂志: 三线建设与我
文|翟 宇
十多年前进入一个科研机构工作之时,我从未想过三线建设与我的工作会出现交集。我当时以为,三线建设与我的关系只会永远地定格在生活层面,那是因为我在那个所有三线建设参与者和子弟骄傲也罢伤感也罢口中时不时脱出的“我们厂”完整生活了整整18年,这个来自山东的山东第四砂轮厂,迁到贵州清镇(清镇过去属于安顺,后来划归贵阳) 来的尽管那些个“我们厂”有大有小,现如今有的早已衰败甚至消失,而有的通过转型也罢扶持也好还在坚持或者已经重获新生。

笔者和父母在“我们厂”的办公大楼前(1984年2月)
“我们厂”这个居住地的定位很好地标识出了生活在三线企业中的人们对自己所来何处的统一困惑,这种困惑随着走出那个小社会之后随之而来的社会交往场景的变化而越发显示出尴尬。尽管这些年来经由学术研究的扩展以及影视作品的制作和传播,知晓三线建设的民众越来越多,但是在一般社会语境中,三线的身份仍是“妾身未明”。即使到了今天,三线建设之“三线”毕竟只是很小众的指涉,你如果冷不丁问如今生活在大城市的旁人你知道三线吗,他或者她的回答很可能是我就是来自三线啊,一个小城市。但是,于我,或者如同一位和我有着同样成长经历的写作者所定义的“最后的三线子弟”来说,三线,不是一座城市,不是故乡,它是我们的过往,它是我们厂。

“我们厂”幼儿园毕业演节目
右边是笔者,左边是孩子的父母来自上海,中间孩子的父母来自贵州。
笔者的父母是山东人(1988年夏)
对于绝大多数三线企业的相关者来说,“我们厂”不在城市,却有着城里人或者一个时期内比城里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更好的生活处境。拿我个人生活的那个厂来说,它曾经是所在省第一家上市企业,所在省多年排名第一的创汇大户,1980年代中期就普及了管道煤气, 1980年代末新建的单元楼就集体装配了抽水马桶。不仅如此,在那个获取外部资讯手段有限的时代,在那个全国能收看卫星电视的人只能看8个频道的时代,我们厂就可以看40个左右的频道了,这对于处于生活环境比较封闭的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那些频道成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窗口,让我们知晓了厂外、省外甚至域外的种种,也正是基于那些窗口在我少年时代传达的信息,我养成了对很多特定对象关注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有着城市人的生活水平,却生活在被农村包围的环境中,是大多数三线企业的真实写照。悲哀的是,从小生活在农村周围的我们,除了小时候顽劣地去农人田中乱踩乱拔之外,对农村生活是所知甚少的,虽说到不了五谷不分的地步,但是基本的农作物是不认识的。这一点后来在和农村出身的同事一起下乡调研时遭到他们的讪笑让我印象更加深刻。
这种城市农村之外的第三种存在和三线这个名称真是相得益彰,当这种第三种存在的特殊勾连起那些三线内迁职工及其子女的生活境遇的时候,特殊不再仅仅是特殊,还动辄散发出一种尴尬的味道。确立恋爱关系时间不长的男女,不仅对对方的缺点比较宽容,恐怕也会经常配合一下对方的喜好。但,即使是这样,十多年前我在看以三线建设为背景也是由曾为三线子弟的王小帅导演的电影《青红》的时候,女友在陪了20分钟之后还是委婉地告诉我她困了,要知道,那个时候,她已经培养了一定的观影爱好。她无法理解我特殊的成长背景也就难以产生共情,而那些交往层次浅显许多的同学们就更不容易理解了。
同样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到现在一直相当敬重的一位老师开了一门地方史课,有一节课是自由讨论,老师让按照五湖四海原则一样的原则选择而来的各地学生讲一下各自家乡的风俗。老师一宣布题目,我手心就开始冒汗。当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意气风发自豪无比地讲述各自家乡的各异风俗时,我一直在思忖我能讲出什么风俗。我所成长的地方,年三十不吃饺子,当地人在没钱的时候穷守岁,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之后就开始通宵麻将,所以,大年初一也是不拜年的。而我们家呢,饺子是要吃的,但是不是和大多数北方同胞们一样地“交子”,而是在初一一早吃。这算哪门子风俗呢?正当我搜肠刮肚之时,老师点我名了,我只好战战兢兢走上讲台,东拉西扯了一阵南北方习俗在我所成长的那个特殊存在的融合之后以一句我本以为我是山东大汉,但几次回到父母家乡之后才发现山东的大葱都比我高之后而草草收场,没想到的是,这之后迎来的却是老师赞许的目光。大概,老师觉得,这个不怎么能在课堂上看到的同学确实展现了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过往经历。老师那个时候年近五十,以她的阅历都对我这种过往没有太多概念,更别说因为我来自南方但是普通话比较标准,和家中电话一会儿北方话一会儿又用他们听不懂的所谓南方话而给那些同学们带来的困惑了。也许,正是因为我的存在,他们知道了三线这个词。
身份认同的纠结是那些内迁职工后代身上的鲜明印记,前些年,一个三线子弟在一篇让我产生了强烈共鸣的文字中道出了我和他这样的三线子弟那注定缠绕一生的困惑和尴尬,他的描述让我感同身受也身临其境。外地求学某次火车旅行中,他遇到了一个女孩。俩人一聊之后才知道是山东老乡,细聊之后,得知居然是同一个县的之后的他俩聊性更浓了。这个时候,女孩开始介绍自己就读于那个县某个具体中学的经历,并问这个男生在县里面哪个中学上的学。尴尬的时刻来临了,男生在费劲地解释了自己籍贯在山东,但是父母早年到了他地的企业而他仍然觉得自己是山东人之后,女孩的眼神开始出现变化,一副那你还算什么老乡的神情。最终,这一场以认老乡开始的搭讪戛然而止,男生的身份认同回归彻底失败。
之所以触动我,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出现了好几次。离开了生长的地方去到不是籍贯所在地的他方求学,类似你是哪里人的问话经常出现,尤其是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初识的时候。当我看到其他同学快速而肯定地给出答案的时候,我通常迷茫,迷茫之后,我会和那个男孩一样费劲地解释,解释之后,我看到的是同学们脸上的迷茫。除了那些其父母是本地招工而进厂的子弟,大多数的三线子弟都会面临那个可能会缠绕他们很久的身份认同问题——你是哪里人?而对所有三线子弟和三线建设者来说,那种成长或者生活经历毕竟有着很大的特殊性。那种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的自成一体的环境,那种父辈在一起工作而我们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都是所谓同学的成长轨迹,那种厂子里有医院、俱乐部、医院的单位制存在,那种小时候动不动发这发那的福利供给,那种即使是本地孩子也会说流利的普通话的语言环境,恐怕都是所有相关者的共同记忆。
确实,仔细想想,过年吃饺子的时间很好地标识出注定要困扰我一生的身份认同困境。从交子时刻吃饺子的祖籍所在地来到了初一一早没有起早习惯的出生地,我们家吃饺子的时间逐渐改变,先是初一一早蒙蒙亮吃,这倒还和北方某些地方类似,到后来越来越晚以至于九十点吃。
这其中的原因,随着年夜饭和当地趋同再加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丰盛以至于交子时刻因为太饱吃不下之外,当地丰富的娱乐活动以至于影响了睡眠也是一个原因。本来我已习惯这种改变,但因为后来看到和我生活背景差不多的小伙伴们的家中依然保持着交子时刻吃饺子的风俗而有些怅然。看来,大学保安那终极性的问题肯定要缠绕一生,正因为“我从哪里来”和“我是谁”并不是不证自明和很容易脱口而出的,所以“我要去往哪里”也异常茫然。在那些善于表达或者说表达能力比较强的人那里,迷茫之后肯定是相关表达的喷薄。
王小帅就是这样的人。他接连拍了三部以三线企业为背景的影片,这正是他儿时成长的环境。尽管在《我十一》尤其是《闯入者》中,三线只是一个大的背景,相关细节展现得并不多,但是这仍然是三线建设影像化在中国最完整的呈现。除开电影,王小帅出了本自传来探寻那个困扰了他大半辈子的问题,那就是——我是谁?这本自传的名字《薄薄的故乡》(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所谓故乡的所在之于他的意义,他是山东人,他是东北人,他是上海人,他是贵阳人,他是武汉人,他是北京人……,但他最终对这些地方都没有归属感。最后,他和自己的身份纠结达成了和解,那就是他可以没有故乡,但不能没有记忆,记忆就是那精神上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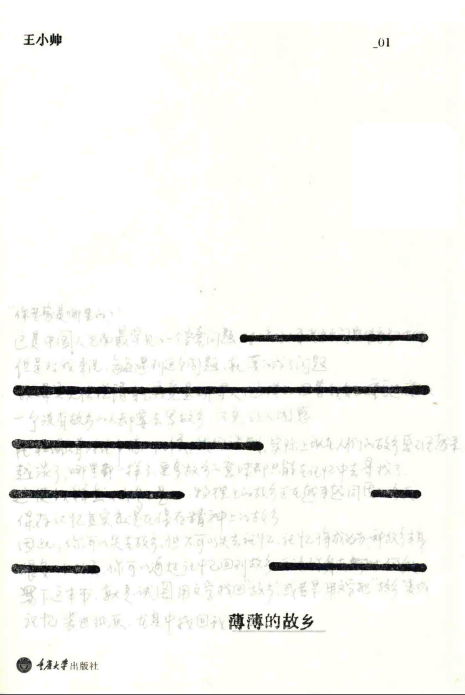
王小帅著:《薄薄的故乡》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王小帅的和解对于所有类似成长背景的三线子弟来说可能具有标杆意义。其实,早在看到他的这些文字之前,也就是我入职一个科研机构之后的几年,我也考虑过以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这种特殊的成长经历一个交代。那个时候我已经作为学术杂志编辑工作了几年,看过一些三线建设相关的学术论述,再加上院里不少青年才俊也想就三线建设的历史展开别出心裁的研究,这种种都激励着或者提醒着我,是不是也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切入三线建设,以在工作层面和自己的过往进行一种跨时空的对接?然而,这种想法一直没有实现,其原因除了自身一贯的懒惰以及想多做少的习性之外,那种曾是局内人的不安甚至不知所措也是主要因素。对于那个我生活了整整18年其后也不时回去的我们厂的所在,说实话,我没有特别地怀念,甚至多么喜欢也说不上。然而,我对这种特殊的所在确实持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去到不时“我们厂”的“他们厂”或者目睹和我小时候生活背景差不多的内迁企业的相关影像资料,我的心中总是有些波澜。这种波澜的聚焦点可以不是任何具体的厂,但肯定是那个牵动了我的父辈亲人在内几千万人命运变化的三线建设。所以,无论学术文章还是随笔文字,之所以迟迟不动笔,还是和感情投入太多,感受太复杂有关。很多事情,你了解越多,投入的精力越大,却往往会有一种无从下笔的感觉。毕竟作为一个三线子弟生活了18年,毕竟我的祖父辈、父辈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了这么一个他们最终安葬于此,生活于此的地方,这种生命的印记恐怕会镌刻一生。
好在我是一个专职的学术杂志编辑,如果暂时不能通过自己动手进行研究来给自己一个交代,那起码可以通过组织相关栏目,刊发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给自己的缺席寻找一下自我安慰。幸运的是,在我所供职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一些同事的引荐下,我得以在2015年和2016年参加了在贵州省遵义市和六盘水市举办的全国性的三线建设学术研讨会。也正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我拜会了在三线建设研究领域进行了卓越开拓工作的前辈们,比如陈东林先生、武力教授和李彩华教授。
更主要的是,这两次会议与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的结识和熟识。徐教授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都是历史学这门行当中人,我之前拜读过徐教授的一些民国史的著述和译述。但徐教授后来开始开拓小三线建设研究并已经取得相当成果的转向,我并不清楚。当我在会上看到徐教授组织完成的一系列成果之后便萌发了想做三线建设栏目的想法,徐教授不仅为我一一向前辈们约稿还介绍不少中青年才俊给我认识。
也就是从2016年开始,我所负责的《贵州社会科学》历史栏目陆续刊登三线建设研究文章。这种围绕三线建设进行整栏目组稿发出的形式,《贵州社会科学》是全国最先出版三线建设研究的两个杂志之一。这几年,在徐教授的帮助下,我陆续获邀参加了一些三线建设学术会议,与一些从事三线建设的新老朋友不断结识和熟识,已经融入了这个学术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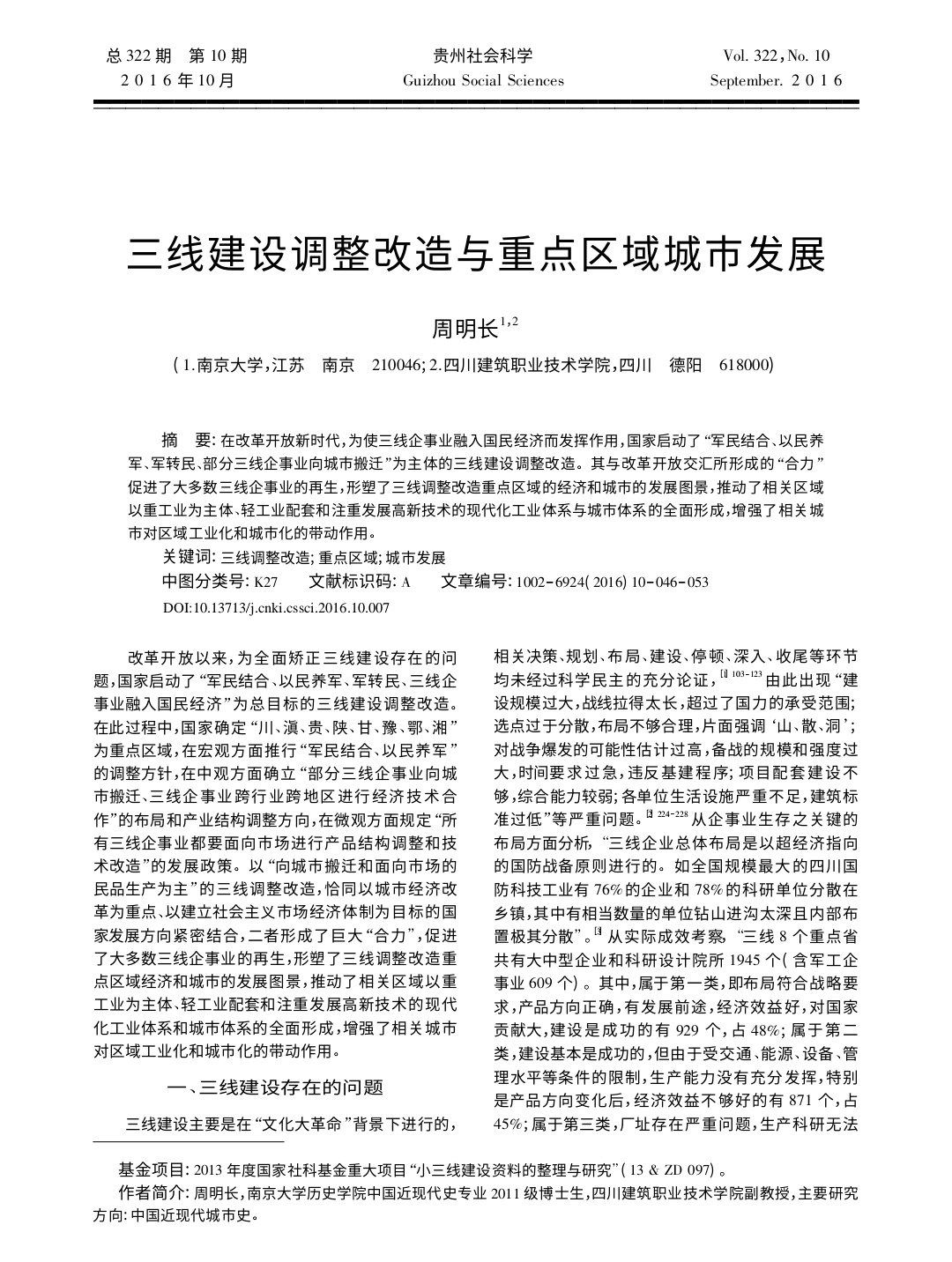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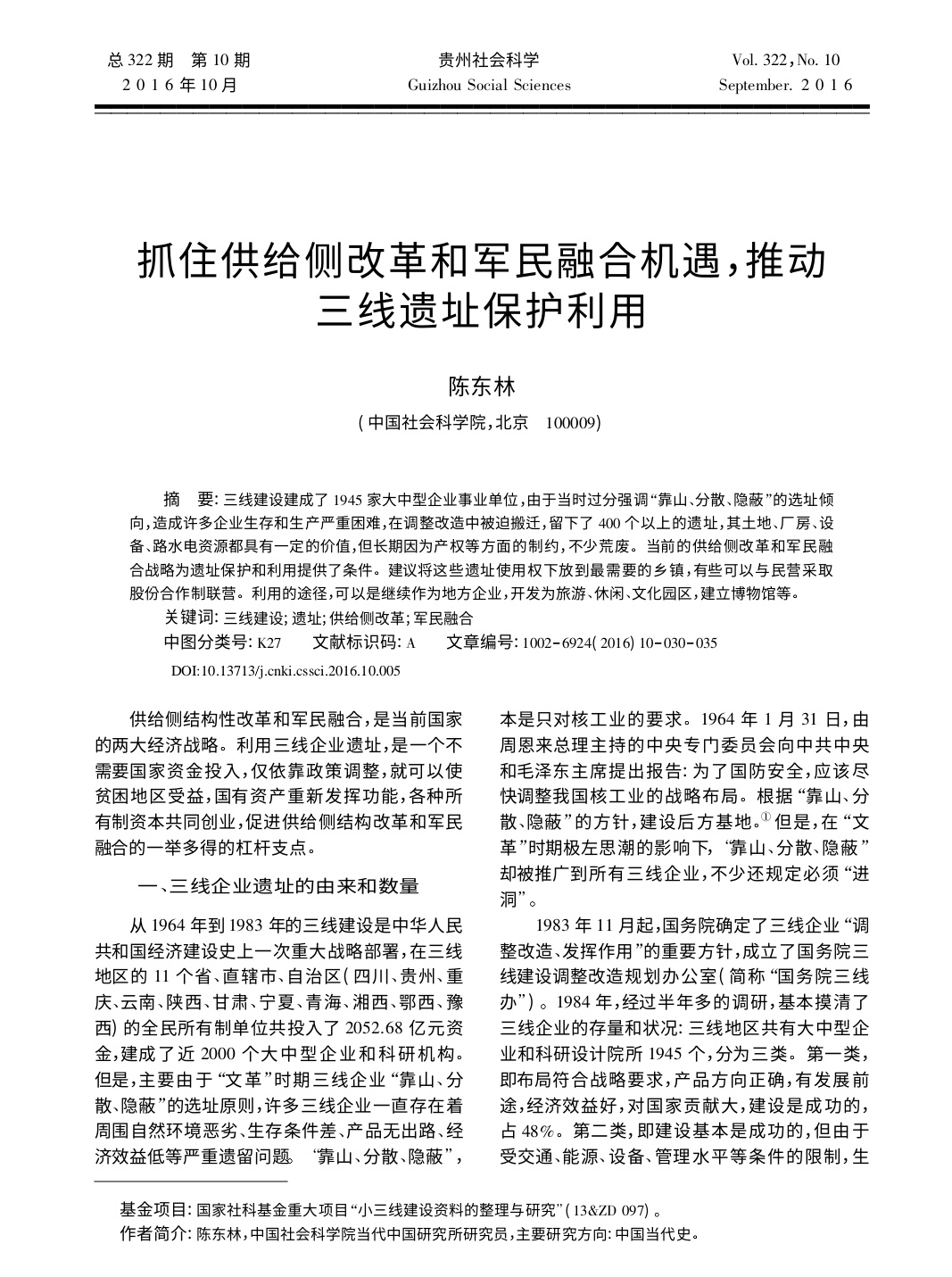
“我的杂志”( 《贵州社会科学》杂志)出版的有关三线建设研究文章。该杂志是全国最先出版三线建设研究的杂志之一。
有趣的是,这些研究者和期刊编辑中,有不少都和三线建设有过这样或者那样的生命缠绕,这让我们在学术交流的“庙堂”话语之下和之余又有了很多充满了浓浓的回忆和生活气息的“民间”交流,那种此中众人才能意会的感悟每每让我难忘和怀念。时至今日,有深度和广度的三线建设研究成果于我所在的贵州省仍然相当稀少。
我期望,随着自己年纪和阅历的增长,那种身份认同的纠缠最终能够和解,那种觉得自己深陷其中的情景意识能够慢慢淡去,最终能够以具备一定视距的“他者”身份来看待自己曾经嵌入其中的三线建设,从而在继续组织好编辑好三线建设我刊这个优质栏目的同时,能够冲破自己心中的藩篱,真正成为三线建设研究团队的一份子。
作者简介:翟宇,贵州省社科院副研究员,《贵州社会科学》历史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思想史。主要代表作:《现代理性的成长: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专著)、《东亚史》(参著)、《现代公民社会的起源》(参著)、《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参译),《苏格兰期启蒙运动的兴起》(论文)、《西方封建概念的流变》(论文)、《‘封建’概念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再认识》(论文)、《个人与国家:弗格森政治思想的一个维度》(论文)等。
本文选自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六辑):三线建设研究者自述专辑》,该书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