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被妖魔化的女权主义
原创 李银河
长期以来,女权主义在中国一直是被妖魔化的。据传,我们的一个女作家代表团在国外讲演时,每个女作家都会事先撇清:我可不是女权主义者。
我猜,其中的含义是多重的:一重是说,我的小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不是女权主义文学;另一重是说,我是贤妻良母、正常女人,不是女斗士或者女同性恋;还有一重是说,我可不恨男人,我喜欢男人。
不管是哪一重意思,背后的逻辑都是:女权主义不是好东西。

在中国的主流话语中,“权”这个字一直比较敏感,容易和闹事连在一起,无论是人权、女权还是公民权。因此,有些赞成女权主义的人把女权主义改为女性主义,使它听上去不那么敏感,不那么咄咄逼人,带上点温和的色彩。其实这是自欺欺人,因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在它的发祥地西方的话语中是同一个字:feminism。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冲突是双重的:一重是虚构的冲突;另一重是真实的冲突。
虚构的冲突指的是人们假想了女权主义的形象:它是仇恨男人的,与男人为敌的;女权主义者都是丑女,都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个个都被孤独的生活逼得变了态。这就解释了那些女作家都要拼命撇清自己的原因。
其实,女权主义中有不同的流派,有激进派,也有温和派;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前者更强调起点的公平,机会的公平;后者更强调实质的平等,配额的保障。
但是,在观点不同、主张不同的各种女权主义流派当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男女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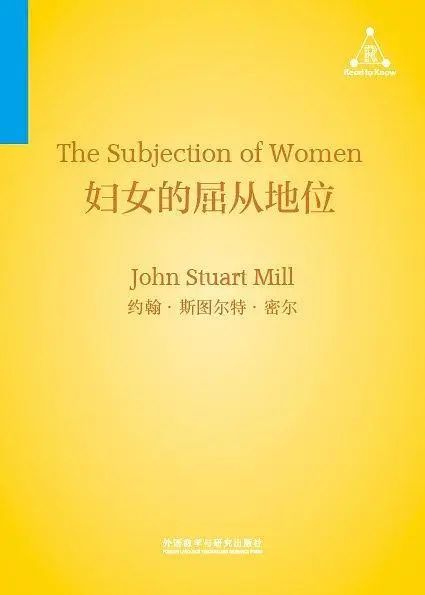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女权主义的,因为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国策;在这个意义上,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女人都是女权主义者,而且绝大多数中国男人也都是女权主义者。我们完全用不着羞于承认这一点。
从五四以来,恰恰是一批男性知识精英首先引介西方女权主义思想进中国,为女性权力代言。共产党执政后,男女平等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所以,女权主义在我国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人们对女权主义的暧昧态度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冲突。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有几千年男权制统治的历史,女权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冲突又是真实存在的。比如,仍然若隐若现的男女双重标准;比如人们对成功男人包二奶这类丑恶现象私下里的羡慕与赞许态度;再如,前几年,为了解决失业问题,有政协委员竟然提出让女人回归家庭的议案。
女人选择工作还是做专职太太是她们自己的权利,别人特别是国家无权决定让一个性别的人回家,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工作的权利,女人是公民,女人就赋有决定自己参加工作还是回归家庭的权利,谁要是剥夺了女人工作的权利,就是违宪,就是违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这样初级的错误也能犯,证明男权制思想还真实地存在着,女权主义还在同我们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沙文主义发生着真实的冲突。

综上所述,在中国,我们应当郑重其事地为女权主义正名,为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正名,反对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价值观念当中的男性沙文主义,反对对女性这个性别的歧视,努力提高女性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领导班子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女性在社会生产劳动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女性平均收入水平(目前大约相当于男性平均收入水平的70%),提高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在整个社会全面实现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主张,创造一个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