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忆与舆论理解近代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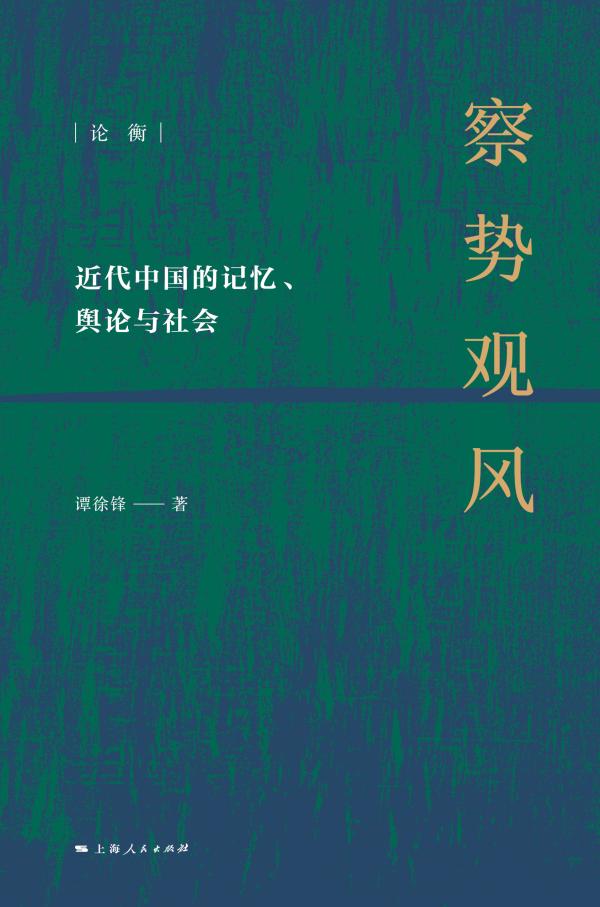
为什么是记忆?
《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就提出了记忆来源的不同与区分,后人则将其演绎为不同的世道。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此处的抉择显然有其主观的因素,为了护持他心目中的“仁”,除了所取的“二三策”,其余大量记忆被删除或减损,个体的认识或经验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说起来不可思议,作为1980年代生于四川东部(今属重庆)的人,当年我与其说先知道自己所在的故乡四川,不如说先是听《三国演义》的评书联播知道魏蜀吴、刘关张与诸葛亮,尽管是演绎,尽管距今快两千年,不过那些人物好像比周遭活生生的四川省离我更亲近一般。我想如果不是对于三国历史有特别留意,很多人哪怕是历史学者可能也很难把自己认知的(演绎的)“三国”与真实的三国史作一个清楚的区分。这里面存在不少无法一是一、二是二的界定,人人都有一个“三国”,但谁是真的“三国”,相对而言却并不那么重要,对于人们而言,那些留存于脑海中的“三国”记忆或许更为要紧,因为更有温度,也时常活化为生活中的知识与力量。这些习焉而不察的记忆无形中改变或形塑了我们的心灵。
所有的历史遗存都源于记忆与遗忘的缠斗,这里面不断复活与竞争的与其说是文本,不如说是个体的心性与情绪。前几年,坊间突然出现一股民国热,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降温,不过众所艳称的“民国范儿”却相当可议,当然,这些“热”风中是否“此中有真意”,只能说“欲辨已忘言”。回到个体,就我祖辈在四川垫江(今属重庆)的记忆而言,可能只是一种痛苦之“范儿”。
我爷爷生前,曾提到我姑奶奶幼时经常在茂密如苞谷林(四川称玉米为苞谷)的罂粟丛里捉迷藏,可见当时鸦片种植之盛,而鸦片危害之大也可以想见。证以那一时期的报纸,种植、贩卖、吸食鸦片都会被课以重税,更有甚者,不抽不种也可能要交税,烟毒之烈,危害之深,令人发指。
我外公十来岁时,家中惨遭棒老二(即一般意义上的土匪,不过四川的土匪有很多种,如教匪、刀儿匠,甚至还有红灯教)杀人灭口,当时其父母被害,家中稻谷被一抢而空,而姐姐则带着妹妹、弟弟躲在后面山坡于凄凄惶惶中熬过了一夜,他自己则因在县城上私塾而躲过这一浩劫,后来一个人将弟弟妹妹抚育成人。殊不知,我老家就在川东,离当时1945年前后的战时首都重庆直线距离一百二十公里,脚夫两天可以步行抵达。如此近的距离,却有如此惨烈的景象,所谓“民国范儿”,绝对没有不少人所谓的那么愉快。
同样是遇到抢劫,四川嘉定的郭沫若幼年则幸运得多,他家从事长途贩货,难免遇到麻烦,不过当地土匪讲究信义,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抢熟人和近邻,只抢大户,得知是误会后不仅所抢货物原样送回,还附上一张字条:
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
同样是土匪劫掠,遭遇却有天壤之别。
对于外公这一小家而言,大时代中不起眼的个体记忆,其实远远没有因为历史事实的远去而烟消云散,尤其是老人的性格就为此变得格外沉稳甚至沉闷、严肃,而且某种程度上,这一性格也形塑了一个家族。
这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家族记忆也是近代中国记忆的一部分,看似小恩小怨,却对于个体影响至深。作为个体,又深知要挣脱这一潜在的影响是何等艰难。
对于个体而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说法,正提示某种创伤记忆的长远影响,这些看似缥缈的时代灰尘,很可能会如影随形地伴随某个人相当久长的岁月,那种恐惧与担忧无法言说,却又无处不在,亲历者时常试图自我催眠与遗忘,却效果不佳。经历了成都高师风潮之后,女主角刘舫变得神经衰弱,甚至影响到整个身心,这些不那么显见却让人揪心的痕迹,有意无意间被历史一带而过。
所有历史都是记忆,都是各种记忆的折叠与改写,有意无意的,这其中既有作者的心血,也有各色人等的情绪,还有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权力,看似冷冰冰的各种历史文本,无疑可以通过记忆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由此可以发掘出历史研究的新机。历史研究无异于在虚虚实实的记忆之间舞蹈,将记忆的各种形状与被施与的手法和盘托出。
说来有趣,去年在山东曲阜开会,偶遇某老师,因为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上过他不少课,一直执弟子礼,所以很是熟悉,他命我陪着去孔林一趟。在这个千年同封的地方,谈学林往事与近事,深切感受到人们以立碑修墓来表达记忆的隆重与谨慎,同时也察觉这里面其实有着无数层累的记忆,而且进一步辐射到整个曲阜、山东乃至中原,如果不仅仅执著于文本,或许还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深入。当然也有堪入笑林者,一着深蓝色中山装的老伯,指着漫山遍野的墓碑,问我们“这伙计生前做多大的生意,怎么有这么多的家业”。老伯大清早在这么有名的地方游览,却并不知晓这座庞大陵墓的主人姓甚名谁,似乎提示我们局中人似乎也不见得就知道当时的所谓历史真相,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或许只是到此一游,有些真相有时只是局外人的“看山是山”。
“国家不幸诗家幸”,“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类似诗文很多都叙说了记忆形成的前因后果,治世、衰世与乱世的记忆相当不同,衰世、乱世因其个体遭遇的痛苦可能比承平时代繁剧很多,所以记忆也格外丰富,尽管对于个体而言,也有不少人觉得“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近代中国对于曾经盛极一时的清朝或人们所艳称的汉唐盛世而言,无疑是衰世,而面临列强紧逼与各种派系割据纷争,又无疑是乱世,注定了这是一个记忆的巨大场域,蕴含着深广的记忆星火。
记忆的研究在中国学界方兴未艾,在我看来,记忆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的通史,作为视角其实更有生命力,可以切入已往历史研究的骨骼与动脉之间,揭示出过往最为柔软的部分。本书的写作,就是试图以几个侧面,试着从史实重建与方法探索两个层面作一些摸索。其中较为注意不同文本、场合的比较,留意本相、异相之间的差异与竞争,期待能呈现历史的复杂性。
记忆在这里更多是一种视角,所关照的对象既有风潮,又有阅读史、个体记忆与文化实践,其中各种文本、记忆之间的互动与角力,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也是期待在今后延伸的课题。
舆论不仅能够影响社会,而且从事舆论生产者也能从中套利,因为拥有话语权,可以成为言论界的弄潮儿,在物质与名望上双丰收。有心人也会利用舆论,俗称“造舆论”,进而影响不少重大事件的进程。
在清末即开始办报的陈独秀眼中,“舆论就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他意识到舆论的威力与破坏力,显然更期待能有不为时潮所裹挟而去的勇气之人,不过他有时也会反其道而行之,如对于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且颇喜引用。
陈独秀的湖南籍追随者、新民学会会员罗璈阶(罗章龙)在给毛泽东的信里感叹,“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
毛泽东回信提出:“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舆论,士气,主义,因为唤起新势力,借着主义的结合而得以整合,而这里面隐约有着曾、左、胡等湖南先贤“以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语)的影子。 近乎同时,面对当时声势浩大的舆论,胡适在1920年9月17日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演讲《提高和普及》则有所反思:“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新名词成为了运动,也就变作一种舆论,当时的风向所在,令不少读者望风披靡。胡适告诫北大学生这种新名词运动“外面干的人很多”,他希望北大人能够放弃这种俗务,去做更多建设性的工作。事实上,近代报刊在中国兴起之后,借着这些活学活用的新名词办报写文演说,进而求得在物质上、精神上的满足,已成为知识人重要的选择项。
善用舆论者,也可以成就政治,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正拟投身政界的蒋廷黻注意到“中国近年舆论的势力确有长进,尤其关于外交”,以为,“有作为的总统和总理是舆论界之王,惟独庸碌无能的才是舆论界之仆。……无论政体是怎样,政治理论是怎样,只要人继续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政治家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舆论的制造。定了一个大政——假使我们说这大政完全是对的——而不能得舆论的拥护就是政治家的失败。”
除了觇国者,足不出四川的近代大儒刘咸炘以为,“疏通知远,即察势观风也。孟子之论世,太史之通古今之变,即此道也……事势与风气相为表里,事势显而风气隐,故察势易而观风难。常人所谓风俗,专指闾巷日用习惯之事,与学术政治并立,不知一切皆有风气”,在他眼中,风无所不在,有大小之别,小者装饰之变,大者治术缓急与士气刚柔。
刘氏以其通人眼光,更强调变化、综合与关联,“史以综合为事。横之综合为关系,《易》之所谓感也;纵之综合为变迁,《易》之所谓时也。宇宙无时不动,动则变化,事必历时而后成。”“史之所以无不包,以宇宙之事,罔不相为关系,而不可离析。《易》之所谓感也。史固以人事为中心,然人生宇宙间,与万物互相感应,人以心应万物,万物亦感其心。人与人之离合,事与事之交互,尤为显著,佛氏说宇宙如网,诚确譬也。……综合者,史学之原理也。……综合关系,即是史识,观察风势,由此而生。专门之书,止事实而已,不能明大风势也。综贯成体,是为撰述。……西人近世始知史广,于是力矫前史专记政治,偏详伟人之非,而注重社会文化。”“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先入而后出,由考据而生识也。”刘氏以专门分类与专门之书“不能尽万端之虚风”,对中国古代“良史综贯之妙”再三致意,有一种包罗万象、力求综合的企图,在网状的综贯之中,试图捕捉到风势的交互,以“明大风势”。
傅斯年则在其未完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从文学作品着眼,认定断没有脱离了时代的文学还能站得住,“所以文学不能离其他事物,独立研究,文学史上的事件,不能离其他事件,单独推想而得。‘灵魂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之全即是灵魂。’文辞中的情感,仿佛像大海上层的波花,无论他平如镜子时,或者高涛巨浪时,都有下层的深海在流动,上面的风云又造成这些色相,我们必须超过于文学之外,才可以认识到文学之中”,强调“文情流变,与时代推移,是我们了解文学与欣赏文学中之要事”。
傅氏的论述让人想起了英国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雷蒙德·威廉斯提出,“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时候,最难以把握的,就是这种对于某个特定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性质的感觉,正是凭借这样的感觉方式,各种特殊的活动才能和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结成一体”,他特意拈出“结成一体”,甚至认为由此可以找回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性格”或本尼迪克特看重的“文化模式”。
在他眼里,“感觉结构的拥有的确到了非常广泛而又深入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沟通和传播靠的就是它”,而且并非通过正规的学习而得,“但新的一代人将会有他们自己的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看起来不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在这里,最明显不过的是,变化中的组织就好比是一个有机体: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他们所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在很多方面又保持了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可以往前追溯),同时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这可以分开来描述),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看起来不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无疑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流风,在近代中国,趋新者正是汲引中西之间的资源,形塑了某种感觉结构,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更迭。
舆论宛若这样一种如网宇宙,以其多样的风云,与时代推移,形成空气与氛围,无形中构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本书则尝试介入时人的生活世界,除了精英的言论,更关注一般人的喜怒哀乐,期待由此可以察势观风。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风与水一样,可以无孔不入,套用傅斯年的话,“风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之全即是风”,这里面不断吹拂的与其说是风,不如说是世运、人心与气象。
“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本书试图追索的个体生命、记忆片段与思想竞逐,无疑都是近代中国的流风余韵,中间更多是激烈的一面,因为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一波一波历史巨浪的卷席之下,壮怀激烈,屡败屡战,摇曳不定的潮与流值得重访与细分,而此前则对于这些面相的讨论过于趋实,而较少注重那些在一切事物中的灵魂,殊不知过于僵硬的外表下面,往往有着曲曲折折的灵魂,只有人“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借用徐志摩语),如果对此不能另辟蹊径,重拾对于“人事”之重视,发潜德之幽光,当然也就无法深入理解孕育这些灵魂的社会。
本文为作者新书《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版)的自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