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师致敬:梵高丨我们穿越大地,只为经历生活
如果有什么画家称得上是“人人皆晓”,那么文森特·梵高必然是当之无愧。

在短暂的37年的生命里,他经历了生活的拮据、疾病的困扰、作品不被认可的痛苦、与好友决裂的崩溃等各种波折······为我们留下了数量众多,主题、形式、技法多样的艺术杰作:将近九百幅油画、一千一百幅素描和十幅版画。

《向日葵》,1889年1月(阿尔勒)
然而,除了《星夜》《向日葵》这几幅常见的作品,以及他与高更相爱相杀的那段相处经历之外,我们对梵高其实知之甚少。
比如,他如何从一个传教士转变成一个艺术家;他的信仰经历了哪些转变;他对绘画进行了哪些探索,受到了哪些艺术家或艺术流派的影响;他是否真的像世人理解的那样,是天才、狂徒、病人以及必然的“悲剧主角”……
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更加真实、立体的梵高~
从传教士到艺术家
宗教在文森特·梵高的生命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他的家族自16世纪以来一直虔信荷兰加尔文宗。在一张摄于1866年的相片中,这位时年13岁的牧师后代乖巧地注视着镜头。

13岁的文森特·梵高,1866年,摄影
梵高不到20岁时就养成了写信的习惯,还在早年的书信中流露出热忱的信仰与对圣徒文字、祷文和宗教研究的热爱。
1869年7月,梵高来到海牙生活,并开始为一家国际艺术品经销商公司古皮尔公司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在1876年1月,他被古皮尔画商解雇。此后,他立志以传教为业。
他离家来到英格兰肯特郡(Kent)的拉姆斯盖特(Ramsgate)小镇,在威廉·斯托克斯(William Stokes)新办的男子寄宿学校林克菲尔德之家(Linkfield House)任教。
期间,梵高依旧热爱绘画创作。

《从拉姆斯盖特学校窗户看见的皇家路》,1876年4-5月(拉姆斯盖特)
然而,梵高头一次感到分裂和矛盾。过去,他总觉得绘画是他的爱好和消遣。如今,他却发现绘画不光能表现世界,它在他心中激起的感情,可以与祷告和冥想赋予他的力量相提并论。
梵高站在十字路口,终于决定两个都不放弃,他将从事牧师的工作,业余时间画画。

《麦比拉的洞》,1877年5月28日(阿姆斯特丹)
但梵高的传教工作并不顺利。1876年年末,梵高回到荷兰。1877年5月,梵高前往阿姆斯特丹,希望进入大学研究神学,但却没有被大学录取。
他又在布鲁塞尔周边接受了福音传教士的培训,不想再度失败,只得作为在俗的布道者向博里纳日的矿工传教。
但他在传教期间受到了新的挫折,最终对圣职工作心灰意冷,转而开启了画家生涯。

《煤厂》,1879 年7-8月(博里纳日)
去巴黎,寻找个人意义上的变革
1880年8月,梵高作出决定:当一名艺术家。但他当时尚欠火候。他清楚自己在技巧上的缺陷,因此必须首先设法完善自己的艺术素养。
在弟弟提奥的建议和支持下,梵高以非凡的激情开始接受艺术家方面的培训,并于1886年年初,前往巴黎。

《抽烟斗的自画像》,1886 年3-5月(巴黎 )
抵达巴黎不久,梵高便入读了费尔南德·柯罗蒙(Fernand Cormon)开办的私立学校(后来更名为柯罗蒙工作室)。
但梵高很快就失望了。他不太欣赏这位老师的艺术才华。1886年6月,梵高便离开了柯罗蒙工作室。此后,梵高经常参观画廊和展览,包括印象派画家的第八次联展,梵高也是在这次联展中第一次见到了高更、乔治·修拉和保罗·希涅克的作品。而高更已经是第四次参加印象派联展了。
梵高见证了法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时刻。当时,本是同根生的印象派画家之间产生了龃龉。奥古斯特·雷诺阿(Auguste Renoir)、克洛德·莫奈、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和阿尔弗雷德· 西斯莱(Alfred Sisley)抵制起了卡米耶· 毕沙罗支持的修拉和希涅克等年轻画家。
9月19日,评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Félix Fénéon)在布鲁塞尔杂志《现代艺术》(L’Art moderne)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创造了“新印象派”这一术语定位修拉等年轻画家的画风。
此时,梵高已经开始用画笔描绘巴黎风光。

《巴黎风光》,1886年6-7月(巴黎)
尽管其中一些作品乍一看像是受了克洛德·莫奈的影响,但他其实并没有加入这场印象派画家的纷争。
梵高很快就意识到,他很难把印象派画家的表达方式强加到自己的绘画中。但他还是想强迫自己接纳甚至模仿印象派画家的手法。
他画的布吕特芬磨坊(Moulin de Blute-Fin)就是明证。

《蒙马特高地的布吕特芬磨坊》 ,1886年7-9月(巴黎)
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这幅画中认出蒙马特高地的菜园。高地上耸立着的是著名的布吕特芬磨坊,又名煎饼磨坊或德布雷磨坊。不远处还能望见胡椒磨坊。
梵高在这幅作品中运用了新的技巧,让人眼前一亮。其中所体现的气氛和变化性在梵高的作品中是前所未有的。他用笔触来分解形状,这种手法让人想到了莫奈、毕沙罗和雷诺阿。
对印象派的研究使梵高对印象派画家处理颜色的方法产生了兴趣。

《花瓶与罂粟、牛眼菊和芍药》 ,1886年7-9月(巴黎)
他的收获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对用色的理解更深入了。这让他在同样的画面中表现出更丰富的色调,也让他更自由地选择色彩;第二,他学会了对补色的运用。梵高认为自己的色调过于灰暗,而补色可以帮助他用鲜艳的颜色创造强烈的反差。

《花瓶与唐菖蒲和翠菊》 ,1886年8-9月(巴黎)
梵高在巴黎度过了第一年,实现了一场个人意义上的真正的变革。在这一年里,他不得不用全新的技巧和方法考验了自己的绘画能力。
逃离巴黎,去往“能和日本媲美的法国南部”
如果说,在1886年的时候,巴黎对初来乍到的梵高象征着事业的转机,那么,不到几个月,这座城市就成了梵高心目中杀人王国的都城。它用种种幻想哄骗画家,却没有一个画商和买主为幻想买单:“巴黎真是个古怪的城市。在这里,人要拼尽全力才能生存,不累到半死就什么也干不了。”
于是,又到了离开的时候。1888年2月19日,梵高在里昂车站搭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第二天,便来到了雪中的阿尔勒。

《雪景》 ,1888年2月(阿尔勒)
他一到阿尔勒,就感觉好像到了日本。他呼吸的是“明朗的空气”,看到的是“欢快的颜色”,还发现“到处都像是色彩丰富的日本风景画和人物画”。
梵高在离开巴黎以前就开始研究日本艺术,现在他不仅继续研究,更加强了对日本艺术的思考,想像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那样到日本去。“哦,我们热爱日本绘画,也接受了它的影响——所有的印象派画家都一样——那我们不去日本吗?我的意思是能和日本媲美的法国南部。所以我相信,总之,新艺术的未来就在南部。”
《玻璃杯里的扁桃花枝和书》(Branche d’amandier fleurissant dans unverre, avec un livre)和《开花的桃树》(Pêcher en fleur)是梵高到阿尔勒之后创作的作品。

《玻璃杯里的扁桃花枝和书》,1888年2-3月(阿尔勒)

《开花的桃树》,1888年4月(阿尔勒)
对这两幅作品而言,开花既是成长也是重生。对梵高而言也是一样。他认为,只有像不断更新的大自然那样革新原有的准则,他才能真正在艺术上获得新生。
1888年5月1日,梵高决定在阿尔勒聚集起这里的画家,并成立一个艺术家的新团体,让大家关心自己的福利,免受市场的侵犯。
他还向高更和贝尔纳发出了热情的邀请:“我正在拾掇一间画室,将来可以给朋友们一起用,画家朋友过来工作也行,住在这里也行。”

《有蓝色搪瓷咖啡壶的静物画》,1888年5月(阿尔勒)
梵高与高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高更曾寄给梵高一张自画像,上面附有一幅贝尔纳的侧面像(触动了梵高的“内心最深处”)。

保罗·高更,《自画像》,别名《悲惨世界》,1888年9月
高更还鼓励梵高沿着夏天开辟的道路走下去:
您想在绘画中通过色彩引起诗意的印象。您是对的。在这方面,我和您意见一致。只有一点除外,我不了解诗意的印象,可能我缺乏这方面的认识。在我看来,一切都富有诗意,而且我是在内心深处的往往有些隐蔽的地方瞥见诗意的。形状和颜色只要安排协调,本身就会产生一种诗意。在我欣赏别人的作品时,只要其中表现出画家的才智,我就会感觉进入一个诗意的境界,甚至不需要母题来打动我。
此时这位法国画家已经产生了和梵高一同创作的想法。
他在信中指出的“一点除外”,让我们了解到两人的和而不同之处。对高更而言,“诗意”属于某种思维活动的范畴。因此,“诗意的印象”是一个赘词。更确切地说,一切都可能富有诗意,因为从理论上讲,画家的主观和感觉世界能够通过任何母题、形状或颜色表达抽象的新印象。
而梵高却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诗意”。在他看来,“诗意”属于感觉和效果,它传递了画家面对自然的感动和作品试图重建感动时产生的“似曾相识”的效果。

《“致朋友保罗”的自画像》,1888年9月(阿尔勒)
高更主张万物平等,而梵高却相信高下有别。万事万物并不全富有诗意,因为它们不都对画家产生效果,而画家也不一定能用画笔重建自己感知到的诗意。
虽然梵高和高更的想法不完全一致,但早在高更下定决心来普罗旺斯定居以前,梵高就深信邀请高更过来相聚势在必行。他自认为已经说服了高更,便去信描绘了自己正在创作的黄房子的油画,并附了一张素描。

《黄房子》,1888年9月(阿尔勒),布面油画

《黄房子》,1888年9月29日,致埃米尔·贝尔纳的信中所附
1888年9月17日,梵高搬到黄房子里住了下来。
1888年10月23日,高更终于来到阿尔勒与梵高相聚。说服高更的不是好友对乌托邦的设想,而是好友弟弟承诺的经济资助。提奥答应购买他的一部分作品,作为来普罗旺斯的回报。至于文森特·梵高,他本来就想在法国南部建立一个画家团体,正指望借此机会把他们两人的合作发展成画家团体的核心。
梵高要向高更展示自己取得的进展和正在进行的创作。因此,他邀请高更一同漫游阿尔勒的各家咖啡馆和妓院,以便夜以继日地观察研究。这位画家对普罗旺斯夜生活的探索既不是为了冶游,也不是为了观看色情表演。他向贝尔纳解释道:“我们可以去里面喝点啤酒,认识些人。我们还可以半靠想象、半靠写生作画。”
而梵高的《青楼场景》(Scène de lupanar)便是“半靠想象、半靠写生”的作品。

《青楼场景》,1888年11月(阿尔勒)
让梵高大为高兴的是,高更同意陪他在夜里四处游荡,并对他的创作构思有所回应。

《夜间咖啡馆》,1888年9月(阿尔勒)
高更将梵高的《夜间咖啡馆》和《青楼场景》进行了变体,绘制了这幅《阿尔勒夜间咖啡馆》。

保罗·高更 ,《阿尔勒夜间咖啡馆》,1888年11月(阿尔勒)
但高更有别于梵高。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让她占据了前景中的主要位置。这个人是咖啡馆的老板娘玛丽·吉努。梵高曾让她的丈夫站在《夜间咖啡馆》的画面中央。而这幅画中的玛丽·吉努则坐着面对观者,似乎和画家同桌。
梵高的作品反映了他所描绘的咖啡馆和妓院的整体氛围,同时也忠于他观察到的空间和场面。而高更的夜间咖啡馆不仅以人物为中心,也充满了暧昧。
1888年11月刚刚过半,高更在阿尔勒不过待了几个礼拜,他就向埃米尔·贝尔纳总结了自己和梵高在艺术创作上的共识和分歧:
总的来说,我和文森特很少有意见一致的时候,尤其在绘画方面。他欣赏都德、多比尼、齐埃姆(Ziem)和泰奥多尔·卢梭,但我对这些人都没有感觉。他讨厌安格尔(Ingres)、拉斐尔(Raphaël)、德加,这几个却都是我欣赏的。我不想多费口舌,就对他说,“长官您说得对”。他非常喜欢我的作品,但在我画的时候,他又总觉得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他是浪漫派的,而我更倾向于原始派那样。
梵高可能也有同感。他在描绘蒙马儒修道院附近的落日的时候,这样写道:
这是蒙蒂塞利式的浪漫,浪漫得无以复加。黄灿灿的太阳光线倾注在灌木和地面上,简直像一场黄金雨。……要是我们突然看见一群骑士和贵妇鹰猎归来,听见一个年迈的普罗旺斯游吟诗人的声音响起,我们一点也不会吃惊。

《蒙马儒附近的落日》,1888年7月(阿尔勒)
高更把绘画当做显灵,他向最内行的观者启示隐秘的奥义、形象或象征。梵高却不然。在他看来,形形色色的艺术和生活交汇于实在的空间,构成了对世界的体验。唯有实在的美才是至关重要的。
1888年12月24日早上,有人发现梵高躺在床上,整个左耳被割掉不见。他在前一天和高更发生争执,继而发作了严重的精神病,事后却忘得一干二净。
他用剃刀自残以后,去了维吉妮(Virginie)女士的窑子。他把自己割下的耳朵给了一个原名加布里埃尔(Gabrielle),化名拉歇尔(Rachel)出卖风情的年轻洗衣妇。
梵高在夜里失血极多,因此费利克斯·雷伊(FélixRey)医生要求他住进天主医院。提奥接到通知后,赶来探望了兄长。由于正值圣诞,他没有在阿尔勒多作停留。高更和他一起回的巴黎,后来再也没有来过阿尔勒(但与梵高之间并没有断绝书信来往)。
梵高受到了费利克斯·雷伊医生的悉心照料。过了十多天,1889年1月7日,他出院回家,开始了漫长的恢复期,并马上投入了工作。

《包扎着耳朵的自画像》,1889年1月(阿尔勒)

《包扎着耳朵并抽着烟斗的自画像》,1889年1月(阿尔勒)
他接连画的这两幅作品在日后都很出名,通常都被称为“割掉耳朵的”自画像,但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包扎着耳朵的”自画像。梵高想要表现的不是痛苦的场景,而是康复的场面。
1889年2月到3月末之间,梵高的疾病数度发作,而后回到了天主医院。1889 年5月8日,梵高决定离开阿尔勒,住进圣雷米的精神病院。
尽管疾病的发作不时地打断他的工作和通信,但他在此仍然创作了许多素描和油画。

《鸢尾花》,1889年5月(圣雷米)
画家在这里接触到了真正的精神病人。对梵高而言,观察他们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他几近“客观地”注视着其他病人,终于知道了自己发病时的样子。
梵高在这样的处境下继续作画既不是反抗,也不是逃避。恰恰相反且自相矛盾的是,对梵高而言,绘画似乎是通过放弃一部分自由来感受疾病的主要途径。但在艺术创作中,他却决意毫不让步。

《星夜》,1889年6月(圣雷米)
1889年9月,梵高心无旁骛地创作了另一幅作品——《黄色麦田里的收割者》。

《黄色麦田里的收割者》,1889年6-9月(圣雷米)
梵高在此重拾了双重性的主题。他笔下的收割者是刽子手、也是牺牲者;是死神、也是垂死之人。就这样,他不把自己“可悲的疾病”当作工作的拦路虎或绊脚石,却当作工作的主要动力。正是“疾病”使他“带着隐约的狂热工作”,并为他赋予了比“荒谬的宗教倾向”更实在的一种意义。
《收割者》中的死亡既没有悲歌的哀婉,也没有夕阳西下的凄凉。画家用“淹没了一切”的“太阳纯金般的光芒”象征了充实。这颗恒星不会让人想到哪个天国,它为整个画面染上了明亮欢乐的黄色,使画中的农夫兼画家融入了自己耕耘和描绘的大自然中。
你只要看过梵高在这年夏末所写的信和所画的画,就会被其中散发的快活和力量打动。

《初生的月亮下的麦田》局部,1889年7月(圣雷米)
生命的最后,瓦兹河畔欧韦时期
1890年5月20日,梵高来到了瓦兹河畔欧韦接受保罗·加歇医生的治疗。

《瓦兹河畔欧韦的阶梯》,1890年5月末(瓦兹河畔欧韦)

《保罗·加歇医生》,1890年6月(瓦兹河畔欧韦)
7月27日,梵高在一座城堡后面的田地里用左轮手枪朝自己的胸口开枪,但没有立即死亡,7月28日,梵高因伤口感染而告别人世。
但梵高的自杀,和他不断接受的牺牲一样,既不是消极的,也不代表对生命的拒绝。画家渴望掌控自己的身体和作品,却没有这样生活下去的能力。于是,他决心带着画架,来到自幼描绘的大自然中,对准自己感受自然、也希望别人感受自然的部位——心脏——开枪,然后骄傲地死去。
《梵高:化世间痛苦为激情洋溢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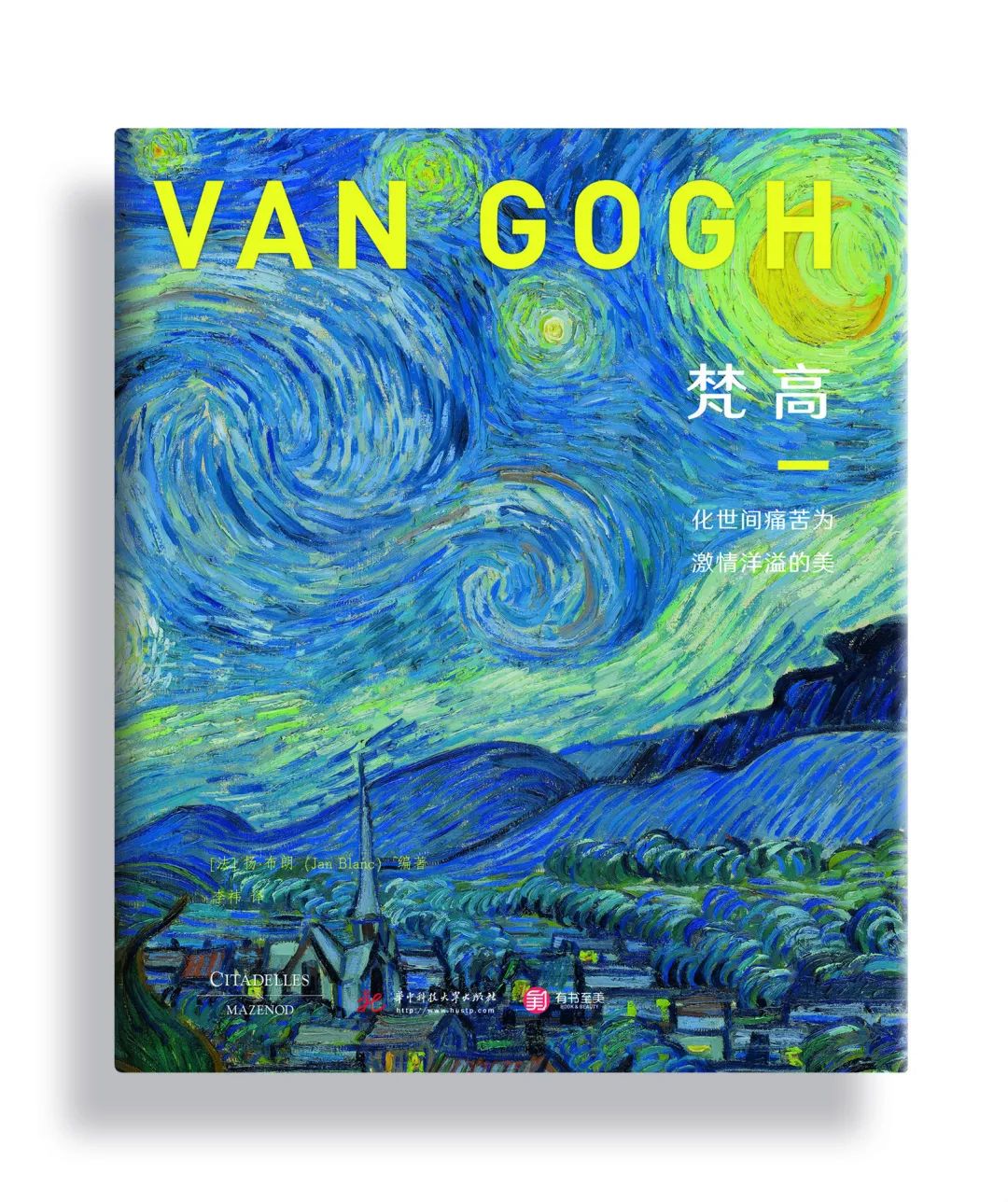
【法】扬•布朗
2018年9月
有书至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书中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梵高的十载艺术生涯,通过近300余幅具有代表性的画作,叙述和分析了梵高的艺术之路。此外,还收录了梵高大量的书信片段,这些“梵高的话”,直观透露了梵高对人生、艺术的信念及对健康、死亡的看法,读者可由此一窥梵高的精神世界。
在时间顺序的基础上,本书还从两条主线来论述梵高的信仰和艺术生涯:梵高是如何从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梵高艺术历程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受到了不同画派和画家的影响。
此外,书中还附有完整的年表和作品索引。便于研究梵高的专业人士,或对这位天才画家感兴趣的读者完整和系统地了解这位伟大画家的艺术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