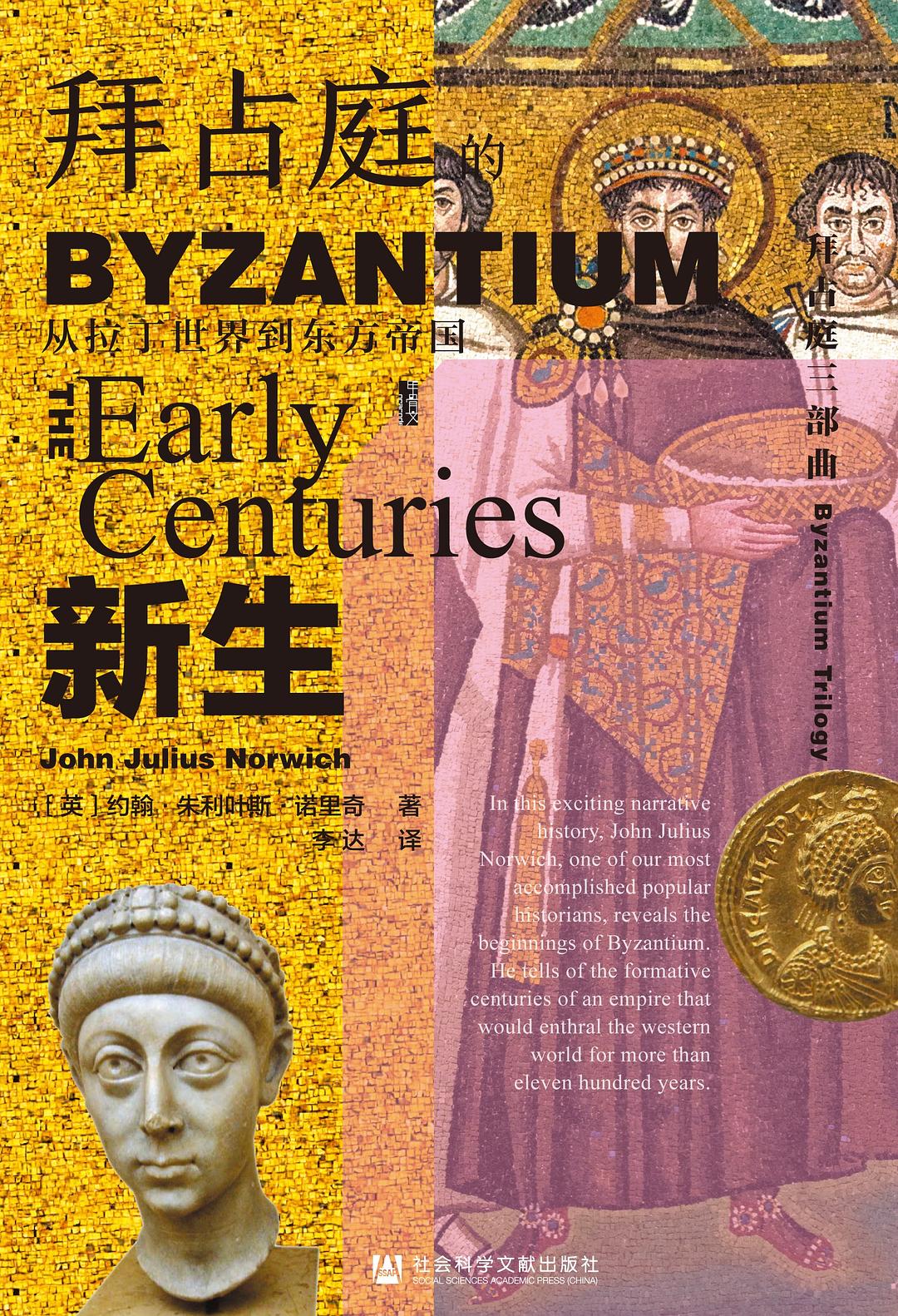神迹加持的天选之子:君士坦丁的“权力的游戏”
世人不复虔敬,国家濒于毁灭,神如何解救我们?……我就是神选的解救者……因此,从遥远的不列颠海洋,那个太阳遵循自然法则落下地平线的地方开始,我在神的帮助下清除了当时盛行的各种恶,希望世人在我的启示下能够重新遵守神的神圣律法。
——君士坦丁大帝,尤西比乌斯(Eusebius)引述,《君士坦丁传》(De Vita Constantini),Ⅱ,28。
首先,拜占庭这个词,无疑是全世界历史之中最引人遐想的地名之一。即使帝国从未存在过,即使W.B.叶芝从未赞美过,即使那里仅仅和起初一样,只是个无欲无求的、位于欧洲大陆最远端的希腊人小聚居区,拜占庭这个名字之中的韵律,也足以让它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无法忘怀,并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幻化出这个名字今天所能唤起的景象:黄金、孔雀石与斑岩,庄严肃穆的仪式,镶有红宝石和绿宝石的锦缎,大厅之上奢华的镶嵌画在熏香的氤氲中发出微光。历史学者曾经认为这座城市在公元前658年由来自希腊城市墨伽拉(Megara)的移民领袖拜扎斯(Byzas)主持建造。现在他们又认为拜扎斯从未存在过,而我们只能祈祷他们说得没错。不可思议的事往往无法解释。
然后,城市选址,同样是独一无二的。拜占庭位于亚洲的门槛上,位于一块宽阔的三角形海岬的最东端,南边是普罗彭提斯海,即今天的马尔马拉海,东北方向是约五英里长、宽阔且水深足以通航的水湾——那里在最遥远的古时就已被称为金角湾,大自然将这座城塑造为绝佳的港口,又是易守难攻的要塞,只需要在靠陆地的一侧建筑工事即可固守,事实也确实如此。即使走海路进攻也相当艰难,马尔马拉海的两端还有两个狭长的海峡防护,即东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西边的赫勒斯滂海峡(或称达达尼尔海峡)。事实上,这里的位置是如此完美,以至于让十七年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建城的卡尔西顿(Chalcedon)居民因有眼无珠而举世闻名:若不是有眼无珠,他们怎么可能错过仅仅一两英里之外、远远优于此地的定居地点呢?

最后,那个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历史上所有的“伟大”统治者——无论是亚历山大还是阿尔弗雷德,无论是查理还是叶卡捷琳娜,或者腓特烈甚至格里高利——都不及君士坦丁一世更配得上“伟大”的称号,因为在约十五年里他做出了两个决定,而其中任何一个决定都足以改变文明世界的未来。第一个决定是皈依基督教——在一代人之前基督徒依然是官方迫害的对象,对其迫害的残忍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将它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第二个决定是将帝国的都城从罗马迁到一座新城市,即他在古拜占庭城的旧址上建立的新城,而接下来的十六个世纪中,那座城市都将冠以他的名字:君士坦丁的城市,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决定及其引发的后续事件,意味着他很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人——仅次于耶稣基督、佛祖和先知穆罕默德。而我们的故事将从他这里开始。
帝国分治
尽管我们能够确定君士坦丁于2月27日出生在罗马帝国达契亚省(Dacia)的内索斯(Naissus),即今尼什(Nis),我们却不能确知具体年份——这在存世资料颇为零碎的罗马帝国晚期历史上,实在太常见了。通常认为他出生在公元274年,但也可能是一两年前或一两年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绰号为“Chlorus”,即“苍白者”,在他的儿子出生时已经是帝国最出色、最成功的将军之一,而他的母亲海伦娜出身低微。一些历史学者质疑她和君士坦提乌斯实际并未成婚,其他人——敌视这个家庭的异教徒——则声称她在小时候就在她父亲的旅馆工作,为索取微薄的钱财而给顾客提供特殊服务。直到她步入晚年,她的儿子执掌大权时,她才最终成为帝国最受人尊敬的女人。327年,年逾古稀的她在皈依基督教的热忱之中前往圣地朝圣,而她也在那里奇迹般地发现了真十字架,并因此荣耀地位列圣人历(Calendar of Saints)之中。
不管他出生于何年,君士坦丁在他的父亲成为罗马帝国的四个统治者之一时依然是个孩子。早在286年,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认为帝国国土过于庞大,敌人过于分散,交通线也太长,仅靠一个君主无法有效统治,于是他让自己的老战友马克西米安(Maximian)与自己分享皇位。他本人对管理东部领地更感兴趣,驻守在马尔马拉海滨的尼科米底亚,这里距离多瑙河与距离幼发拉底河基本相当。在他的支持下这座城市的规模扩大,也更为华美,直到可以与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乃至罗马城相比。但在戴克里先的时代,罗马城除了往日的光辉记忆之外没有任何足以支持其发展的资质。其地理位置意味着它无法有效作为三世纪帝国的都城。当马克西米安成为帝国西部的皇帝时,他一开始就清楚自己将主要在米迪奥拉姆(Mediolanum,今米兰)管理帝国。
两个皇帝的管理确实优于一个皇帝。但不久之后戴克里先决定进一步分配皇权,任命两个“恺撒”,这两位将军尽管地位低于他和马克西米安(马克西米安的头衔是“奥古斯提”),但在他们管理的领域之中依然拥有最高权威,最终还能够继任帝国的最高职务。最早的两位恺撒之中,一位是来自色雷斯(Thrace)的粗暴野蛮的职业军人伽列里乌斯(Galerius),负责管理巴尔干;另一位则负责管理高卢,承担将反叛的不列颠收归罗马帝国统治的特殊任务,他正是“苍白者”君士坦提乌斯。
这一安排的缺陷即使在当时也显而易见。尽管戴克里先竭力强调帝国依然是一个未分割的整体,依靠统一的法律与机构管理,然而他或者他的继任者不可避免地会把帝国分为争执不休的四个政权。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事态平稳地发展了一段时间——在这一时期年轻的君士坦丁在戴克里先的宫廷中生活,某种意义上作为人质以保证他的父亲安分守己(毕竟四帝共治时代的四位君主没有一人完全相信他的同僚们),但身为皇帝身边人的他依然保持显赫地位。
他也是以这样的身份陪同皇帝参与295~296年的埃及远征,返程时他穿过凯撒利亚(Caesarea)。据记载,他在那里时给年轻的基督徒学者尤西比乌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尤西比乌斯成了当地的主教以及君士坦丁的第一位传记作家,然而此时的他只是个大约三十岁的俗世中人,是凯撒利亚著名的奥利金神学学院的主要支持者潘菲鲁斯(Pamphilus)的朋友和门徒。此后他在《君士坦丁传》之中写道,书中的主人公
……拥有一种气度,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为之折服,那时的他已经展现出皇帝的伟大。因为没有人拥有堪与他相比的风度与俊美,也没有他健壮的体格;此时他在体能方面已经远超同时代的所有人,让他们恐惧不已。
君士坦丁称帝
两年后的君士坦丁在另一次对波斯的远征中,成了皇帝的得力干将,而考虑到他那些年极少离开戴克里先身边,我们可以认定他见证了303年蓄意焚毁新建成的尼科米底亚大教堂一事,这也为随后八年间近乎无法控制的著名迫害运动拉开了序幕。但在305年,发生了一件罗马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皇帝退位。在当了二十年皇帝之后,戴克里先已经厌倦权力,他离开了公众视线,隐居到相对偏远的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萨隆纳,居住在自己执政时建造的大型宫殿之中,此外他还迫使马克西米安与自己共同退位,即使后者极不情愿。
幸运的是,在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之后,不必详细讨论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后续事件,只需要提及伽列里乌斯和“苍白者”君士坦提乌斯——此时的他抛弃了海伦娜,与马克西米安的养女狄奥多拉(Theodora)成婚——按照计划加冕称“奥古斯都”,但他们的继承者,即两位新“恺撒”的任命问题却存在激烈争议。君士坦丁发现自己被忽略,担心性命不保的他趁夜逃出了伽列里乌斯在尼科米底亚的宫殿,并为逃避追击而割断路上驿马的腿筋,一路来到布洛涅(Boulogne)与他的父亲会合。那里一支罗马大军在君士坦提乌斯的指挥下正准备远征不列颠,将四处劫掠的皮克特人(Picts)赶回哈德良长城以北。父子二人共同渡过英吉利海峡,在几周后就达成了目标。然而不久之后,306年7月25日,“苍白者”君士坦提乌斯在约克逝世,而尸骨未寒之时,他的朋友兼盟军——法兰克仆从骑兵的指挥官阿勒曼尼国王克洛库斯——代替他立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在这个短暂的夏季远征期间,这个年轻人似乎得到了当地军团士兵的一致敬仰,他们立即欢呼支持。然后他们在那里将皇帝的紫袍围在他的肩上,用盾牌将他托举起来,齐声欢呼。
这是个伟大的胜利,当消息从高卢逐渐传开之后,各省纷纷向这位年轻的将军表示忠诚与支持。但君士坦丁依然需要得到正式认可。因此他在加冕之后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给尼科米底亚的伽列里乌斯送信,以及他父亲的官方讣告和一幅他本人戴着皇帝的月桂冠、带有西部奥古斯都(Augustus of the West)特征的画像。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记载称伽列里乌斯收到这张画像时立即将它扔进了火中,而他的幕僚们费了一番唇舌才让他意识到主动与一个更受欢迎的对手为敌的危险。然而这位皇帝在一个问题上依然十分坚定:他毫无理由地拒绝承认这个年轻的僭越者——事实上君士坦丁确实算得上僭越者——为奥古斯都。他不情愿地承认他为恺撒,但仅此而已。
对君士坦丁而言这就够了——至少目前如此。也许他还没有准备好掌握最高权力,他在接下来的六年间留在高卢与不列颠,睿智且高效地管理这些省份——尽管在被激怒时他同样暴戾甚至残忍。(306年某个法兰克部落发动叛乱,被镇压之后,上千名俘虏在大竞技场中被喂了猛兽,同时代人的记载称连这些猛兽都因猎杀如此多的猎物而精疲力竭。)另一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奴隶以及其他受压迫者的境遇。而他的清醒,以及在男女之情上的正直,与他绝大多数的先辈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这种正直并不能阻止他在307年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米内尔维娜(Minervina),为了获取更显赫的盟友而与老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福斯塔(Fausta)成婚。老皇帝此时推翻了他两年前逊位的宣言,重新穿上紫袍并挑战伽列里乌斯,并且与自己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联合起来开创大业。两人一同笼络了整个意大利,还至少拉拢了西班牙和北非。然而他们的皇位仍算不上稳固。伽列里乌斯从多瑙河流域——很可能得到了东方军团的支援——发动的联合进攻依然对他们构成威胁,而且如果君士坦丁同时从高卢对他们发起攻击,他们的未来就更无希望了。因此一场婚姻对双方而言都是有利的,对马克西米安和马克森提乌斯而言,他们也许可以在需要时获得君士坦丁的支援,而君士坦丁与两个皇帝有了亲属关系。
马克森提乌斯
本打算统治整个帝国的君士坦丁,到底有多久仅满足于统治帝国一个相对偏僻的角落,我们不得而知;311年4月,老皇帝伽列里乌斯颁布了一份容忍基督徒的敕令,就此在理论上终结了这次大规模的迫害,几天之后就在萨瓦河畔的西尔米乌姆逝世。
伽列里乌斯的死让三个人得以分享最高权力:瓦莱里乌斯·李锡尼安努斯(Valerius Licinianus),即李锡尼(Licinius),原本是老皇帝的酒友,在三年前被提升为共治的奥古斯都,此时正管理伊利里亚(Illyria)、色雷斯和多瑙河各省份;他的侄辈马克西敏·代亚(Maximin Daia),于305年被封为恺撒并掌控帝国东部;以及君士坦丁本人。但还有一个人,尽管他理论上并不是皇帝,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被不正当地剥夺了本该属于他的皇权,这个人正是伽列里乌斯的女婿马克森提乌斯。他是老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西米安在前一年因为误判形势,在君士坦丁离开时于南高卢起兵与他对抗,结果战败被处决或被迫自裁。马克森提乌斯长期以来厌恶自己杰出而年轻的妹夫,而自君士坦丁继位之后,他就一直在加固自己在地中海地区的权力基础。早在306年,在他和他父亲在意大利起兵之前,他就已经授意罗马城的禁卫军推举他为“罗马皇子”,并接受了这一称号。而五年之后的他和他的三个对手一样强悍,足以以他父亲之死为借口公开与君士坦丁决裂,称他为谋杀犯与叛徒,下令在意大利全境的铭文与庆典之中去除他的名字。

战争显然已经不可避免,而在得知伽列里乌斯的死讯之后,君士坦丁也立即开始备战。然而在出兵进攻他的对手之前,他必须先与李锡尼达成协议,毕竟马克森提乌斯控制的是理论上属于李锡尼管辖范围内的领土。对君士坦丁而言幸运的是,李锡尼不能亲自前往收复这些土地,因为他忙于与东部的马克西敏·代亚对抗以保证自己的地位,因此得知君士坦丁决定为他收复意大利的消息时大喜过望。这次协议再次依托婚姻保障——李锡尼本人迎娶了君士坦丁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Constantia)。
在外交基础打好之后,君士坦丁在311年秋季出发前往科尔马(Colmar),在那里越冬并制订计划、准备给养。佐西姆斯(Zosimus)称他的部队由八千名骑兵和约九万名步兵组成。也许这仅是他拥有的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但高卢不能没有军队驻守。而且他很清楚马克森提乌斯的军力规模,他相信这支部队的实力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为了确保取胜,他亲自指挥大军,在312年夏初率部出征。
十字架的神迹
君士坦丁的意大利远征以及推翻马克森提乌斯一事可以迅速说完。从塞尼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他突袭夺取了苏萨(Susa)——他行军路上的第一座重要城市,然而他拒绝他的部下进行惯常的掠夺。他声称他们不是征服者,而是解放者。在都灵城外,情况要艰难得多。马克森提乌斯的部队拥有一些所谓的“熔炉甲骑兵”,这些骑兵和他们的马匹都身披重甲,这种装备方式很可能源自波斯,而在一千年之后又被中世纪的骑士们效仿和发展。但即使是他们,在君士坦丁最精锐的部下手持齐肩高的包铁棍发起冲击时,也最终被击退,而当他们在一片混乱之中向城下撤退时,市民拒绝打开城门。都灵就此被攻破,随后米兰也被占领,而后在一番血战之后布雷西亚(Brescia)和维罗纳(Verona)也被攻破。君士坦丁继续向东,抵达了阿奎莱亚(Aquileia),距离的里雅斯特(Trieste)不远,直到那时他才转向南方,经拉文纳(Revenna)与摩德纳(Modena)向罗马进军。
在这次漫长的行军期间,马克森提乌斯一直留在自己的都城之中,按绝大多数基督徒乃至一些非基督教史学家的记载,他忙于进行各种令人生厌的巫术,施放咒语,召唤恶魔,甚至献祭胎儿,以避免自己即将面对的厄运。对这些故事不必太当真,尽管马克森提乌斯缺点很多,但他从来不缺少勇气。他相信自己的禁卫军执政官(Praetorian Prefect)鲁里库斯·庞培安努斯(Ruricus Pompeianus)以及其他几位出色的地方部队将军,从这一点来看,他留在罗马在战略上是完全合理的。但当君士坦丁的大军高奏凯歌,庞培安努斯战败被杀时,他亲率最后的也是最精锐的部队出城迎战。
两军在312年10月28日,即马克森提乌斯夺权的七周年纪念日,于罗马城东北方向七八英里处,弗拉米尼亚大路(Via Flaminia)的萨克萨卢布拉(Saxa Rubra),即“红岩石”交锋,水流不大的克里梅拉河(Cremera)在那里汇入台伯河(Tiber)。后世的传说声称,也正是在这里,在这一战之前或者这一战之中,君士坦丁经历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次神迹,尤西比乌斯如此记载:
……一个来自天堂的非凡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而对这一景象的说法若是出自他人之口未必可信。但胜利的皇帝本人在很久之后,他受自己亲友与整个社会尊敬之时对这部史书的作者提及了此事,并发誓称他所说属实,而在时间的检验之后,谁还能质疑他所说的一切的真实性呢?他声称大约在正午时分,太阳开始西沉时,他亲眼见到天空之上出现光芒四射的十字符号,位于太阳之上,上面还写着铭文“以此征服”(Hoc Vince)。见到这一景象的他,和他所有的士兵一同呆立。
据说在这明白无误的上帝指引之下,君士坦丁击溃了马克森提乌斯的部队,将其一路赶向南方,赶到台伯河向西急转弯的地方以及位于那里的旧米尔维安桥。在这座格外狭窄的桥边,马克森提乌斯建造了一架浮桥,他可以通过浮桥有序撤退,并迅速将其拆毁以避免追击。他溃退的部下此时拥上了桥,每个人都拼尽全力想逃命,君士坦丁的部下则紧追不舍。他们本可以逃走,但桥梁的建筑工匠过早地撤走了桥上的加固件,整座浮桥突然崩塌,数百人落入湍急的水流。那些没能过桥的人盲目地向唯一的逃生之路,即那道旧石桥冲去,然而正如马克森提乌斯所预料的,那道桥太窄了。不少人在桥上被撞死,还有不少人被践踏而死,更多的人则被同伴挤落河中。而篡位者本人也落水溺亡,他的尸体之后被冲到了岸上。他的首级被挑在长枪上,在君士坦丁于次日胜利进入罗马时被挑在他的前方。此后首级被送到北非,以警告马克森提乌斯的支持者。与此同时,马克森提乌斯的名字也被从所有公共纪念碑上除去,正如一年前这位征服者的名字被除去一样。
米尔维安桥之战使君士坦丁成了自大西洋到亚得里亚海,从哈德良长城到阿特拉斯山的欧洲土地的统治者。而且虽然这或许并不能标志着他皈依基督教,但至少表明他在保护与资助他的基督徒臣民。在罗马的两个半月间,他不仅自己出资补贴二十五座名义上的教堂,并建立起几座新的教堂,还要求其属下的各行省管理者在他们的领土之上也如此行事。在他离开罗马之前,他将拉特兰家族在西里欧山上的宫殿——在他进入罗马之后不久就前来与他会合的皇后福斯塔在罗马停留时即居住于此——送给了新任教皇米尔提亚德斯(Melchiades)。这一宫殿在此后的一千年间均由教皇掌控。而后他自己出资建造了罗马的第一座君士坦丁式教堂——拉特兰圣约翰教堂,至今它仍是该城的大教堂。重要的是,其中央有一座大型的独立圆形洗礼堂,这在此后极大增加了受洗的人数。
因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皇帝在米尔维安桥边感召的十字,不仅是他一生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堪与圣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受的感召相比——从其后续影响来看,也堪称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不是个能轻易回答的问题,而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问另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见于这一时期的另一份主要参考资料,即基督徒学者与演说家拉克坦提乌斯的记述。他在迫害之中幸存下来,大概在这一时期被君士坦丁任命为他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的家庭教师。无论那时的他是不是皇帝的随从,至少拉克坦提乌斯此后也应当有很多机会询问皇帝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此事发生一两年后,他如此写道:
君士坦丁在梦中受到指引,将上帝的徽号绘制在他的士兵的盾牌上,再率部出征。他仿佛奉命行事一般在他们的盾牌上描绘上“X”,并在字母上画出一条先垂直后在字母顶端曲折成弧的线,代表基督。
他的记述仅限于此,没有提到其他景象,只提到了梦。这个虔诚的基督徒与基督教的辩护者甚至完全没有提到救世主或者十字架出现在皇帝面前。至于那个上帝的徽号仅仅是由“X”(chi)和“P”(rho)组成的花押字,即希腊语“基督”的头两个字母,而这也是基督教铭文中常见的符号之一。
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尤西比乌斯在325年完成《基督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时完全没有提到这一战之前任何的梦境或者奇景。直到他在君士坦丁逝世多年之后写下的《君士坦丁传》里才记述了与那段引文相同的事件。他将拉克坦提乌斯的记述展开,记载当夜基督出现在皇帝的梦中,命令他将在天堂中看到的那个符号绘制在旗帜上,“作为与他任何敌人作战时的庇护”。尤西比乌斯称君士坦丁于次日照做了。结果是,包金的长枪交叉成十字架,配有月桂环绕的神圣花押字,即拉布兰旗(labarum)。尤西比乌斯在多年之后看到这一旗帜时,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皇帝和皇帝的孩子们的金色肖像也被挂在了这一旗帜的横杆上。
那么,我们从这一切的记载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当然是,在战场上出现十字架的幻象,这个在西方教堂与艺术馆的油画与壁画中被描绘了无数次的景象,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果确曾发生,同时代的记载中无人提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事实上直到《君士坦丁传》问世,才出现这一说法。皇帝本人似乎从未如此宣称,即使在他应该说出这个故事的场合,他也不曾说过,而尤西比乌斯似乎成了唯一的例外。在皇帝逝世后不久,耶路撒冷主教西里尔(Cyril)对皇帝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Ⅱ)保证,近期空中出现十字形光斑一事是上帝的慈爱,甚至胜过他祖母海伦娜在圣地发现真十字架一事。如果主教清楚君士坦丁看到如此神迹,他又怎么可能将其忽略呢?最后,尤西比乌斯也特意提到“全军……都目睹了这一神迹”。如果属实,那这九万八千人还真的都是守口如瓶了。
另一方面,基本可以肯定,在这场决定性的战争之前,皇帝就已经受到某种圣灵感召。拉克坦提乌斯单调的记载可能属实,但这类经历未必都会以梦境这种易于描写的方式发生。有证据显示,自两年前处决他的岳父马克西米安之后,君士坦丁在宗教方面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并愈发倾向于一神论。310年发行的货币上原本属于古罗马众神的位置仅仅保留了一位神灵——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不败的太阳”(Sol Invictus),君士坦丁也宣称于多年前在高卢作战时看到了有关太阳神的神迹。而这一信仰——此时帝国最受欢迎也传播最广的信仰——似乎没能让他满意。尤西比乌斯提到在君士坦丁前往意大利时,他清楚自己很快就要参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战了,而他要为此赌上自己的一生。他虔诚祈求神的指引。简而言之,312年夏末的君士坦丁是最急于改宗的人,他的祈祷也理所当然地收到了回应。
如果接受这一假说的话,尤西比乌斯的说法就更容易理解了,这与其说是蓄意造假,倒不如说是无意之中的夸大,而这种夸大更多是由皇帝本人而非记述者完成。在君士坦丁的一生之中,特别是在米尔维安桥之战后,君士坦丁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执行神圣使命的感觉。在他的晚年,这种感觉愈发强烈并掌控了他,而且在生命末期回顾自己一生中的那些大事件时,他给记忆添枝加叶,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在他的时代,绝大多数人都相信神迹以及上天指引的存在,而他本人回忆称,在一个应当看到神迹的时候看到了神迹,他人自然很容易相信神迹确实出现过,而尤西比乌斯更是最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质疑他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