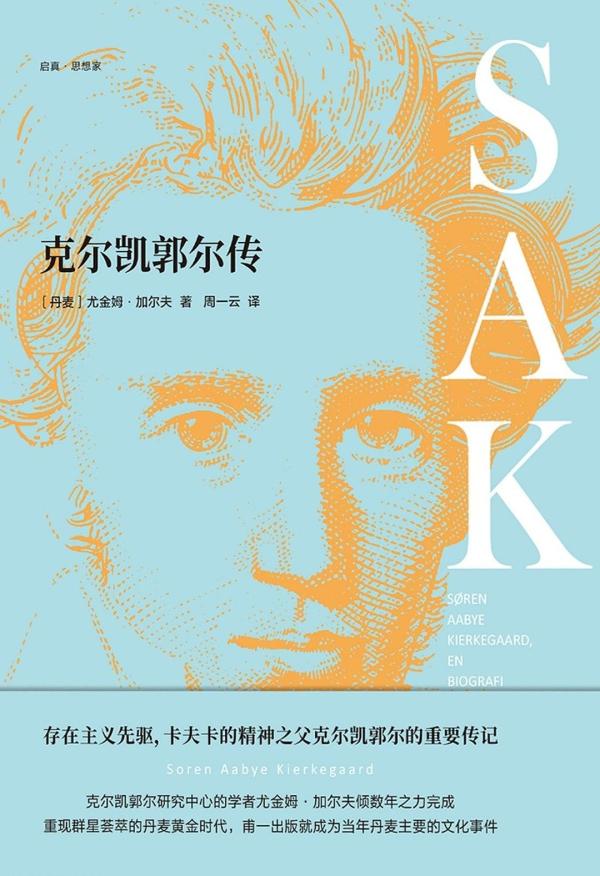克尔凯郭尔与叔本华著作相见恨晚,两人的相似之多让他不安
【编者按】
丹麦神学博士尤金姆·加尔夫的《克尔凯郭尔传》全面通透描述了克尔凯郭尔的生平,2000年在丹麦一问世就被称为重要的文化事件,获得众多好评。时隔二十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翻译出版了这部传记,为哲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便利。
尤金姆·加尔夫(Joakim Garff)是克尔凯郭尔研究专家,对丹麦神学、神学与哲学交叉的领域有深入的研究。现就职于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是克尔凯郭尔著作丹麦语全集出版项目的主编之一。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克尔凯郭尔与叔本华”一节内容。克尔凯郭尔在生前最后一年才开始研读叔本华的作品,两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都有相似之处,连名字的缩写也“互为逆反关系”。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个人化的增长而出现了一批悲观主义思想家,他们对理性作为人的管理机制有着最小的信任,相反却强调那些非理性力量,主体的夜间一面,其激情,其欲望的把握。其中之一就是阿图尔·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在一八五四年五月开始读他的作品,并继续了整个夏天。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没有更早就了解这位意气相投的德国思想家。保尔·马丁·穆勒在一八三七年论不朽的论文中提到过他,而克尔凯郭尔精读过这篇论文,但也许他当时被叔本华吓坏了。因为穆勒将叔本华的努力当作“现代泛神论之虚无一面”的例证,他对这位德国思想家嗤之以鼻,以“最直白的表述将他的哲学特征归结为反基督教的和虚无主义的”。
不能确定是否正因为如此,克尔凯郭尔才在一八五四年受到叔本华的吸引,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已经几乎不再买书了,却在短时间内搜集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叔本华作品和关于他的作品:新出版的《关于叔本华哲学的通信》,两年前出版的《附录与补遗》,克尔凯郭尔做论文答辩那年出版的《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最后,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自然界中的意志》。当时年轻的克尔凯郭尔正在运用意志和他自己的好斗天性做斗争。

遍布札记中的详细解释和批评性意见表明,克尔凯郭尔读得最多的——尽管和往常一样跳跃穿插——是一八四四年出版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是克尔凯郭尔真正感兴趣的作品。叔本华试图在这部作品中证明,生存最深刻的本质,乃是一种盲目的、不屈的生命意志或者冲动,它以远远超过人所意识到的范围和程度控制着人。个人的意志源自一种无所不包的生命意志,它不惜一切代价要保存并延续生命,而且慷慨地挥霍个人以保存人类。智力是意志的奴隶,当事后需要合理化时智力可以为意志提供方便的主题(motiver)以供利用,但智力本身对意志的决定毫无影响。这样,意志在和理智的关系中是那强壮的盲人,肩负着明眼的残废。一个人的智力越发达,他的生活就越痛苦,所以,天才永远是不和谐的造物。因为世界惨状的印象乃是来自意志,而不是可以疗救的外部缺陷,所以关键在于安抚生命意志。在叔本华看来,这可以通过献身于无私无欲的审美享受,献身于禁欲和道德自我牺牲来实现。叔本华赞同佛教中旨在摆脱一切欲望的那一派,而波斯版的《奥义书》则成为他的圣经。“我们的意愿本身就是我们的不幸;与那意愿是什么毫无关系。……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所意愿之物可以结束我们的意愿,而实际上我们自己所能做的只有放弃意愿。”如果认识的主体可以从意志的主体中解放出来,献身于无欲望地观照客体,那么主体就在观照意志的纯粹客观化,即观念之中而得到安宁。
“奇妙的是我叫索·奥,我们互为逆反关系”,克尔凯郭尔写道,他要和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缩写为“A.S.”)的姓名形成逆反关系就必须将自己限制在“索伦·奥比”(Søren Aaby)名字的缩写(S. A.)。叔本华是一位“意义重大的作家”,他继续写道,“尽管完全不能同意,找到这样一位深深触动我的作家还是十分惊讶”。对克尔凯郭尔来说,居然能发现一位和他一样反黑格尔、反历史主义、反学术和仇视女性的哲学家是奇怪,甚至令人不安的。他们甚至在生平细节上也相似:叔本华的父亲也是一个大商人,他和一个年轻近二十岁的女子结婚,死后留下一大笔财产,供儿子度过漫长的哲学家一生,将他置于——几乎是克尔凯郭尔式的——对死去父亲的感恩负债之中。不过在叔本华的爱情生活中却没有雷吉娜,他只有在威尼斯的一段关系和在德累斯顿的一档子事儿,后者的结果是一个女儿,不幸只活了几个月就夭折了。叔本华一直没有结婚,却不算独居,终其一生和一只接一只的卷毛狗相伴,这些狗共同的名字是“阿特曼”,印地文的“自我”。叔本华和大学的紧张关系也和克尔凯郭尔一样,不同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在作品中攻击哲学教授。当他受聘于柏林大学的时候,黑格尔正在成功地传播异端邪说,于是他将讲课时间安排在与黑格尔同时,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但听者寥寥。他对世界的看法不属于考试的内容,当然也就引不起学生多少兴趣。叔本华于是开始尝试翻译,将康德翻译成英文,将休谟翻译成德文,他还修改歌德的法文译本,出版意大利文版的布鲁诺,同时配有拉丁译文,但也还是没有多少人买账。不过这些都没有在叔本华的自我感觉上留下多少印象,它永远是膨胀的,并且有着克尔凯郭尔式的特质,几乎是随着外部世界的抵抗而增强。叔本华的书无人问津,大部分都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样送回造纸厂了事,而此书在作者去世前两年才出了第二版。但是叔本华没有一秒钟怀疑过自己在哲学上的里程碑意义。他写作时的论证带着明显的艺术感觉;他直言不讳地坚持说,与一切先前的哲学——除柏拉图以外——不同,他的哲学就是艺术,而克尔凯郭尔也在叔本华那里发现了他爱莱辛的地方——“风格”。叔本华在修辞中的节奏是因为,他和克尔凯郭尔一样富有乐感;他热爱莫扎特,经常在长笛上为自己吹奏他的歌剧选曲,这种才能或许足以使克尔凯郭尔嫉妒他。

可见A.S.和S.A.之间的相似之处有不少,然而有时太像也不是好事。克尔凯郭尔看到叔本华将记者叫作“意见出租者”时,不由得喜出望外,认为这个说法“真的有价值”,但随即在页边空白处补充道:“从某个方面来说我发现读叔本华开始近乎不快。我有这样一种难以言表的严重焦虑,生怕用了别人的话却没有承认。但是有时他的表达方式是如此类似,在我夸张的焦虑中也许会把我的说法归于他。”这样的一个愉快的又不快的例子是“吹牛者”(Windbeutel)这个词引起的,“叔本华把这个词运用得真妙”,尤其是当他谈到“黑格尔哲学和所有教授哲学”的时候。克尔凯郭尔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词,用来形容这个“哲学谎言的时代”再贴切不过。他一度羡慕德语,但在经过考虑后为丹麦语中这样词的缺席找到了一个既可爱又可疑的解释:“我们丹麦人没有这个词;这个词所形容的也不是我们丹麦人的特性。在丹麦国民性中其实没有吹牛这样东西。”丹麦人可以松一口气,但是只能松一口,因为克尔凯郭尔接着又说:“然而我们丹麦人有另一个错误,唉,一个相应的错误;丹麦语也有一个词,德语中或许没有,那就是吸气者(Vindslugere)。这个词经常用在马身上,但也可以更普遍地用。于是情况大概就成了这样:一个德国人吹气——一个丹麦人把气息吸进去。德国人和丹麦人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相互关系。”A.S和S.A.就这样在对称的镜像中重逢:A.S.与吹牛扇风作战,S.A.与抽风吸气作战。
而在另一些方面克尔凯郭尔首先坚持的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稍微简单化一点可以这样说,克尔凯郭尔将心理学问题当作伦理学来谈,而叔本华则将伦理学问题当作心理学来谈。对叔本华来说,福祉(saligheden)在于成为客观、纯粹、无利害的沉思;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则是关于成为主观,将自己与永恒福祉(evige salighed)激情充沛地联系起来。不过,克尔凯郭尔并不特别在意叔本华的抽象立场,他更关心后者的生存实践,他在札记中进行了各种尖锐的批评。叔本华生活中有一段插曲将这个问题表现得尴尬无比。挪威科学院于一八三七年悬赏征集论文,题为:《人类的自由意志能否由自我意识来得到证明?》。叔本华提交了一份论文而得到金奖。就在此事发生前不久,丹麦科学院也就相关问题征文,题目出得很佶屈聱牙,只有希本的脑袋能想出来:《道德哲学的来源与基础在何处可诘究?是在直接意识的德行理念的解释中,抑或是在另一认识根据中?》。叔本华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却没有得奖;不但没有得奖还受到很多批评,因为,根据评审委员会的意见,他不仅误解了题目,犯了许多形式上的错误,而且以一种“极其不恰当和冒犯”的方式谈及一些晚近最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将这两篇有奖征文合在一起,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书名加上长篇序言出版。他在序言中讽刺了丹麦科学院那狭隘的判断力。他这样做完全在正当的权利范围内,如果——这是克尔凯郭尔的异议——他在这样做时没有和自己的伦理学处在可笑的错误关系之中的话:“然而这并非无可解释。他,才华横溢地代表着如此仇视人类的人生观的他,为得到设在特隆赫姆(仁慈的上帝啊,特隆赫姆)的科学院加冕的桂冠而兴高采烈......而当哥本哈根没有给叔本华加冕另一顶桂冠时,他大吵大闹,出版论文时在前言中一本正经地口诛笔伐。”

克尔凯郭尔的异议直指他对叔本华批判的核心,加倍重复(reduplication)的缺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这一点在他反思叔本华作为“德国之命运”时得到一个独特的戏剧性转折:“叔本华真正懂得,在哲学界有一个阶层的人士,以传授哲学谋生......叔本华在这方面无可比拟地粗暴。”到这里为止还算好,但接下去就不客气了:“叔本华没有品格,没有伦理品格,没有希腊哲学家的品格,更没有基督教警官的品格。......叔本华怎样生活?他离群索居,偶尔发出一些粗暴的雷声——却无人理睬。看,就是这么回事。”在一个如此享有特权的地位充当悲观主义的代言人,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是赤裸裸的智术(sofisme),因为“智术存在于一个人所理解的与其所是之间的距离,那不具备其所理解之品格的人,是为智者(Sophist)”。
克尔凯郭尔远非第一个对叔本华提出这样异议的人。他的回复也很有针对性:道德哲学家所建议的美德不能高于他本人所具备的,这是一种古怪的要求。可以补充说,这或多或少正是克尔凯郭尔所做的,他持续地自称“诗人”[正是出于这个理由],而他对叔本华之缺少加倍重复的批评,也应该理解为一种替代或间接的自我批评,才真正有意义。此外,叔本华其实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自己制定的苦行规条:一八三三年以来坚持不懈、风雨无阻地在法兰克福郊外的乡间长距离散步,洗冷水澡,生活有规律而准时,活像伊曼努尔·康德——或索伦·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在死前一年研读的这位叔本华,还有六年好活,与他的丹麦同行相反,他看人生前所未有地光明——一种从晚年的银版照片上的这位愤世嫉俗的男子身上并不易觉察出来的东西。但是在一八四八年多次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幻灭感,接受他的苦涩信息的时代已经成熟,悲观论者叔本华于是经历了奇怪的成功,而且成功到了让他几乎随之而变成乐观论者的程度。于是在他最后一部作品的最长部分包括了一系列人生智慧的格言警句,为读者提供了“尽可能舒适地度过一生的艺术”的一些小小练习。这恰恰符合好逸恶劳的布尔乔亚的趣味,克尔凯郭尔为之如此愤怒,几乎将札记撕成碎片:“毫无疑问,目前德国的情况是这样的——从文学痞子和搬运工、记者和不入流作家围着叔本华转,就不难看出——现在他要被拖上舞台接受掌声和欢呼。我敢拿一百比一打赌,他——他高兴得头重脚轻;他根本想不到要摆脱这些垃圾,他现在高兴了。”所以叔本华只是在外部世界让他不得不如此的时候才是悲观论者,一旦时代对他有利,他的悲观主义随即变成一种风格,他的哲学也上得厅堂,而他对体系的敌意则纳入了体系:“于是,他责无旁贷地给禁欲主义之类在体系中分配了位置。……他不无得意地说,他是让禁欲主义在体系中占据位置的第一人。老天爷,这完全是教授口气,我是第一个在体系中给它位置的人。”
晚年克尔凯郭尔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传记的方式来阐释叔本华的哲学,他也用同样方式对待过——例如马腾森和明斯特——而他也并不怀疑,叔本华会怎样从他所陷入的谎言中解脱出来:“不,这件事情也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把握。到柏林去,把这些流氓恶棍赶到街头剧场,忍受充当所有人当中最有名的,每一个人都认识的。......我在哥本哈根实践过,当然是在较低程度上。......我还敢于做过另一件事——正因为我一直置于宗教指挥之下——我敢于自愿成为漫画讽刺的对象,遭到低微的和高贵的,全体群氓的嘲笑:一切都是为了破除错觉......但A.S.完全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他一点也不像S. A.”。
从这个个人视角产生出一个更加原则的问题,它——如下面将说明的——在一个小小的辩证回转之后,以相当个人的形式回到克尔凯郭尔这里:“叔本华鄙视基督教,在和印度智慧的比较中嘲笑它。这是他的事情。......我不反对叔本华竭尽全力对着新教尤精于此的‘卑鄙乐观主义’大发雷霆,我很高兴地知道,他表明,那完全不是基督教。”克尔凯郭尔在这里和别处一样,对那些公开弃绝基督教的人们极其宽容,但是他必须针对一个特定情况提出抗议,即叔本华将人生等同于痛苦,“这样就取消了基督教”。因为,如果人生本来就已经是痛苦,基督教将失去“那借助否定形式来辨识”的手段,而成为一种“赘言,一种浅薄的观察,胡言乱语,既然人生本是痛苦,那么一种关于做基督徒就是受苦的学说也就成为荒唐可笑的了”。
克尔凯郭尔忧心忡忡地强调叔本华将人生等同于痛苦的错误。无忧无虑的浅薄时代大大受惠于“被忧郁症抹黑”,但人生是快乐的,人生不是痛苦,人生只有在基督教介入时才成为痛苦。克尔凯郭尔在这里呼唤攀登者约翰尼斯,后者早在《附笔》中就制定了“这个原则:基督徒就是受苦”,所以每一种将“扼杀或弃绝人生快乐”的观念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那就是如果那单一者在与一个外在于他的超越性权威、一个神的关系中,被要求弃绝肉体。

尽管存在着区别和不同意见,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还是对克尔凯郭尔产生了推动性作用并加强了他的批判。而他,本来极少为未来神学学生贡献思想的,在遇到叔本华之后做了一个例外:“如同人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嘴里含个东西,如果可能,以免吸进受感染的空气,因之也可以向那些不得不生活在丹麦的无理由(基督教)乐观主义之中的神学大学生们建议:每天摄取小剂量的叔本华伦理学,以保护自己免受这废话的侵害。至于我本人则是另一回事,我受到其他形式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