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这种“野味”,吃多了为何易遭“报应”?
新型冠状病毒的宿主到底是谁,目前还是一个无法确定的问题,绝大部分学者倾向于“罪魁祸首”是蝙蝠——当然,“罪魁祸首”这四个字也委实有些冤枉,毕竟蝙蝠君也没想到以自己的其貌不扬还能上得了餐桌,惹得下大祸;何况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在中国古代极少认为此物可以食用,《本草纲目》中虽说也以“伏翼”之名将其入药,可没说这玩意儿能直接炖汤喝。
如果说古代笔记中寻找一种记载最多的、吃后会引发灾难的野味,据笔者的印象,大约应该是鳝鱼。

很多人一听鳝鱼是“野味”,恐怕会皱起眉头:此物难道不是养殖的吗?其实鳝鱼人工养殖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在古代绝对属于野生动物,但由于捕捞容易,所以经常为人们所食用。
鳝鱼味道鲜美,古籍中多有记载。清代著名学者和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记录了鳝鱼的三种烹饪方法,一种是炙鳝段:“切鳝以寸为段,或先用油炙,使坚,再以冬瓜、鲜笋、香蕈作配,微用酱水,重用姜汁。”一种是炒鳝丝,还有一种是做鳝丝羹:“鳝鱼煮半熟,划丝去骨,加酒、秋油煨之,微用纤粉,用真金菜(即黄花菜)、冬瓜、长葱为羹。”
据徐珂撰《清稗类钞》所记,同年光间,淮安出现治鳝的潮流,很多名厨都以擅长烹制精美的鳝肴而闻名,甚至有了“全鳝席”:“多者可致几十品。盘也、碟也,所盛皆鳝也,而味各不同。”具体这几十道鳝肴怎么制作,没有细讲,笔者只在书中一处找到了“一鳝三吃”的做法:一曰虎尾,专取尾之长及寸者,去其尖,加酱油调食之;二曰软兜,专用鳝脊,油沸后投入锅中,似煮似炒;三曰小鱼,则专取鳝鱼的肠和血,煮之使熟,食用时再调以酱油。而徐珂说这样精细的烹饪只是“普通之制法” ,足以令人遐想其他的制作方法是何等复杂。
食用的鳝鱼主要有白鳝和黄鳝两种,其中白鳝是上品,而黄鳝则是普通人家食用。道光年间著名学者杨懋建在《京尘杂录》中说:“京师最重白鳝,一头值数缗。”可见其贵重。当时黄鳝的价格不及白鳝的十分之一,大户人家请客时,端上餐桌的如果是白鳝,则夸为盛馔,如果上来的是黄鳝,则訾为不敬。据清末学者陈莲痕所著之《京华春梦录》记载,当时北京最有名的治鳝馆子名叫杏花春,所做之溜鳝片是享誉京城的佳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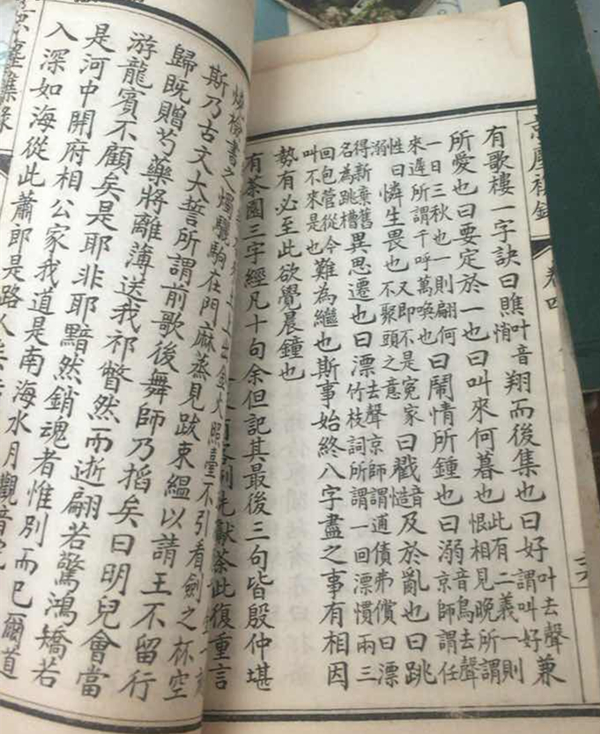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作为一种美味的食材,鳝鱼在古代笔记中的形象很是不佳,几乎一直是某种“负面”的存在。比如慵讷居士所著《咫闻录》中所撰故事:一个姓刘的人老而生女,钟爱异常。女孩刚刚及笄,一夜,忽有一穿着杏黄色衣服的美少年卷帘而入,对她上下轻薄。女孩又惊又怕,口不能言,自此这少年每夜光顾,折腾得女孩一病不起。父母打探到原因,却不知如何除妖。一天有个姓朱的遇雨求宿西廊,刘翁同意了。姓朱的对刘翁说:你家有怪,我能驱之。遂作法事,书符诵咒,引着刘翁至庭院内的水池边,将池中的水抽尽,“见有黄鳝,粗如巨桶,睡于泥中”。大伙儿一起动手将其拽起,用斧子斫成数段,烹煮后让女孩吃下,她的病立刻痊愈了——不难体悟,在这个故事里,鳝鱼与蛇在志怪小说中“作妖”的缘由相仿,在于此物能够引发的某种性暗示。而在古代笔记中记载更多的,则与故事的结尾截然相反,吃鳝鱼不但不能治病,反而会遭遇“报应”。

二、群鳝啮臂,夺人性命
“嗜鳝业报”或“食鳝报”在古代笔记中十分多见,这里摘录几则,以证笔者所言不虚。
明代作家钱希言在《狯园》里记苏州南禅寺和尚云峰上人,“酒肉沙门,不习经典,广求滋味,无愧于心”。他平生最爱吃鳝鱼,不仅食用量大,而且烹饪方式十分残忍,“或生剥,或沸羹,或断其头,日夜烹杀”。万历年间南禅寺大火,火一直烧到沧浪亭后面的僧舍,云峰上人眼见火起,突然惦记舍内囊箧,返身冲回舍内,“烟迷不能出”,人们听到他的惨叫声,见他在火海里昂着脑袋,扒着墙壁,躲避着渐渐舔噬衣襟的火舌,“与釜中鳝鱼无异,咸以为杀生之显报焉”。
类似的“报应”在清代学者王椷所著《秋灯丛话》中亦有记录。新城河边有一株柳树横亘水面,经常见到一只长丈许的大鳝鱼盘踞其上。村里有个地痞总想将其捕捉下锅,便暗中练习没羽箭张清拿手的投石之术,日积月累,渐有所成。这一天他见鳝鱼又在柳树上歇息,一石头打过去,正中鳝鱼的头部,鳝鱼掉落水中,“河水尽赤”,那个地痞用网打捞半天,也没有将其捞上岸,只得悻悻而去。后来有一天,天降大雨,地痞在家中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叫他的名字,召唤他说:“河中有很多从上游漂下来的木头,赶紧捞出来卖钱!”他顶个斗笠出了门,却没有见到喊他的人影,跑到河边一看,果然有很多大圆木流下,高兴地下了河。谁知刚到水深处,“忽变为大鳝,急向岸上呼曰:‘寄语老母,鳝鱼索命矣’!”然后就随波而没了。
如果说这篇“鳝鱼索命”纯属杜撰,那么清代学者汤用中在《翼駉稗编》里的记载则真实可信:贵筑县有个年近六旬的郑姓老翁,酷爱吃鳝鱼,每顿都要吃。有一天他到集市上买鳝,“必欲得肥大者”。卖鱼的让他自己到鱼缸里挑。“郑挥袖裸臂,探手摸之,群鳝绕臂竞啮,旋绕旋紧!”郑某疼得一声惨叫倒在地上,他的儿子连忙将他背回家,将咬住胳膊的鳝鱼或揪或剪,但这些断鳝依然没有松口,“齿尽入肉”。郑某长号不已,一命呜呼……事实上直到今天都有很多类似的新闻报道,将黄鳝一刀切成几段后,黄鳝的头部还会突然咬住下厨者的手指,致其受伤、中毒甚至截肢。联系笔者此前一篇叙诡笔记里引用《听雨轩笔记》中的文章,可知一些鳝鱼的头部毒性很大:一群人打捞到一条“遍体金黄而背微黑”的大鳝鱼,有个乞丐将其割成数断,分给群丐食用,其他乞丐都没有事,但吃鱼头的乞丐突然发烧并陷入昏迷,多亏医生及时救治才幸免于难。
三、鳝鱼抬头,声似鬼鸣
民间有谚:“黄鳝不吃头,田螺不吃尾。”这是因为野生鳝鱼喜欢在淤泥中钻洞,“饮食”很不卫生,甚至以腐肉为食,所以体内尤其是头部积累了不少有毒物质;此外,鳝鱼死后,其蛋白质结构崩解,组氨酸转化成有毒的组胺,数量达到一定浓度后,人吃了就会发生组胺中毒,产生头晕、头痛、心慌、胸闷、呼吸困难、心跳血压下降等症状。就算没有发生这些情况,吃野生鳝鱼还存在着被寄生虫侵袭的风险。据媒体报道,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做“颚口线虫病免疫诊方法的建立与应用”课题时,去杭州五六个农贸市场采购了10斤黄鳝,结果总共分离出了整整250条活的颚口线虫。科研人员介绍:“颚口线虫不但存在于黄鳝的内脏中,也存在于肌肉中,其中肝脏位置最多。”颚口线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好几年,会全身游走,游到哪里,就会损伤哪里的组织器官,“特别是进入到脑子里,危害最大,危及生命。”
仔细研读古代笔记不难发现,很多谈“报应”的文章,无论怎样诡异玄奇、不可思议,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劝人方”,通过“必有恶果”来奉劝人们适可而止,非要究诘其真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体会到古人的良苦用心。就拿食用野生鳝鱼来说吧,显报也好,索命也罢,其实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这种野味的后面藏有重大的健康风险,才编排了一些可怖的故事,或者将某些嗜鳝者的其他遭遇牵强附会,让人们对这种食物敬而远之。民国学者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中的一则笔记,就是体现了这种意图:

汉阳王某,驾木筏去苏州,他“以钱八百于中途购鳝四十余斤,贮于巨桶,当日杀食数尾”。当天夜里三更时分,王某忽然听见木筏上一片沸腾之声,他吃惊地点燃火把观看,“见桶中群鳝直竖,头出水面七寸许,声似鬼鸣”。一同乘坐木筏的人们被吵醒,也都齐聚观看,“声更巨”。大家都感到十分害怕,于是将巨桶中的鳝鱼倾倒江中,“王自是戒食鳝”……
事实上鳝鱼把头抬起不过是水中缺氧的缘故,但一旦生发了鬼魂的联想,自然就无人敢吃了。
在民国学者郭则沄所著笔记《洞灵小志》中,笔者找到了一篇关于鳝鱼的文章,虽然看似与前面提到的那些笔记截然相反,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曾任四川候补道的吴养臣曩居秣陵(即南京),秦淮河岸有一家名叫“问柳”的酒楼,门临衢陌,楼后青溪,酒楼的厨子就在溪水边洗涤食材。因为黄鳝美味,点菜的人多,厨子便买了很多黄鳝“储巨缸中以待客”。酒楼的主人有个小女儿,心地善良,每次都偷偷放走一些鳝鱼。“主人爱是女,故亦听之,由是习以为常。”有一天,酒楼突然起火,火势迅速扩大,封住了从门口逃生的道路,并向后面蔓延。客人和酒楼的伙计、厨子避无可避,仓皇坠水者不在少数。那个女孩也在火舌逼近时跳进河里,她不会游泳,自忖必死无疑,谁知落水不久,身子下面便有物承之,“逐水漂流甚远,遇小舟获救”。小舟上的人们仔细观看,才发现承接女孩使她不至沉入河底的竟是“群鳝结为巨团”——郭则沄不禁慨叹:“鳝岂预知有火,且知女之必坠是处,而相率来拯之耶?”
鳝鱼当然不可能有救人的举措,吴养臣讲述的故事可以肯定是基于落水女孩及时获救这一事实之外的杜撰。现如今鳝鱼的人工养殖已经十分普及,吃鳝鱼早已没有了那些健康风险,但重新读起这些鳝鱼还属于“野味”年代的笔记,竟然让人感到古人穿越而来的苦心劝诫:拯救野生动物就是拯救人类自己——时至今日,也许每个人都能更加深切地感受、理解和认同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