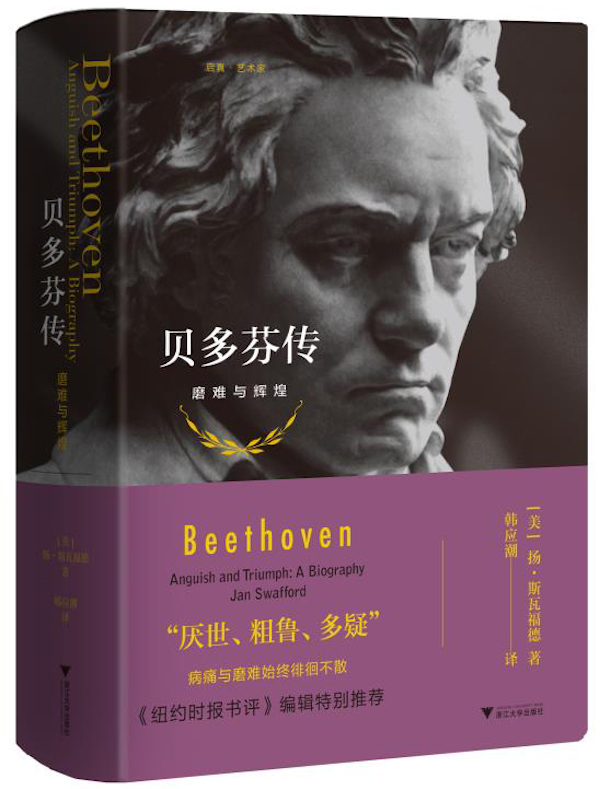贝多芬的遗产︱《“英雄”交响曲》:写给拿破仑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本文作者扬·斯瓦福德(1946— )系美国作曲家、作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后于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取得硕士以及博士学位,主要以一系列音乐家传记而闻名,这些传记包括《查尔斯·埃夫斯传》《勃拉姆斯传》等,并著有《古典音乐经典指南》等。本文节选自斯瓦福德所著《贝多芬传:磨难与辉煌》(韩应潮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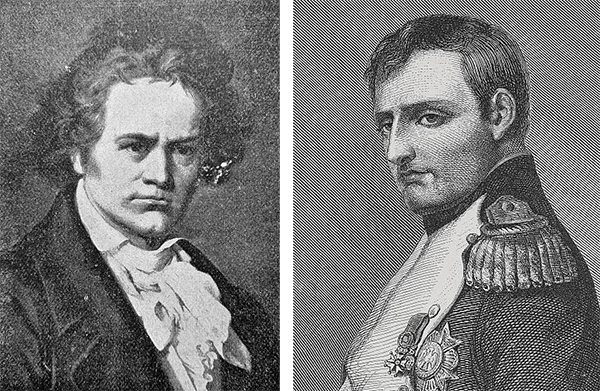
贝多芬和拿破仑的画像
1803年年末,贝多芬回到了他在维也纳河滨剧院作为驻团作曲家的狭小公寓。在那里,斯蒂芬·冯·布伦宁带了一个年轻的莱茵兰人维利布罗德·约瑟夫·梅勒(Willibrord Joseph Mähler)去见他。梅勒是一位喜爱多种艺术的公务员:业余歌唱家、诗人、歌曲作者和肖像画家。贝多芬一般来说对认识任何来自故乡的人都感到高兴。更令他信任的是,梅勒出生于贝多芬母亲的故乡埃伦布莱特施泰因。当梅勒请求听一些东西时,贝多芬同意了,演奏了《“波拿巴” 交响曲》的变奏曲—终曲。接近乐章终点时他继续演奏下去,即兴弹出新的变奏,用了两个小时。
“没有一个错误的小节,”梅勒回忆道,“或者是听上去不像原创的。”和音乐一样,他也记得键盘前的贝多芬,“他的手一直静止;就像他的处理一样美妙的是他从来不随便前后上下移动手腕;他的手指似乎只是轻轻在琴键上划过,只有手指在起作用”。当天梅勒没有看到那位用超过乐器所能承受的力量弹坏琴槌和琴弦的演奏家。贝多芬还能弹出最精致的连音。卡尔·车尔尼指出,他弹得最好的常常是缓慢、深沉的音乐;他“演奏的柔板和连音……值得 赞美”。
因为梅勒是一位亲切的年轻人,且在贝多芬眼中来自地球上最好的地方,次年他得以说服缺乏耐心而坐立不安的作曲家坐下来画一幅肖像。成果是奇特而令人难忘的,足以和波恩时期作曲家的祖父老路德维希的画像并列。两幅画都阐释了音乐家的生活。老路德维希在画中是一位威严的重要人士,正在翻动一本乐谱的书页。梅勒画中的小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是一个天才的形象。

梅勒所画的青年贝多芬
他的左手拿着一把里拉琴,这是音乐家的一般象征,特别象征着歌唱的阿波罗。右手举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伸出,按画家的话说“就像是在被音乐热情激起的时刻,他正在打拍子”。他已经知道贝多芬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离不开惊人的音乐激情。他也画下了贝多芬粗大、方形的手。在肖像中贝多芬的穿着整洁而时尚,他的头发剪成法国式的新罗马风。他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神尖锐。这也是细致观察的结果:其他人说在公共场合贝多芬经常面无表情,他的感情主要体现在棕色的小眼睛的目光里。在私下喝酒后,他才会变得快活,喜欢逗乐。无论什么场合,他都容易发怒。
画像的背景就和人物一样含义深刻。在画的左侧,按梅勒所说是一座阿波罗神庙。在另一侧,贝多芬的身后是一片阴暗的森林,顶部是一棵枯死的树。 阳光普照的神庙代表古典的过去,既包括古代也包括颂扬规则和限制的18世纪:理性。阴暗的森林代表荒野、神秘、情感、浪漫主义:非理性。这意味着在19世纪的最初几年中,贝多芬开始走上“新路”的同时,这位画家已经将他画成古典和浪漫之间的桥梁。虽然梅勒不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但是他敏锐地观察到 这位模特既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位刚刚出现的偶像和一段新诞生的神话。这是贝多芬自己最喜欢的肖像,和祖父的肖像一样,他一直保存着它:两个理想和现实中的音乐家。
1803年冬天到来时,贝多芬致力于完成《“波拿巴”交响曲》并探索它在“新路”上新的开辟。它的影响在接下来几年中导致几乎难以置信的大发展,一些作品延续了英雄气质,另一些不是,但它们全部都惊人地强健而新鲜。
大约到1804年4月,《“波拿巴”》的乐谱已经抄好可供使用。罗布科维茨大公给了贝多芬一大笔钱——一千八百弗罗林,以独占交响曲六个月,让他家中的乐队能够排练并为来访的宾客演出。贝多芬需要为一首他知道打破了许多界限的交响曲的命运担心。他已经开始接受听力的逐步恶化。
同时,他的作品出版得很顺利,反响也不错,因此他有理由对新交响曲的接受抱有希望。在几乎一整期以贝多芬的画像为封面的杂志中,《大众音乐杂志》这样称赞《普罗米修斯变奏曲》的出版:“无穷尽的想象,独特的幽默,深刻,亲切,乃至热忱的情感都是它的特征……曲中巧妙的表现是v. B先生几乎所有作品的标志。这令他成为第一流的器乐作曲家。”第二交响曲在杂志上得到的评论是:“有价值、宏大的作品,它的深刻、有力和艺术技巧罕有其匹……它 值得由最优秀的乐队一再演奏,直到多得惊人的、独创的、有时被非常古怪地安排的乐思足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成为伟大的整体。”他的音乐中原来被认为特别、罕见,乃至奇怪的元素越来越受到赞美,至少在进步的圈子中。换句话说,乐评家开始认识到贝多芬的个性,并发现他作品中令人困惑的纷杂表面下的整体性。
虽然他在音乐上的敌人不再强大,他却还有身体这个最大的强敌。贝多芬搬进布伦宁的住处时,他得了非常吓人的重病。他从重病中恢复后,仍然有好几个月一直受到发热的困扰。他的下颚和手指上长了脓肿,脚被感染;手指的问题最后几乎需要截肢。在准备排练交响曲和继续创作《莱奥诺拉》时,疾病缠身让他变得更易怒了。当时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新计划。在歌剧草稿中他记下了两段乐思,一段是钢琴协奏曲cv的开头,一段是交响曲的开头;一段温柔,另一段动力充沛,但两者共享一个相同的节奏动机。在这里他找到了他最伟大的协奏曲,以及他最著名的交响曲的主导动机。
G大调钢琴协奏曲的前四小节:



拿破仑·波拿巴
现在贝多芬知道被自己奉为解放者,以致以他为中心来创作自己最具雄心的作品的英雄自封为帝了。贝多芬没有停下来思考实际问题,没有想过这桩新闻会带来的后果。他非常清楚地看出了它的含义。拿破仑不是解放者,只是为他自己的权力和名声才扮演这个角色。怒不可遏的贝多芬向里斯吼道:“他现在和普通人也没什么不同了!现在他也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践踏一切人权。他会把自己抬升到众人之上,成为暴君!”他扯掉了交响曲的封面,把它撕成两半,扔到地上。如果里斯多年后回忆起的确实是贝多芬的言行,那么无论在哪个方面贝多芬都是正确的。在他的回应中,这件新闻令他的理想和历史观念备受打击。他知道18世纪80年代的革命梦想现在已经完结,因为拿破仑曾是唯一能够实现它的人。革命已经死了;革命万岁。
但贝多芬当然没有扔掉第三交响曲。1806年分谱出版时,标题被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Sinfonia eroica, composta per festeggiare il sovvenire d’un grand’uomo”)。这是经过缜密考虑的标题。记忆中的伟人是贝多芬和许多其他人心目中拿破仑应成为的最高形象。这个想象中的英雄已进入坟墓,而拿破仑自己仍然在战场上胜利进军。不仅是英雄之死,现在这首交响曲也标志着梦想的终结。但过去的标题并未将交响曲本身及其在贝多芬心中与拿破仑的联系抹去。 它甚至没有让贝多芬把手稿上的拿破仑名字完全去掉。1804年8月,贝多芬把这首交响曲和一些其他作品提供给布赖特科普夫和黑泰尔时说:“交响曲的标题确实是波拿巴……我想它会令听众感兴趣。”交响曲的一份扉页保留了下来,时间是同一个月,出自他人之手。在扉页顶部,“标题为波拿巴”一语被用力地擦去,以至于纸的有些地方都被擦破。当贝多芬被某物或某人激怒时,他不愿看到那个物名或人名。但在扉页的底部,贝多芬自己用铅笔写下了“为波拿巴而作”(“Geschrieben auf Bonaparte”),并没有擦去它。

这是当时整个欧洲的矛盾情绪的生动反映。“每个人都爱我,都恨我,”拿破仑自己这么表示,“每个人都拿起我,丢掉我,然后又拿起我。”作为生涯中象征性的中心,拿破仑在1804年 12 月2日的加冕本身也成了一段神话。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盛大典礼和仪式中,教宗庇护七世在场并为他祝福,拿破仑自己把查理曼皇冠戴到头上,成为法国皇帝。为自己加冕是这位白手起家的征服者,现在是自封皇帝者的终极象征。这样,他宣称自己是查理曼大帝的继承者,因而象征性地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直到当时的弗朗兹二世皇帝,它已传承千年之久。拿破仑不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的执政;他是新建立的世袭君主国的君王,而革命者相信这种旧政权的形式已被大革命完全消灭。 法国政府在接下来几个月中颁布的法令之一是一份帝国教理问答,要求教会教授所有儿童过去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是独裁政权。
这份新的教理问答包括这些内容:
问:为什么我们要遵守皇帝规定的责任?
答:首先,因为创造了帝王们并按他的旨意分配他们的上帝赐予我们的皇帝在和平与战争方面的才能,让他成为我们的君王,并让他成为自己在地上的权力和形象的代理人。尊敬和服务皇帝就是尊敬和服务上帝本人。
问:我们该如何看待不遵守皇帝规定的责任的人?
答:据圣保罗使徒所说,顽抗上帝本人意旨的人会永堕地狱。
问:第四条戒律禁止我们做什么?
答:我们不可违抗上级,不可伤害他们,不可辱骂他们。
这显然是对现实和宗教中的专制君王的定义。虽然拿破仑只是短暂做过雅各宾党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独裁者,事实上并不站在法国大众一边,但他的统治仍然有进步的成分。1804年春,他的政权颁布了《拿破仑法典》,一部确立革命的某些基础的民法典:个人自由、信仰自由和财产权。过去的贵族和阶级特权被取缔,确立了完全世俗的政权。民法典的影响巨大而长久。但在进步的条款之外也有一些反映拿破仑对民主的憎恶的规定。法典压制了女性的权利,并以损害雇员的权利为代价加强了地主和雇主的权利。拿破仑支持启蒙时代对科学和理性的信念,但他蔑视公众意志和议会辩论。在这些方面他和德国的启蒙主义者,包括贝多芬(他也不相信民主,虽然尊敬议会制度)并不远。
因此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对贝多芬和许多其他人来说,“拿起和丢掉”拿破仑的过程将会继续。实际上,在法国仅与英国作战几年后,与奥地利的条约不再有效,新的反法同盟再次形成,因此演出一首称为“波拿巴”的交响曲不再安全。同时,战事再起也毁了贝多芬“不可挽回地”去法国旅行或定居的计划。
因以上原因,第三交响曲将以《“英雄”》为标题闻名于世。但就像贝多芬告诉出版商的一样,它确实是《“波拿巴”》。

在第三交响曲之前,交响曲和协奏曲主要被认为是公众体裁,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短时间内搞定的流行作品,有时公开演奏中还或多或少是视奏。海顿和莫扎特在这些限制下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贝多芬正在改变这种形式。一次又一次试奏后,前所未有的音乐逐渐在音乐家们的心灵和手指上刻下印记。
第三交响曲的首演定为1805年7月在维也纳河滨剧院举行。它是小提琴家弗朗兹·克莱门特(Franz Clement),贝多芬和剧院乐队指挥的友人的一场慈善音乐会的一部分。首演之前这首作品在罗布科维茨的宫殿至少试演过四次,在另一个音乐爱好者家中至少试演过一次,每次都有受邀的来宾参加。在排练期间,贝多芬做了一些试验和修改。卡尔·凡·贝多芬在给布赖特科普夫和黑泰尔的另一封信中再次试图出售乐谱,写道:“还没有听到交响曲之前,我哥哥相信如果第一乐章的[呈示部]反复的话会太长,但几次演奏后他认为第一部分如果不重复效 果不好。”贝多芬担心乐章的长度会令听众疲倦,但最后他决定按心中音乐的需要行事。
有传言说大事即将来临。海顿的老朋友和贝多芬的新相识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冯·格利辛格向出版商戈特弗里德·黑泰尔汇报:“交响曲在罗布科维茨大公的学园和一位名叫维尔特(Wirth)的活跃音乐爱好者住处已经演奏过了,赢得了非同寻常的掌声。这是天才的作品,贝多芬的仰慕者和诋毁者都这么对我说。有人说音乐中的东西比海顿和莫扎特的多,说交响曲被提升到了新高度!反对它的人认为整首作品缺乏整体性;他们不喜欢宏大乐思的堆砌。”
在公开首演之前,《大众音乐杂志》的第一位乐评家对它的评论不那么友好:
这首长作品,特别难以演奏,确实是非常宽广地扩展,是大胆、无拘无束的幻想曲。它并非完全缺少惊人和美丽的篇章,其中可以认出它的创造者的精力和天才的精神;但它常常听上去迷失在无规律中……评论者确实是凡·贝多芬先生最真挚的仰慕者之一。但在这首作品中,他必须承认他发现了许多刺耳而古怪之处,因此全曲的概观并不清楚,整体效果几乎完全失去了。
贝多芬再次被指责用这样一种自由但并不合适的体裁创作幻想曲,一种充满古怪乐思,曲式不明确的散漫乐曲。他作品的多数早期乐评都是这样的。
1805年4 月7日在维也纳河滨剧院举行的公开首演中,听众们一定感到迷惑不解。他们无法想象音乐的未来多么依赖这首费解而恣肆的作品。没有节目说明帮助他们理解,当时它也没有使用“拿破仑”或“英雄”的标题。和往常一样,贝多芬的指挥也怪模怪样:在响亮的乐段,他踮起脚尖,转动手臂,就像尝试飞起来一样;在弱奏乐段,他几乎要匍匐在指挥台上。
听众们坐着听完了奇异、宏伟的第一乐章,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要第一次听就能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爱乐者们无法抓住飞逝的似乎还未成形的主题,等待着从未清楚出现的熟悉的曲式标记,以及从未真正到来的解决和高潮。他们听到再现部之前圆号在错误和弦上的进入,以为这是个尴尬的错误。卡尔·车尔尼在场,据他说,演到一半时有人喊道:“如果这种东西能停下来,我会多付一个十字币!”不过,因为一个十字币比一美分值钱不了多少,这只是一个玩笑。
听众们觉得《葬礼进行曲》比较容易听懂。虽然曲式不同寻常,但它不像第一乐章那么复杂,他们肯定能听出它是一首法国风格的葬礼进行曲。知道op. 26钢琴奏鸣曲的人会想起那首作品中的葬礼进行曲,推测这首交响曲也是同样的一组特性乐曲的组合。明显令人愉悦的谐谑曲大概激起了一些掌声。但对当时的听众来说,芭蕾音乐和英雄宣言的混合音调的终曲变奏曲应该是最奇特的。最后,贝多芬显然被稀疏的掌声激怒了并拒绝致谢。
他等着看全世界的反应。惊人的是最初的评论都试图显得平衡而温和。第一份较长的同时表示怀疑和尊敬的评论出现在《真诚》上:
贝多芬新的降E大调交响曲上演了,爱乐者和业余听众们对它的反响不一。贝多芬特别的好友们坚持认为这首交响曲是一部杰作,它是更高级音乐的真正风格,如果现在它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是因为公众的艺术教育还不足以让他们理解音乐中所有高贵的美。但过了几千年后它们一定会见效的。另外一些人完全否定了这部作品的任何艺术价值,认为它显示了对特异和古怪的毫无限制的追求,它完全不美,也没有崇高和力量。通过奇怪的转调和粗暴的对比,将最歧异的东西放在一起,例如以宏伟风格演奏的田园风旋律,大量刺耳的低音,三支圆号等等,这种真正的,但并不令人喜爱的独创性并不需要花很大代价获得。然而,天才并不仅仅因与人不同、想象力丰富而成功,而必须通过创造美和崇高。贝多芬自己在他之前的作品中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还有极少数人站在中间;他们承认交响曲有很多美丽的地方,但承认音乐整体常常完全不连贯,这首最长,可能是最难的交响曲似乎永不结束的 长度甚至令资深爱乐者都无法忍受,更不用说一般听众了。他们希望v. B先生能够运用他广为人知的伟大天赋为我们提供和他前两首C大调和D大调交响曲,他优雅的降E大调七重奏,有精神的D大调五重奏,以及其他早期作品类似的音乐,这样B.就会永远和最伟大的器乐作曲家处于同列。但他们害怕如果贝多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他和音乐都会走上邪路……公众和自己指挥作品的v.贝多芬先生在当晚互相不满意。对公众来说交响曲太难、太长,B.自己太没礼貌,因为他对鼓掌的听众连点头致谢都做不到。
事实上贝多芬不可能期望比这更好的首演评论了。但他不会这么看这篇乐评,下一代人也不会这样。后来,像这位乐评家一样的人引发了关于天才和革命不可能在他们的时代被理解的浪漫主义神话。
但接下来几年中对这首交响曲的评论并非如此。(1806 年后,乐评家们可以研究出版的乐谱,它已加上“英雄”标题。)《大众音乐杂志》上的第二份评论出自同一位乐评家:
在音乐会上我听了贝多芬新的降E大调交响曲……由作曲家自己指挥, 演奏的是一个实力优异的乐团。但这次我并没有理由改变我之前的观点。确实,这首B.的新作品有伟大和惊人的乐思,且符合我们对作曲家天才的期待,它的谱曲有巨大的力量;但这首交响曲会大大改善(它持续一整个小时),如果B.自己能够将它删减,并令全曲更轻松、明晰、统一。
它的实际长度是40—45分钟。据说贝多芬说过:“如果我写一首一小时的交响曲,人们会发现它足够短。”他的意思是他会按自己的想法决定作品的长度,听众一定会接受——总体上说,确实如此。对作品的不理解在其他地方同样发生。
但乐评家的意见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807年1月的《大众音乐杂志》对交响曲在曼海姆演出和出版的乐谱评论道:“第一乐章很感人,非常有力而崇高……葬礼进行曲新颖而有着高贵忧郁的个性。尽管考虑到它与外乐章的关系,我们仍然乐于沉浸在它激起的情感当中……谐谑曲一小步舞曲是一段非常活泼、不断运动的音乐,三声中部中三支圆号的持续音提供了特别出色的对比……终曲有很高的价值……然而,它仍然不能避免被说成特别古怪。”
仅一个月后,《大众音乐杂志》称第二乐章是无法“由任何没有真正天赋的人想象、创作、达到如此完善地步的胜利”。1807年4月的《大众音乐杂志》在一次莱比锡的演出后评论:
城里最高水准的艺术之友大量聚集在一起,笼罩在真正严肃的注意和死一般的寂静中……每个乐章完全无误地表现出应有的效果,每个乐章结束后响亮的鼓掌声表现出听众们的巨大热情。乐队自愿集合进行更多的无偿排练,仅仅为作品本身的伟大和特别的愉悦……因此这首最最困难的交响曲……的演出不仅仅是极为精准……在研究后,在排练和公开演出中多次聆听这首作品后,我们只想说第一乐章,如火般宏伟的快板,它惊人的多样性 与完全的整体性相结合,它明晰而纯净同时又极为复杂,它非常长,而它的美妙令人无法抗拒,它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乐章。
两年间评论意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乐评家和许多听众对这首最为困难,史上第一次要求多次聆听,或许必须研读乐谱才能真正理解的交响曲的热情急速增长。但《“英雄”交响曲》的风格、规模和前所未有的雄心反映了拿破仑时代的精神,因此人们很快就理解和喜欢上了它。1807 年,时尚杂志《奢侈与流行杂志》(Journal des Luxus und der Moden)按流行的说法称它为“最伟大,最独创,最有艺术性,同时也是最有趣的交响曲”。数年后,第三交响曲甚至成了交响曲的代名词。1810年2月的《大众音乐杂志》写道:“无论对这首丰富而宏伟的艺术作品说什么都是肤浅的。”《“英雄”交响曲》的回响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费迪南德·里斯曾说他认为这首交响曲演奏时天堂和大地都会震动。在象征意义上,他的预言是正确的。
对贝多芬来说,它的影响更加直接、相关。他总是有敌人,恶毒的敌人——尽管他一直认为他们比事实上更大量、更恶毒。虽然胜利永远并非完美,但它仍然必须被称为最高层次的胜利,正如他所希望,也是他完全应得的。至少直到第九交响曲的创作,他在自己的交响曲中最喜欢《“英雄”》。但它仍然不够好,从未足够好。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超越《“英雄”》,但他愿意尝试,在相当不同的方向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