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专题 | 虞云国:海上之盟作为金宋关系起点再审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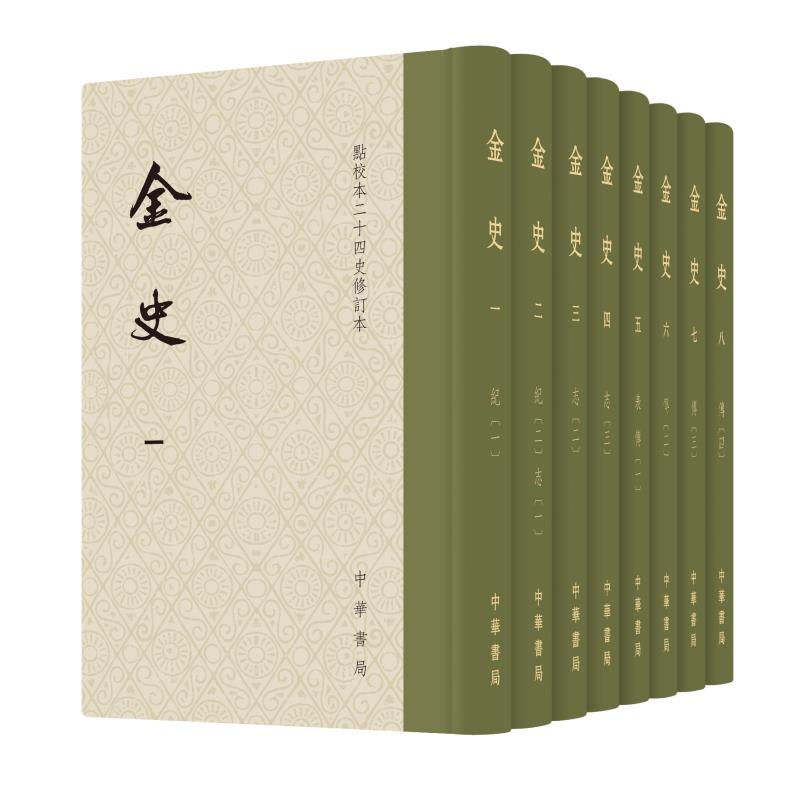
一
后代对元修《辽史》《宋史》与《金史》颇多批评,但元朝史官对辽、宋、金三朝一视同仁,各予正统,虽有承袭辽金统绪而同为少数民族主政的自身考量在内,客观上仍值得充分肯定。元修三史保存了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历史的最基本资料,相对说来,《金史》质量最好,评价也最高。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金毓黻就强调:“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宋辽金史》)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前言》里,邓广铭先生更是强调:“宋史研究会的会员同志们所要致力的,是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决不能局限于北宋或南宋的统治区域”,首倡“大宋史”观。其后,也有辽宋西夏金通史问世,但似乎仍是按时段与分专题的辽史、宋史、西夏史与金史的汇总。由此引发两个感想:其一,从字面上看,“大宋史”总让人产生这一时段中国史以宋朝为主导的感觉;其二,“大宋史”虽早有登高一呼的引领者,但在后继者那里,因学力不逮或识见所囿,仍不免各司其职而分多于合,诚可谓任重而道远。
上世纪末叶,相继有学者倡导“中华一体”论(张博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费孝通),这是出于维护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政治考量,为中华民族构建的古代共同体,当然有其必要性。而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民族政权,也确实都有自称“中国”的文献证据。但这里的“中国”,其内涵实即“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毕竟不能等同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在这一长时段里,与北宋相继并峙的辽朝、西夏与金朝,与南宋先后共存的金朝、西夏及后来蒙元,都不是当时中国境内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与宋朝长期抗衡的独立政权;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境内不同独立国家之间的对等关系,而不再是前朝曾有过的中原王朝与北方周边民族的关系。我在撰写《细说宋朝》时尽可能地贯彻这一认识,并在《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互动》(《两宋历史文化丛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有过集中的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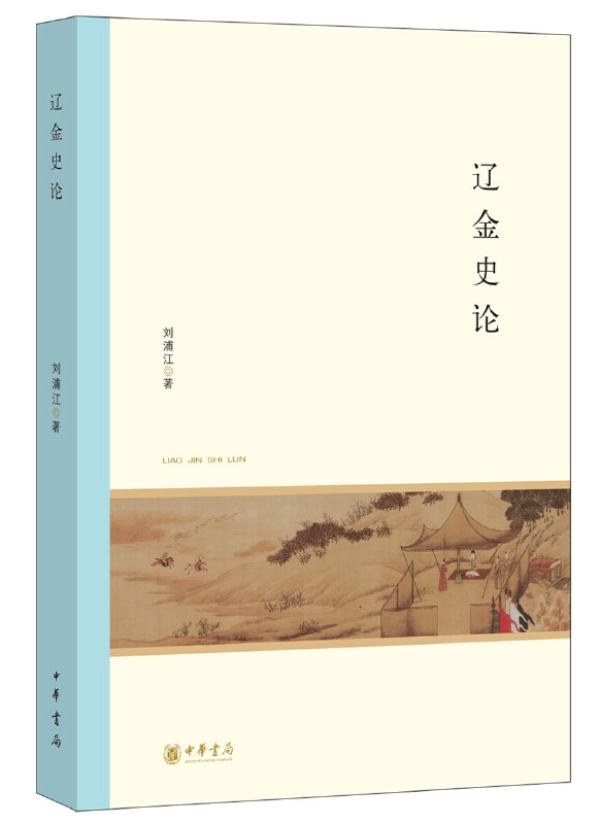
已故辽金史家刘浦江自序《辽金史论》时指出:“尽管有不少宋史研究者声称他们兼治辽金史,可深究起来,他们感兴趣的无非是宋辽、宋金关系而已;而所谓的宋辽关系史,实际上是宋朝对辽关系史,所谓的宋金关系史,实际上是宋朝对金关系史。”他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却言之有理。反躬自问,作为宋史学者,我入门之初读过《辽史》与《金史》,在其后研究中也一再查阅与利用过辽金二史;《细说宋朝》也述及辽朝、西夏、金朝的史事,对宋辽关系、宋金关系与宋蒙关系的关注则更深入。好在我从没敢自称“兼治辽金史”,确如他所说,我“感兴趣的无非是宋辽、宋金关系而已”;在论说宋辽关系与宋金关系时,尽管也较自觉秉持“中国境内诸政权互动”的平等意识,但仍习惯以宋朝视角加以考察,论述的更多确是“宋朝对辽关系史”与“宋朝对金关系史”。
继廿四史点校本《辽史》修订本出版之后,中华书局新近推出了修订本《金史》,将有力推动辽金史研究,对宋史研究也贡献了后出转精的最佳点校本。作为宋史学者,我也仍将从金宋关系史视野利用新校本。金宋关系长达两个甲子,其中可分若干时段,每个时段开端都构成新的节点,限于篇幅,本文仅以金宋关系起点“海上之盟”作为切入点,重新审察这一事件如何深刻影响中国境内乃至东亚诸政权互动,进而浓墨重彩改绘地缘政治版图。题目之所以称“金宋关系”而不作“宋金关系”,一方面当然试图摆脱原先立足于宋朝的局限,一方面揆诸双边关系,较之宋朝,金朝确实在包括海上之盟在内的更多节点与时段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反观海上之盟的金宋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在当时中国境内乃至东亚连锁搅动了其他政权参与的多边角逐。
二
1114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以宁江州(今吉林松原石头城子)之战拉开反辽序幕,随即取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茂兴古城)大捷。就在这年,燕山大族马植见辽朝败相已现,密见赴辽的宋使童贯,献“取燕之策”,童贯约其伺机归宋。1115年,金朝正式立国;马植则易名李良嗣,弃辽投宋,受到宋徽宗召见。他的“联金复燕之策”,鼓荡起宋徽宗、童贯、蔡京等君臣久蓄于胸的“燕云情结”,大获赏识,赐姓赵良嗣。1118年,宋派马政率使团横渡渤海,进入辽东女真控制区,与金太祖阿骨打商议联金攻辽的可能性与具体细节,是为“海上之盟”。
从表面上看,海上之盟由宋朝主动发轫,但接受与否的决定权却在金朝。史书记载,阿骨打与心腹大员“共议数日”(《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下称《会编》),才下决心订立联宋攻辽的盟约。金朝虽欲借宋朝之力对付辽朝,1120年进入正式谈判时却首先坚持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原则,拒绝以上行下的宋朝“诏书”,表示只接受对等交往的“国书”。金太祖随即让宋使赵良嗣前往观看金军攻取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之战,以轻取上京的军事实力作为主导金宋谈判的筹码,并在结盟条款上明确规定:金取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宋取燕京(今北京);灭辽以后,“许燕京七州”归宋,“而不许云中及平、滦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而并非宋朝一厢情愿的原“燕云十六州”;宋朝将原交付辽朝的五十万岁币转致金朝;订盟之后“不可与契丹讲和”(《会编》卷四)。由此可见,在确立盟约条款中,金朝完全占主导地位,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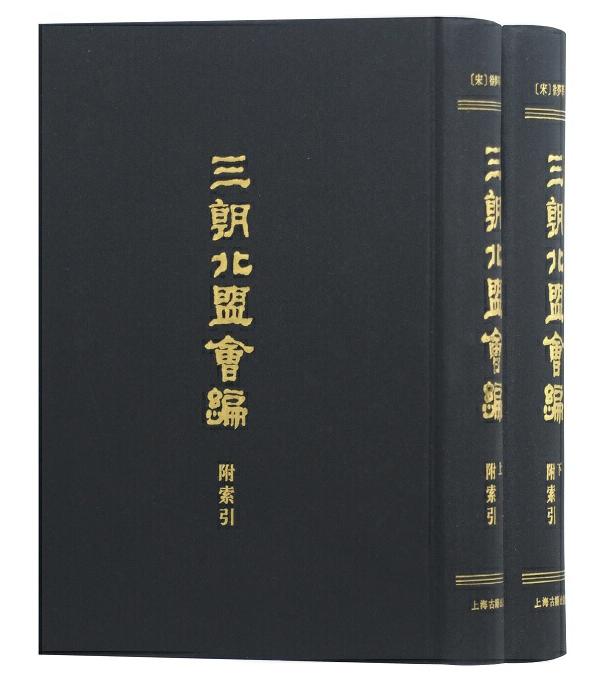
相比之下,宋朝在决策海上之盟时毋宁说是轻率而颟顸的。其始初动机只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燕云情结”,试图借金反辽之机轻松收回后晋割让辽朝的燕云十六州,对这一决策必然引发的多方连锁反应缺乏缜密深入的全局分析与长远预判,不仅严重低估辽朝的抗衡能力,而且忘乎所以地高看自己的军事实力,对最大变量的金朝更是掉以轻心。宋朝一意打算收回的是全部燕云十六州故地,但宋徽宗在付与缔盟使者赵良嗣的御笔里却交代:“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会编》卷四)这道御笔有两大失误。一是结盟谈判未开,已先将辽朝在辽宋关系中的既得利益与主导优势拱手转送金朝;二是将宋人所指的“燕云十六州”故地混同于“燕京并所管州城”,浑然不知后者仅指辽朝南京析津府(即燕京)管辖的“燕京七州”。在边界谈判前,一国之君竟出此荒唐无知的指导性御笔,足见决策行事之懵懂草率。尽管在谈判中赵良嗣力图扩大燕京的辖区,要求将西京(今山西大同)等其他诸州都包括进去,却被金人以不属燕京管辖为由断然驳回。赵良嗣复命,宋朝再派马政出使交涉,尽管这次在国书中逐一注明燕云十六州,却遭到金朝断然拒绝,不惜解约了事。两国关系从来以实力发声,宋朝只得服软。
1122年,金人约宋履约攻辽。宋朝由领枢密院事童贯主兵,他刚镇压方腊不久而踌躇满志,两次率师北上伐燕,孰知一败再败。面对覆亡在即的辽朝,宋军竟也露出了银样蜡枪头,不得不请求金朝出兵。尽管宋军无能,但金宋结盟压缩了辽朝的生存空间,更对辽天祚帝形成心理威慑,他先后拒绝西夏约攻宋朝与联手抗金的请求,最后放弃燕京向西出逃。与此同时,辽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随之激化:燕山地区汉人实力派另立天锡帝耶律淳,号称“北辽”,在和宋与降金之间首鼠两端;耶律大石则审时度势,毅然脱离天祚政权,突围西行,建立西辽。
1122年岁末,金太祖攻克燕京。宋军因未能履约自取燕京,宋徽宗不得不照单全收金朝追加的苛刻条件,接收了燕京及其下属六州;对内却命王安中撰写歌功颂德的《复燕云碑》(值得指出的是,云州等地未归宋朝实际接收,但宋徽宗集团对内隐瞒了这一信息,北宋军民庆贺的却是收复“燕云”),似乎真的由他完成了太祖、太宗的未竟伟业。至此,金宋海上之盟全部交割完毕,金朝却看穿了宋朝麒麟皮下的马脚,“自此有南牧之意”(《会编》卷十六引《秀水闲居录》)。
宋朝仍不自量力而自作聪明,次年竟私下接纳了由金朝任命的燕京留守、原辽朝旧臣张瑴,唆使他叛金为宋朝火中取栗,收复全部燕云故地,全然不顾盟约条款有“不得密切间谍诱扰边人”(《大金国志》卷三十七)。金朝讨伐张瑴,缴获了宋徽宗“御笔金花笺手诏赐瑴者”(《会编》卷十八引《北征纪实》),援约向宋朝索取张瑴。接到朝廷指令,前线主事者“斩一人似瑴者”以搪塞金人问罪,金朝识破李代桃僵,扬言兴师自取。徽宗闻讯,立马认怂,密诏杀死张瑴,函首金朝。这一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之举,让已获金朝特许归宋统辖的原辽朝常胜军彻底寒心。1124年,就在灭辽大局铁定的当口,宋徽宗却命一番僧为使者,“赉御笔绢书”,去招降危在旦夕的辽天祚帝,或许想再玩一把联辽抗金的儿戏。金军截断了天祚帝南下之路,遣使援引“海上元约不得存天祚”,责问“中国(指宋朝)违约”(《会编》卷二十一引《北征纪实》)。宋朝自以为得计,一再背盟违约,日渐引起金朝最高统治集团的严重反感。出于诸种因素的叠加,1125年,金太宗在灭辽之后,彻底终结金太祖与宋结盟的基本政策,正式向宋朝开战。次年,金东路军南攻燕京,郭药师统领常胜军虽有守土之责,却阵前反戈,倒向了金朝。燕地复为金有,宋徽宗的“燕云”梦也终成烟云,但金宋关系再不可能回归海上之盟前的原点,先前的盟友已转化为今日的敌手,等待宋朝的是灭顶之灾的靖康之变。
三
倘若跳出中原王朝与汉族政权的狭隘立场,将视野放宽到十二世纪初叶中国乃至东亚的大格局下,对海上之盟引发诸政权的多边互动及其应对得失,很有必要再作客观理性的历史评说。
海上之盟前夜,辽朝稳据当时中国境内与东亚的霸主地位。在澶渊之盟后,辽朝与北宋和平相处,虽以兄称宋,但每年都接受对方的岁币,明显处于强势。辽朝与西夏既是宗藩关系,又有政治联姻,结盟以抑制宋朝。十世纪末,辽朝已取代宋朝对高丽行使册封权,明确了宗藩关系;澶渊之盟后,高丽对宋朝国书中表达的宗藩关系仍予默认;辽朝容忍北宋高丽间的朝贡关系,未多加干预,也缘于自己对高丽的影响力在宋朝之上。
然而,辽朝未能善处与境内女真民族的关系,激怒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海东青便成为打破东亚政治平衡的黑天鹅。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金宋随之谋划订立联手灭辽的海上之盟,对金宋双方来说,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关键在于,订盟与履约过程中双方之间的斗智与角力是否具有道义合法性与策略可取性。综上所述,金朝最高决策层在订约前慎重权衡,在订约中坚持结盟的对等性,以明确的条款规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掌控着结盟的主导权;在履约过程中既承担了约定的军事责任,对条款确定的应得利益也寸步不让,行事上无可厚非。其后,宋朝虽在军事上未有实际助力,但金宋结盟在声势上鼓舞了金军的斗志,重创了辽朝的士气人心。面对辽朝顽抗与宋朝失信,金朝凭实力说话,不断扩大战果,获取利益,不仅灭亡了辽朝,也洞烛了宋朝的腐朽。金朝灭辽前一年,已威慑西夏,迫使其审时度势,以事辽之礼承认金朝的宗主地位。高丽在文化认同上虽 “乐慕华风”(郑麟趾《高丽史》卷十五《仁宗世家一》)而倾向宋朝,但靖康之变前一年,目睹在金军凌厉攻势下北宋已命在旦夕,也不得不终止自金朝立国以来依违于宋金之间的观望态度,改奉金朝正朔,确认金丽之间的宗藩关系。1127年,金灭北宋,继辽之后成为中国境内与整个东亚的霸主,在声威上也更高出辽朝一头。在金宋关系起点上,金朝无疑是海上之盟的最大获益者。
不言而喻,辽朝则是海上之盟的最大受害方。辽朝在军事上虽未受到宋朝多大的威胁,但昔日兄弟之国与当下敌对之国结盟对付自己,对其军心民心的瓦解作用不容低估;又未能借助藩属国西夏主动援辽之请,增强制宋抗金的实力,始终陷于被动应付之局。作为金宋海上之盟的直接牺牲者,辽朝不仅终结了昔日霸主的地位,而且吞下了覆亡的苦果,从政治地图上被抹去;西迁中亚的大石政权虽承契丹余绪,但已黯然退出了东亚。
最后来看宋朝,出于“燕云情结”起意海上之盟,虽未可厚非,但决策轻率,对结盟后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局也未有远虑。宋朝在订盟之际便未争取主导权,在条款措辞上行事昏愦,履约过程中还一再失信。更因高估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北伐失利出乖露丑后,仍执著于“复燕”梦,措置乖张,乃至频出昏招,虽以高昂代价换来了几座空城,随着辽朝覆亡,宋朝唇亡齿寒,金朝却从盟友变为敌国。金太宗南侵灭宋,在道义上当然有其非正义性;但宋朝自海上之盟起就一步步踏上了不归路,不仅未从中获益,反而留下靖康之变的亡国惨痛。建炎南渡虽延国祚于东南,却退出了中原;在中国境内的地位,也从与辽朝基本对等的兄弟之国屈辱倒退到与金朝的君臣之国,成为仅次辽朝的大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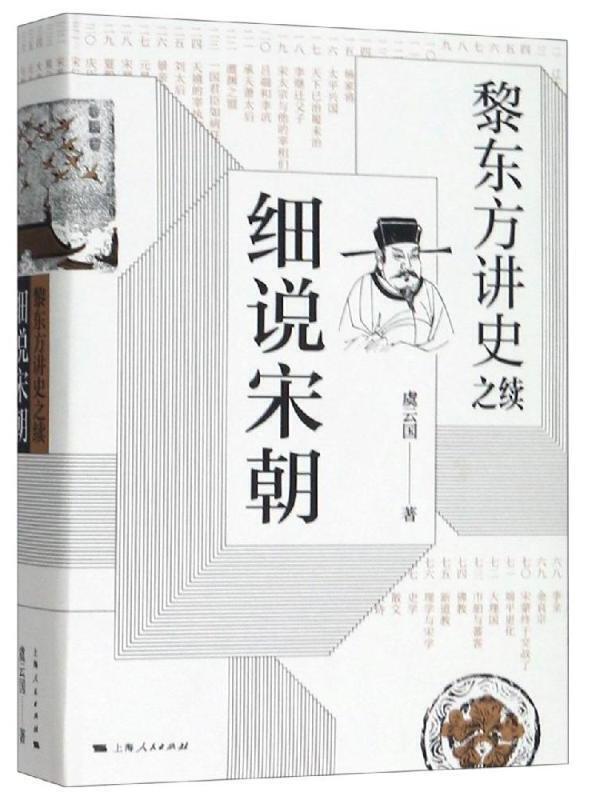
后人往往认定,对宋朝来说,海上之盟无异于玩火自焚而自取其祸。这一说法,看似有理,却值得商榷。据王夫之分析,当时宋朝不外乎三个选项:“夹攻也,援辽也,静镇也。”“夹攻”就是海上之盟的联金灭辽,即“自蹈于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援辽”旨在“辽存而为我捍女直(即女真)”,但从童贯攻辽一再惨败,便足以推断:既然“攻之而弗能攻也,则援之固弗能援也”。“静镇”就是“守旧疆以静镇之”,即“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直而勿夹攻,不导女直以窥中国之短长”;但他随即指出,金朝挟灭辽之锐气,也必然“以吞契丹者齕我”,宋朝仍不可能“划燕自守”。据王夫之所见,以当时宋朝的财赋实力,“尽天下之所输,以捍蔽一方者,自有余力”;以兵力论,从建炎初年的两河抗金到渡江之后的江南周旋,若非童贯之流掌兵,官军也“犹堪厚用”;而宗泽、张浚、赵鼎等“俱已在位”,中兴四將“勇略已著”,论将相人才,也可谓“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无才也”。据他所论,宋朝“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无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质言之,无论当时抉择哪个选项,宋朝都无往必亡。在他看来,倘若“庙有算,阃有政,夹攻可也,援辽可也,静镇尤其无不可也:唯其人而已矣!”也就是说,只要庙堂决策高明,将相政略得当,任何选项无不可行,“静镇”更是上选,关键在于主国之人。那么,宣和年间(1119-1125)主宰庙算与阃政的是哪些人呢?他在另一处直斥道:
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非必亡之势。(《宋论·徽宗》)
其激愤的抨击虽不无情绪化倾向,但仍比那种皮相之见更中肯綮。仅仅七年,宋朝就从海上之盟一路狂奔,跌入靖康之变的惨境,究其根本,宋徽宗与蔡京等“六贼”的最高统治集团才是这“必亡之势”决定性的内因与主因,金宋海上之盟充其量只起因缘际会的催化剂作用。船山史论倒也颇有外因通过内因才起作用的辩证因素。
历史有时似乎会重演。即以南宋而论,出于靖康之耻的民族主义情绪,复有1234年的联蒙灭金之举。但近乎重演的历史毕竟不是全息克隆版,我曾将北宋末年的联金灭辽与南宋后期的联盟灭金作过比较: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情绪和收复失地情结在两个决策中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海上之盟完全是徽宗集团出于对三国关系和实力的盲目估计,主动作出了错误轻率的决策。而联蒙灭金的选择,南宋无疑较理智地分析了当时三国关系的既有现状,虽明知唇亡齿寒,却出于被迫和无奈,以便两害相权取其轻,因而不能简单将其与海上之盟混为一谈。(《细说宋朝·金哀宗》)
由金宋海上之盟延展开去,必然涉及北宋覆亡的沉重教训,虽已超出海上之盟作为金宋关系起点的预定论域,却仍值得后人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