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纬读《饥饿中成长》︱饥饿病——当下最致命的“疾病”
饥饿症(hyperphagia)是一种因人体的生理机能发生紊乱造成的疾病。然而,饥饿病(hunger epidemic)不是一种病,它是人们无法得到食物、居无定所而引发的一系列身体和社会问题。任何天灾人祸都会引爆它。但是,当一个人在和平盛世沦落为乞丐或者流浪者时,大部分人对他们都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这个人太懒?还是他是瘾君子?骗子?精神病患者?难民?《饥饿中成长》(Loretta Schwartz-Nobel, Growing Up Empty, HarperCollins, 2003)告诉我们,事实并非那么简单,这还可能是社会制度、法律制度或政府政策等方面不够完善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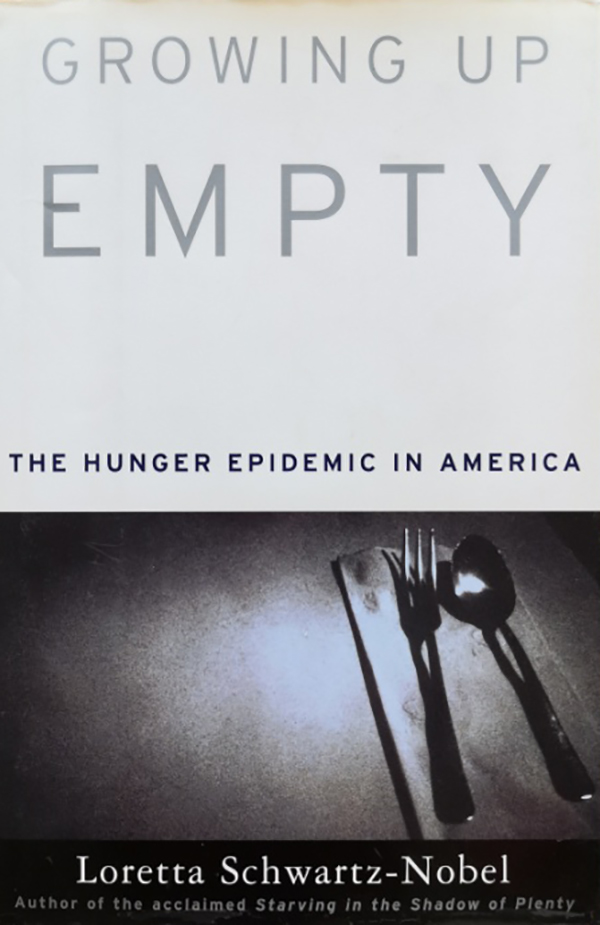
站在美国95号高速某出口“停车”牌下的乞讨者
知名记者洛雷塔·施瓦兹-诺贝尔走遍美国,访谈了城市贫民窟、乡村棚屋甚至中产阶级家庭中的饥饿者,于十七年前完成了《饥饿中成长》。除了各机构的职员和志愿者,出于保护当事人的考虑,作者一律采用化名。置于今日,该书仍极具参考价值。最近,洛杉矶的流浪者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2018年,一万人里便有十七名美国人成为无家可归之人;同年,九百一十八人暴尸街头。2019年9月份刚过,死亡人数已经高达一千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三人死在了洛杉矶街头。在这群流浪者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曾经的华尔街银行家和企业家肖恩·普莱森斯(Shawn Pleasants),他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流浪者中不乏音乐家和摄影家。
破碎的婚姻
十八岁那年,洛雷塔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八年后第二个孩子降生。当时的丈夫是一位医生,现在小有成就。正当她为研究“饥饿”问题忙得不可开交,并获得一定知名度时,她的前夫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提出了恢复自由和结束婚姻的要求。迫于生计,她不得不搁置兴趣,撰写报酬较高的商业性主题。
犹太女子鲁思的状况更惨。受访时,她仍然居住在一个高档社区。跨进社区,触目是瑰丽的建筑、豪华的私人轿车和精心养护的绿地,甚至连普通商店看上去都很高级。四年前,在他们全家整装待发准备参加一次重大的家庭聚会时,丈夫说他和办公室助理有了私情。他连哄带骗,将岳父和妻儿们送出了家门,自己则坚持留在家中。回到家中,鲁思崩溃了,丈夫不见了,连同他的衣物和所有文件,除了桌上的两百美元。
失去了经济支柱,还有三个小孩待养,年迈的父亲留存的一点积蓄也很快被花光。他只是离开了,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房子也在他的名下。她和孩子们不能领取政府救济,她也不能卖掉豪宅,父亲的退休金在筹房款时已被她掏空。上法庭,她没有钱雇请律师。她翻箱倒柜,幸运地找到了五千美金。在法庭上,他态度绅士、衣着体面,而她看上去却更像一位精神病患者。最终,法院判定她的先生必须定时支付孩子们一定的抚养费。事实是,他只有心情好的时候,才会每过八个星期支付一点微薄的抚养金。成为家庭主妇的时间太长,她只能找到兼职。兼职不允许请病假,不代缴社会医疗保险。1995年,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指出,有一千一百五十万单亲父母有孩子的监护权,当中只有六百四十万人有正式的子女抚养协议。在达成协议的人中,只有一半(约三百二十万)的人收到部分付款或全部付款。2016年的数据表明,这种状况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一个人享受惯了奢侈的生活、穿惯了精致的衣服,一旦贫穷降临时,往往受伤更深,生活也会变得更艰难。后来,鲁思的丈夫申请了破产,房屋被银行拍卖,水电也被掐断。她利用自己在犹太人教堂掌管食物的权力,偷偷往自己家里拿食物,比如花生酱之类的,平时也去食物储藏室(food pantry,为饥饿家庭免费发放食物的地方)。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叫饿,她只能提供薯片给孩子们充饥。她可以为孩子们申请学校的免费早餐和午餐,考虑到那样做,孩子在学校可能会遭受同学们的凌辱,她坚持给孩子带上金枪鱼三明治当午餐。访谈时,鲁思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怨恨。
在最后一次家暴中,伯莎被丈夫打残,腰部以下全部瘫痪。伯莎带着两个女儿居住在不见阳光、蟑螂横行的破屋子里。谈到已经故去的丈夫时,她没有任何怨言。她出生于一个饥饿的单亲家庭,母亲酗酒,大部分钱都用来买酒。七岁那年,母亲和两位兄弟外出乞讨时,她被一位身材高大的男性强暴了。自那以后,她害怕和男性交往,直到遇见她的丈夫——乔治。乔治令她浴火重生,但是军队生活改变了乔治。
退伍之后,乔治变得不顾家庭,整日外出,只在她领工资的那天出现。有一天,当她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晚餐时 ,乔治毫无理由地对她拳打脚踢,最终她的脊椎骨断裂,躺在地上昏迷不醒。邻居和她的孩子将不省人事的她抬到了床上,而不是医院,因为邻居没有报警。邻居说她一路看着乔治长大,认为他一直都是好孩子,她不想让他坐牢。据美国反家暴联盟统计,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和四分之一的男性遭受亲密伴侣的身体暴力。家暴不仅使女性的身心遭受严重创伤,也往往迫使她们处于失业的边缘,即使身体正常,她们也完全无暇顾及工作。
从贫穷到贫穷
伯莎说军队改变了乔治,不妨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军属,看看普通的军人家庭生活。1984年8月,十三岁的丹尼在家中后院自杀。自杀前他留下了一张字条:“亲爱的妈妈,我爱您,希望您不要因我悲伤。至少我死了,您还可以少养活一口人,一切即将变得更好。”他的父亲是陆军中士,当时正在韩国服役。事实上,当时他们的家庭已经比其他军队家属条件要好一些了,他们享有一千三百美元的无息贷款,还有紧急食物供给,但对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服役,未计入)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他们经常食不果腹。懂事的丹尼终日收集易拉罐,仅仅是为了筹钱给家里买食物。
1982年,军队的薪水低于国民收入将近百分之十四,到2000年时稍微有点提高,但仍然存在百分之十一的鸿沟。通常军队提供的住房补贴和食物补贴是微不足道的,有家庭的军人不得不在离服务场所很远的地方租房,这样又额外增加了买车的收入,拥有了车又意味着增加了其他支出,比如说保险、税和汽油。如果能够入住部队提供的住房,他们可以免费使用水电煤等,但是房源紧俏,申请到的几率非常小。
即便如此,仍然有人梦想着通过入伍改变现状。尤其是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常常抵挡不住宣传的诱惑,或者深受祖父辈的影响,选择参军。政府承诺军人享有免费的医疗保险、牙医保险和衣物折扣优惠。除了衣物折扣优惠,军属无法享有其他福利,而且衣物通常都是属于比较好的品牌,折扣下来的价格远不如沃尔玛这些低端超市出售的衣物实惠。约翰成长于一个困难家庭,他对政府救济轻车熟路。年少的他梦想着军队能够改变他的人生,使他的经济情况稍微好转。事与愿违,他得到军队的房子和简易的免费家具之后,欢天喜地地把妻子和年幼的孩子接到一起共同生活,却很快发现自己没钱了,不得不预支下个月的薪水。结果可想而知,他再次过上了依赖政府救济的生活。在妻子的眼里,军队里穷困潦倒的生活改变了丈夫,曾经异常贴心的丈夫被生活折磨得脾气暴躁,亲密的爱侣日益疏远。
过去到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不顾安危移民美国,追求“美国梦”。我认识一位来自东南亚的朋友,为了“美国梦”,她的父亲变卖所有家产,追梦过程也异常艰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父亲先送两个儿子冒着生命危险飘洋过海到美国。在儿子们获得了合法身份之后,他们全家才于八十年代飞抵美国。仍在当地生活的富有亲戚表示也想移民的时候,她告诫说,美国不是天堂,并不像移民中介宣传的那样,到处都是工作机会,帮人遛狗、当服务员、理发等等;美国还有其他昂贵的支出。
赛琳娜来自墨西哥,她的小儿子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就被判了“死刑”。出于母亲的天性,她坚持生下了儿子。两岁时,医生说她的儿子必须动手术,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未经过丈夫的同意,她偷偷地带着十来岁的大儿子和年幼的小儿子从美墨边境游到了美国,过着非法移民的生活。她和早几年来到美国的父母居住在佛罗里达,家具是从垃圾堆里淘来的,一盆绿色植物也是从街边捡来的。尽管现实里的美国不是天堂,生活依然艰辛,身份也不合法,还得终日担心遣返,但是,在墨西哥,她的儿子可能早已夭折,在美国,有地方提供免费医疗,她儿子的生命得以维系,赛琳娜心满意足。
如何摆脱饥饿
美国政府下发的救济粮票(food stamp)非常有限,而且审查制度相当严格,毫无人性化可言,甚至在申请过程中还可能遭受职员的言语凌辱。如果饥饿者找到了工作,不论工资是否足够购买日需食品,政府都可能终止这项救济。这对每天努力工作、承受高价房租、有多个孩子需要抚养的低收入家庭是严重的打击。部分教堂也会定期提供免费食物,问题是,饥饿者在这个教堂吃了顿午饭,下一顿晚饭便成了未知数。洛杉矶的普莱森斯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曾获得一部手机和电脑,他充分利用图书馆的免费网络获取各项资讯,将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有条不紊。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美国可以找到免费充电的地方,却不一定能够找到免费网络。
艾米由贫困的祖父母抚养长大,从小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十八岁那年,她眼睁睁地看着奶奶去世,作为一名卫校的学生,她感觉无能为力,认为读书无用。冲动之下,她选择了离校,与有车的表姐妹远驾到了举目无亲的佛罗里达。她没有任何的专业技能和特长,无法找到工作,却交了一个男朋友。在她怀孕之后,孩子父亲断然离弃了她。为了孩子不被政府强制送去寄养家庭,她只能偷偷在专门为男性提供服务的酒吧工作,为此又生了一对双胞胎。无奈之下,她带着三个孩子厚着脸皮回到爷爷身边。后来,她遇到了一位同样贫穷、拖家带口的丈夫,重新组织了一个五个孩子的家庭。他们租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房子里,直到被举报涂料含铅和地下室有蛇,不适合居住为止。幸运的是,在失去栖息之所之后,他们很快被“灯塔收容所”(Light House Homeless Shelter)收留,由于收容所制定的一些激励政策,他们还可能最终成为收容所提供的公寓的真正主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艾米那样的好运。大多数收容所床位紧张,实行男女分开制,孩子随母亲。收容所里人口杂乱,还充斥着暴力、偷抢、辱骂,最可怕的还有疾病。即使身处收容所,也不一定有充足的食物保证。一位受访者曾经在收容所目睹小孩饿得扑向被堵塞了的马桶,掏出污秽之物送往口中。极具讽刺的是,当没法通过正当渠道得到食物时,孩子的父母亲只能偷窃。假若被发现有偷窃行为时,政府便终止粮票供应。最终,家庭被拆散。大人进监狱,有房住,有饭吃。孩子被送往寄养中心,政府付钱给寄养家庭,让他们帮助抚养小孩。
政府的救济相当有限,众多运行良好的私人救济机构因此诞生。创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位于圣地亚哥的“乔神父村”(Father Joe’s Village),至今已经营了六十九年。他们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住房还有免费医疗。乔神父像精明的生意人一样经营着这个村子。为了不受政府的过度管束,他减少来自政府的经费支持,他们甚至得到了比尔·盖茨的捐款。浏览乔神父村的网站,我们可以看到因各种原因而失去家园和经济来源的案例,部分人在那里重振旗鼓。帕特里克是七个孩子的父亲,在他失去了电子装配专家的工作后,无力支付房租,他和家人被迫成为无家可归者,这时他们找到了乔神父村。年幼的孩子们进入村里的托管所,他和未婚妻可以安心地去寻找新工作。伊丽莎白因患细菌性脑膜炎而失去了经济来源和房产,但在乔神父村里得到较好的照顾,逐步恢复行走能力。
在佛罗里达州, 1989年两位女性创办了卡里达中心(Caridad Center),专门为当地农场工人家庭提供免费医疗和牙医服务,此外,还为他们提供食物、衣物和孩子家庭作业的辅导,该中心目前占地七千六百平方英尺。来到这里寻求帮助的人大部分是贫困的移民。当洛雷塔采访卡里达时,她说她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只是一个曾经的难民,一位踏上北美土地的寻梦人。一位受益于中心的移民说,在墨西哥一无所有,在美国他们至少可以吃到米饭和豆类,还有卡里达。
城市里流浪人群的增多,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景观。当看到新闻画面里的老鼠在流浪人群和他们的街头藏身之处来去自如,我不仅直打寒颤,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想起十四世纪流行整个欧洲的黑死病。根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到六十的人死于黑死病。后来科学家推测,这就是鼠疫引起的瘟疫。现在,大部分流浪者并不是直接死于饥饿,疾病和寄生虫才是他们的头号杀手。1995年国际世界卫生组织将“贫困”列为“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J. N. Hays, The Burdens of Diseas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10-313)。
在我即将为本文做个总结时,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脱贫专家,其中的“夫妻档”于2011年出版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贫穷的本质》。我未曾阅览过他们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不知道他们的研究是否能够为美国减少饥饿者做出贡献,但是,当我深陷各位饥饿者的故事中时,我发现生活有时候确实充满无奈或者不公,不可否认地是,有些人的境遇着实可以通过一个机构稍加引导和扶持,再通过当事人自身努力和做出恰当的选择而得到改善。
美国的部分收容所和其他救助机构早就意识到这点。随机点开一个收容所的网站,我们都可以发现他们的使命之一便是“帮助他们成长和培养独立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说,各个机构早就意识到摆脱贫穷的最好方法便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永久地免费提供救助。当然,针对身患重病、残疾在身和年老体衰的人群,则另当别论。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部著名的英国纪录片——《人生七年》(56 up)。自1964年起,导演迈克尔·艾普特(Michael Apted)对十四位七岁儿童进行长达四十九年的追踪,结果发现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似乎会世代相传。读完所有关于饥饿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唯一能帮助饥饿者的路径,是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同时,更注重精神上的支持,创造一个他们可以继续接受教育或寻找工作,从而获得稳定收入的环境。富人得了抑郁症,他们有足够的金钱接受药物和心理治疗。穷人得了抑郁症只会将自己的生活弄得越来糟。有些收容所相应制定了一些激励政策,比如提供一些家庭廉价房,穷人可以每月支付一定金额,到一定时间之后,便拥有房屋的所有权。上文提到的艾米,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还有收容所的影响,她逐渐意识到年轻时候的任性与无知,重新走进校园,希望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从而找到一份好工作。针对尚未成家的年轻人,也许学校需要培养他们规划人生的能力,比如人生目标和未来的家庭规模等方面。
希望饥饿不再困扰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