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艇的滋味:去划水吧,活成一条滔滔的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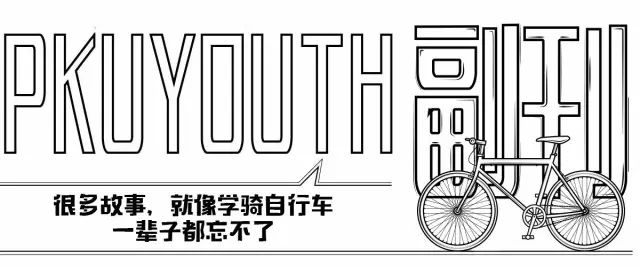
全文共3648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本报记者
张睿阳 国际关系学院2017级本科生
我在与水拼命博弈。偌大的湖像一块凝胶一样咬合着我的桨,两股暗劲缴缠在一起,桨撕裂水,艇劈开风,大风掀过救生衣,发出刺拉拉的声响。倏忽间,我把几十米抛在脑后,再回头看稻香湖被赛艇劈开的裂隙早就自我愈合。
艇像一枚细长轻盈的白叶子浮在水心,八根修长的桨成为叶脉,自然延伸到水中,我喜欢赛艇在水天之间自然漂浮的样子,平桨状态下把手搭在船舷,静止的人就变成了稻香湖的眉心痣。舵手一声令下,细长的赛艇就变成柳叶刀,飞速地切割稻香湖的皮肤,术后缝合的工作交给春风。
水绕桨的肢端,艇进我的生命。

△稻香湖深潜赛艇训练基地
移船相近邀相见
成为女子单桨八人赛艇队员,订闹钟起个大早,坐五块钱地铁去深潜中心划十几万的赛艇,对我来说曾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事儿。码字的时候看着被桨柄磨得皮开肉绽的手,还有掌心儿日益变厚的茧,才能切肤地感受到这个故事真实地开始了。


△稻香湖深潜中心装备配置
在春季选课网即将关闭的前五分钟,我决定用三十七个意愿点选李杰老师的地板球。但当我周二早上睡眼惺忪地出现在邱德拔时,却听见体育老师用充满磁性的声音说:“大家好,我叫郑重。”后来我才明白兵荒马乱的选课季点错行已然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身高一米七六,在地板球课上像一根奔跑的大葱,下课的时候郑老师把我和身高一米八的刘安纳一块留下:“你们愿意加入北大赛艇队吗?”
这是一支清奇的队伍。我、刘安纳和董金格分别被郑老师从地板球课和壁球课上猎取,张诗曼被从北大篮球队挖来,汤米·林赛晚上在五四跑步时被蹲守在操场的郑老师拦截,觉得他的身高和腿长具有赛艇运动员的天赋。剩下的人多被百团大战的传单吸引,招新那天一根单桨直插云天像一面大旗。四面八方招徕的人儿汇入同一条河流。

△女子八人单桨赛艇队
身高和力量是入门门槛,我侥幸凭借身高跌跌撞撞闯入这个大门。第一次见到队友们时,在心里惊叹这简直是一群曲线完美的丹顶鹤,他们在测功仪上训练的时候脊背挺得笔直,力量的瞬间爆发都被仪表上的数据和折线图捕捉,躯干四肢的动作完美流畅,真是兼具美与力量的尤物。
我有幸和这群人成了好朋友。北京春天的风和太阳都融化在稻香湖里,赛艇划起来带着风,董金格的卷发被揉乱后微微扬起,风的频率和桨的频率合拍。汗水被风锁在毛孔里,杨雨晴回头看的时候鼻尖渗出几枚细细的汗珠,被湖面反射的光照得亮晶晶的,就像刚刚被洗过的水蜜桃。太阳攀上脸,女孩们裸露的脚踝也泛起红色。男孩们划着四人艇闯入视野,四个人手臂的肌肉线条按着同样的节奏若隐若现,在湖的另一端吹口哨,不一会儿就划得很远了。这幅画就像是青春自然美学的最好诠释。

△男子四人单桨赛艇队
刚刚结束了一场训练,英国留学生汤米·林赛跟我分享自己烘焙的盐加多了的巧克力黄油饼干。那是我吃过最美味的手作饼干之一,尽管金格告诉我幸福感来源于芝士黄油的热量和训练四小时后的饥饿。去稻香湖的地铁耗时漫长,我就倚在柱子上听汤米用京味儿口音讲故事——他的父亲威廉·林赛先生是历史学家,带着全家来到中国,毕生致力于保护长城,汤米和哥哥用无人机拍摄了在英国BBC播放的长城纪录片。他酷爱跑步,参加过斯巴达勇士赛,也热爱着赛艇。
第一次见何菂师兄的时候,高达一米九的他像一棵挺拔的树。他在外留学时曾是剑桥大学赛艇队的主力军,保留着来自英国的一丝不苟的风范,一身笔挺的风衣配上西裤和皮鞋是训练前的标配,训练时把外套一褪就是专业的运动服,和印着小怪兽的袜子。当我今年第一次在朋友圈发了露出手臂穿裙子的照片,师兄开玩笑地评论:“手臂肌肉线条完全没有……你有认真训练过嘛?”
周二早晨的地板球课上,我又将与好朋友美籍亚裔留学生刘安纳相见。我们悄悄把手伸到对方面前,手心和拇指已经皮开肉绽,对称的伤痕像是孪生,两个人握着球杆相视一笑,地板球课上,这是只有我们两个女孩懂的小秘密。
长风破浪会有时
三月三十一日,大风裹挟北京,黑云压城。平时大大咧咧揣着手机上水的我,今天小心翼翼在手机外面套了塑料袋。我拧紧桨栓扣,上滑座,听水浪击打着艇身发出嘶吼。
风很大,我还在与水较劲、厮打和博弈。我总是喜欢掌控万事万物的安全感,我也想把水掌控,后来我才能明白,这世界上所有无形的、深不可测的东西都不可能被握在手心里,就像稻香湖里的水、藏在黑夜里的霾、云端的流体、哲人的思想,还有人心。我掌握不了湖水,可是我能握住桨柄,把笔直的桨插入水中,就是硬挺与柔软两个极端的博弈。
一不留神,桨入水太深,水吃掉了我的桨叶,我完全陷入被水掌控的被动,桨柄被别住,向我的头劈来,我大声惊叫,动弹不得,挣扎了很长时间才重回入水位,那是我第一次与那股力量正面交锋。

△大风天的稻香湖
最初,我会对水感到恐惧,那股柔软而不可抗的力量像黑洞一样从我手中夺走桨柄,我会急于把桨抽出水面,倚靠浮力寻找一种粗糙的平衡,来安抚自己瞬间的心惊肉跳。蹑手蹑脚的水上行走是走不远的,我渐渐抛去心理的束缚对湖水迎面回击。水是种奇妙的东西,缓慢地试探它它就会用柔软的长臂将你缴缠得不能动弹,快速出击它就会顺势变成硬挺的盾牌迎面而上,用桨叶把阻力的厚障壁击碎以后,艇已然破浪向前。
痛苦是有的,牺牲也多。每次划艇回来手上必添新伤,转桨的手指被磨得皮开肉绽,洗澡的时候一不注意碰到热水就疼地龇牙咧嘴。掌心的水泡好歹蜕成了茧子,也许以后会变得更加厚硬,我时常会悲戚地觉得,以后别人牵我,会不会感觉这粗糙得不像二十岁女孩的手心。

△防止受伤的护手胶布
多数时候摸不到真正的水和艇,局促一室之内,在测功仪上一练就是几千米,没有风也没有阳光,空调的扇叶呼呼地吹加上白炽灯默默地亮。
不过很庆幸我的朋友们是一群会苦中作乐的有趣的人,一台小小的蓝牙音箱安放在训练室的角落,用音乐的节奏给最后几百米打热血沸腾的强心针,室内空气不好,汤米就扛过来一台小米净化器,这个屋子成了我们的快乐秘境。直到后来,汤米每次去稻香湖都拎着一个防水音响放在赛艇上,桨划到之处必有笙歌。
大风的那天,防水音响在桨端卖力嘶吼,狂怒的大风压过了郑老师的指令,桨叶掠过水面时发出撕裂般的声响,单薄的救生衣像防弹衣,我觉得自己在渡过一片枪林弹雨。赛艇掉头的时候刚好太阳落山,稻香湖粼粼的金色波光被风击碎,压低重心随着水浪的波峰与波谷起承转合,歌的节奏越来越快,艇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离太阳越来越近,船桨触岸,满湖金色,我用尽全身力气完成了一场璀璨的求生。
轻舟已过万重山
赛艇与其说是竞技,更像自然美学的范畴。八支桨自然延伸,艇就能达到平衡,桨按照相同节律起承转合。在看郑老师发的完美视频的时候,艇中人如同孪生,脊背保持优美的曲线,桨叶以近乎平行的姿态在水中波动,画面中的波纹漾出令人舒适的美感,艇和水衔接在了一起,轻盈得如同掠过水面的燕子,把力量的瞬间迸发柔化成了中正有序的平衡。

△赛艇之美
在加入赛艇队之前,我在经历溺水——那是一段颇不顺利的日子,生活与学业让我焦头烂额,我堕入无端的失眠或噩梦,水压的差异使我丧失形状,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悄无声息争夺我的意识,宛如茫然置身河口,涌来的海水与淡水竞相褫夺。
运动是一种自愈的尝试。赛艇训练带给我的安全感源于我在握着手柄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脑子里只有速度、距离和节奏,休息的时候可以放空自己任思维东西南北流淌。没有拖沓慵懒的节奏,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却能逃离外面飞快运转的世界,一切焦虑都纷纷落地。虚拟的艇在思维里劈风斩浪凌厉向前,在疾风万里中收住了劲。水可以阻拦桨,思维比艇走得快。
第一次高强度的训练结束后,我收获了三个血泡,可那天睡得很香,梦里出口和入口调换了,一切都新鲜得冒泡,把水深深吸入肺里,变回重生的感觉,仿佛心灵被拓展得又广又深——我不再做溺水的梦。
郑老师是个无比温柔的人。最初我像无知的婴儿一样被抛上了艇,四周就是白茫茫一片海。我囿于狭窄的天地里蹒跚学步,每一点滴细微的进步都在被量化,被温柔地鼓励,被一只大手牵引着走向前去。
温柔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

△训练结束后的加油
最初,面对未知的领域就像挣扎着溺水,我说过,无形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很难被掌控,但并不妨碍迎上前去窥探,尝试,摸索,甚至自我救赎。也许我永远都不会像专业选手一样把艇划成完美的诗,但我在努力日臻进步,让艇渡过昨日之我。那个温柔的声音像水一样包裹着我,告诉我别害怕,向前走。
周日晚上我们在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赛艇对抗赛,解说员是北大的王琦和清华的刘星宇。牛剑的水上之争已有一百八十年的传统,剑桥已领先一个艇身,舵手心率高达二百。赛艇是一场力量和心理的双重博弈,我的心也在冲刺阶段怦怦直跳。以后我们还会一起经历很多心跳时刻,无论是在观众席、水上或者领奖台,因为我们曾经汇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我们的心跳和桨频合拍。四月二十日,我们将相约西安灞河,为北大的荣誉打响一场圣战。

△一起扛艇入库
总之,这段经历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手上的伤口、训练的汗水、纯粹的快乐,旁观身边刚开始萌芽的年轻的爱情,都让我充满力量走向前去。想要活成一条滔滔的河流,亦可赛艇。
于是我跌入温柔的梦境里去。在梦另一端的河流里,轻舟已过万重山。
图片来自作者
微信编辑|赵兰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