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社会、文献与文化史: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系列报告纪要
2019年7月1日至4日,南京大学文学院组织了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系列报告。
书籍史研究方兴未艾,对文学、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科产生较大影响,推动众多问题的深入探究、新领域的拓展,以及学科的融合。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是在融合书籍史以及中国传统的书史、版本目录学、出版史等诸多内容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研究领域,其旨趣在中国古代文献的基础上研究文献与社会文化的丰富关联,从特定角度揭示中国文化赖以传衍的机制和精神。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系列报告以程章灿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为依托,由八位研究团队成员各自选自一个有代表性的专题,组成系列,旨在促进重大课题研究向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转化。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是程章灿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此一研究旨在突破传统文献史研究的旧有框架,借鉴“书籍史”此一新文化史研究视野并力求超越,研究对象从“书籍”扩展至“文献”,时间范围从“宋元明清”扩展至整个文明史,同时排除其理论弊端,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思想、学术、社会、文化内涵予以全面深入的阐论,特别注重发掘古代文献的文化建构意义。项目由多位在古典文献方面素有研究的学者承担,以“长时段”的时间观念,弱化单纯的线性进程,各以一个较大问题为中心,如古代文献的核心问题、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中古时期的历史制作与知识传播、治乱交替中的文献传承、宋代的文献编纂与文化变革、明代图书生产与社会文化、清代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以及古代石刻文献的内涵与意义,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多方阐释中国古代文献文化的丰富内涵。
以下是该系列报告的各讲纪要。
【赵益】古代文献形制体式的变迁及其意义
本讲属于“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第一卷总论《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文化》中的一个专题。第一卷总论并不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各个专题的总体纲领和内容归纳,而同样是一个专题研究,旨在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一些宏观性思考,发现、论证古代文献在历史、社会与文化各个方面的核心问题,幷尝试进行回答。除了对“文献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外,具体内容为:历史方面有“中国古代文献的历史独特性”、“古代文献形制体式的变迁及其意义”、“古代文献积聚、散佚与整理、恢复的内在机制”;社会方面有“中古时期的书籍传钞与知识分享”、“近世商业出版与社会变革”、“通俗书籍与近世社会一般伦理道德建构”;文化方面有“文字、书面语、文献载籍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经典的意义及其校雠、编刊与阐释的互动”、“印刷书籍与近世人文和学术发展”。
本讲《古代文献形制与体式的变迁及其意义》首先提出,旧有“书籍制度及其发展变化”的研究,往往囿于单纯的物质形态的历时性描述,已经陷入僵局,迫切需要变换视角。拓展思路,并借鉴法国书籍史研究者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关于“文本抵达读者的不同方式”的思考,可以发现,文献形制与体式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外在物质形态,而实质上是对书籍传播、阅读甚至其文本内容发生作用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文献形制体式的变迁与文献承载、传播和阅读紧密相关。文献的承载、传播和阅读的需要直接推动了从简策到卷轴再到册页制度的进化,并以最优化的形制体式表现出来。而不同的形制体式又造成不同的传播、阅读方式,形成某种时代特征,上古时期的“单篇别行”、中古时期的“经传注疏合编”和近世时期的“杂志体出版物”是三个典型的例证。第二是文献形制、体式与文献内容紧密相关,亦即文献形制体式的变迁影响了文献的内容。这个方面又包括两点:(一)载体和形式决定了其所承载的内容的某些特质。大的方面如文言书面语及其特质的形成,小的方面如纸张对文学、艺术的直接影响等;(二)形制和体式影响书籍流传历史过程中的内容变化。比如不同的书籍制度下,产生文本错误的原因不同,防止错误的机制也有差异;而印刷书的出现,固化了文本,减小文本错误,大大强化了内容的传承与接受。
总结而言,古代文献形制与体式是文本抵达读者的两个方式之一,其发展变化归根结底是文献承载、传播和阅读的需要所决定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趋向于在容量大小、便携程度、阅读效果、收藏保护等方面的最优化。形制和体式的变迁影响到文献内容,它不是与文献无关的东西,而是文献本身丰富意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徐兴无】上古典册及其文化景观
“早期经典”是指在“早期中国”的历史阶段生成的中国文化经典,约略相当于中国传统文献学中的“古书”,特别是西汉后期至东汉中期写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描述的自上古以来的经典系统。所谓“早期中国”,是西方汉学提出的历史概念,约略相当于中国的上古至秦汉时期,只是不以中国的朝代划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可作一长时段或超越性的考察,所以,“早期经典”这个概念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解释的视角与尺度,用来探讨早期经典的发生过程、文献形态、阐释形式与经典意识的形成等等。“早期经典”和“简帛古书”有所区别,它们还包括传世的古书;和“早期文本”的研究也不尽相同,后者更多地指研究周秦汉唐等钞本时代的文本书写形态。
现代学术无论受到疑古还是考古的影响,都对早期经典的形成展开了实证性的研究。随着简帛文献大量出土,中国和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早期文献的研究愈加深入,传世经典的早期生成方式和文本形态也越发清晰。但是经典的形成,其本质是一个思想史的过程。将文本阐释为经典,即经典意识的形成和解释的过程,才构成了经典的历史。所以,探讨早期经典的形成,最终目标并不是还原经典书写的过程和现场,而是揭示经典阐释传统的发生与形成,以及这个传统对塑造中国文化的作用。历史表明,中国早期经典的形成过程,也是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过程,特别是孔子通过整理阐释古代文献来建构道德、政治和文化范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孔子之后,诸子将先秦的立言传统发展为思想经典,汉代经学确立了经典解释制度,而民间宗教则运用神秘的信仰确立其经典的权威。这些问题,构成《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中的《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分卷中讨论的内容。
本讲《上古典册及其文化景观》,将册与典作为两个文本观念,借用西方社会语言学关于文字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语言景观”的理论,认为:上古时期简册文书与甲骨、铜器铭文、石刻等文字的载体一样,都是王权与神权等权威的象征物,具有史官和书写制度的保证并在相关的仪式中展示,是诉诸视觉和在场效果的“文化景观”,简册及其文字的权威也因为“景观”得以树立。












随着这些权威性的文书被不断地选择、编纂、套用、引用,文书由在场公示性或封藏性的文字转为供人查考的历史档案和知识;而有关春秋时期的史料充分说明,在贵族教育中形成的《诗》《书》,史官制度中丰富的档案文书如《易》《志》《世》《训典》《语》等被统治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引证,构成了活跃的引证话语,并且出现了自觉解释文本字句的意识。由于出现了解释的需要,在各种解释的实践过程中,文字才能超越了载体、制度、仪式成为具有独立性、主体性的存在,并且进入了个人阐释的场域。正是解释催生了经典,在这个过程中,“册”字的义项乃停留在标示文书载体的地步,而“典”字的义项越发丰富,生发出历史文献和经、礼、法的义涵,“典籍”以及经“典”命名的文献也得以出现。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定义“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典,五帝三王之书也”;南朝顾野王《玉篇》定义“册,简也”,“典,经籍也”,皆说明“册”与“典”的分道扬镳,恰恰象征了早期经典意识的发生。
【于溯】史部的发生:一个文献学视角
文献有内容,也有 “内容之外”。“内容之外”的信息,比如装帧、材质、版式、卷帙,书写形态、历代著录等等,可能其他学科关注较少,而文献学向来关注较多。如果文献学不止关注、收集、记录这些信息,还进一步利用“内容之外”去重新检视“内容”,那就为学术提供了一种“文献学的视角”。《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史部的形成》分卷,就是以文献学的视角来谈史学史的问题。
研究史部的形成及样态,《隋书·经籍志》几乎是唯一直接、完整的材料。与很多目录相比,隋志的突出特点是提供了海量数据。所以,研究史部的出现不能只看何时一级目录里有史部、史部下又有哪些二级目录。隋志也在通过具体的部帙数、统计数描述史部,史部的生成和流传状况,都藏在这些数据里。
在隋志著录的4800余种书里,绝大多数是20卷以下的小书。超过50卷的书在隋志中只占3%,其中半数都是史部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它透露了史部出现的偶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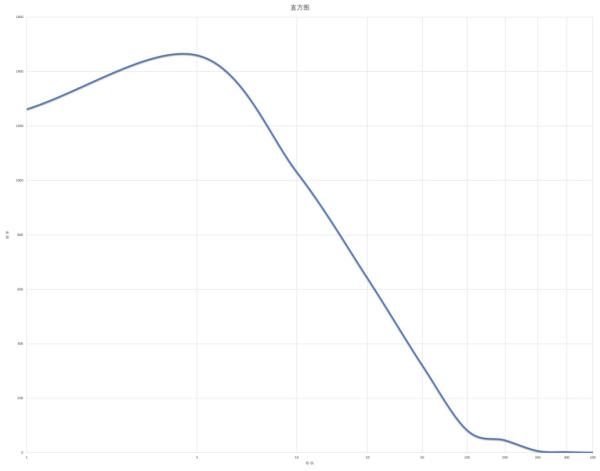
晋太康初,秘书监荀勖校书,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能分四部而取不出四部的名字,是因为制作者也知道这所谓四部并不是一个具有严格目录学意义的图书分类。荀勖是要将皇家藏书平均切割为卷帙大致相等的若干块,使校理者各领取差不多的工作量,以优化时间成本。具体切成几块,一要考虑尽量保证同质书不打散,二要考虑可用的校理人手(以及他们各自擅长的专业领域),三要考虑进度。《中经新簿》的四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综合考量的结果。后人每困惑此目何以将皇览簿、汲冢书分置于丙丁部下,其实四分本是权宜。“能叙学术源流”并非此目的核心精神,它还兼有工作计划表的作用。所以,如果不是荀勖这次校书,未必会出现一个成分杂糅的丙部;如果不是几种大卷帙后汉史在太康前已经问世,如果别集大兴的时代提前,荀勖也未必安排史书去挑丙部大梁。不过,目录不仅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它也能作用于学术、影响学术的未来走向。丙部一旦出现,就不会轻易消失,两晋南北朝官书管理制度的延续性,也保护了四分法。从《中经新簿》到隋志,其实是一个先定四分、再纯洁化四部的过程;部类意识是在四分之后逐渐明晰的。
隋志不仅著录了4800余部书,还对这些书按类做了50余次统计。如果读者自己复核,会发现这些统计数据绝大多数是错的。这种“错误”,可能和《汉书·地理志》著录的户口数和县目对不上一样,是两组数据来源不同造成的。所以,“错误”率描述的,就是这两组数据所依据的两种目录间的差异。在一级目录层面,史部的“错误”率最小。这说明当时皇家图书馆馆藏变动的重点不在史书,或者说,史书一直有良好的存藏状况。如果利用隋志二级目录存亡书数据做一个亡佚率的统计,能看到同样的结论。尽管我们总说汉唐间史书亡佚严重,但这种印象不宜落实在隋志的时期;或者至少相对于当时的经子集而言,史部的保存情况还是最好的。

通过隋志这个数据库,可以得到的信息还有很多。总之,文献学的野心不应止于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学,也不应止于贴合或颠覆已有的文学或史学或哲学的解释框架。今日的古典文献学应该提供面对古典文献的文献理论,并勾勒出一部文献的文化史。无论处理在现代学科分类中属于哪个学科的文献,文献学的视角,都应该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独立的视角。
【巩本栋】略谈宋代的经学文献编纂与文化变迁:以《孟子注疏》为例
历史的脚步进入宋代,随着雕板印刷技术的普及,各种文献数量迅速增长。宋太祖开宝年间编纂刊刻的《大藏经》多达五千馀卷,真宗朝编纂的《道藏》,也多至三千馀卷,宋初编纂的四部大书中,有三部达千卷之多。在研究中如何处理这浩如烟海的文献,是颇令人踌蹰的。反复思考,我们以为从个案入手,以文献的编纂、刊刻流传为中心,以揭示其特点和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展示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为宗旨,来撰写《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宋代卷,或比较恰当。
宋代的经学文献极为丰富。在《十三经注疏》中,由宋人编纂的就有四种,即邢昺的《孝经注疏》《论语注疏》《尔雅注疏》和题为孙奭编纂的《孟子注疏》。对前三书的编纂,历来没有争议,而对後者却议论纷纭,自宋至清,遂定为伪作。然重新考察这一公案,《孟子注疏》虽非孙奭所撰,撰者倒也没有作伪,作伪者,闽中书商也。唐人陆善经为《孟子》作注时已删节赵歧注和章指,撰者承之而已。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宁宗时期刊本《孟子注疏解经》,卷首虽以《孟子音义序》充当《孟子正义序》,文字内容并未作改动。《孟子注疏》内容虽疏略,然依注作疏,每章引赵歧《章指》,浅近周详,时有精义,后世亦不能废。



据宋人吕南公《灌园集》卷十七《读〈孟子疏〉》,《孟子注疏》乃出於闽中士人徐生之手。吕南公生活於宋神宗熙、丰年间,是书亦产生於这一时期。吕南公熙宁初应进士举不利,退而筑室灌园,著书讲学,不事进取。他特别撰文推举、表彰徐氏《孟子疏》,实与其不满王安石新学大有关系,然由此也为后人探讨其人其书的编纂刊刻提供了重要线索。
某一理论为社会所接受的程度,取决於这一理论为社会所需要的程度。《孟子注疏》产生於熙丰年间,是自中唐以来孟子升格运动背景下的产物。随着孟子地位的上升,《论》《孟》以“兼经”的身份进入进士科举考试的范围,而这反过来又推动着《孟子》学的兴盛和《孟子》一书的更为广泛的传播。
《孟子注疏》一书的单疏本,在北宋后期或至迟在南宋高宗绍兴中就已出现了。因为,据《金史·选举志》记载,金海陵王天德三年(绍兴二十一年)即设立国子监,此後公私之学教读和科举用书,悉由国子监刊印颁行。在国子监颁行的经学典籍中,就明确规定着:“《孟子》用赵歧注、孙奭疏。”
至於《孟子注疏》的注疏合刊本,则要到南宋宁宗朝才出现。南宋高宗承祖宗家法,崇儒右文,尤其是自绍兴十二年宋金和议以後,恢复旧时礼乐制度,校刊编纂书籍,思想学术活跃,文化复兴。由浙东茶盐司和绍兴官府主持的、系统的经疏合刊本,陆续问世,至宁宗朝,遂有题为孙奭所撰的《孟子注疏解经》的出现。
唐孔颖达奉诏主持《五经正义》的编撰,贾公彦编纂《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徐彦编为《春秋公羊传注疏》,杨士勋编纂《春秋谷梁传注疏》,至北宋,又有邢昺奉敕编撰《孝经》、《论语》、《尔雅》诸疏。十二经疏的撰者,除徐彦外,皆为经筵名臣或国子博士,且其书多为奉敕而撰,然《孟子注疏》的撰者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下层士人。其思想的深度既不能与前代名儒相比,其所作的阐释也只能是在赵歧注基础上的衍化,然而,其书最终进入了官方的经学体系,成为儒学的经典读本,由此反映了孟子地位不断升格、儒家思想不断被简化和通俗化的文化发展大势。
【俞士玲】竞争或使命:毛晋藏刻书与国家文化权力分享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书籍史研究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版本目录学和印刷技术史的研究取径,开始关注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并将之放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框架中探讨其力量和意义。中国书籍史研究因明代书籍生产和消费皆为古代出版高峰,故明代书籍史研究相对而言最为活跃并富有成果。但本土研究亦面临多重葛藤:如明代刻书数量庞大且超越前代,但传统文献学又流传着“明人刻书而书亡”之全盘否定之语;又如中国现代性是以否定和反叛传统文化的姿态出现的,并带有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深刻企慕。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强有力的形象迫使我们思考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并在晚明令人欣慰地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之相应,书坊作为私人经济出版形态也被赋予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先进性;戏剧、小说或多或少因在西方文学中的主流地位因而在近代以来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和阐释中被赋予主流地位,同时因其被归属于下层人民的创造,因而明代书坊的戏剧、小说刊刻成为明代书籍史的研究主体,然而小说戏曲绝非明代刊刻最多的图书类型,而以商业出版为框架进行明代书籍史研究出现了很多削足适履的现象。有鉴于此,“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特设《明代图书生产与社会文化》一卷,本卷不是在商业出版的框架中讨论书籍的社会史和文化史,而是在书籍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中发现商业因素,如出版资助、稿源交换和买卖、出版流通中介、士商结合等等;本卷多从书籍生产切入,并引入读者因素,将图书生产与原创性的知识生产分开;本卷还关注明代书籍编者、作者、刻者和读者的身份变化以及知识产权问题、意识形态控制和市场潜在的颠覆性力量等。
本讲即在晚明帝国藏书、刻书优势地位丧失的对比框架中,讨论毛晋以私人资本建立的藏刻书事业如何行使、分享甚至颠覆了国家的文化权力。天启七年(1627)秋冬,毛晋三次做了有关“十三经”、“十七史”的梦,毛晋之梦与孔子梦周公、刘勰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南行之梦之传承文化使命相同,不同的是传承文化的形式有别。毛晋母亲以为毛晋三梦是有关读尽经史而成醇儒的天启,而在图书生产极其发达的明代,毛晋将梦解读为通过刻书而复兴礼乐文明的神谕。毛晋“搜求遗逸悬金购”,承担了国家“访求遗书”的使命;其藏书承担了秘阁的藏书功能;校订十三经、十七史,本为官学权威,是国家文化功能,资料表明,毛晋校订经史伊始就深知有“奖我为功臣者”和“罪我为僭分者”,但他承担了筑“箾”(文王乐舞所执)之职,其志也为江南同人、同社所认知并支持。毛晋藏刻书不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实现了对国家文化权力的承担和分享,同时具有某种颠覆性的力量。
【徐雁平】清代的小说戏曲阅读
考察清代文献文化史的进程,首先要注重文献对社会文化影响的连续性。在强调清代文献文化史与前代的连续或一致的同时,自然也要追问其本身特色何在:是否有某些新内容出现,或者此前不太引人注目者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些不同或变化是否有助于建立清代文献文化史的框架?这些问题是否凸显出“清代”,而不是“宋元”以及“明代”?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特设《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分卷,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依循此思路,本卷在结构时,突出代表性问题,并以问题的探究大致呈现史的脉络,若以主题略作提要,可列举出:书籍的流动,书商的作用,雕版印刷之外还有抄书,《读书分年日程》与《说文解字》可测出读书风气与学术风尚,与家族有关的文献迅速增长,女性与书籍的关系可看得更加清晰,阅读小说戏曲是读书人的重要休闲方式,石印出版对晚清科举文化作用明显,西学书籍的涌入改变了国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方式。
如何进一步揭示这些特色主题的关联或者将其串连,而不致成为一盘散珠,则必须重视文献的流动与传播中的粘合作用。本次讲座的题目是《三教之外又多一教:清代的小说戏曲阅读》,着力拓展小说兼及戏曲阅读方面的文献,对清代私家藏书目录作进一步探究,试图揭示一个应该普遍存在然文献记载不多的小说戏曲阅读活动。
报告者指出:小说戏曲作为闲书、无益之书、荡情佚志的有害之书,在清代的社会文化中以逼人的态势生长,“侵入”正经书的领地,愈来愈成为难以控制的社会文化问题。它的异军突起,虽然不能贸然称之为“文化革命”,但确实影响了明清人的生活方式,牵涉娱乐活动、情感世界甚至文化制度,钱大昕称“小说演义”之书在三教之外又添加一教,已看出其力量渗透到整体生活方式之中。少数私家藏书目录中有小说戏曲著录,较为隐私的文人日记中有相关阅读记录,这些反映了读书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或片断在追求功名或苦读的过程中,也有松懈下来追求逸乐的一面。报告者还以李棠阶、严修等理学家日记中的看小说记录为例,分析简约的文字中暗涵的看与不看的“张力”。文化制度上限定与观念的是非判断,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规定、约束日常生活,读书人的购买、借阅、浏览以及向家人讲说小说的事实,皆显示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及世俗意味。而小说进入社会生活并产生影响,《红楼梦》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个案;它与社会多层面的关联及多种作用方式,也为从外围考察一部小说如何成为伟大的经典提供路径。也要对其影响作时间与空间以及接受者等方面的区分,这也为小说戏曲或其他书籍的传播研究作有益的提示:分期研究之外,有必要重视分区域研究,而在区域研究中,群体研究可能贴近清代社会文化及读书人生活的现实。
【张宗友】文献足征的理想
古代中国,治世、乱世交替出现。作为民族生存智慧与历史记忆载体的古代文献,随着时代之治乱相继,而经历种种劫难:秦始皇之焚书,隋炀帝之禁纬,清代之文字狱,加上水火之灾、虫蛀之厄、流匪之劫掠,都足以使某一时、某一地或某一部类、某一家藏、某一学术流派的文献,罹遭巨大损毁乃至灭顶之灾。《汉书·艺文志》所载典籍,迄今百不存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类典籍,全部亡佚;清初绛云楼之珍藏,悉烬于火:都是其中显例。
与此同时,以经史为骨干的传世文献,虽历经种种灾厄,而能传承不坠,在新的时代条件与阐释传统中与古为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今日中国奋力前行的重要力量源泉。治乱交替中的文献传承,其内在机理,值得深入探讨。
从地理上看,中国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相对封闭的地域之内,能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有其内生的强大的生命力,会按照既有的个性与节奏,不断向前演进。文化传统及其生命力,通常体现在作为载体的古代文献之中。因此,深植于古代文献的文化内驱力,是古代文献不断得以生产与承传的根本力量。
自秦汉以降,古代中国由封邦建国的宗法社会,转型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实现大一统是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历代帝王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无不重视文治,致力于营构同本朝政治架构相适应的文献体系;为此,通常会大规模征求、整理、编纂文化典籍,并伴以禁毁行为。汉代建国伊始,即整理兵书;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成帝时,使刘向、歆父子整理藏书,使先秦以来的文献第一次有了官方定本,影响极为深远,历代均加以仿效。晋代荀勖,依刘氏故事整理图书,编成《晋中经簿》。南朝宋、齐、梁、陈,复依荀勖之例,撰成四部书目。唐初,为南北朝纂修纪传体国史,形成了官修正史的撰述传统,又为后世所效法。宋初,纂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四大书。明成祖纂修《永乐大典》,是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清高宗弘历纂修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是一个寓禁于征、寓毁于修的大型文献工程。以上诸例表明,帝王威权有时成为文献生产、禁毁的决定性力量。
从孔子开始,中国知识阶层就有“文献足征”的文化理想。知识阶层,不仅是古代文献的掌管者、阅读者,也是整理者、传播者、生产者;其中的“创造性少数”,进能“致君尧舜上”,施展抱负、兼济天下;退能独善其身,治学、讲学,以著述传世。例如,经过朱子的表彰,《四书》与《五经》并列,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指定范围,四书类文献由此勃兴,成为古代中国突出的文化与出版现象。可以说,知识阶层是推动文献不断生产与传承的主体力量。
【程章灿】方物:从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献生产的地方性
究竟石刻算不算书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争论持续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但是,石刻属于文献的一部分,属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十分重要而且极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作为一种文献类型,石刻有什么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其形成之前的文化动因以及形成之后的文化意义又是怎样的呢?《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特设《作为物质文化的古代石刻》分卷,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石刻文献不仅包括石刻实物本身,也包括石刻拓本,还包括以文字、图像等方式整理出版的石刻书籍。石本、拓本、书本,这是石刻文献存在的三种物质形态,因此,石刻文献也就具有了丰富的、与众不同的物质性。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观察石刻文献,可以对石刻文献的生产、传播、收藏、流通以及使用等过程,取得新的更深刻的认识,比如石刻生产过程中的刻工与拓工所发挥的作用、汉代碑刻的礼物功能及其所反映的社交网络、秦始皇刻石以及汉末三国刻石的政治运用、朱熹对石刻的文化利用、碑帖及摩崖碑刻的景观呈现、拓本收藏与玩赏中的商品流通等。自宋代以降,石刻日益成为古代中国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细分起来,中国古代石刻又具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往往与其物质形态密切相关。摩崖石刻就是其中的一种。摩崖石刻依山崖岩石而镌刻,既具有取材自然、规模宏大、开放展示等特点,又具有“托体同山阿”“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摩崖石刻源远流长,从秦始皇所刻碣石山、汉代《石门颂》、泰山经石峪、唐玄宗《纪泰山铭》等,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摩崖石刻,具有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方物:从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献生产的地方性》,以永州摩崖石刻为中心,重点讨论永州摩崖石刻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永州位于潇湘二水交汇之地,又处于荆楚--岭南南北交通要道之上,具有独具特色的“水石文化”。这种山水泉石的地利,为永州摩崖石刻的产生提供了自然地理的条件。中唐时代,生性浪漫的文学家元结对永州山水泉石情有独钟,他对阳华岩、朝阳岩、三吾胜迹的命名与文化开发,他对《大唐中兴颂》的改写与书刻,使永州摩崖成为南北乃至中外文学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并由此形成永州摩崖石刻的地方性。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永州摩崖石刻生生不息,不断衍化、生产,形成了三大系列:偏重政治性的铭颂、偏重文化性的榜题以及偏重文艺性的诗文,这不仅丰富了永州地方文化和古代石刻文化的内涵,而且从永州摩崖的特殊角度,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与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