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普通人,她如何成为作家,成为八月长安

编者按:这是刘婉荟开始写作的第十年。她已很难回忆起09年在晋江文学城注册第一个笔名、写下第一句话时自己在做什么。她从光华紧张的大三中抽身而出,来到日本交换。异国求学的一年如同碍于条件而无法写作业的“晚自习停电时分”,她与国内的学业、实习隔海相望,得以理直气壮地不务正业。此时写作对她来说一度只是爱好和消遣,不曾被列入人生清单,也从来称不上梦想。
她曾经选择了所有普通人都会走上的道路:为了前途而选择并不喜欢的经管专业,为了稳定而不愿从压抑的工作中辞职。她认真工作、努力干活,隐藏起写作者的身份;同时坚持更新、写完故事,对读者负责。
然而这些故事与它们的成功,使写作这条岔路逐渐明朗。处女作《你好,旧时光》的落笔激起遥远的回响,最终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这是一个普通人成为八月长安的故事。而现在的刘婉荟,或许仍在成为八月长安的道途之中。
记者|宋喆 张漫溪 买祎然
编辑|张卓辉
2009年12月,北京正是冬天。刘婉荟从西直门附近的图书公司走出来,五套《你好,旧时光》的样书堪堪挤进她的背包,将帆布质地的书包撑出了棱角。
她乘地铁回学校,穿越31楼昏暗不见光的走廊,从半空高悬着的衣摆裤脚下经过,推开宿舍的门,走进去,然后迅速地把五套样书拿出来,看也不看就直接放到了书桌顶端的柜子里,动作小心翼翼,生怕袋子破了,让别人看见。
还好,她的室友不知道,也没有问。
刘婉荟曾在31楼的楼道里听别人说起这本书,那时它还在网上连载,名叫“玛丽苏病例报告”。这七个字从陌生女同学的嘴里吐出来,飘进她的耳朵,她的第一反应不是骄傲,而是慌张,“千万不能让她们知道是我”,“如果不小心被同学知道了,我就去跳湖”。
时年二十三岁的刘婉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大四学生,电脑里的小说存稿和投行的工作简历看起来格格不入。成为网络写手,或是意见领袖,在2009年的校园中,也是不务正业,甚至有点丢脸和危险的事情。那时候,她白天连轴转,晚上写小说,还没有人能把“刘婉荟”这个名字和那些散落在晋江文学城上的、挖坑不填的笔名联系起来。
那个月底,《你好,旧时光》登陆当当和卓越网络书城,首印两万册很快售罄。第二年再版,新添八万字番外,分上下两册上市。之后,以“八月长安”为笔名,她接连出版了《暗恋·橘生淮南》与《最好的我们》,从公司辞职,自创工作室,以写作为“天职”。
八月长安无法为自己的成名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一篇新的连载发表在网上,溅起零星水花,落入某个女生宿舍的深夜话题和网文推荐里,绽开一圈又一圈的波纹,以某种衍射效应,越过毕业季和工作,最终改变了她的人生。
然而在样书装进背包的那个冬日,她尚对此一无所知。
“非典型光华毕业生”
刘婉荟是打着石膏走进北京大学的。暑假时她穿着租来的溜冰鞋,从哈尔滨植物园的某条坡道顶端向下俯冲,遇上一个大坑,结结实实摔了一跤。左臂上的绷带和石膏包裹住剩下的夏天,将毕业表彰、开学典礼和迎新晚会缠在一起。

八月长安的十八岁生日,摄于泰国皇宫
正式上课是九月十一号,八点钟,高数B。她打着石膏坐在电教三楼大教室的倒数第三排,板书一个字也看不清。讲台前的年轻老师说话带一点江南口音,她走了半分钟的神,“此后再也没有听懂过数学”。
期中考试过后老师在黑板上用大字写下了四行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他讲了张继落榜的故事,人生一时的起落造就了千古名篇,他觉得很值。台下笑声一片,他红着脸解释说,自己是怕他们考得不好,心里难过。
那几乎是刘婉荟唯一一次看懂高数B的板书。大二的一个晚上,刘婉荟回宿舍,路过两层楼之间的拐角,听到有个同学正趴在窗前和父母打电话。
“你们不明白,你们真的不明白……”
对话从紧攥的手机中漏出来。另一端的父母语气困惑,多年经验告诉他们自家孩子但凡努力了就能拿第一。那个同学只是疲惫地重复,你们不明白,你们真的不明白。
她没有停留,两个台阶从脚底匆匆沉下去了。
揣着哈尔滨市文科状元的名次,选择光华几乎不需要理由,但最明亮的地方或许不是最合适的地方。光华塑造她,改变她,成就她,也消磨她,她花了很久建立起自己和这所学院的联系,找到最好的朋友,找到自己的定位,接受自己作为普通人的现实。
刘婉荟一直不像典型意义上的光华毕业生。人生梦想是“六十岁拍一部属于自己的动画片”;印象最深的实习是在动画公司整理项目流程;大三时所有人都忙着实习和网申,她早早申请了早稻田大学为期一年的交换生项目,走了。
她从小看日本漫画长大,自然很想看看向往的世界的模样。审核方要求她附上一封有份量的日本文化方面的推荐信,于是她从教务处冲到二教,去找那位素昧平生的资深教授。对方正在上课,教室太热,她呆不住,就走到教学楼前面的扶手上坐下。那年新落成的二教是她最喜欢的教学楼,她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晃着腿,心里完全放空,冥冥之中觉得老师一定会答应她。
一切如她所愿。2008年夏天,她乘着飞机远渡重洋。
“晚自修停电时分”
异国生活闲适安逸,课很多,却有机会让她做想做的事。四处旅行,教一个日本舞台剧演员英文,到老师家开办的幼儿园当中文老师,从便利店买食材自己做饭,看书,“就像是在过自己的小日子”。
一日她被大雨困在高田马场街头的咖啡馆,见到落地窗外的机车少年锁车进店,换上制服围裙,抖落一身雨水,俨然礼貌恭谨的打工店员。雨天人不多,对方打扫卫生时与她攀谈起来,提到自己高中毕业,还未读大学,打算先攒钱环游日本,弄清自己想做什么再做决定。
“你未来想做什么?”对方问她。
她还没有想好。
光华的同学大多会在大三暑假乃至更早开始实习,同一栋宿舍楼里有竞争有焦虑也有牢骚。她在外交换,不与竞争;又不乱传话,实在安全,自然成了国内同学的情绪垃圾桶。MSN对面的消息一条条发过来,她合上电脑,侥幸拥有隔岸观火的姿态。在日本的那一年如同“晚自习停电时分”——“当你有条件往某个方向努力的时候,你不努力,就会付出很高的心理成本。但是那一年,就像高三晚自习忽然停电了一样,你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条件不允许。那时候不务正业,是很开心的。”
“停电后的晚自习教室”一片漆黑,刘婉荟把练习册压到草稿本下面,在纸上写下了小说《橘生淮南》的第一句话。
二十三岁之前,她的人生与写作毫无关联。小时候在图书城看《魔术快斗》全三册单行本漫画,兜里没钱,只看不买,结果中暑晕倒、被抬进图书大厦办公室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人家的书;读大学后每周去中关村图书大厦买书,全场常年八折周年庆,一庆庆一年,她知道每层楼卖什么,也曾坐在地板上看书到打烊。在阅读之外,唯一和“写作”沾亲带故的,可能就是在人人网上写日志。

重返中图签售
2008年10月,她把已经改过一稿的《橘生淮南》发到了晋江文学城上。留学生公寓二十四小时拉着窗帘,分不清白天黑夜,苍白的日光灯照着桌面和书架,一台又厚又重的惠普笔记本竭力运转,背板烫得能摊鸡蛋。她在隐秘的马甲之下胡言乱语,不必担心熟人的解读和窥视。回想起来,这篇处女作更多是一个自我丰沛情感的出口,如同失恋之人总爱发朋友圈,但也不全是为她自己那段无疾而终的暗恋而作。
这之后她换了许多笔名,比如“喜之螂”和“藤子不二熊”。那时晋江注册不限制,从匿名论坛时代走出来的用户也对披马甲习以为常。为了避免挖坑不填引起读者不悦,她常常搁下遍地是坑的旧笔名,在新的笔名下写新的文章。即将离开日本的夏天,贴在书桌上的日程表全部排满,而她总是越忙碌就越想做点别的。期末考试、注销账户、退保退合同、打包行李,学业压力与生活琐碎包裹着旺盛的表达欲,在“八月长安”这个新笔名下喷薄而出。笔记本内置的风扇呼呼转动,键盘起落之间,她发表了长篇《玛丽苏病例报告》。小说连载第十二天,文末评论区出现了第一条读者留言。
——“灯亮了”
2009年7月28日,八月长安乘着飞机从东京回到北京,在学校做短暂的中转。一天之内她见了许多大学同学,和不同的人吃了四顿饭,还要努力维持小说的更新。回到哈尔滨后,因为家里只有拨号上网,而她的笔记本必须连宽带,在半断网的情况下,许多更新都是在网吧完成的。有时她在家里写好稿子,导入U盘,到网吧上传;有时忘了带U盘,就在网吧手打一遍。一边叼着烟一边玩劲舞团一边大喊大叫说自己怀孕了的女人坐在她身边,她疯狂敲敲击键盘。手机震动,是母亲叫她回去吃饭。
她会把这些无害的生活细节写在每一章的“作者有话说”里。轻松的调侃背后,那段日子的底色始终是焦灼的。就像是日光灯忽然亮起,晚自修却已过去大半,所有的人都扑回作业上埋头猛写,她也不得不重新摊开练习册。
整个暑假她都在准备网申。九月开学后,落下的大三专业课、大四专业课和通选课拧成一股绳,将她绑起来,拖进纷繁的现实之中:英语日语考试、网申笔试面试、期中论文、小组合作……平衡找工作、学习和写作是不可能的,也无暇去想,她已经到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地步,时间分配和任务权重被抛到脑后,车到山前必有路,DDL前必出活。
和离开日本前的日子一样,重重俗务压在肩上,写作反倒成为一种排遣。她白天顶着北京大雪满地泥泞跑到老远的地方面试笔试,回答一些诸如“如果在职场里遇到了性骚扰该怎么办?”“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小孩会不会影响工作?”的问题;晚上回到宿舍,换下高跟鞋一步裙,挤出时间来更新,效率高得吓人,最后竟保持了一周三更的频率。
《玛丽苏病例报告》也的确和之前那些尝试不太一样。和八月长安的自嘲相反,这个小学生的故事意外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与关注。离开日本前,编辑凌草夏通过晋江的站内短信联系上她,两人开始商量出版事宜。8月中旬,小说开通VIP,彼时付费阅读和电子支付都不是常态,读者需要购买盛大点卡,才能为自己的阅读账户充值,对此,她在“作者有话说”里反复向读者表达“对不起”和“谢谢”。8月底,将名字改成“你好,旧时光”后,这本书最终走上了出版日程:读者群活动,豆瓣赠书活动,样书寄出,上市。 2010年1月5日,《你好,旧时光》上市一周,她就把全文的结局放在了晋江上,算作给读者的承诺和交代,“结局没什么藏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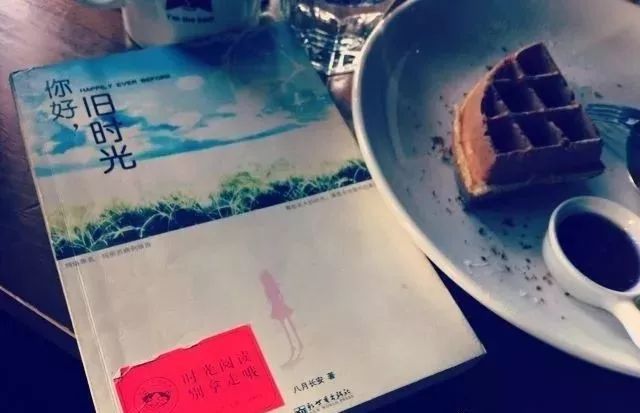
《你好,旧时光》初版,有错字,无番外和后记
图书出版的喜讯如同一枚小石子跌入潭中,很快被大四的焦虑与忙碌吞没。关于拿书那天的记忆也连成一片,她只记得自己打电话给父母报喜,然后偷偷送了一套书给自己最好的朋友——对方也深知她的作风,拿到书的第一刻不是想着拆开,而是藏起来。
她完全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作家,写作的定位和规划也一片空白。“大四的学生如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出路没有。”那时候她最紧迫的任务是找一个蜂房,做一只工蜂,写字楼里的女白领,“穿普拉达的女魔头”。
这本书的更新与出版的确改变了她,她认识了一群从十三到三十岁不等的读者,她开始意识到网络责任感,不再频繁换马甲、改笔名。在小说上市的冬天,她找回了来到晋江创作之初的心境与热爱,也一度有过丰满的毕业计划,想把包括《橘生淮南》在内的几篇旧文全部写完。但她自己也承认,这些决心只是毕业综合征,“写写文,看看文,其实都只是一点点兴趣和坚持,都算不上什么梦想。”
“成为一名作家”,这件事情依然比60岁拍一部动画片的人生理想还要遥远,甚至从没有被纳入到人生计划之中。
“自由自在的废物”
作为责编,凌草夏第二次见到八月长安,是《你好,旧时光》新版上册出版的时候。临近毕业,她瘦了很多,相比第一次见面没有刻意打扮,“整个人像是没有睡醒一样,来去匆匆在公司呆了一会儿就走了”。
毕业季尘埃落定,她最终签了上海,在一家外企做管理培训生,平时负责投资分析,偶尔也参与内部审核。白天掐着点打卡上班,晚上回到家抓紧一切时间玩PS3。大部分公司都不希望员工中出现作家或KOL,因此她必须小心掩藏起作为“八月长安”的身份,在层层的报表和企划之下,写作依然是副业,是零花钱的来源。只是平时路过书店,她就会走进去看看,自己的书被摆在哪里。
而蜜月期过后,工作中不尽人意的一面也逐渐显现。在一切始终与人有关的职场里,他人落后的价值观,甚至偏见或恶意,不断影响着团队间的沟通与她的工作效率。迷茫和挫折一齐涌向她,她在随笔里写自己想做“自由自在的废物”,要赚很多钱,要曾经有所成就,才能心安理得地窝在沙发上,不会觉得未来没有希望。那时她已然把自己的努力视为“一种责任感和带引号的牺牲”,成就也变成了“一种血淋淋的,要献祭时间、快乐和人性才能获得的东西”,“这是一种等价交换”。
她已经不在晋江上更新,与粉丝交流的场地移到了微博和博客。2011年,刚上线不久的新浪微博一次只能发140字;博客也依然是诞生KOL的沃土。在读者的催促下,她忙里偷闲,完成了《暗恋·橘生淮南》与《最好的我们》,振华中学的故事逐渐展开,每个人物都被安放在了恰好的位置。

2017年5月6日八月长安在上海书城福州路书店举行签售活动
她迎来了她的首次读者见面会。2012年2月26日下午两点,西单图书大厦一层东厅举办了《暗恋》新书签售会。宣传海报上的八月长安留着短发,身穿学士服,被许多人留言调侃说看起来像韩寒。她那时很担心没有人捧场,发微博的语气都带着一丝紧张,还自我解嘲“如果没人去,我就脚底抹油直接溜走去喝下午茶”。
那天她到底没能喝到下午茶。现场坐满了人,责编凌草夏在长桌的一头客串主持,她和读者聊了聊天,接着就开始签售。点头,微笑,书一本本地递过来,合影收进取景框,花和礼物被放在她手边的桌子上。那是她第一次以真身面对读者,现场的反馈给了她“作为作者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这之后,新作《最好的我们》上市,她也面临着一轮全国签售。此时请假飞去签售地已不现实,她必须在写作和工作之间择一而从。而此时的她,已经有了选择权。
八月长安承认自己一直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做一切事情都要留足后路,所以才去学自己并不喜欢的经管,因为好找工作;所以即使忙成工蜂,也不会破釜沉舟,要等到写作这条路的前路变得明朗,在兴趣、前途和收入方面压倒工作,才肯考虑辞职。
做出辞职的决定是在夏天,她眼里上海最美丽的季节。晚上的云很低,很白,大片大片地从头顶迅速流走,天低得让人产生幻觉,“仿佛一伸手就能抓住一片云,又仿佛你什么都能做”。
“十年后”
写不出稿的时候,八月长安有很多事情可做。
看书,练琴,学画画,学外语,看《灵能百分百》和《一拳超人》,打游戏。从《战神》《刺客信条》到《荒野大镖客》,2017年沉迷于《塞尔达荒野之息》,刚通关了《勇者斗恶龙11》,偶尔也涉猎Gal Game,比如《闪之轨迹》。
这些爱好构成了她的生活本身。除此之外,公司里也有许多事情等着她。身为老板,她要对很多有编剧梦想的同事负责,要把控项目进度、洽谈合作,这些事情和压力能让她找回工作的感觉,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

八月长安,摄于2017年
她的生活轨迹在北京、上海、青岛之间画了一个对勾,身份也从学生变成上班族,辞职后专心写作两年,又建立起自己的公司。对她来说,写作是“天职”而不是“职业”,是一种乐趣而并非名义上唯一的赚钱渠道,“写作永远是写作,我保持我的写作习惯,穷死也不会改”。这种习惯包括反复修改与自我批评,也包括缓慢更新,一卡文就打游戏,以及“十年来都无法从头到尾只写一本书”。
十年前,创作对她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灵气多得溢出笔尖,表达欲走在脑子前面,落笔成文,网络流行语信手拈来,字里行间的抖机灵让她回顾起来常常尴尬不已。
但她新的作品《这么多年》却花了很长时间等待它的问世。十年后,八月长安对待创作更加审慎甚至苛刻,关注点逐渐转移,毕竟青春小说的大厦行将封顶,即使在大框架下重新开掘,得到的“也还是原来那些东西”。尚未发表的《这么多年》被她视作关注点和个人风格转移的一步,小说在出版时曾遭遇阻力、一度停滞,情势明朗后审视这部作品,她已经没有办法再将三年前的东西呈现给读者了。“我不太希望这个故事后面的发展,又是一个轻盈的、简单的、《最好的我们》式的结尾”,全文一改再改,为了这个故事最终“坍缩”的一刻,她愿意付出更长的时间。
现在八月长安已经不想做“废物”了。脱离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面对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论成功与否,她都不可能是一个“废物”了。她希望能够写得更好,这是一个追求,哪怕她现在认可的东西可能会没有以前的作品那样讨喜,她也想要偷偷地、慢慢地完成它。
她还是会怀念旧日的网络空间,相熟的读者在文末评论区盖起高楼,盛况一如天涯论坛。他们讨论不负责任的小学老师带给自己的童年阴影,聊起文中出现的鸡兔同笼与工程问题,互相安慰,互相调侃。曾经她有机会认真回复每一条评论,在内容简介栏上写下“内有H”,以测试点击率是否会上升;她还一度热衷发微博,甚至以“……(未完)”“最后一条:……”为格式连载日常段子。
她确实感激“作家”这个身份带给她的一个好处:大家的关注和催促将她变成了一个更负责任、更有头有尾的人。

2017年5月28日八月长安在苏州凤凰书城举办签售活动
如今她的微博粉丝越来越多,大号到了121万,小号也涨到39万。这里已不再是从前可以随意表达的半熟人平台,它掺杂了工作事务,还需承受他人的审视与解读。早年她曾在微博和演讲上说起自己的工作纠纷和出版官司,但是为了不引起新的风波,如今这些都已沉到很深的水底,她主动回避,不复重提。
高考结束后她作为市文科状元接受媒体采访,被塑造成一个“用好课堂四十五分钟”“从来不上补习班”的好学生样本。2015年的时候,她去《天天向上》录节目,节目组给她的设定是,“任何一个细节都能展开两百字描写的、感情细腻的作家”。但这些聚光灯下的时刻,都算不上她创作生涯的重要环节。她无法为自己的成名寻找一个戏剧性的时间点。前IP时代的作家未曾经历网络造星的过程,那时候的一篇小说在女生宿舍里口耳相传,最终反过来改变了她自己。
那年冬天背着五套样书回到寝室的刘婉荟常常觉得,北京的马路宽到她好像永远都过不去,建筑方正广大,一切都在衬出她的小。如果没有背包里那五套《你好,旧时光》,身为普通人的她,原本可能不会成为八月长安。
(文中图片来自采访对象)
新媒体编辑|李番 张漫溪
责任编辑|张炜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