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栋读《法国文明史》︱“文约而事丰”的文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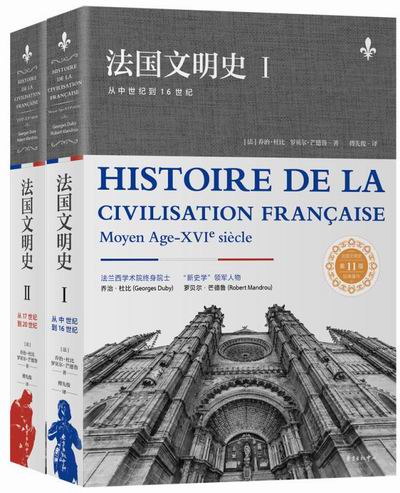
乔治·杜比(Georges Michel Claude Duby, 1919年10月7日-1996年12月3日)是法国重要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著有《11—12世纪马孔地区的社会》《布汶的星期天》《大教堂时代》《三个等级:想象的封建社会》等;主编过《法国农村史》《私人生活史》《西方妇女史》等多卷本著作。他深受围绕在1929年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周围的学人群体影响,将心态和人种学融入到农村史、区域史、艺术史等领域的写作中,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中世纪史专家”(雅克·勒高夫语)。
很多史学工作者都有写一部通史的意愿。所谓的“通史”,按刘家和先生的辨析,就是它“必须具备一种把历经古今变化的历史视为同一体不断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把历史视为常与变的统一)的精神”,因此断代史、专门史中蕴涵了通史精神(《论断代史〈汉书〉中的通史精神》)。反过来说,通史中或许包含了时代精神。一部通史性的作品,集中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状况,甚至还置入了作者的师承。而且,读者还都可以通过作者所构造的故事,多少找到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和伦理训诫。
二十世纪早期,何炳松依据法国史家瑟诺博司的《应用到社会科学中的历史方法》,编著了《通史新义》,指出“社会乃一种关系之综合,此种关系非吾人直接所能观察者也,盖纯由想象得之”(《通史新义》第八章)。如果将民族国家看作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史学写作的主流形态。在《经济社会史年鉴》于1929年创刊之前,法国的民族史主要关注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用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以政治为偶像”“以个人为偶像”“以编年为偶像”。1929年之后,经济社会、跨民族方面的内容开始得到凸显。一些多卷本的史学作品,例如,古希腊史专家格洛兹(Gustave Glotz)主编的十二卷本《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路易·阿尔方(Louis Halphen)和菲利普·萨格纳克(Philippe Sagnac)主编的二十卷本《民族与文明》(Peuples et Civilisations),表现了民族史中的互动倾向。1946年,《经济社会史年鉴》更名为《年鉴:经济、社会、文明》,在去掉“史”、加上“文明”一词后,“社会”被置于讨论的中心。乔治·杜比、罗贝尔·芒德鲁(Robert Mandrou)受这种观念影响,于1958年合作出版了《法国文明史》。进一步讨论这部著作的新颖之处可以发现,它展现了“心态”,因而可以将它归为“心态史”作品。
一
两大册的《法国文明史》(傅先俊译,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4月第1版)依法文第十一版译出,分为三部分:“中世纪”“现代法国”“当代法国(19至20世纪)”。“中世纪”部分由杜比撰述,占五章的篇幅,“现代法国”“当代法国”由芒德鲁所写。相比1958年的法文版,现有的中译本增加了知识分子研究专家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执笔的“回顾当代法国”一章,它除了将“下限推进到最近年代[1983年]”之外,还展现出当时身为讲师的西里奈利对社会前进的信心。全书共十八章,每章均用几页文字交代了本章的论述主题、重要观点,让读者可以扼要地了解作者的用心。
杜比一开篇就谈到,法国文明是围绕几个中心慢慢形成的,“然后沿着几个方向发展传播”,因此希望“通过本部历史书,明确地界定那些凝结点,找出传播的方向和界限”,最终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构成当今法国的所有地区”(第4-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讲述空间、人群、文化与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著作。
杜比将法国文明史的开端设定为公元1000年,而不是克洛维受洗的498年,也不是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而奠定法兰西雏形的843年。按杜比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在公元1000年左右,异族入侵告一段落、各个领地的个性逐渐显现,另外就是信息来源明确、史实相对清晰。换言之,十世纪之前,各地隔绝,勃艮第、法兰西与阿基坦未能统一,且统一的物质基础并不完备,资料也以传闻性的居多。十世纪之后开始孕育了一种新制度,“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新意识和新习俗组成的社会形态”,即封建制(39页)。杜比对封建制的看法不同于汉学家葛兰言,后者从社会学和历史比较的视角出发,将封建制看作是一种过渡性体制,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杜比还认为,十二世纪是“从1070年起至1180年,即从卡昂修道院三一大教堂的落成为起点到巴黎圣母院的祭台建成为止”,也是“整个中世纪最富有成就的世纪”(77-78页)。十三世纪是“一个普遍繁荣的时代”,交通和物质交流频繁、城市得到统一;十四至十五世纪是“法国文明史演进中的第一时期”(145、191页)。在杜比看来,中世纪并没有在十五世纪末结束,“而是旺盛地存活着”,一直延伸到了十七世纪。
作为近现代史尤其是人文主义研究专家,芒德鲁在《法国文明史》中呈现出另一种风格,时时对照古代和现代法国人的异同,呈现出一种雄辩式的笔调。芒德鲁将十六世纪以来五百多年的时间分为“现代”“当代”两个阶段,“分界线在18世纪末,在1789年8月4日夜间或者8月26日那天”(261页)。现代阶段是城市加速发展、乡村生活基本无大变动的时期,其中的十六世纪“确实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时代”,而当代是资产阶级向全世界发出开放信息的时期,是“第二次创造世界的开端”,其中的“19世纪80年代则是决定性的时期”,走上了“一条不再回头的共和国之路”(337、660、641、671页)。即便谈到历史上的多次宗教内战,例如“代表欧洲历史转折点”(布克哈特语)的圣巴托罗缪惨案,芒德鲁也不是将它们看作“文明的暴死”,而是认为应该“从中看到一系列的过渡和演变,应该尊重而且不抹杀过去”(338页)。在谈到两次世界大战时,这种乐观主义仍然明显:“各种纷扰反映出深刻变动中世界的冲撞和不安,同时法国文明仍然在不断地创新。”(724页)
“回顾当代法国”一章先谈到1939年以来的“灰色调”,说这些“并非是最主要的。在事件中扬起的尘埃落定后,法国获得了半个世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767页)可见,作者延续了乐观主义的基调,向读者确认了1939年以来近半个世纪法国在各方面的进步,也给自己增强了未来进步的信心。
作为中世纪研究专家,杜比并未严格按照学术界通行的历史分期,去“断限”文明演进的一般秩序。杜比站在法国统一和连续性的角度考虑文明的开端,而不是讨论文明的起源(origin)问题。开端是历史学家的主动选择,可以按照不同的主题分别加以设置,而起源是一个神性问题,甚至还有所谓的“起源崇拜”。芒德鲁认为实证主义的开端是在1850年,结束则在1900年,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或之后。
杜比专注于法国历史情境的学术探讨,而芒德鲁在古今对照中找到历史上法国人对新世界的好奇心,西里奈利则主要关注知识界的状况及其对时代的反映。如果说他们在将法国描绘成一部“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文化和饮食水平”改进的历史之外,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以经济社会视角为基础讨论这一千多年法国人的“意识”“思想和行为方式”是他们的重心(72页及以下各处)。“思想”“意识”“习俗”“集体心理”时时闪现在全书各个章节。因而,这部著作既符合年鉴学派倡导的历史观,又展现出历史学家各自的性格、兴趣和爱好。
杜比、芒德鲁在书中较少运用参考性脚注,但中文版译者恰当地提供了一些解释性的注,方便读者的阅读。刘知幾提道,“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且要求尽量做到“文约而事丰”(《史通·叙事》)。《法国文明史》在这一点上相当接近。
二
年届七旬的译者傅先俊先生提醒我们,基佐有一套同题讲义《法国文明史》,但它只写到十四世纪即法国中世纪结束,对十五世纪以后的法国社会演变未加以讨论,因此杜比、芒德鲁的著作将补足基佐的讲义。文明(civilisation)在基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基佐作为首相、福音派信徒,从政治的视角关注法国的历史进程,认为“文明是一个事实(a fact)”,而不是一种理念(an ideal)。在基佐看来,进步才是文明史写作的动力和参考标准。这种进步体现在社会、心态和个人性质上,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基佐在比较欧洲文明之后,得出的基本看法是法国文明为“最重要和最富有成果的文明”(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一讲)。叙述上,基佐多谈起源,谈法国文明中的罗马因素、日耳曼社会。
除基佐之外,十九世纪写作法国史较有影响的学者包括米什莱、拉维斯(Ernest Lavisse)。例如,拉维斯主编的《法国史》中,“当代”部分始于法国大革命,结束于1918年。芒德鲁则将“当代”的终点落到1939年;西里奈利将之落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当代史作为专业历史学的分支,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现。这大概是因为,过去和当代的距离不够,写当代史难以保证历史的客观性。即便承认当代史,历史学家对它的起点也不尽持相同看法。反殖民史研究专家博诺(Robert Bonnaud)在《历史的体系》(Le Système de l’histoire,1989)一书中提到历史的三个阶段:中世纪以前、现代(1467-1917年左右)、当代(1917年以后)。档案上的时间分类更细一些,1800-1940年7月10日的档案属于现代,1940年7月11日以后的属于当代。历史学界对当代的认知并不同步,或者说,当代本身是多样性的。《法国文明史》跟中学教科书保持一致,将1789年作为当代的起点,但该书却认为1775年以后的危机仍“属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一部分”(49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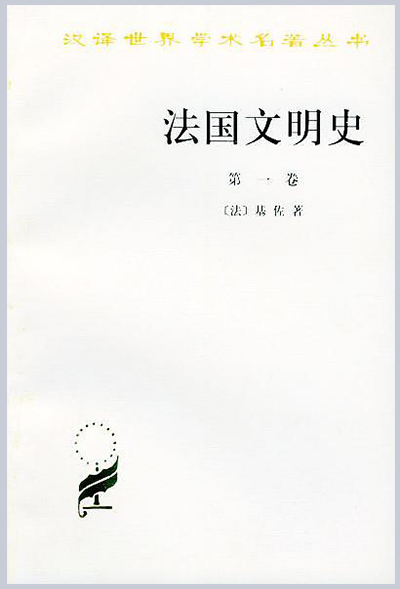
钱锺书引过芒德鲁的《近代法国导论》,说“心知之需名,犹手工之需器(outillage mental)”(《管锥编》“一四三 全晋文卷一〇五”)。“outillage mental”,一般译成“心态工具”“心性工具”,大意是说每一个时代皆有它自身的思想词汇、科技,而不为另一个时代所有,或者说从前一个时代改良而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同是写文明史,杜比和芒德鲁从经济社会史的路径出发讨论集体心理、心态的演进,而不将一种与当时时代不符的心态工具放到对过去的理解中。这种做法还与二十世纪上半叶流行的从血缘、种族和语言角度解释民族起源、民族特性的范式区别开来。
细究起来,历史学中有关心态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芒德鲁的老师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办者。1941年,费弗尔在《情感与历史》(“La sensibilité et l’histoire”)一文中强调有必要讨论情感及其表现的历史性。在费弗尔看来,情感不是由于外部世界刺激而产生的自动回应,而是一种社会表达。要重建情感生活,就有必要利用三种资料——“风俗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实际的情况是,杜比、芒德鲁除了利用上述三种资料,还使用了地图、数字等。
牛津大学的学者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在《法国(1848—1945)》(France, 1848-1945)中提到,民族的理想形式在平时和战时或危机时刻表现各异,但共通之处在于:“就法国而言,首要也是最具影响的理论便是它代表‘文明’。” 1929年经济危机时,费弗尔组织了以“文明”一词为主题的研讨会,参与者包括马塞尔·莫斯和韦伯(Louis Weber)。费弗尔在这次的主题讨论中追溯了“文明”一词及其观念群的演变过程,认为文明和进步交织在一起,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末,而进步属于道德与社会改良的一部分(Febvre, “Civilisation”)。在区分不同层次的文明时,费弗尔关注价值和信仰,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文明。在这次讨论之前,费弗尔就提道:“文明不是完全由物质创造,即不是由机器和不同复杂程度的工具组成的。文明是一套观念、情感和信仰体系。”(“Un champ privilégié d’études”)

杜比在自传History Continues第九章中说,他“早至1955年”就开始展开心态史的研究,和比他小两岁的芒德鲁一起沿着费弗尔开创的道路前进。他们合作的成果就是《法国文明史》。1956年费弗尔去世后,芒德鲁从《年鉴》杂志编委会的名单中消失了,布罗代尔成了杂志的全权负责人。在布罗代尔担任《年鉴》主编期间,杂志花了更多篇幅关注非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同样作为费弗尔的学生,布罗代尔在1962年出版了一部面向中学生的《文明史纲》。布罗代尔在其中谈到了文明一词的衍变,认为应利用社会科学的成果,从地理、社会、经济和心态角度研究文明。芒德鲁在理念上遵循老师的看法,将十六世纪看作一个具有活力的时代,多从心态上讨论大众文化的变迁。虽然都强调文明的连续性,但布罗代尔更看重诸文明之间的接触、交流和适应,用长时段的视野对之加以观照,将843年8月《凡尔登条约》看作法国边疆定型的年代。
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法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但殖民地、移民的内容却很少出现在《法国文明史》第二册当中。在1969年之前,研究殖民史的学者对土著居民更感兴趣,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列维-斯特劳斯谈论巴西的“非虚构作品”《忧郁的热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忧郁的热带》遭到著名的伽里玛出版社的编辑婉拒,理由是他们认为“旅行故事不受法国读者欢迎”。可见,在1969年之前,法国谈论民族史的连续性是主流。换言之,越南、摩洛哥和突尼斯独立后,历史学家开始将遭到消解的法兰西整合成一个集中讨论的主题,强调它的连续性,将多维度的“我”转变成“我们”。
三
受神经科学、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当前历史学界存在一种“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例如,泽尔丁的《法国(1848-1945)》就试图讨论“六种情感:抱负、爱、怒、骄傲、品味和焦虑”。具体说情感,它还包括开心、悲伤、恐慌、怀旧等。作为专题之一,情感史诠释个体和社会、人类的感受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法国文明史》用了较多篇幅谈科技的进步,表现出科技中也包含了情感。第十七章主要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科技和艺术成就,赞赏“自由探索知识的氛围与前人创造的条件”推动了法国知识界的繁荣活跃(725页)。
基佐提议在研究文明史之前有必要学习通史。换句话说,文明史不等于通史,也不同于文化史。“Civilisation”一词于1756年首次出现在法国米拉波的《人类之友》中,既表示一个持续的过程,又展现一种存在状态,且于1772年才出现在英国文学家鲍斯韦尔的《约翰生传》中。德国学者则将文明看作是第二层次的、只处理外部事物的概念;文化(Kultur)表现的是他们对民族骄傲和成就感的自我理解,更侧重思想、艺术和宗教上的事物。虽然文明史和通史、文化史一样,都可以按时间顺序来写,但文明史更侧重经济、社会和科技上的内容,《法国文明史》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在全球化时代里,诸文明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应该成为文明史的一部分。按照年鉴学派的理念,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应该成为文明史讨论的重心。财富的增长、物质的交换和科技的变迁属于经济文明的内容。人类的社会关系在互动中得到发展、成长,属社会文明的内容。从词源学上说,与“civilisation”相关的动词“civiliser”(使文明),是一则法律术语,用来描述刑事诉讼向民事诉讼的转变(本尼维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第十九章)。法律尤其是民法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因而法律文明应该在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杜比、芒德鲁对法国的法律描写得相对较少,只提到《南特敕令》《民法典》等律令,没有谈到《共和十年宪法》、确立免费义务教育的《费里法》等。
接触、交流才有创造的可能。保罗·利科在论“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时写道:“每种文化都没法承受和化解现代文明的冲击。这里出现了一种悖论:如何在变得现代的同时又能返回根源;如何在复活沉睡的古老文明时又参与到全球文明中。”(Ricoeur, History and Truth)回应这一悖论不是一部著作所能独立完成的使命,但在《法国文明史》中,我们能找到一些回应的痕迹,或深或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