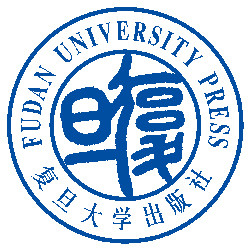不跪的大学!120年前那场“震旦决裂”,如何炼成复旦风骨
原创 小复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05年春日,风云际会之时,马相伯先生毅然携震旦出走的师生,另辟蹊径,再创新校。
沪上各界贤达,纷纷援手,共襄盛举。是年下半年,农历中秋次日,这所承载着新希望与梦想的学府,终得开学之喜。
校名初定“新震旦”,意在光复旧日辉煌;后更名“复旦”,取“旦复旦兮,日月光华”之意,寓意学校如日初升,生生不息。复旦在这一年中经历新生与涅槃。

复旦新创仅过了一个学期,马相伯便因故离开学校。全新的复旦差点经历一次停办重组,此时学生大哗,最终由各位名流校董苦心支持,严复亲自主持大局,复旦才在之后几年勉强立足。
时光荏苒,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元时复旦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占据,最终被迫迁至无锡惠山李鹤章祠,再迁回上海徐家汇,于李公祠中继续办学,这一办又是十年。
直至1913年掌校的功勋校长李登辉先生,以远见卓识,于1922年将复旦迁至日后之永久校址——江湾(今邯郸校区相辉堂周围)。
自此,复旦如鱼得水,如鸟归林,开启了全新的时代篇章。

“从震旦到复旦”语出马相伯《一日一谈》之中,马公在这篇访谈中提及诸多出走震旦、新创复旦的细节。
关于1905年时复旦从震旦中分离并重新建校的风波,学界虽然有所描述,但是常以民族主义矛盾笼统解释,较多从民族主义角度关注建校早期马相伯与耶稣会的博弈。
无论是法文文献《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还是在中文文献《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马相伯《一日一谈》中,都没有避讳当时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风波。这些描述虽很难说客观,但却从内部披露了一些关于这场风波的细节。
首先,马相伯《一日一谈》二十四《从震旦到复旦》里的记载,是大家最熟悉的:不过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因其中的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我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复旦初办的时候,经济非常艰窘,校址又没有。
马相伯的这段提到了自己离开震旦是因为与之上课与管理理念不同,最终我们了解下来也确实如此。
但很多年以来,我们赋予了马相伯出走震旦、新创复旦举动太多不存在的、民族主义语境的意义。
实际情况其实要单纯得多。从1904年底开始,震旦新来的教务长南从周与包括马相伯在内的中国师生,在教学理念,尤其是课程内容上发生冲突,无法调和,最终导致学生离校另创新校。
其实马相伯在20世纪与法国天主教会及震旦大学之间,关系始终保持密切,并没有因为出走震旦而影响两者的关系。
更多的有关震旦风波的记载,仍未被学界充分利用,其中就有法文的教会文献。1918年7月—10月合刊的《中国通讯》,从耶稣会士内部的角度用更详细的细节记录了震旦和复旦的风波。“
第二年(1904),南从周神父(P. Flix Perrin)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务长,有两名神父和四名辅理修士协助他的工作;这时学校已经有了100名学生。
徐家汇天文台的旧房舍被让给了他们。这所年轻的学校希望在两年的课程中教授“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击剑、舞蹈、钢琴,毋庸置疑还有拉丁文和哲学”;“拥有总教习头衔的马相伯和那些最胆大妄为的学生相处得不好,他们想要将自己的课程强加于人,并以英文来替代法文”。最终的一场冲突导致了决定性的分裂。
“1905年3月初,马相伯决定并让人在中文报刊刊登启事,今后他将负责管理震旦的财政。这项决定引起了最具影响力的学生,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是学校创建者的不满。他们宣称天主教会无视过去的惯例企图独揽震旦,他们退出学校,并且怂恿他们的同学也这样做。许多人效仿了他们;3月7日,马相伯宣布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也无法继续管理震旦了,他离开了学校;一大群人随之而去,这项事业只得终止了。第一时期的震旦存在了两年。”
《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则记录:“至一千九百零四年岁首,学生增至十倍。相伯先生谓锐进之时机已至,即请耶稣会命。安徽传教司铎南从周遂被召至沪,而为震旦之教务长矣。南公尽改旧章,学生抗不从命。相伯先生恐己故阻南公之施设,辞职而去。”
中西文献中同时提到,从震旦到复旦的主要原因是马相伯与南从周之间关于学校课程设置的不同看法。
最终的导火索是“英法文”之争,从这点来看似乎并未涉及任何民族主义的内容。在此需要提及的是,震旦大学建立的初衷其实本为“译学馆”,因此正如李天纲提出震旦学院带有“译学馆”“译社”性质,即马相伯和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时期商议的“Akademie”,并非常规大学;因此震旦大学创校时,其实注重的是拉丁文教学。
《震旦学院章程》:“本院以广延通儒,培成译才为宗旨”,学业二年,“首年读拉丁文,次年任读何国文,以能译拉丁文及任一国之种种文学书为度。”
然而,之后在实际教学中逐渐发现拉丁文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于是逐渐调整,根据张若谷的《马相伯先生年谱》记载,早在震旦大学成立的第二年,课程设置就调整为“所定课目,大别为四:曰语文学,曰象数学,曰格致学,曰致知学。语文一科,以拉丁文溯其源,仍分习英、法、德诸现代语,以应世用。”
由此可见虽然拉丁文教学依然没有废除,但英语法语等“现代语”的比重明显增强。
而在英语和法语之间选哪个语言之间的问题上,根据马相伯的《一日一谈》中记载,1905年初,南从周担任教务长之后,便推出新的课程改革方案“废英文,重法文,教育各权皆掌之西教习”。
于是才在学校引起轩然大波。这与《中国通讯》中记载的“他们想要将自己的课程强加于人,并以英文来替代法文”相一致。由此可见,“从震旦到复旦”转变的根本原因其实是震旦大学内部的“英法语言之争”。
另外,在之后成立的《复旦公学章程》中,也明确拉丁文作为本科(“正斋”),文科(“第一部”)和理科(“第二部”)列在最后一门课程。
拉丁文教学仍然保留,但已经与基督新教所办的学校类似,英语是第一外语,且作为课堂教学语言。
作为此次风波的焦点,震旦大学的学制也因这场风波产生了一定的变化,《震旦大学二十年小史》记录了风波前后的震旦学制变化:“李、南两司铎长校时(复课之后),改肄业期为四年。
第一年为中文教授,第二年始以法文教授。此两年名曰附科。至第三年,始称本科。授法文、英文、文学、中外历史地理、哲学、经济学、法学、算学、物理学、博物学。至第四年,分为文理两科。”
由此可见,风波之后分别重启的震旦和复旦之间,除英语和法语的区别之外,其他课程上,并无本质性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从震旦到复旦”的过程中,有英法文之争,也有课程设置的“话语权”之争,但之前我们一直认为的“民族主义”似乎并没有涉及。
正如李天纲教授在《从震旦到复旦:清末外语教育与民族主义》所提示的那样:脱离震旦学院之后的复旦公学,更加持有一种“语言世界主义”,而不是“语言民族主义”的价值观,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马相伯最终因为“第一外语”与“第二外语”课程,与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学校震旦学院分道扬镳,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是段不甚愉快的经历。
震旦大学名义上仍是教会创办的学校,耶稣会提出让马相伯带薪休养,马相伯很不开心。1905年春天矛盾到不可调和,大部分学生都跟着马相伯出走,最终在吴淞重新创办学校。
这所学校最早名称是“新震旦”,后来于右任就说新办学校是“光复震旦”,就改名复旦。历史进入了“复旦”的时间。
/ 今日荐读 /

《巍巍学府:复旦·上医与近代中国(1905—1949)》
王启元 著 顾雷 编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年5月
本书深入挖掘复旦大学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历史渊源,从两校在民国时期的起源、共同经历的近代史风云,到2000年的合并,展现了两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办学历程。
复旦学者王启元先生不仅梳理了两校在吴淞同处、功勋校长均为耶鲁毕业生等历史细节,更突出体现了国人办学创求、追求独立的精神,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丰富的史料,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教育与时代交融的历史画卷。
本书不仅是对复旦大学创校120周年、上医建院98周年的献礼,更是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一次深刻回顾与致敬。无论您是教育史研究者,还是对近代中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本书都将为您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深刻的思考。
本期编辑 | 陈丽英 凌皓雯(实习)
本期摄影 | 陈丽英
原标题:《不跪的大学!120年前那场“震旦决裂”,如何炼成复旦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