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自我演戏以来(1907-1928)〉校勘及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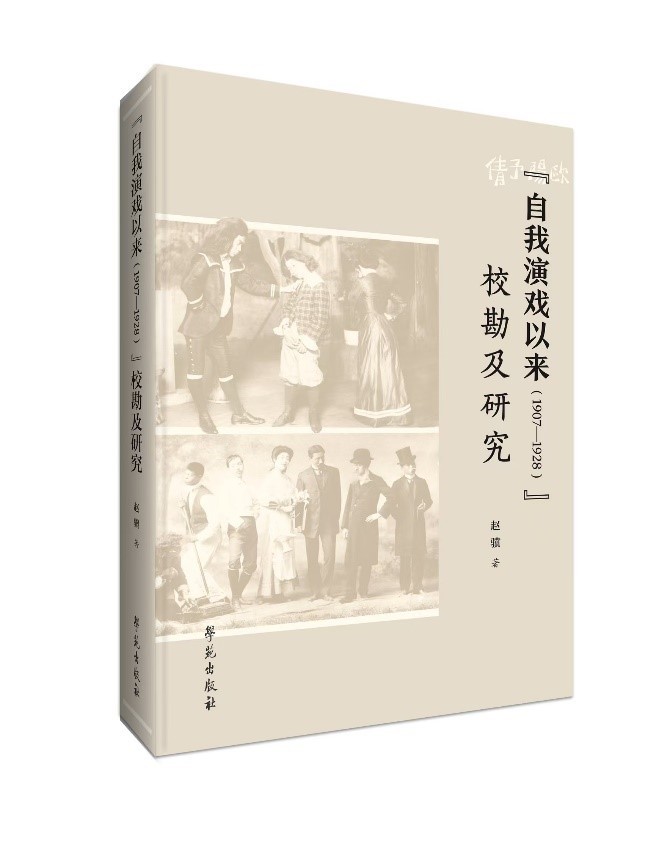
《〈自我演戏以来(1907-1928)〉校勘及研究》,赵骥著,学苑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研究中,欧阳予倩始终是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他既有中国话剧“奠基者”之称,又是传统戏曲的革新家,更是涉足电影、音乐和舞蹈的多面手;他既能在职业演剧中游刃有余,塑造了红楼尤氏、潘金莲等诸多女性角色,又能在时代的洪流里坚守“中国式演剧”的艺术理想。其艺术实践、理论探索和戏剧教育三轨并行,贯穿了中国戏剧现代化转型的激荡岁月。《自我演戏以来》作为欧阳予倩先生的经典自传,记录了他从留日学生到话剧先驱,再到京剧名伶和戏剧教育家20余年间筚路蓝缕、纵横捭阖的从艺经历。这部作品不仅是欧阳予倩个人艺术生涯的写照,更是中国早期话剧运动的重要文献,被誉为“一部近代中国戏剧变迁史”。
上海戏剧学院赵骥教授以《自我演戏以来》的校勘与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欧阳予倩这一重要早期论著不同版本的系统性整理与深度阐释,不仅还原了历史现场的肌理,为戏剧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持,还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早期话剧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以史为鉴,重构戏剧现代性转型的中国路径,在学术层面为当下戏剧文献资料整理与戏剧史研究工作树立了新范式。
一、文献校勘:中国近现代戏剧历史的再发声

图1,《宝蟾送酒》剧照,欧阳予倩饰宝蟾
对《自我演戏以来》的校勘、研究工作绝非简单的文字考证,而是一场对中国近现代戏剧历史碎片的考古式复原。《自我演戏以来》自1929年在广东戏剧研究所《戏剧》杂志连载以来,就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而备受关注,如当时南京《中央日报》对其中部分内容就进行了转载。而后又集结成书,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于1933年、1939年先后两次出版,1959年欧阳予倩对原书做了较大修改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重新出版。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欧阳予倩记忆的偏差及社会环境、观点变化等因素,该书内容仍存在不少舛误和遗漏。因此,校勘著述以“辑佚钩沉”的严谨态度,将不同时期各种版本的原始文献重新缀合,以1959年版为校勘底本,通过比对各版本,多方查阅民国时期大量报刊、档案、族谱、戏单等文献,考订全文内容,创造性地构建起多重考证体系:时间锚定——结合史料和当时的演出记录,对原书中的个人经历和演剧事件进行了精确的时间标注,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研究者的“时间不明”问题,还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时间线索;空间复原——以地方小报、戏单广告等文献还原早期话剧的生存空间,揭示春柳剧场“高雅艺术”表象下的资本运作真相;关系网络——借助族谱、日记、档案等文献资料,勾勒出欧阳予倩跨越政、商、学、艺四界的立体社交图谱等等。这种“以文献证文献”的方法和“显微史学”的功力,使一些尘封的史料重新发出巨大回响。

图2,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演出《黑奴吁天录》纪念明信片
尤为可贵的是,校勘中特意保留褪色戏单上的涂改痕迹、报刊广告中的夸张修辞,亦将欧阳予倩的舞台照、春柳社早期剧照乃至欧阳予倩夫人刘韵秋女士画作等纳入校勘范围。对于欧阳予倩的记忆偏差,如将新剧同志会《家庭恩怨记》的演出地点误记为“大舞台”,将剧中角色小桃红的饰演者误记为自己等情况,作者均在保留原版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史料在注释中进行了研究和修订。这种对历史“毛边”的珍视,使校勘本本身成为复调叙事的载体——既呈现欧阳予倩作为亲历者的主观视角,又透过文献裂隙折射出时代的多重镜像。
考据之外,这部校勘著述更注重从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视角对《自我演戏以来》进行深入解读和研究,对书中提到的人物、事件和演出均进行了详细的补充和注释。例如通过《浏阳麻田蛇头欧阳五修族谱》,解释“簪缨世家”出身的欧阳予倩何以能游走于张謇、李济深、陈铭枢等政要之间,特别是1929年欧阳予倩由沪赴穗的详细经过以及广东戏剧研究所开办的相关文献补佚,明确了欧阳予倩广州之行,并非所谓的“在野”之旅,而是承奉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正式之任命,其管辖的戏剧研究所乃一实体,隶属广东省教育厅等史实。1907年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春柳社”,上演新剧《黑奴吁天录》,归国之后春柳旧部重组新剧同志会,在上海及周边城市演剧,因演剧风格过于“日化”,致使“营业不振”,遂以“文社”之名远赴长沙演剧,欧阳予倩虽躬逢其中,但其书对之语焉不详,赵骥通过搜集存留坊间的《文社湘剧场特别广告》《寿春茶园特别广告》等史料,补充了文社长沙演剧的详情,尤其是文社的组织架构,与昔日的春柳社有几分相似之处。随着湘省时局动荡,文社演剧深受影响,为了生存,文社成员离开“湘剧场”之后,进入长沙的茶园演剧,与旧戏同台,直至1914年初,方始回沪。这段史料的钩沉,不仅修正了欧阳氏书中记述之不足,亦填补了话剧史研究之空白点,颇具新意。作者通过爬梳《申报》《晶报》等旧时报刊上大量的史料,欧阳予倩家庭及其个人生活等细节,进行详尽的梳理,如1925年欧阳予倩50周年“磁婚纪念”仪式以及其他与旧时同学好友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特别是从纷繁杂芜的报刊中辑录出欧阳予倩与日人辻听花、东北大学教授许觉园等之间的书信往来,真切地反映出20年代欧阳予倩心路历程之变化,此等问题尤当引起学界之关注。1933年,“福建事变”,欧阳予倩涉事其中,一般史籍少有述其,赵骥通过台湾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时期档案,还原欧阳予倩与“福建事变”的隐秘关联。此外,还通过梳理民国小报的戏剧评论,考证“南欧北梅”并称现象,指出这一说法最初源于上海新舞台的营销策略,进而折射出商业资本对戏剧明星制的塑造。
因作者长于文献梳理,并且掌握了大量的史料,其在校勘、研究《自我演戏以来》之过程中,与同时期的《菊部珍闻》《戏杂志》戏曲资料相互参照,揭示出欧阳予倩看似个人化回忆录中暗藏的时代密码。这种将个体记忆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解读方式,不仅丰富了原文献内容,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全面的历史、文化背景,让文献校勘超越了技术层面,升华为历史话语、文化话语的解码实践。
二、学术重构:戏剧现代性中国路径的再发现

图3,新剧《双星泪》剧照,欧阳予倩饰武双星
校勘著述的研究并未止步于史料整理,其最大突破在于以《自我演戏以来》为基点,重构中国戏剧现代性的发生谱系。一是破除了春柳社中国话剧起源说的“神话”,通过丰富的史料揭示出春柳社与日本青年会之间密切的关系——春柳社能在东京“本乡座”演出,其背后离不开日本上流社会的赞助,而明治政府资助青年会的不菲巨款,实为用作培植亲日势力的文化渗透,这种“殖民现代性”的视角,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过去将春柳社推上中国现代话剧圣坛的传统史观。二是重新评估了长期被边缘化的“文明戏”的历史价值,过往研究多将文明戏视为“话剧不成熟的胚胎”,而该研究则从欧阳予倩观察到文明戏演员“用京剧身段说白话”的表演方式出发,揭示出这一戏剧形态独特的现代性特质:文明戏演员这种中西杂糅的舞台实践,恰是戏剧现代性在中国土壤中的本土化萌蘖。研究指出,文明戏中幕表制与剧本制的拉锯,非但不是艺术幼稚的表现,反而创造了迥异于西方镜框式舞台的“流动现代性”,其实质指向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即兴创造”与“剧本中心”的永恒张力。著述将文明戏置于上海市民社会的文化生态中考察,发现其商业性运作与通俗化取向并非艺术堕落的标志,而是戏剧从士大夫书斋走向市井茶馆的必然路径。这种研究视角打破了“艺术/商业”“高雅/通俗”之间的二元对立,为重新书写中国话剧史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框架。
三、范式突围:戏剧史研究的双重维度
对《自我演戏以来》的校勘、研究彰显出戏剧史研究的双重维度:一方面是以文献为中心的实证性研究,通过对史料的深耕细作,夯实学术根基;另一方面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建构,在史实细节中提炼具有当代意义的学术命题。欧阳予倩由话剧转向戏曲的亲身经历与本著述中对此所做的相关研究、阐释即是一个典型例证:著述既通过《我怎样学会了演京戏》等文本细读还原欧阳予倩个人选择舞台艺术道路之变化过程,又将其置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博弈中,指出欧阳予倩在戏剧舞台上的“跨界”,实为探索戏剧民族化道路的自觉努力,而这种“努力”贯穿其毕生对戏剧艺术的追求中。正是这种“微观考证”与“宏观透视”的辩证统一,使本书的研究成果兼具历史厚度与思想深度。
《〈自我演戏以来(1907-1928)〉校勘及研究》是一部具有一定开创性和突破性的著作,对欧阳予倩生平和艺术成就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揭示了一个更加真实、生动、独特的欧阳予倩,这种对史料的深度挖掘与整合,不仅是对一位伟大艺术家的致敬,更是对中国戏剧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在学术研究上创新了范式,强调了在历史语境中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重要性,为我们理解中国早期话剧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