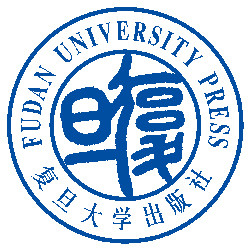《红楼梦》里出场极少的这两位女性,却是贾府衰败结局的预言家
在《红楼梦》中,有两位女性出场机会极少,但在小说故事的整体结构中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位是贾元春,另一位就是秦可卿。
贾元春对贾府的命运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她的入选贵妃,使贾府之盛达到了顶点,而元春死后,贾府就被抄,从此在政治上也就告别了那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盛巅峰。
相比贾元春,秦可卿只不过是贾母的“重孙媳妇”,原本是营缮郎秦业由育婴堂抱来的弃婴。但她的身世与故事扑朔迷离,不仅牵引着读者的心,更与荣宁二府的命运、全书的悲剧性主题大有关系。
虎兕相逢大梦归——贾元春
【原文】
只见画着一张弓,弓上挂着一个香橼。也有一首歌词云: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官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第五回)
茶已三献,贾妃降座,乐止。退入侧殿更衣,方备省亲车驾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等忙上来解劝。贾母等让贾妃归座,又逐次一一见过,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后东西两府掌家执事人丁在厅外行礼,及两府掌家执事媳妇领丫鬟等行礼毕。贾妃因问:“薛姨妈、宝钗、黛玉因何不见?”王夫人启曰:“外眷无职,未敢擅入。”贾妃听了,忙命快请。一时,薛姨妈等进来,欲行国礼,亦命免过,上前各叙阔别寒温。又有贾妃原带进宫去的丫鬟抱琴等上来叩见,贾母等连忙扶起,命人别室款待。执事太监及彩嫔、昭容各侍从人等,宁国府及贾赦那宅两处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个小太监答应。母女姊妹深叙些离别情景,及家务私情。
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贾妃垂帘行参等事。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齏,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贾妃亦嘱“只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记念”等语。贾政又启:“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请别赐名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题,便含笑说:“果进益了。”贾政退出。贾妃见宝、林二人亦发比别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软玉一般。因问:“宝玉为何不进见?”贾母乃启:“无谕,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进来。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进前,携手拦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第十八回)
讲解
作者并不一味地去写贾府的颓败,而是如戚蓼生所说的“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盖声止一声,手只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把贾府的颓败之势与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趋势扭结在一起叙述。秦可卿命归黄泉,贾元春则“才选凤藻宫”,“宁荣两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言笑鼎沸不绝”(第十六回)。元春的“才选凤藻宫”究竟给贾府带来怎样的政治利益,小说里对此着墨不多。但在“才选凤藻宫”之前,小说第四回便通过贾雨村这一角色,写出了四大家族所连结成的贵族势力如何一手遮天。小沙弥说:“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第四回)元春“才选凤藻宫”之后,贾府的政治前途达到了顶点。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这一顶点上,元春唱出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旋律。
《红楼梦》写的是一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大家族的故事,但从讲述这个故事的一开始,作者就一直不断地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忧患意识。在第一回的石头神话中,当石头要求到人间去享一享荣华富贵的时候,一僧一道就说:“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甄士隐的故事,作为小说的序幕,实际上是整个贾府故事的缩影,故甲戌本的脂批称之为“小荣枯”(第二回夹批)。
第二回则由冷子兴(所谓“冷眼旁观人”)之口说出贾府虽外表“峥嵘轩峻”,实质上只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五回通过太虚幻境写宁荣二公的家族忧患。第十回至第十三回则写第一位维系着家族命运的女性秦可卿因家族忧患而命归黄泉。宁、荣二公通过警幻仙姑以色警幻,在全书中第一次奏响了“挽家族于颓败之中”的悲壮主题曲,秦可卿的临终托梦再次奏响这一主旋律,并具体提出了力挽狂澜的方针策略。
贾元春具有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她关心宝玉的成长,自入宫后,时时带信出来与父母说:“千万好生扶养,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忧。”在贾宝玉的婚配问题上,元春选择了薛宝钗。在一次端午节,元妃赐予宝、黛、钗的礼物是大有深意的,宝钗与宝玉的礼物一样,都是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笔一领,而林黛玉的礼物则与迎春、探春、惜春相同,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宝玉感受到这种做法大违心意,宝钗则一反常态。这位从来不爱花儿粉儿的“天然去雕饰”的冷美人却一直把元妃所赐的那串沉甸甸的红麝香珠串戴在手上。元妃之选择宝钗,显然着眼于宝玉的成长与家族的利益。
省亲时,贾府的铺张排场令她担忧。她在轿内看到大观园内如此豪华,便默默叹息奢华过费。临回宫时又叮咛贾母、王夫人:“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第十七至十八回)元妃省亲的事让赵嬷嬷想起贾府曾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这淌海水似的银子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康熙数次南巡时,曹寅接驾,那奢华靡费的程度非元妃省亲之可比,而曹寅因此也留下了巨额亏空,这巨额亏空曹寅自然是无法偿还的,它作为一个巨大的包袱留给了曹,成为曹被抄家的一个重要罪状。元春对贾府的奢华靡费的担忧显然出于对家族命运的考虑。
贾蓉就曾与贾珍谈起贾府的家底,他说:“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他心里纵有这心,他也不能作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顽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够一年的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贾珍笑道:“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柏木作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贾蓉又笑向贾珍道:“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贾珍笑道:“那又是你凤姑娘的鬼,那里就穷到如此。他必定是见去路太多了,实在赔的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项的钱,先设此法使人知道,说穷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一个算盘,还不至如此田地。”(第五十三回)
在太虚幻境的“红楼梦曲”中,元春的曲子是:“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这位把贾府的政治命运推向顶点的贾元妃在繁盛的顶点时对她父母说的话却是“须要退步抽身早”。
贾妃省亲时,贾府不仅大兴土木,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大观园,而且贾母、贾政、王夫人以至薛姨妈等纷纷对她“欲行国礼”,政治身份的意识使贾母等人感受到了庄严肃穆,也体验到了政治上的优越感。所以当贾妃欲行家礼时,“贾母等俱跪止不迭”,贾政则自称“臣”、“政夫妇”,面对自己的孙女、女儿,贾母、贾政等人看到的却是皇帝的权威。然而,贾妃却始终“欲行家礼”,她把令贾府无尚荣耀的“才选凤藻宫”称为“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她对父亲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
从元春的性格来看,她贤淑、端庄、内向、抑郁。她显然不具备薛宝钗那样的人际手腕,尽管她以“才选凤藻宫”,进宫之后又加封为贤德妃,恩准元春省亲,回宫之后,“龙颜甚悦,又发内帑彩缎金银等物,以赐贾政及椒房等员”(第十九回),但是,她始终感受到皇权的重压,当她省亲时,见到大观园石牌坊上题着“天仙宝境”四字,她连忙命人换为“省亲别墅”,强调了皇权的存在。在宫中,她更是“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她似乎正艰难地承担着政治环境中的各种压力。如果真能像薛宝钗那样,“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皇宫的权力斗争中大展拳脚,贾府也许会更加“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贾府的兴盛也许可以更长久地延续下去。
然而,事实上,她政治上的无能加重了她的压抑,最后落得个“虎兕相逢大梦归”的结局。高鹗续书把贾府的被抄家写成与元春之死无关,这是不符合前八十回的暗示的。但无论如何,元春死后,贾府就被抄,从此在政治上也就告别了那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盛巅峰了。
画梁春尽落香尘——秦可卿

向上滑动阅览
【原文】
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薰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不知不觉已交三鼓。平儿已睡熟了。凤姐方觉星眼微朦,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来,含笑说道:“婶子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婶子,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子,别人未必中用。”
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愿?你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否极泰来:否、泰,《易》的两个卦名。天地交,万物通谓之“泰”;不交闭塞谓之“否”。后常以指世事的盛衰,命运的顺逆。否极泰来,谓厄运终而好运至。,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诸事都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
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凤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只是我与婶子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事云板连叩四下,将凤姐惊醒。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闻听,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处来。(第十三回)
讲解
相比贾元春,秦可卿只不过是贾母的“重孙媳妇”,原本是营缮郎秦业由育婴堂抱来的弃婴,在小说的第十三回,读者对小说的故事才刚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她便一病而亡,从读者的视线中永远地消失了。但是,尽管如此,她的故事仍然牵引着读者的心。这其间的原因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作者采用了他擅长的扑朔迷离之笔去写秦可卿的私生活,二是现存各种《红楼梦》版本中的秦氏故事留下了诸多未完成的乃至互相矛盾的痕迹,形成为无法解开的谜团。
早在1921年,差不多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发表的同时,署名臞蝯的《红楼佚话》就谈到有人曾见过《红楼梦》的“旧时真本”,其人物结局与程本大异,其中,“又有人谓秦可卿之死,实以与贾珍私通,为二婢窥破,故羞愤自缢,书中言可卿死后,一婢殉之,一婢披麻作孝女,即此二婢也。又言鸳鸯死时,见可卿作缢鬼状,亦其一证”。1927年,胡适意外地得到了“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惊喜不迭,立刻写信告诉钱玄同: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批者为曹雪芹的本家,与雪芹是好朋友。其中墨评作于雪芹生时,朱批作于他死后。有许多处可以供史料。有一条说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此可以改正我的甲申说。敦诚的挽诗作于甲申(或编在甲申),在壬午除夕之后一年多。……又第十三回可卿之死,久成疑窦。此本上可以考见原回目本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后来全删去天香楼一节,约占全回三之一。今本尚留“又在天香楼上另设一坛(醮)”一句,其“天香楼”三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今始知为删削剩余之语。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
甲戌本的脂批多处点明此本中的删剩之文,譬如,小说第十二回,写贾府的人听到秦可卿死亡的消息,所有的人“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脂砚斋批道:“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在“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处,脂批:“删却是未删之笔。”在“因忽又听得秦氏之丫环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处,脂批:“补天香楼未删之文。”在该回结束处有一眉批:“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
又有回后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这里,脂砚斋告诉我们,读者所读到的甲戌本的有关秦可卿的文字,乃是删余之文,在未删改之前的原文中,秦可卿不是病死,而是“淫丧”。这与臞蝯所了解到的“旧时真本”甚为吻合。
1959年,毛国瑶在南京发现了靖应鹍所藏的又一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版本,称“靖藏本”。毛氏将其中不同于有正本的一百五十条批语抄出,是为“靖批”。当他准备再校录正文的时候,适值靖氏外出,该本子被其家人售给了鼓担,从此迷失,毛国瑶所抄的这些批语则留了下来。这些批语曾经三次于不同时间发表在不同刊物上,但每一次刊出的内容并不一致,而且后出者会出现新的错误(1974年靖藏本首次公开发表在南京师院的《文教资料简报》第21、22合刊上,1975年又发表于北师大《红楼梦研究资料》中。文字有所不同。故这一版本以及“靖批”的真实性历来受到学界的质疑。)但是,“靖批”的出现却为红学中许多原本疑团重重的问题披上了更加扑朔迷离的外衣。
关于秦可卿之死,“靖批”把甲戌本的回后眉批与回后评合为一条,并在“因命芹溪删去”之后加上六个字,成为“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更加把“淫丧”具体化。今天的读者已经读不到“遗簪”、“更衣”之类的故事,但是,读过这一条批语的读者恐怕很难放弃对“遗簪”、“更衣”之类的历史本事的遐想,它加深了读者对秦可卿原本故事的猜想。
赵冈、陈钟毅根据靖藏本推测第十三回被删的情节:“秦可卿一定是在宁府某处遗落了她佩带的簪子。此物后来被贾珍拾到。他认识此物是秦氏的,于是亲自送还给可卿。此时秦氏正在天香楼上更衣,贾珍一头闯入,丑事因而发生。”高阳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时当盛暑,想是可卿新浴初罢。‘更衣’二字,在从前的用法很多,涵义微妙;说不定这一段中还包括‘窥浴’在内。”这样的探佚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故事化倾向。
当代作家刘心武曾经指出秦可卿故事的诸多疑窦:一、据脂批,佚稿中有“淫丧天香楼”、“更衣”、“遗簪”等情节,今本皆无。二、秦业领养女孩,于理不合。三、所谓“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的说法没有可比性,贾府中的“重孙媳”就只有秦可卿一人。四、秦可卿卧室的摆设从“风流种子”的角度看,这种描写并不高明,从暗示秦氏高贵出身的角度看,则是大有深意。五、秦氏的气质及其在贾府中的如鱼得水,与她的来自育婴堂的出身并不协调。六、警幻仙姑透露,秦可卿本来许配与贾宝玉。七、秦氏向王熙凤托的梦与其原本营缮郎女儿的身份不符。八、北静王祭秦氏而不祭贾敬。九、秦氏的棺材正显示她出身之高贵。
……又据有关史料,曹曾替雍正死敌塞思黑藏金狮子,刘心武认为曹有可能替雍正死敌收留、教养子女。秦可卿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的女儿。小说中的张太医也非寻常人物,他是秦可卿的父母派来传达旨意的,他开出的药方的前五种是:“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刘心武认为这是暗语:人参、白术为秦可卿父母的代号,全五种药解读为:人参白术云,令熟地归身。即父母说:令你在熟悉的地方自杀。因为她的父母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所以叫秦可卿自杀。刘心武把这些想象写成了“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刘心武的文学想象读者尽可以一笑置之,但他总结的这些疑窦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小说之中,令二百多年来的读者百思不得其解而又欲罢不能。
倘若我们不舍近求远,不去玩味秦可卿故事的隐喻意义或历史本事,而是直面秦可卿故事在全书中的具体展开过程、直面这一故事与小说中其他故事的衔接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会对秦可卿故事与全书的悲剧性主题的关系更感兴趣。
在小说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图谶中,与秦可卿有关的图是:“画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缢。”其判词是:“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这一图谶既暗示了秦可卿的“淫丧天香楼”的结局,又显示了秦可卿之死与荣、宁二府的命运大有关系。
宁国府的主事者是贾珍,管家者自然轮不到秦可卿,然而,秦可卿却怀具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她的忧患绝不仅仅是宁国府的命运,而是整个贾府的命运。张太医在给秦氏看病时指出:“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忒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第十回)她的病死即是她的“思虑太过”的直接结果。
她的“思虑太过”集中表现在她在王熙凤梦中所说的话。在这番话中,可以见出秦可卿已经感觉到了贾府乐极生悲、“树倒猢狲散”的趋势。不仅如此,她还定下了破败之后的可保永全的良策:多置田庄房舍地亩。因为在破败之时,祭祀产业是不入官的。秦可卿的这番思虑与宁、荣二公同出一辙,宁、荣二公之灵对警幻仙姑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性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第五回)可见秦可卿具有与宁、荣二公一样的家族决策者的风范。她明知贾府已经到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临界点,但她却要力挽狂澜;她虽将魂归薄命司,却要把可保永全的救世良方留给下一任的管家人王熙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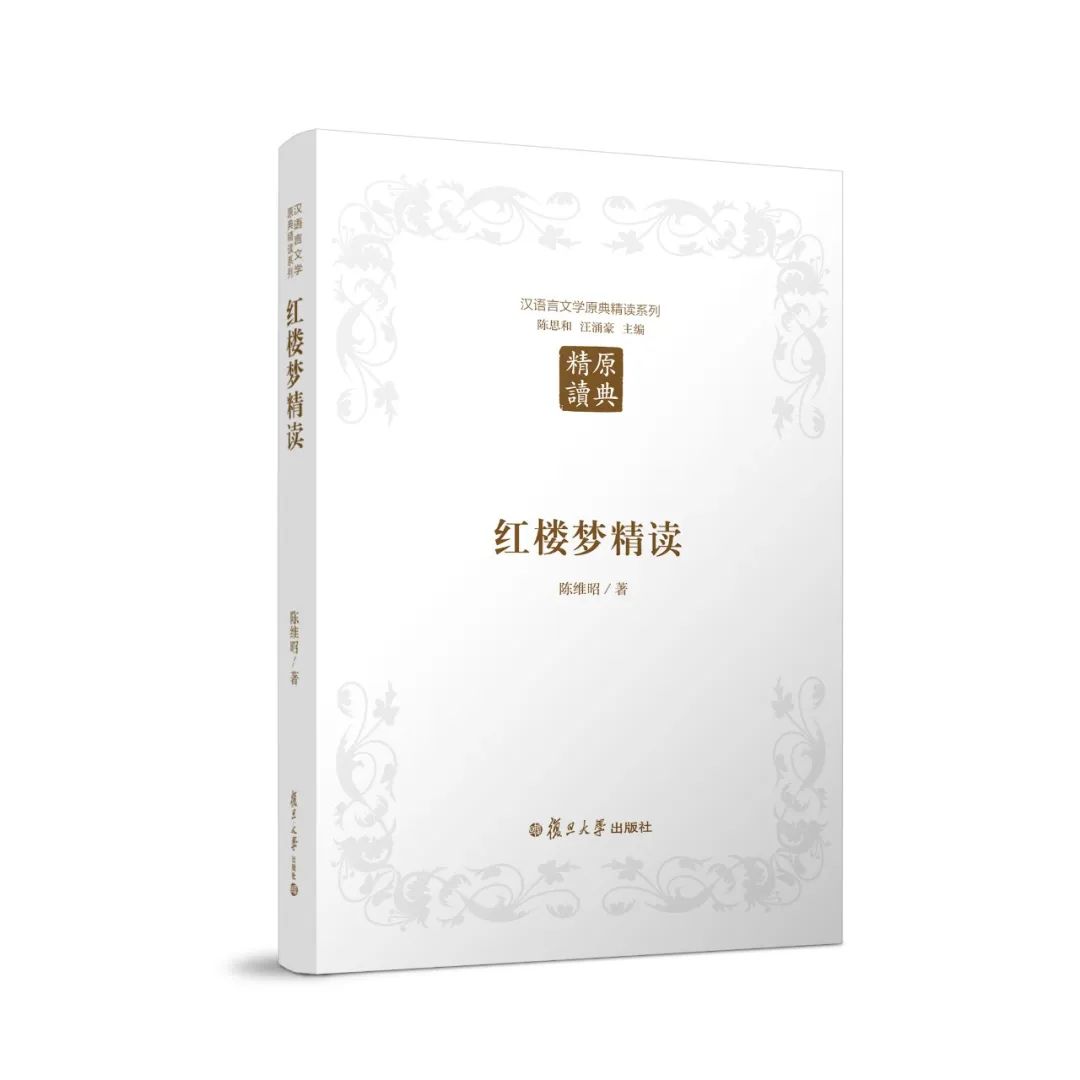
红楼梦精读
陈维昭 著
宋文涛 编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维昭教授的《红楼梦精读》,集中介绍和探讨有关《红楼梦》一书的诸多问题与谜团。全书共九讲,分别就这部名著的作者与成书、楔子与原型、评点与版本、命意与人物、结构与修辞、前八十回与续书等多个议题,结合原作加以聚焦讨论,力求在现有的研究语境下为以上问题寻绎出最佳答案。作者用笔轻灵,文思缜密,行文立论优游不迫而又张力十足,是一部优秀的红学研究著作。
原标题:《《红楼梦》里出场极少的这两位女性,却是贾府衰败结局的预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