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上海社区餐饮街:化解商居矛盾有哪些低成本解决方式
越来越多餐饮企业“选址”社区,并将其视为重要的市场策略。社区餐饮指的是在社区、服务社区日常需要的餐饮门店,大部分沿街经营,与购物中心、“商场”综合体的餐饮有所区分,大多有着较低的人均消费、离家较近的距离和较为窄小的沿街门面。
社区餐饮不仅是餐饮企业经营的空间,还承载着居民日常消费、社区互动。作为餐饮市场最贴近民生的一个侧面,社区餐饮生存状况反映了企业在社区这一具体空间和政府、居民互动。此外,社区餐饮还作为社区的“会客厅”“街道眼”,强化社会连接、保证城市安全,具有社会、文化等多层面价值。
目前上海的社区餐饮企业生态如何?社区餐饮在带来便利性、烟火气的同时,为何引发和邻近居民的矛盾,又有哪些解决方式?
2024年7月至10月,研究员走访上海10条社区餐饮“街”(杨浦彰武路、大学路,浦东蓝村路、南泉路、浦电路及徐汇天钥桥路、静安威海路、黄浦宁波路、浙江中路、福州路)并访谈了2位街道主任和若干居民(消费者),描述了上海社区餐饮生态特征、影响并分析原因,基于居民、街道主任和商家的访谈,呈现商居矛盾的解决方式,展示社区这一城市空间中商家、居民、政府相互需要、制约的互动过程。
社区餐饮趋势:大牌化、轻质化、平台化
饭馆、餐厅最早在居民身边出现,是因为政府减少市场管制,希望以“社区商业”促进城市活力。在中国,社区餐饮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宋代的“街市制”。街市制打破“坊市制”分区、宵禁等商业管制 ,宋代商业因此繁盛 ;在欧美国家,社区商业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后在二十世纪70年代应用于反郊区化的城市“步行友好”社区,也广泛影响中国现代城市规划。近二十年,社区商业建设在中国受到国家政策鼓励 。
研究员观察到,社区的餐饮生态正在显示出大牌化、平台化、轻质化的趋势。
(1)大牌化:大牌餐饮存在感强,消费者感到社区“缺乏个性”
社区餐饮门店包含三种类型:连锁企业、个体商户与公建民营的社区食堂。三者之间会有转化:个体商户可能转化为连锁,开出自己的品牌;连锁企业可能负责运营社区食堂;连锁加盟户在积累经验后,也可能开自己的个体店铺。
近年来社区市场持续受到头部、大型连锁餐饮品牌关注。不少以前在商场开150平方米门店的连锁品牌,以社区店的新商业模式涌入社区餐饮市场,开30-75平方米左右的社区店。例如,华莱士、绝味食品、瑞幸和蜜雪冰城开出“万店”,茶百道、喜茶、袁记云饺、吉祥馄饨、呷哺呷哺(H股、A股上市公司)、海底捞 以及Manner咖啡开出“千店”,南城香、柠季、库迪、沃歌斯、紫光园等开出“百店”(图1)。
店铺转手给大企业,或成为大牌加盟店的现象大量发生。例如,南京西路街道300米左右的威海路上,连锁店占80%,原有个体商户搬走后,换成库迪、柠季、Manner等被人熟知的店(图3);宁波路上的个体西餐店也换成了袁记云饺(图2)。

图1、图2、图3 :2024年7至10月,杨浦、黄浦、静安新开业社区连锁品牌门店。这些店原来都由个体商户经营。以下图片若无说明均由澎湃研究员 吕正音拍摄。

图4、图5、图6: 2024年7至10月,宁波路、彰武路、南昌路,部分社区个体餐饮商户。
头部、大型餐饮品牌门店在街上“存在感”高,挤压个体商户生存空间。个体户有几种路径:一是闭店“回老家”。杨浦一家个体咖啡店表示,他所住大楼里餐饮业界朋友“没留下几个”,导致大楼“物业都撤了”。二是变成大牌“加盟店”,从个体老板成为“大牌”员工。
(2)平台化:社区店“做外卖”,企业感到平台“有帮助” 但“费率高”
网订柜/店取、扫码下单,以及平台选址、点单、支付等数字化模式,正在被餐饮大牌、个体商户甚至社区食堂广泛使用 。社区里已有堂食的店纷纷加入平台,形成“堂食盈利+外卖走量”的“组合拳”。据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数据显示 ,上海合作外卖平台的企业约有6万余家,占餐饮企业总数的60%,每天约有300万单。
不仅堂食店大部分做外卖,还出现大量“纯外卖店”。小商户的纯外卖店投资小、成本低,门槛低,但各项投资均在平台,其盈利模式过于依赖平台。由于近年费率提高,40%的纯外卖个体商户没能存活。
另一种形式是大牌连锁企业和平台“合作”开的“外卖卫星店”。百度慧眼 、美团、阿里等大平台企业开辟 “智能”选址系统 ,助推品牌企业在社区开大量“只做外卖”的“卫星店” 。该模式因品质放心又省人工、租金成本而迅速扩张。根据美团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截至2024年6月底,已有120个品牌在全国累计开出超800家卫星店。例如,老乡鸡与美团外卖达成卫星店战略合作,计划在2024年内开设50家“卫星店”。这被一部分企业认为有助于企业“快速触达客源”(通常是连锁),但被另一部分企业(通常是个体户)认为“平台费率越来越高”,给企业带来不小的压力。
(3)轻质化:重餐饮商家搬离社区,商户选址感到“两难”
“在居民区沿街选址容易被投诉‘太麻烦’,而租商场门店的话租金又高,怎么办?”一家江西菜餐馆道出自己的两难境遇。商家认为选址社区“很难”的原因是“取得楼上五、六层楼居民认可不容易”,除非“房东就住楼上”,“如果不能避开,就需要改变业态,经营轻餐饮”。
在大牌餐饮总体往社区选址的同时,重餐饮企业却离开居民密集处,流向社区商业综合体等场所。据研究员观察,上海多家中餐厅、川菜馆、烤肉馆、火锅店等油烟、噪音重的餐饮企业,仍大多分布在配有油烟管道设施的商业综合体内。
大部分受访商家提到“居民要求太高”,且不清楚街镇的“管理依据”,认为其“过于偏向居民”。一家静安烘焙店表示,烘焙“香味”也会被居民投诉“不符合常理”;徐汇一家酸菜鱼餐馆表示,“调整了两三次”仍无法获得“希望开窗睡觉”的居民满意,感到“无奈”。仅有零星“重餐饮”还在社区沿街。研究员观察到,这些商户得以“豁免”的特征是在地时间长、以邻里、熟客生意为主,且安装了功能较强的排烟管道。
制度视角:整体式城市更新、平台机制和12345考核制度
社区餐饮生态形成平台化、大牌化和轻质化的特点,可能与城市“新建绅士化”、平台经济依赖和12345投诉在基层考核中愈发重要有关。
(1)政府“新建绅士化”造成社区餐饮“阶层置换”
社区商铺的门面租金相对商场便宜,且攀升较慢,导致前述不少大牌、连锁企业转向社区,而社区“大牌”比例变高的现象。
根据2024年7月的中指报告 ,百mall商铺平均租金在二十几元/平方米/天,但购物中心涨幅0.25%,而街上商铺仅有0.09%。加上消费降级、商场人流变少,本应该是商场主力的大牌连锁餐饮利润下降,出于“降本增效”“寻找市场增量”等考量,头部、大型连锁餐饮品牌商场关闭商场门店,转而选址租金压力较小的社区商铺。房东偏好把商铺租给更大牌的商户,认为这样“交租”稳定。这无形中挤压了小商户的生存空间,造成了前述个体商户退出市场的情况。
促使商户搬迁的因素多来自整体式的城市更新、“焕新”商圈等,被学界称为“新建绅士化” 。新建绅士化是指再开发项目产生的社会空间上“直接和间接”的阶层重构。李鹏鹏、刘思利等学者指出 ,新建绅士化通过“急剧提高邻近区域的生活成本”,损坏原有社会关系,导致“低收入阶层因经济、社会原因主动迁出”,即价格阴影效应,在阶层的直接置换之外还存在着阶层的间接置换。
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黄浦区一个体咖啡店表示,他在收到所在街道即将改造为新商业街区的“通知”后就搬离;杨浦区一小吃快餐店表示也因街道需要更新大学周边“商圈”面临搬迁;虹口一面包烘焙店表示,他原来是该社区商业中心的“门面”;几个月前跟物业协商挪了位置,将人流量最好、位置最好的商铺让给了某大型连锁体育用品店。
“大牌化”伴随着“绅士化”显著影响原有社区商业营收,让个体企业流失。一家徐汇咖啡店告诉研究员,由于附近的更新项目周期较长,商铺的长时间空置,空置率目测可能达到50%,对仍在地的商铺也产生影响:“旁边的商铺搬空之后,我们店的营业额也减少了50%。”“大牌化”也会让社区缺乏个性。有消费者表示,虽然产品的标准化,但“社区”认同感缺乏:“如果社区的店都是‘同一套’品牌,社区之间有什么区别?”
(2)平台帮助扩大“知名度”,增加曝光量
社区堂食店和平台合作多,是因为需要“打品牌”。平台优点是增大获客范围、打响品牌。一家小吃快餐店表示,平台和餐饮企业“互帮互助”,企业依托平台获得初始积累并稳健扩大规模。一家轻食餐饮店表示,“2018年获得初始投资后,平台帮助‘背街’上3家外卖店快速触达客源,也帮助选址论证更充分”,和平台合作只是把经营成本“更多地分配到平台而非房租,比纯做堂食“风险更小”。
然而,也有受访企业表达了对平台的复杂态度,认为平台经济是“双刃剑”:每单赚得少、存在等同“强制”收费。据研究员了解,2021年某外卖平台高抽成、“二选一”机制曾在2021年被政府根据国家《反垄断法》处罚,罚款年度销售额的3% ,并被要求“全面整改”。类似情况2024年似乎仍未好转,商家利润进一步被“削薄”;另外,想在平台上获客还需缴纳“推广费”,被大部分企业认为这等同于“强制收费”,感到“无奈”。这导致了前述社区堂食店多做外卖、大牌进社区开只做纯外卖的“卫星店”的现象。
(3)街镇平衡经济发展和居民诉求“有困难”
餐饮选址社区,影响社区环境,受居民投诉,产生利益冲突。例如,南京东路商圈附近的宁波路、牛庄路,后厨入口和居民共享里弄内部道路,居民深受餐饮“油烟”“噪音”“排污”的困扰,“不能开窗睡觉”“阴天晾衣服有油烟味”“家里晾衣杆上都是油烟”“晚上吵”是居民抱怨的主要内容。
五角场商圈附近社区居民出现类似餐饮店频繁装修造成“噪音”太多,酒吧夜间营业声音嘈杂等问题。大学路居民表示,“大学路商铺房东是业主,业主有权决定商户去留”,而开发运营企业却“招租了大量餐饮”。
上海2012年为居民开通了12345投诉热线,设置投诉、反馈渠道。2021年将12345工单的满意度考核纳入基层绩效 ,是最早将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且纳入官员考核制度的城市之一。
而且,上海还提出比国家标准更严格的油烟、噪音等餐饮环境管理标准。2004年《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施行十年后,2014年《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修订,对餐饮项目选址、油烟污染防治提出较高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一倍;2015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法》 修订,增加了“选址禁区”要求,并提升了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但餐饮企业现在仍缺乏选址禁区上更细致的要求。一家社区餐企对研究员表示,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需要先租经营场所(又称为“住所” )地址,但在选址及合同签订时,无人“预警”选址的注意事项,也缺乏“哪条路可以租给哪类企业”的公开、书面文字。而非政府端的选址服务目前还并未和政府打通数据系统,也不能提供类似的“咨询服务”。
为何易于引发矛盾的问题不能在颁发营业执照前的选址阶段杜绝?其实,早年的法规存在由环保监管者评估选址的环节,但随后为了“优化开店流程”,国家“证照分离”改革方案施行,餐饮项目环评手续不再作为办理营业执照的前置条件。2016年,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 修改,对餐饮项目的环境影响登记表实施备案管理,2019年上海明确“不产生油烟”餐饮项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的项目类型 。
2022年后,上海将油烟、噪音超标监管的执法权归到上海街镇基层政府,完成事权的下放 。街镇管理社区餐饮企业的依据是2004年施行的《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第5条规定,“非居住”房屋新开“餐饮店”需要特别注意油烟排放口位置:和居民住宅、医院或者学校的距离应“大于10米”,如果不能保证,则一定要大于5米,且须征得“相邻私有房屋所有人”和“公有房屋承租人”的书面同意 。
但《办法》第5条规定没有说明,转换功能后的建筑开办餐饮该如何管理。这在2019年针对《办法》的评估报告中也有指出 :“‘居改商’‘商改居’后商居距离过近,依然按照《办法》第5条来管理则无法开餐饮,易造成闲置资源浪费。“居改商”“商改居”后建筑能否开餐饮店,该按什么准则管理,让街道基层政府感到困惑。
“制度化”协商解决商居矛盾的三种方式
商居矛盾很能体现社区餐饮的特点,也是实践中基层协调的重点。据研究员观察,商家在居民来协商时如果没有解决问题,居民拨打12345后可能面临三种结果:罚款并限期整改,包括升级设备、调整业态或重新选址。
油烟超标等环境影响的执法处罚裁量的严厉程度已有所降低。2024年,上海对餐饮企业的环保罚单数量、处罚力度比2021年前后更低。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网站数据显示,各行政区罚单的罚款额度一般在1万元至2万元,较少以最高罚款额度(5万元)罚款,也较少出现2019年、2021年因环保不达标而处罚“停业”的现象 。
更换设备也不便宜。一套符合环保标准的油烟处理设备需花费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如果商家经营状况良好,有能力负担,自付成本更换静音油烟净化设备,确实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例如,浦东南泉路某居民小区沿街餐饮,因受居民投诉而安装新设备,油烟和噪音扰民情况有所改善(图7)。

图7:2024年10月,南泉路一中式餐企自行安装的静音油烟净化设备。
近两年餐饮企业盈利水平不佳,不低的设备更新、维护成本更容易导致餐饮门店的停业或搬离。
停业或搬离后,需要重新选址、调整或更换业态。这也让商家觉得风险高、不确定性大:“已投入的店面装修成本‘打水漂’了,加上换厨师、重新装修,以及合同违约金等成本,都需要自己负担;另外,放弃已经累积的老客户,营收也不一定能保持。”一家徐汇的川菜馆表示。
更轻量化的矛盾解决方式,多和社区居民协商有关。研究员2024年10至11月调研发现,存在三种低成本的解决方式。
方式一:商居共同出资,共建共享设施
这种方式通常在餐饮门店密集的“餐饮街”,且社区有制度化的“协商”平台。例如,沿街店铺在浦东新区餐饮聚集的蓝村路、南泉路餐饮中占比超50%,“街居联盟”借助2023年“特色街区综合改造”项目,为几家餐饮门店新增共用烟道,也通过店招整改,统一安装了噪音隔音板。在社区和成本共摊机制下,改造基金;共享除烟管道解决了油烟,但也会增加设备噪音等额外麻烦,很难普及。
有居民反映,隔音板确实减轻沿街住宅的噪音困扰,但是共享烟道本身也会产生一些低频噪声和震动,会进一步困扰烟道附近居民;且设施建好后,底楼餐饮似乎很少有重油烟餐饮,因此设施本身使用效率存疑。
店招上是遮挡共享烟囱管道、降低噪音传播的挡板(白色);附着在居民楼和沿街店铺楼顶的共享烟道和二级净化设施。该楼内居民表示,公共楼道里有设备噪音(图8、图9、图10)。

图8、图9、图10:2024年10月,南泉路沿街共享烟道(水蓝色管道)。
方式二:商居共商“补偿方案”,居民适当妥协
为了避免矛盾升级,有商家会在入驻时给居民“送礼”或“给红包”,通过一定补偿解决矛盾;一家浦东东北菜餐馆表示,在商住楼底层开店,需要获得“楼上居民”的签字同意,为此需要帮付水电费,也就每月“小几千元”“不算贵”。店主还提到一些较容易实现的情况:“如果房东恰好住楼上,或楼上是门店员工宿舍,则更方便。”
有居民在沟通、了解餐饮企业经营难处后,会选择“让步”,和商家协商“补偿方案”,同时调节自身行为来降低干扰。例如,一户宁波路居民会选择中午、晚间餐饮营业高峰时段出去“买菜”“溜达”,或是避开油烟浓重期及阴天来晒洗衣服。
方式三:社区提供资源,协助商户将厨房和门店分离
社区可以通过闲置空间资源“置换”解决此类问题。例如,静安闻喜路一家餐饮店本来喜欢在店里“炒菜”,后由于油烟太多又没有足够预算,经协商,在离居民区较远的园区以较低价格租用厨房,烹饪完送过来,以“半成品加工”的方式解决油烟扰民问题 。
以商居协商为主并予以“制度化”,能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基层公务员投入)和商家隐形的、不确定的(合规)经营成本。
由居委会和商户代表形成的自治组织(常被称为“商居联盟”)来协商矛盾,是一种“制度化”地平衡环保和经济活力、就业生计的方式,可以将以上“轻量化”处理方式的流程固化下来,作为可选用的流程出现。
据研究员了解,目前上海存在此类商居联盟,通常由居委会(或业委会)和商户组成,可以代表业主、商户和物业进行沟通,其人员通常热心社区事务,且在当地居住、经营较久,有一定威信和协商、组织能力,可为商户争取到弹性空间和回旋余地。不过,商户流动大也会造成该组织“松散”,也有可能出现商户“被代表”或“有贴牌、未参与过事务”等流于形式的情况。商居协商平台的“制度化”,还需进一步完善。
建议:商居协商制度化
第一,优化开店流程、打通政府部门壁垒。对此,可行的措施有:在颁发经营许可证前就提供选址服务和“负面清单”,提早排除风险,预防餐饮企业后期因商居矛盾可能产生的成本。基层政府会在前期介入选址“提醒”的做法,目前仅长宁区等个别区实施,可以扩大到全市范围。
第二,在租房合同签订前,增加“制度化”社区协商流程,并融入“公约”。在矛盾进入投诉渠道之前,建立商居联盟等社会沟通渠道,促成企业、居民的互动协商;并依托可能存在的社区改造基金作为改造费用的基础,探索共同讨论改造方案、出资改造的方式。
第三,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价值导向应更多元,特别重视商业空间的社会性以及对社会网络的塑造作用,如更多兼顾社区人口结构的留存和“文化多样性”的保存,并更多地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餐饮+”业态,为社区发展独特个性提供支持。
个体商户作为民营经济的最小单元,在保存地方商街个性和多样性上比连锁商户更具有优势,也是民生、就业保障的最小单元,对社区的价值超出了其所提供的日常商品。
另外,政府需要更少地干扰社区商业的发展规律,更多地鼓励社会自治组织发展,通过轻量化、制度化的协商流程(平台)解决社区市场和社会的问题;同时,政府需要更加规范市场,注意餐饮互联网平台规则和法的衔接,加强对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规范,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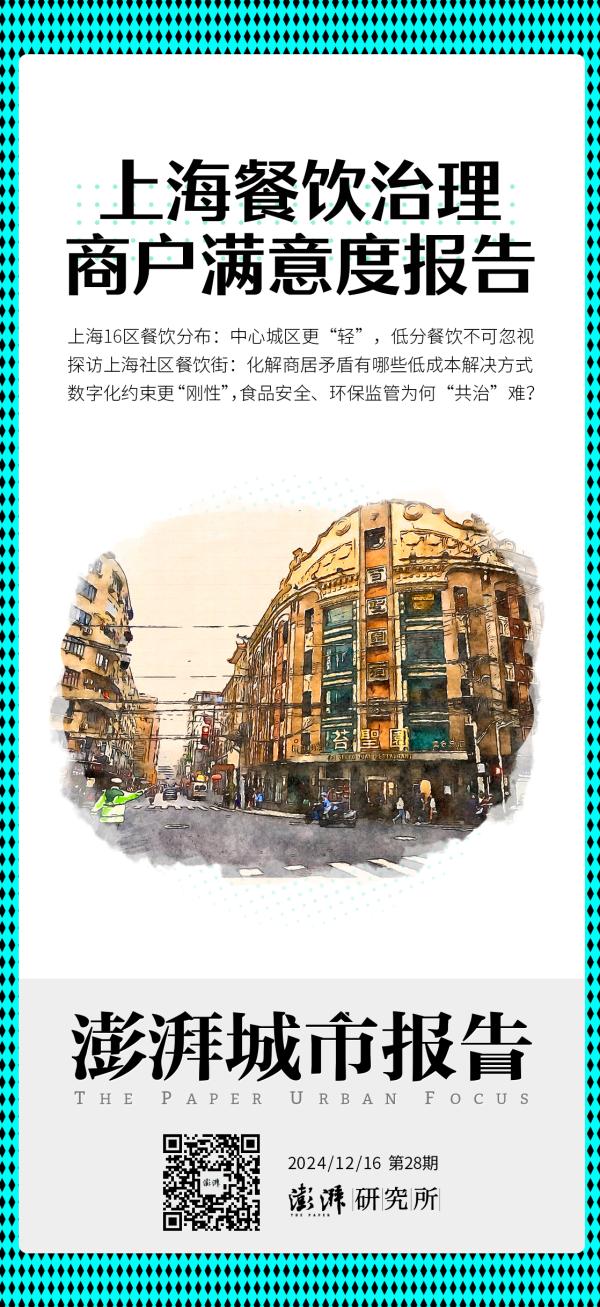
白浪 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