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被遮蔽的天空下……败退与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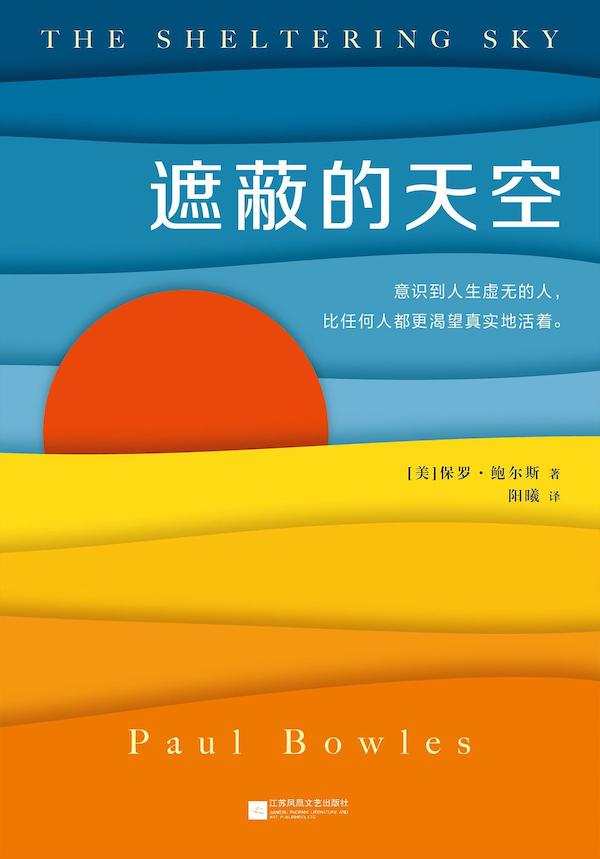
在今天读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1910-1999年)的这本早在1949年就出版的长篇小说《遮蔽的天空》(原作书名: The Sheltering Sky,阳曦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似乎有一种感受时光倒流与前瞻未来兼而有之的错置拼接之感,似乎是七十年前的那捧尘沙在指缝间一直滑落到今天——在作品面前,时间消失了,这几乎是所有堪称伟大的经典作品的标配。据说在美国文学史上,像《遮蔽的天空》这样能同时入选兰登书屋现代文库二十世纪一百部伟大英语小说和《时代周刊》1923年以来一百部伟大英语小说这两大文学榜单的经典作品是很少见的——而且在文学史上,关于旅行、婚姻、爱情、欲望、死亡的故事太多了,为什么是保罗·鲍尔斯?而且在我看来,关于人生意义、存在价值、人生的虚无与真实等等思考与哲理的写作也太多了,为什么是保罗·鲍尔斯?答案漂浮在“遮蔽的天空”中,同时也埋藏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
《遮蔽的天空》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二战结束后,结婚十二年的波特和姬特和他们的朋友特纳一起前往非洲撒哈拉旅行,故事的焦点是这对夫妻的情感困惑与欲望的诱惑及冲动。波特和姬特的行为各有乖张,但是都不能说是疯狂的、盲目的,相反的是,他和她都过分地沉溺在自我审视、自我怀疑之中,由此而产生的是无法摆脱的疏离感与恐惧感,生命的乐趣与意志在这种状态中不断溃散。在极端的自我追问中,情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变得越来越脆弱与幻化,迷惘、痛苦、疏离、背叛、逃避、虚无、死亡如影随形,人只能在其中迷失、麻木,直至在生命的最后瞬间才发现生命原来极为宝贵和脆弱。更为残酷的是,夫妻俩在内心都曾经对这次漫游存有一种修复几近破裂的关系的愿望,但是事与愿违。尤其是波特,他有更强烈的修复夫妻关系的渴望,但他同时对必将随之而来的情感负担感到恐惧,甚至需要通过对这与世隔绝的偏远沙漠的感觉来掩盖这种恐惧。“一路上她一直陪伴着他,并且尽量克制着抱怨的频率和刻薄的程度。”(第8页)这是书中关于这对夫妻关系的第一次描写,它从一开始就显得残酷而精准,而且与在大地上的游荡紧密相连。它似乎要警告那些轻易地把“诗与远方”和浪漫爱情挂在嘴边的文青:正是在漫漫长路中,种种贫乏、误解、赌气、偏见、固执、疏离、怨恨乃至背叛,都有可能因为天边的一片无辜的云彩、酒吧中邻桌投射过来的一道目光、因一件小事错失一辆班车等等事情而接二连三地演绎与发展。可以说,既希望随时取悦对方但又随时准备反击对方以维护自尊心,大家都希望对方先多迈出几步之后自己才体面地做出回应,一旦遭受挫折就会口不择言地伤害对方,负载着这些极其脆弱、敏感和痛苦的关系而长途旅行无疑是错误的选择。
在平常的日子里,爱一个人已经很不容易,平庸与无聊是很容易就出现的敌人。鲍尔斯关于欲望、迷惘和情感困惑的描写像刀锋一样划破意识的表层,夹持着寒意的锋利与精准使人心悸,两个人的世界无论如何看起来情投意合,终究是一个异质的、危险的世界,是无穷尽地相互搏斗的黑夜。而在漫无目的而且充满艰难、危险的旅途中,与环境及他人的关系而产生的意见冲突、意志较量、情感硬化都是更为危险的爆炸品,危机一旦降临就很难阻止它的爆发。在这时,逃避冲突、互相欺瞒、直至期待在一次不期而至并且可以不负责任的外遇中纾解愤懑之心就成了生活中残酷而真实的桥段。在各种生活情景中,“尽管他们常有同样的反应,同样的感触,但最终却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他们看待生命的角度几乎截然相反,意识到这一点让她感到悲伤”。(109页)尽管姬特知道波特真的爱她,尽管她也想变成他所期待的样子,但是她就是做不到,因为深植于她内心深处的恐惧总会占据上风,任何伪装都是徒劳。因此“事到如今,爱湮灭已久,也看不到任何重燃的希望”(109页)。波特也是一样,直到生命垂危才发现敢确定原来自己一直为妻子而活着,但是已经无法延续了,因为生命已走到尽头。当姬特经受不住(其实也是由于她潜意识中的默许)特纳的诱惑而终于出轨之后,她相当确定在波特的内心深处已经感知到了真相,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发现的。但是她不敢问,因为知道会更加激怒他,会使“他们之间暗流涌动的一点儿温柔必将荡然无存,也许永远无法修复。尽管两人之间的联系已经如此纤细脆弱,但她仍无法承受失去它的痛楚”(112页)。于是只能听任怀疑与背叛继续在原来的轨道上飞速滑行,这幕爱情悲剧的最后结局极为残酷,在波特处于生命垂危之时,姬特以麻木的冷静选择了离开与抛弃,转而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但是在鲍尔斯的笔下完全没有流露出任何道德的谴责,一切都只是冰冷而坚硬的事实而已。像许多其备受瞩目的作品被认为是作者某种程度的自传一样,《遮蔽的天空》也被认为是保罗·鲍尔斯的个人经历与心理的产物。但是他自己试图澄清这个问题,当被问到“姬特的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像你的妻子简·鲍尔斯?”的时候,他承认这本书和她的经历有关,但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他坚持说姬特不是简,波特也不是保罗·鲍尔斯。
在这场爱情悲剧中,姬特的内心世界远比波特更为复杂和更让人震惊。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也是鲍尔斯这部作品中极为关键的议题,是她的逃避责任。在她与特纳的暧昧关系发展中,她既不想与特纳发展下去,同时又知道自己迟早会屈服于他的诱惑——不是因为他本身真的有那么大的诱惑力,而是因为只要她顺从这种诱惑,就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得到了解脱,她无法抗拒这种可以解脱的诱惑——“多快乐啊,不必负责任——不必为即将发生的事情作决定!要知道,即使没有希望,即使做或不做任何事都无法改变必将到来的结果——你也不可能为此负责,自然也不可能后侮,最重要的是,你绝不可能产生愧疚。事到如今她仍希望自己永远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她深知其中的荒谬,却无法放弃这一缕希望。”(259页)关于这个问题,收入本书的托拜厄斯·沃尔夫撰写的“导读”有极为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在绝对的臣服中,姬特找到了无须思考的满足状态,就像吸毒一样再也离不开这种状态。“姬特的堕落是创伤所致,但最令人不安的是,她拒绝承担意识和责任的重负。‘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呢?’……这部小说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迫使我们直面现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声音,告诉你拒绝责任、拒绝选择的劳苦将带来莫大的自由,哪怕正是那些选择造就了今日的你。渴求随波逐流的‘无须思考的满足’并不新鲜,但要满足这种欲望,我们现代人有无数种方法: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极权主义宗教、毒品、权威崇拜、大众市场广告、电视成瘾、色情作品……”;“这些东西毫不留情地侵蚀着个人的价值感,我们节节败退的抵抗是我们这个时代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出戏剧。《遮蔽的天空》以坚定不移的目光观察这样的挣扎,冷静而中立地描绘了走向投降的每一步。……那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属于我们的时刻。”到这里为止,我们终于爬上了山顶,看到了在“遮蔽的天空”背后最可怕的图景,那幅属于我们自己的图景。在被遮蔽的天空下,没有什么比意志的缓慢溃散更真实、更令人无奈。我们还能或者还有资格责备姬特的逃避责任吗?在被遮蔽的天空下,我们的败退难道还不能使我们感到羞耻吗?而我们最后残存的坚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动摇呢?应该相信在冥冥之中会有人说:虽然你的意志不得不节节败退,虽然你一再尝试放弃,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相信你仍然在坚守。这是你过去的所有选择、所有经历所决定的,坚守与等待是你的本能与宿命。
对于鲍尔斯的作品,包括这本他最重要的小说,评论家的各种解读多有启发性,但是应该看到也有不少评论只是出于某种流行的文化观念,如“乡愁”、“诗”、“远方”、“生命价值”等,更有甚者马上就可以转到心灵鸡汤频道,什么生命的意义就在每一天的努力之中、应该从容淡定地面对死亡之类,都是试图在鲍尔斯的小说和他的沙尘与天空之间缀饰上软性的励志文化花边,其实可能与鲍尔斯的世界关系并不大。比如,关于他自己和他书中主人公的旅游与漂泊的动机,可能并非如人们通常解释的那样富于精神性、社会性的因素,而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是很自然就去旅行,就像他住在丹吉尔一样,是自然发生的事;在追问下去,他会说喜欢四处漂泊只是因为总想远离他出生的地方,因为那里的生活使他感到无聊。而所谓无聊,在他看来就是在那中间没有他想要的东西。而且人生短暂,一个人应该看看这个世界的更多的地方。就是这样,他的目光坚定而冰冷,并没有太多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总是温热的乡愁。他更注重的是真实生活中的真实质地,即便是在最容易诱发浪漫想象的地方,黄沙就是黄沙,岩石冰冷就是冰冷。喝茶,黑夜,骆驼队,手与天空……还有更多,都是鲍尔斯面对的真实世界。但是他并没有刻意地把原来所熟悉的文明生活与异乡、异文明的生活作比较,也没有要在自然人与文明人之间作文章的意思。他曾经说,其他民族真的有非常不同的生活形态,但我并不以为自然人和文明人有什么不同,我也不会将两者并列在一块,而且自然人总想成为一个文明人,我从来也没希望成为其他民族部落的一员。
不少评论家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解读他的作品,固然不无启发,而且从他曾经把让—保罗·萨特创作于1943年的哲理话剧《禁闭》翻译为英语的写作经历来看,的确是与存在主义有扯不开的联系。但是鲍尔斯看起来不是那种可以简单被某种主义归纳的人。据说他拒绝被称为一个存在主义者,不愿意给生命和世界贴上某种标签,不管是“孤独”还是“选择”。在1991年《滚石杂志》(The Rolling Stone)刊登的艾伦·金斯堡的私人照片中,有一张保罗·鲍尔斯坐在地上煮茶的照片。那是1961年7月,鲍尔斯在麦地那的老朋友家里,正在烧一壶薄荷茶,艾伦·金斯堡在这里和他待了一个星期。如果说“天空”是最大的隐喻,“沙漠”、“火车”、“茶”、“酒”等也是具有各自隐喻的事物,是深深地掩埋在滚滚尘沙之中的镜子,随时可以映照出在事物中被人们遗忘或被有意遮蔽的义蕴。关于他的创作源泉,鲍尔斯说他只能在写完以后才找到。听起来似乎有点矫情,但是他接着说,农场的主人责备一个睡着了的小孩,而小孩说“我一直到醒来了才知道我睡着了。”这话倒是挺真实的。或许创作对他来说,真的有点像进入睡眠状态那样的氛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预设的观念、写作的源泉,这会使写作者获得更大的自由,就如鲍尔斯说当你在开始旅行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那里,这是最自由的状态。

说到旅行,我觉得鲍尔斯有一张黑白照片是非常精彩的诠释。在照片中,他身旁是从大到小堆起来的几只旅行箱,在我看来那些箱子就像一只随时生火待发的轮船,我很能想象当鲍尔斯把它们垒起来的时候的那种心情。他觉得自己不是游客,而是旅人。“游客在外旅行几周或者几个月后总是归心似箭,但旅人没有归途,此地和彼地对他们而言并无区别,所以旅人的脚步总是很慢。他们可能花费数年时间,从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事实上,在待过的那么多地方里,他觉得很难说清到底哪里才最像家乡。”(第8页)鲍尔斯在1947年迁居丹吉尔,在这里写出了《遮蔽的天空》等小说作品。丹吉尔(Tangier)被称为“非洲之角”,是摩洛哥北部古城、海港,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湾口,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是腓尼基人的重要贸易站,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为国际共管区,具有特殊的国际化色彩,在鲍尔斯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咖啡馆和薄荷茶也可以说是丹吉尔的形象特色之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等一些西方知识分子都曾经汇集在这里,成为今天的旅游文化文本上的重要符号。据说当年杰克·凯鲁亚克和金斯堡来丹吉尔找到巴勒斯的时候,发现他的《裸体午餐》手稿被从大窗户吹进来的风刮得四处散落,巴勒斯竟然提议不必按原来的页面次序整理,就这样按被打乱的次序钉在一起交付印刷出版,这是文学创作中的编码神话。在今天,丹吉尔是摩洛哥境内大多数移民和来自中东、西非的难民进入欧洲的中转站,这种集种族、漂泊与异乡文化于一身的文化象征也正是鲍尔斯笔下的油彩版上的基本底色。在鲍尔斯勾画的丹吉尔形象中,斜坡与台阶往往通向大海,而房子总是连接着可以互相进出的房子,城墙与街道拐角构成立体主义的平面设计,所有的立面似乎共同拼接出一幅倒影在镜像中的舞台布景。保罗·鲍尔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访谈中说:“我找不到自己,真的,我没有自我。” 正如意识到人生虚无的人比任何人都渴望真实地活着一样,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没有自我的人,其实是比任何人都更知道何谓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