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灏读《诊所在别处》︱从惩戒到减害:美国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的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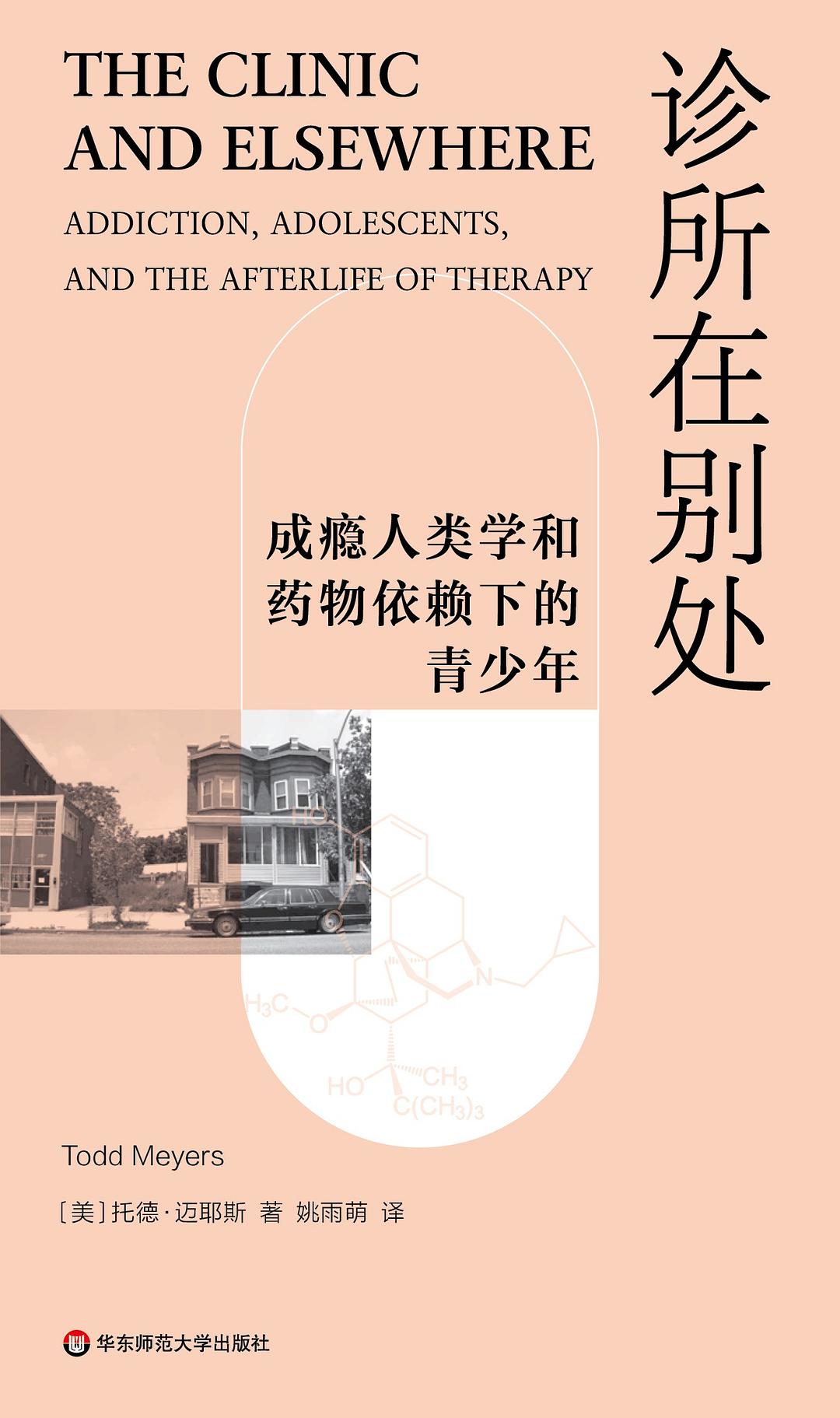
《诊所在别处: 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美]托德·迈耶斯著,姚雨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4年5月版,248页,55.00元
自上世纪末以来,一个“幽灵”,阿片类药物滥用的“幽灵”,始终在美国的土地上徘徊。这场由阿片类药物滥用所引起的危机被冠以了“阿片类药物危机”(opioid crisis)的名字,在过去二十年里,已累计造成超过65万美国人死亡,仅2020年就给美国带来了1.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017年,美国政府正式将这场阿片类药物危机宣布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持续至今。这个阿片类药物滥用的“幽灵”究竟何时才会从美国的土地上消失,仍充满未知。
在新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引入的《诊所在别处: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The clinic and elsewhere: addiction, adolescents, and the afterlife of therapy,直译为《诊所与别处:成瘾、青少年与治疗的后世》)一书里,人类学家托德·迈耶斯就跟踪了十二名在美国巴尔的摩某诊所接受阿片类药物成瘾治疗的青少年的生活。但是,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不是有关阿片类药物成瘾青少年亲身经历的疾痛叙事,而是一本“治疗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rapy)的民族志。在这本书里,所谓的治疗指的是过去二十年里成为阿片类药物成瘾治疗明星的丁丙诺啡。
迈耶斯跟踪的这十二名青少年都在诊所里接受了丁丙诺啡的治疗,参与了相关的临床试验,可是他们在离开诊所后的结局却有很大不同。这些青少年在离开诊所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种在临床试验中被证明有效的治疗方式,为什么回到真实世界里,疗效差异却如此悬殊?我们又该如何定义某种治疗方式是否成功?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必须离开诊所,去到那些青少年在诊所外的地方,由此才能看到——用迈耶斯的话说——所谓的“治疗的后世”(afterlife of therapy)。但是,在探访治疗后世之前,我们需要回溯美国社会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主流观点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深刻转变,以理解治疗和丁丙诺啡在阿片类药物成瘾治疗中的特殊意义。需要知道的是,丁丙诺啡本身也是一种受严格管制的阿片类药物,历史上并非所有人都认同阿片类药物成瘾可以且应当治疗,更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可以用一种阿片类药物来治疗另一种的成瘾问题,可如今这种治疗方式在美国却已成为对抗阿片类药物成瘾越来越主流的方法。
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
阿片类药物是作用于人体内的阿片受体并产生类似吗啡效应的一大类药物,包括从罂粟中直接提取出来的天然化合物(如吗啡、可待因)、半合成化合物(如海洛因、右美沙芬、羟考酮、丁丙诺啡)以及完全在实验室中合成的化合物(如美沙酮、哌替啶、芬太尼)。它们在医疗上用于镇痛、止咳、止泻、麻醉等目的,但因能产生欣快感、具有高成瘾风险而在不同国家都受到严格管制。
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不断恶化。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21)的最新数据,2021年美国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的患病人数已超660万,相当于美国人口的近五十分之一,比1990年上升近7倍。阿片类药物由于会影响大脑的呼吸中枢,服用过量容易致死,全球每年近80%的吸毒致死与其有关。2021年以后,美国每年因阿片类药物过量死亡人数超过8万(相当于每天200多人),是2000年的近10倍。这一死亡率几乎抵消了美国提高人群健康水平的所有努力,使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在新冠疫情前停滞在78.5至78.8岁之间,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被越拉越大,并在2020年后显著下降至77.4岁,而同期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则已上升至78.5岁。
自上世纪末以来,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始于上世纪90年代,由奥施康定等处方阿片类止痛药的滥用引发,源于药厂的过度营销和声势浩大的疼痛管理倡导运动。第二阶段则始于2010年左右,以海洛因滥用增加为特征,当时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处方阿片类止痛药的监管,同时海洛因价格下降,大量已对处方药上瘾的人开始转向吸食海洛因。第三阶段的危机则始于2013年,由芬太尼等强效合成阿片类药物的滥用主导,超过了处方药和海洛因。最近,还有学者提出,随着越来越多滥用者开始混合使用芬太尼与可卡因、冰毒等兴奋剂,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已经进入了第四阶段。
处理药物成瘾的道德模式
在药物成瘾的处理上,有两种传统的模式。第一种是道德模式,这种模式认为药物成瘾是个人的道德问题和个人选择的结果,不值得同情。成瘾者应自行承担成瘾的后果,因而需要接受矫正和惩戒,使其遵守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第二种是疾病模式,认为药物成瘾归根结底是一种大脑疾病,与成瘾者的遗传基因、环境因素及大脑结构有关,因此,成瘾者需要的是医学上的治疗,而非针对个人的矫正和惩戒。
美国历史上,道德模式长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倾向于道德谴责和采用强硬的司法手段进行矫正和惩戒。这一传统可追溯至19世纪的禁酒运动。当时美国酗酒问题非常严重,导致家庭暴力增加。禁酒运动最初主要由神职人员领导,通过道德劝诫减少过量饮酒及公共场合醉酒的问题,禁酒运动的支持者会在自己的签名边上标一个大写的“T”字,表示自己滴酒不沾(teetotaler),对饮酒零容忍。尽管禁酒运动减少了美国人的饮酒量,但到了19世纪中叶,皮下注射器的发明却让吗啡在美国得到大量使用。除了止痛之外,吗啡还被医生视作“万灵药”,用于各种不同的健康问题。另外,在美国内战期间,吗啡也被广泛用于治疗受伤的士兵。这就导致吗啡成瘾者明显增多。
因此,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越发严格的针对阿片类药物进行管制的法案。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要求所有专利药品生产商必须在药品标签上标注具有成瘾性的成分(主要是指阿片、吗啡、可卡因、咖啡因和大麻)。1909年,《吸食阿片禁止法案》(Smoking Opium Exclusion Act)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明令禁止将阿片用于非医疗目的的联邦法案。1914年,《哈里森麻醉药品税法》(Harrison Narcotics Tax Act)开始对医生向成瘾者提供阿片类药物进行管制。1919年,在韦伯诉美国案(Webb v. United States)中,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做出裁决,认为药物成瘾不是一种疾病,医生不可以将阿片类药物用于成瘾者的治疗。这一裁决相当于在法律意义上反对了有关药物成瘾的疾病模式,并成为了美国日后一系列毒品政策的重要基础。
1930年,美国成立了联邦麻醉药品局(Federal Bureau of Narcotics),由哈里·安斯林格(Harry Jacob Anslinger)担任局长。在他长达32年的任期里,安斯林格推行了极其严格的禁毒措施。他是疾病模式的坚决反对者,对于药物滥用者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就是“把他们给抓起来,然后把钥匙扔掉”。1951年的《博格斯法案》(The Boggs Act)则在联邦层面对毒品犯罪设置了强制性的最低刑罚。到了尼克松时代,“毒品战争”也正式打响。1973年,尼克松在药物滥用执法办公室(Office of Drug Abuse Law Enforcement,ODALE)的基础上成立了美国缉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负责打击国内外毒品犯罪。
尽管尼克松之后的政府对毒品政策有所调整,但总体上延续了道德模式的强硬路线,严打毒品犯罪。然而,随着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出现,美国有关药物成瘾的主流观点却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减害措施在美国的兴起
减害措施在美国的兴起2021年11月,纽约市政府支持和资助在曼哈顿开办了两家受监督注射点(supervised injection site,SIS),允许吸毒人员在机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使用毒品。据《纽约时报》报道,首日就有70多人前来使用毒品。这种做法背后的想法是,与其让吸毒人员在街上胡乱吸毒,导致药物过量进而死亡,不如让他们在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监督下使用毒品,万一发生意外,还能及时抢救,避免死亡。这种机构在我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许多人会问:这不就在纵容吸毒犯罪吗?可是,这种做法所代表的减害(harm reduction)理念在过去二十年里却愈发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主流。
减害,顾名思义,就是要减少药物成瘾给成瘾者带来的伤害。减害理念首先承认药物成瘾是一种疾病,它认为道德模式是在污名化药物成瘾者,药物成瘾者需要的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帮助和治疗,而非矫正和惩戒。但另一方面,减害理念又反对传统的疾病模式对于戒断(abstinence)的执着追求,认为药物成瘾是一种慢性疾病,就像是糖尿病和高血压,它是无法根治的,也未必需要完全戒断。因此,对于药物成瘾的治疗来说,与其执着于戒断的幻想,不如把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如何减少药物成瘾的伤害上。这些伤害就包括过量服药死亡、因共用针管而导致的传染病传播和非法毒品交易。
基于这样的逻辑,就出现了一系列针对药物成瘾的减害措施,包括前面提到的受监督注射点、针具交换项目、纳洛酮发放项目(纳洛酮是阿片类药物过量的急救药,纳洛酮发放项目会给成瘾者及他们的家人、朋友、警察等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人发放纳洛酮,这样如果成瘾者使用阿片类药物过量,其他人就可以立即实施抢救,从而避免死亡)、芬太尼检测试纸(芬太尼药效强、价格低,很多毒贩会把它掺杂在其他毒品里,但芬太尼的致死性也很强,芬太尼检测试纸的目的就是帮助吸毒者检测毒品里是不是含有芬太尼,从而避免吸食掺杂了太多芬太尼的毒品)以及《诊所在别处》这本书所讲述的以丁丙诺啡为代表的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opioid substitution therapy [OST],为阿片类药物成瘾者开具某些特定品种的阿片类药物,最主要的是美沙酮和丁丙诺啡这两种药物,但在有些国家甚至还会开具海洛因,从而减少成瘾者对于从非法渠道所获得的阿片类药物的依赖)。
除此之外,减害理念还特别强调尊重药物成瘾者的自主性,它不要求成瘾者必须完全戒断,而是“在其所处的位置、就其所处的阶段,为成瘾者提供帮助”(helping people where they are)。减害理念认为,除了戒断之外,成瘾者实际上还面临着其他许多需求,比如住房、更加安全的吸毒用具以及用于治疗吸毒过量的药物,这些需求都应该被看到,而且被满足。
虽然美国社会有关减害措施的争论从未停止,但总体而言美国社会对减害措施的接纳度越来越高。有关药物成瘾的道德模式构成了20世纪美国毒品政策的重要基础,美国联邦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减害措施的极大反对者,并明令禁止将联邦经费用于任何形式的减害措施。可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是民主党政府)却开始放开对于减害措施的支持。2021年10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发布了有关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应对的新战略,首次将减害作为优先战略之一。2021年12月,作为《美国救助计划法案》(American Rescue Plan Act)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政府进一步拨款3000万美元,用于资助社区层面的减害措施,这也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通过有关减害措施的经费项目。至少就目前而言,针具交换项目、纳洛酮发放项目、芬太尼检测试纸以及美沙酮和丁丙诺啡替代治疗已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得到支持,受监督注射点还在评估阶段,但很有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也在联邦层面得到批准。
乍一看,美国在药物成瘾问题上的这种态度的转变,着实叫人吃惊。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毒品政策历史学家戴维·赫茨伯格(David Herzberg)就表示,这种转变是“对美国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警察文化(policing culture)所做出的深刻且根本的改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几乎从来不会看到什么全新的事情,可(这种态度的转变)就是新的事情。”但是,这种转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其他国家也有警示作用,但它的答案显然不会那么简单,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及历史因素参与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首先,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府在“毒品战争”中投入大量资源,但未能获胜,反而见证了过去二十年里愈演愈烈的阿片类药物危机,药物成瘾人数急剧上升。其次,长期以来的大规模监禁导致美国的监禁率飙升,到2008年最高峰的时候,美国监狱里关押了230万囚犯,相当于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囚犯都关押在美国的监狱里,其中高达85%是涉及药物使用障碍或是涉毒犯罪。据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美国每年在大规模监禁上要花费810亿美元,但财政预算却在缩水,迫使政府调整监禁政策。此外,大规模监禁也遭到了民权运动的反对。一方面,人们质疑,美国的大规模监禁只是伪装良好的种族隔离手段。尽管研究显示,不同种族的美国人吸毒比例相似,但在某些州,黑人因吸毒入狱的比例是白人的20到50倍。美国民权律师及法学研究者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甚至将美国的禁毒政策比作是“新的吉姆·克劳法”。另一方面,就像美国最大的减害倡导组织全国减害联盟(National Harm Reduction Coalition)所言,减害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正义运动,植根于要求平等和正义的行动主义。”人们认为,美国的零容忍禁毒政策导致对药物成瘾者的污名化和权利剥夺。特别要提出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艾滋病疫情是美国减害措施的重要推动力。当时,许多静脉吸毒者因为共用针具而感染上了艾滋病,静脉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防治问题成了当务之急。医疗从业者认为,相比于戒毒,通过提供干净针具的方式来切断艾滋病在静脉吸毒人群中的传播途径可能更加可行、有效。吸毒者也认为,他们理应享有艾滋病防治的权利,而不是被关进监狱。因此,许多民间人士及团体都开始倡导减害措施。
当然,最终将减害措施推到舞台中央的还是美国在过去二十年中遭遇的这场阿片类物质危机。首先,药物成瘾者已实在太多,惩戒无济于事。其次,由于阿片类药物的特性,因服药过量致死的人数特别多,降低死亡率故而成了更高的优先级。第三,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复发率在美国高达40-60%,许多医疗从业者开始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究竟能否完全治愈这个问题不抱太大希望,而是更加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慢性疾病,只能缓解却无法根治。第四,药物成瘾者的形象在这场危机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有关这场危机的原因通常被说成是药厂的贪婪、医生的盲目、美国经济的下滑以及弥漫在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成瘾者不再成为指责的对象,而是无辜的受难者,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甚至你自己,因此公众对于成瘾者的态度也开始发生改变,反感少了,同情多了,鄙视少了,尊重多了。最后,医疗领域围绕减害措施的有效性及成本有效性也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随着这方面的证据变得越来越多,使用减害措施的说服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强。所有这些因素都让减害措施似乎成了美国当下在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方面最经济、有效且可行的办法,先避免死亡,然后再谈怎么戒瘾,就像爱因斯坦医学院蒙蒂菲奥里医疗中心(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的传染科医生布赖安娜·诺顿(Brianna Norton)所说:“如果他们都死了,那我们就不可能治疗他们的阿片类药物成瘾了。”四年前,诺顿医生在纽约减害教育者组织(New York Harm Reduction Educators)下开办了一家诊所,专门为吸毒人员治疗他们的传染性疾病,而纽约减害教育者组织也就是后来纽约所成立的两个受监督注射点之一。由此看来,减害措施在美国的兴起大概也可以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绝佳的例子。
丁丙诺啡的前世今生
正是由于减害措施的兴起,“治疗”(treatment)一词在美国逐步替代了“禁”(prohibition)和“戒”(abstinence),开始成为应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主要策略。在此背景下,丁丙诺啡作为治疗药物闪亮登场,但就像迈耶斯在《诊所在别处》里所写到的,丁丙诺啡其实算是“旧物新用”。目前,美国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标准治疗药物主要是丁丙诺啡、美沙酮和纳曲酮,其中证据更强的则是丁丙诺啡和美沙酮。丁丙诺啡和美沙酮都是长效阿片受体激动剂,被用于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替代治疗。
美沙酮是第一种获批用于阿片类药物成瘾治疗的药物,但它与丁丙诺啡的命运却完全不同。1947年,美沙酮被美国批准用于止痛和镇咳。到了60年代,文森特·多尔(Vincent Dole)和玛丽·尼斯旺德(Marie Nyswander)的研究发现:美沙酮所具有的长效吗啡样作用可以减轻阿片类药物成瘾者对于药物的渴求。经过近十年的研究,1972年,美国药监局终于批准将美沙酮用于阿片类药物成瘾的长期治疗方式。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在禁毒问题上态度强硬,对于减害措施的接纳度很低。当时新成立的美国缉毒局将美沙酮列为二级管制药品,与吗啡和可卡因属于同一级,监管非常严格,只允许美沙酮诊所等经过联邦政府认证的阿片类药物治疗项目(opioid treatment programs,OTP)可以开具美沙酮,而其他医疗场所则无法开具。然而,全美只有大约1500家美沙酮诊所,候诊时间也很长,完全无法满足阿片类药物成瘾者的治疗需要。而且由于当时美国社会普遍不接受减害措施,人们会认为用美沙酮来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只是用一种瘾替换掉了用一种瘾,那些在美沙酮诊所接受治疗的人根本就是缺乏戒瘾的决心。这种态度存续至今,导致许多成瘾者不愿意走进美沙酮诊所。
因此,丁丙诺啡也就作为美沙酮的潜在替代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966年,利洁时公司(Reckitt,国际著名的清洁及卫生用品生产商,旗下品牌包括杜蕾斯、滴露、巧手等)的化学家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在研发止痛药的过程中发现了丁丙诺啡。1978年,唐纳德·贾辛斯基(Donald Jasinski)等人发表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证明丁丙诺啡在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方面有着与美沙酮相当的效果。而且,由于丁丙诺啡只是阿片受体的部分激动剂,对于阿片受体的作用存在天花板效应,所以据说滥用的可能性要比美沙酮更低,使用起来更加安全。但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政府在毒品问题上的工作重心仍是在禁毒而非减害,所以并没有表现出对于丁丙诺啡太大的兴趣。直到九十年代后期,阿片类药物危机悄然而至,并推动美国毒品政策的天平朝着减害这一端倾斜的时候,美国政府才开始想要寻找比美沙酮更好的治疗方式,并最终将视线投向了利洁时公司的丁丙诺啡。
后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立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NIDA)直接资助利洁时公司进行药物研发,也就有了后来的速百腾(Subutex)和舒倍生(Suboxone)这两种专门用于阿片类药物成瘾治疗的丁丙诺啡剂型。当时,美国政府可能还没有想到阿片类药物危机后来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觉得利洁时公司在这两种药物的研发上可能没法收回成本,所以还特别将利洁时公司的这两种药物纳入了“孤儿药”清单,给予其税收优惠和独家开发专利。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药物成瘾治疗法案》(Drug Addiction Treatment Act),这就使得丁丙诺啡拥有了与美沙酮完全不同的待遇,因为该法案允许医生只需要接受八小时的培训就可以在自己的门诊办公室里开具丁丙诺啡,可及性明显提高,而不是像美沙酮那样必须得在美沙酮诊所里才能开具。2002年,美国药监局正式批准了速百腾和舒倍生。随后,这两种药物就作为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标准治疗在美国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从2004年到2011年,丁丙诺啡在美国的使用量增加了2318%,而美沙酮的使用量则只增加了37%。如今,丁丙诺啡——主要就是利洁时公司的速百腾和舒倍生——已经成为美国阿片类药物成瘾治疗市场上最主要的药物,对于利洁时公司来说,收回成本完全不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
治疗的后世
过去二十多年里,有关丁丙诺啡疗效的研究已经卷帙浩繁。检索Cochrane数据库,可以发现有39篇系统综述与丁丙诺啡有关,而在纽约大学的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证据地图(OUD Evidence Map)上,则可以找到500篇有关丁丙诺啡的临床试验。从减害的角度来说,虽然成瘾者好像只是换了种正在使用的阿片类药物,但研究显示,相比安慰剂,丁丙诺啡确实可以减少成瘾者的非法药物使用,降低药物过量死亡风险,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降低犯罪率,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家庭关系,并帮助成瘾者重新走上生活的“正轨”。
但是,在有关丁丙诺啡的临床试验中,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相当大部分的临床试验都以治疗保持率(treatment retention,通常是计算成瘾者在开始治疗后的180天内坚持规范治疗的比例)为重要的结局指标,而这个比例对于丁丙诺啡来说并不算特别高。根据Cochrane数据库的一篇综述,在临床试验中,低剂量丁丙诺啡的治疗保持率为60.3%,中剂量为65.3%,高剂量为65.5%。也就是说,在临床试验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接受丁丙诺啡治疗的患者会在180天内放弃治疗。要知道,临床试验的设置往往非常严格,因此如果在临床试验中都只有不超过三分之二的治疗保持率,那么回到真实世界,这个比例可能只会更低。实际上,根据去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的一篇通讯,在2016-2022年之间,美国现实中的丁丙诺啡治疗保持率只有22%,而且这个比例在2016-2022年之间基本没什么变化。目前在美国,对于阿片类药物成瘾治疗来说,医生往往会建议成瘾者长期服用丁丙诺啡,否则复吸率很高,而且一旦复吸,由药物过量所导致的意外死亡风险会变得更高。
可是,放弃治疗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在患者离开诊所之后的“后世”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对我来说,迈耶斯的《诊所在别处》这本民族志的主要意义可能恰恰就在这里。我是一名医生,当我们的患者在医院里住院的时候,我们可以“盯”着患者接受治疗,可是一旦患者出院离开我们的视线,他们是不是还愿意继续接受治疗,就不再是我们说了算。同样在临床试验中,研究者会严格控制试验条件,保证治疗依从性,可是在真实世界里有太多混杂因素会影响到治疗方式的效果。关于治疗效果,我们会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疗效(efficacy),一个是有效性(effectiveness),前者是在理想情况下通过严格控制试验条件所得到的治疗效果,后者则是在真实世界中所得到的治疗效果。然而,在疗效与有效性之间却往往会存在很大的鸿沟。某种治疗方式也许在理想情况下可以给患者带来很大的获益,可是在真实世界中就未必能带来同样的获益。道理很简单,在理想情况下你可以“盯”着患者接受治疗,可是在真实世界中你却做不到。当然,我们无意指责患者,但实际上,治疗依从性这个概念往往会成为指责患者的工具:“你不配合治疗,还想不想把这个病给看好?”然而,患者回家以后为什么不配合治疗,这个问题往往会牵扯到许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患者怎么理解疾病(“我根本就没病,为什么要治疗?”)、怎么理解治疗(“是药三分毒,能不吃就不吃。”)、怎么理解疾病与治疗的关系(“我这个病不是这种办法能治好的。”),包括患者的治疗动机(“我一定要把这个病给看好。”),包括患者有没有能力坚持这个治疗(经济压力、工作条件等结构性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患者坚持治疗的可能性),还包括治疗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怎样正性或负性的改变。
在《诊所在别处》这本书里,迈耶斯讲述了劳拉的故事,劳拉从14岁开始滥用阿片类药物,后来被父母强制送进治疗中心,开始接受丁丙诺啡替代治疗以及其他社会心理治疗,刚进去的时候劳拉很反感,可在住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却爱上了这里,以至于出院的时候,她还有些恋恋不舍,“与工作人员以及很多玩得好的青少年一一拥抱告别”。但是,在出院以后,劳拉却过得不顺,她失去了治疗中心里那种特有的“结构”(structure),失去了她在那里所收获的友谊还有“其他可以依赖的东西”。她的父母说是说管她不严,实则很“控制”,她的家庭对于她来说就是“爱的囚笼”,条条框框很多。所以,劳拉出院以后就特别想回到治疗中心,于是她又开始滥用阿片类药物,结果如其所愿,她又被送了进来。再入院的时候,迈耶斯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劳拉回答得很简单:“我想这儿了呗!”
还有塞德里克和梅根的故事。他们是一对情侣,都只有16岁,两个人都在滥用阿片类药物。他们住院住过好多次。他们虽然不信任医生,而且也不喜欢在治疗中心里像是“黑猩猩”那样被“投喂药物”,但还是很希望能够治好自己的毒瘾,他们憧憬着一个没有毒瘾的共同的美好的未来,所以他们在生活中会“自我用药”,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加药减药。“吸一点海洛因,然后吃丁丙诺啡……有时候加一点奥施康定……就像在实验室里,这个加一点,那个减一点……总有一天,会痊愈的。”他们有一本共用的笔记本,两个人会在笔记本上记录每天服用的各种药物的剂量,从而互相监督。对于医生来说,这显然是治疗不依从的典型表现,根本就是瞎吃药,可是对于塞德里克和梅根来说,他们两个人在“自我用药”方面的这种互动的过程却是他们亲密性的某种表现。
医生往往只会待在自己的“诊所”里,他们看不到也不关心患者在离开他们“诊所”以后的真实生活的样貌。可是,恰恰要去到“诊所”以外,也就是去到迈耶斯所说的“别处”,我们才能找到那些可能会影响到某种治疗方式的效果的因素,这些因素甚至在更大程度上会决定这种治疗方式的效果。以前,在人类学领域,有一种人类学家整天枯坐书斋空想,却从来不去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中做田野调查,这种人类学家有个名字叫做“扶手椅人类学家”。同样,那些从来只是待在自己的“诊所”里凭空指责患者依从性不好、却从来不去深入了解患者的真实生活究竟如何影响到他们的依从性的医生,或许也可以被叫做“扶手椅医生”。我们不应该凭空指责患者依从性不好,而应该尝试着更多地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这些选择发生在“别处”,因此也只有去到“别处”,去到患者的生活世界,去到那些“由小巷与广场组成的迷宫”,才能理解在患者的选择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更深层的原因。同时,我们也只有在理解了这些选择之后,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治疗与照护。所以,迈耶斯的这本书,虽然英文名是《诊所与别处》,但中文名译作《诊所在别处》,也不失为一种巧思——因为“诊所”无法完全决定某种治疗方式的效果,反倒是在“别处”可能潜藏着许多会影响到这种治疗方式的效果的因素,于是乎,真正的“诊所”可能恰恰就发生在“别处”。
参考文献:
Lassiter, Pamela S., and John R. Culbreth, ed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ddiction counseling. Sage Publications, 2017.
Wu, X. Parallel Development: Medicalization and Decriminalization in the Changing Media Framing of the Opioid Overdose Crisis. Socius, 2023(9): 1-16.
Des Jarlais, D.C. Harm reduction in the USA: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an archive to David Purchase. Harm Reduction Journal, 2017(14): 51.
梁笛,进退维谷的美国大麻合法化. 澎湃新闻, 2024-3-9.
Roberts, Laura Weiss, ed.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Textbook of Psychiatry.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 2019.
Sivils, A, Lyell, P, Wang, JQ, and XP Chu. Suboxone: History, controversy, and open questions.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22 Oct 28;13:1046648.
Louie, D.L., Assefa, M.T. and M.P. McGovern. Attitudes of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toward prescribing buprenorphine: a narrative review. BMC Family Practice 20, 157 (2019).
Jaffe JH, O'Keeffe C. From morphine clinics to buprenorphine: regulating opioid agonist treatment of add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rug Alcohol Depend. 2003 May 21;70(2 Suppl):S3-11.
Duff, J.H., Shen, W.W., Rosen, L.W., and J.R. Lampe. The Opioid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Brief Histor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2-11-30.
The ASAM Nation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Opioid Use Disorder: 2020 Focused Update. J Addict Med. 2020 Mar/Apr;14(2S Suppl 1):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