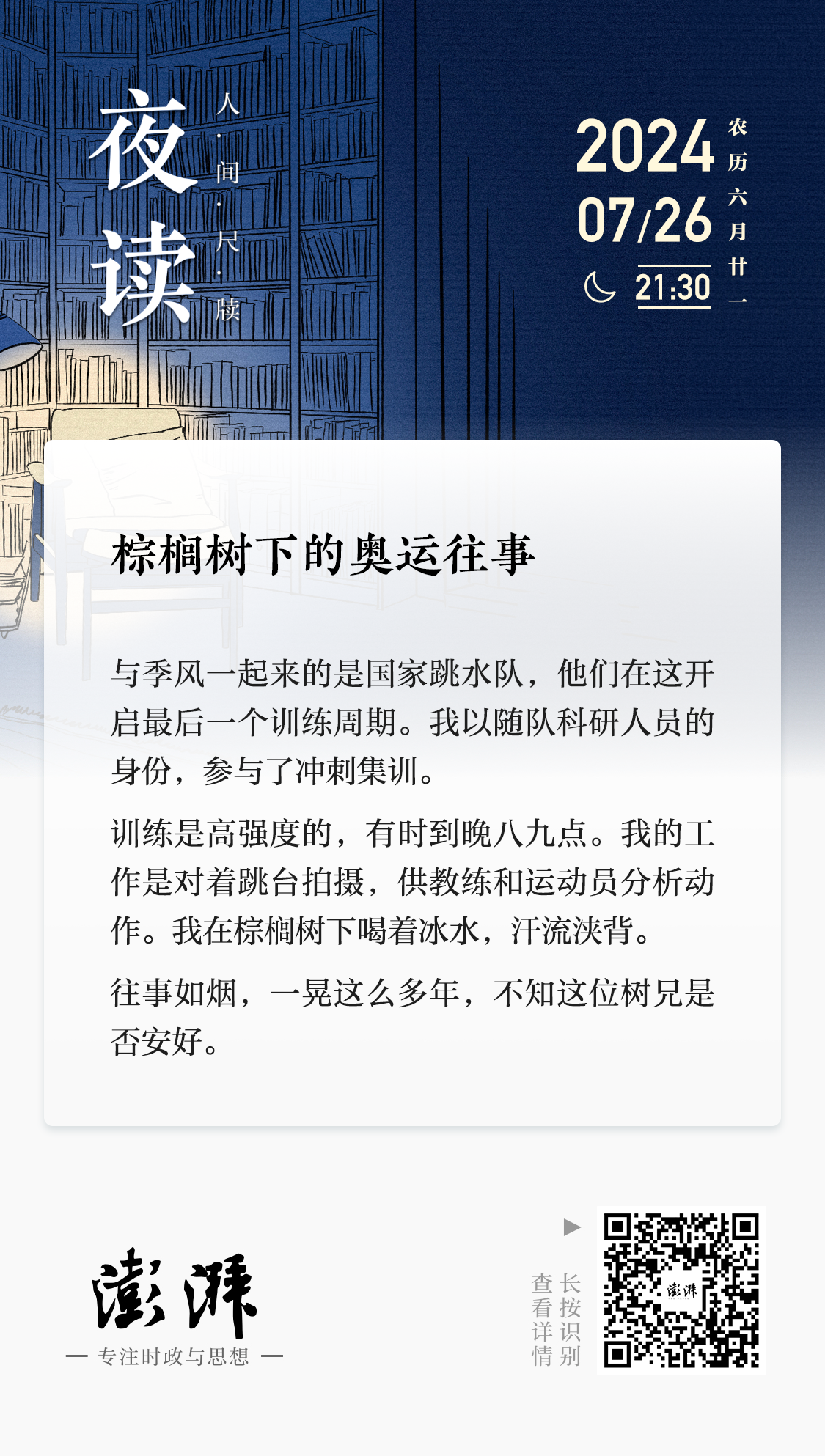夜读丨棕榈树下的奥运往事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奥运时间”来了。这届奥运会,我比较关注中国跳水队,不仅因为她是当之无愧的“梦之队”,还因为一段往事。
2016年5月,广州,亚热带季风携着潮湿的暖流如约而至,天气阴晴不定,前脚还是艳阳,后脚突然就来场雷暴。等路人狼狈地奔向街道旁的屋檐下躲雨,天又晴了,太阳从云缝里射出几道光,满地是闪亮的小水洼。
与季风一起来的,还有国家跳水队,他们要在广州开启里约奥运会赛前最后一个训练周期,持续到8月,然后直飞奥运赛场。那时,我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竞技体育研究中心实习,以国家跳水队随队科研人员的身份,参与了赛前的冲刺集训。
每天下午三点,我们准时从酒店出来,走进浓稠热浪,三五成群地朝越秀山进发。越秀山乃白云山余脉,远看深山茂林,其实只是白云山的一个犄角,娴静独处在繁华闹市中。集训选在这里,是因为里约奥运会跳水比赛地场很少见地设在了室外,为了让运动员适应巴西的热带气候,特地在越秀山顶筹建了一个训练基地——那里原本是个露天游泳场。
越秀山在越秀公园内,走进公园,就进入了一片由巨大榕树与灌木交织成的雨林世界。踏着石子小路,我们混迹于游客中。通往训练场的路会经过一些景点,有孙中山读书治事处纪念碑和五羊石像。训练场被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植被环绕,是越秀山的最深处。东西两侧是状似古罗马遗迹的看台,中间一整块游泳池,最南边一小块供跳水使用,如果从高处俯瞰,真有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感觉。
运动员的训练是高强度的,通常要持续到日暮时分,有时甚至要挑灯夜战,到晚上八九点。
我的工作地在高处,一个与十米跳台紧挨着的小山坡。我一下午都要坐在一颗棕榈树下,架起高速摄像机,对着跳台随时准备拍摄。训练中的每一次跳水,经我拍摄下来后,同步到跳台下的大屏幕上回放,供教练和运动员从中分析动作。这样的视频,我一下午得拍摄三四百段。
运动员训练时,我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务必得把从十米台上高速下落的运动员始终锁定在镜头里,不然会被教练训斥。还好经过前期几个月的实践,我已形成了肌肉记忆,右胳膊已然达到“用意不用力”的化境,可以轻松扭动控制杆,从上而下,牢牢地运动员锁定在画幅中心,直到他们入水后为止,全程构图完美。
初来乍到,我这样异乡人的最大失误,是低估了当地蚊虫的“热情”,尤其是在植被茂盛的户外。天气闷热,自然是短袖短裤轻装出行,可也就两三天功夫,我腿上就密密麻麻布满了被蚊虫叮咬的新鲜红点,两条腿上大概得有一百个左右,有的教练甚至被叮起了很多流脓的大包。
驱蚊水根本没用,我双腿发痒到无法入睡,就算勉强睡着,半夜也会再痒醒,反复用硫磺皂清洗,可也没什么效果。所有人都苦不堪言,最后没办法,只得全副武装,长袖长裤,连脖子都围了起来,只露双茫然的眼睛在外边,成契诃夫小说里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
当时午后温度接近40度,我们如此一丝不露,体感可想而知。下午训练时,汗水源源不断往下流,为防止脱水,我只能不停喝水,身体水循环像开了5倍速。队里为我们着想,在有人的地方都配了小风箱,还可以往里加冰块。于是我就坐在棕榈树下,喝着冰水,吹着冷风,可依然汗流浃背。冰火两重天。
我还有一个独特的问题要面对。当时只有我在最高点,头顶还有一棵笔直的树干通向天际,雷暴又频繁光顾,我总担心背后的树会被雷劈到,每天总要心理建设一番,宽慰自己此乃杞人忧天。我们当时的科研工作刚好就是运动心理学方向,而我每天首先要对自己做心理疏导。
好在上午闲来无事,我就躺在酒店大床上,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下午在越秀山顶,与蚊虫、酷暑以及大雨雷电搏斗之余,全身心投入在训练当中。
在重重茂林里,独辟这么一处秘境,所有人都清晰冷静地专注在自己的事情里,这让我想起张居正曾引用过的一句佛经:“如入火聚,得清凉门”。那段日子,有严酷的体感环境,却又有清凉的心境,实在奇妙又难得。
那年盛夏,蓄力已满的国家跳水队,从广州飞往里约,在奥运会上斩获7金2银1铜。临出发那天,我们在空旷的训练场上打包科研设备,四周植被静谧如斯,只有鸟虫在咿呀咿呀作响。我身后那棵棕榈树,依然伫立在高坡,身姿曼妙,俯视着这一切。我们三个月的集训,它都尽收眼底。
往事如烟,一晃这么多年,不知这位树兄是否一切安好。前缘难再续,后会遥遥无期,只能聊以此文纪念这段棕榈树下的奥运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