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冰川告别
【编者按】
冰川的增长与衰退,既体现了地球绕日转动的规律,也体现了人为因素对自然的影响。冰川学家杰玛·沃德姆曾多次带领探险队前往世界各地的冰川,研究证明了冰川事实上充满微生物(从前被认为是冻结的无菌环境),这些微生物就像我们的森林和海洋一样,是处理碳和生成营养物质的活跃的“专家”,是影响人们依赖的利润丰厚的渔业和肥沃的农田的关键系统。至此,一个由冰川架构的生态系统被揭示了出来。本文摘自《聆听冰川:冒险、荒野和生命的故事》[美]杰玛·沃德姆著, 姚雪霏等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5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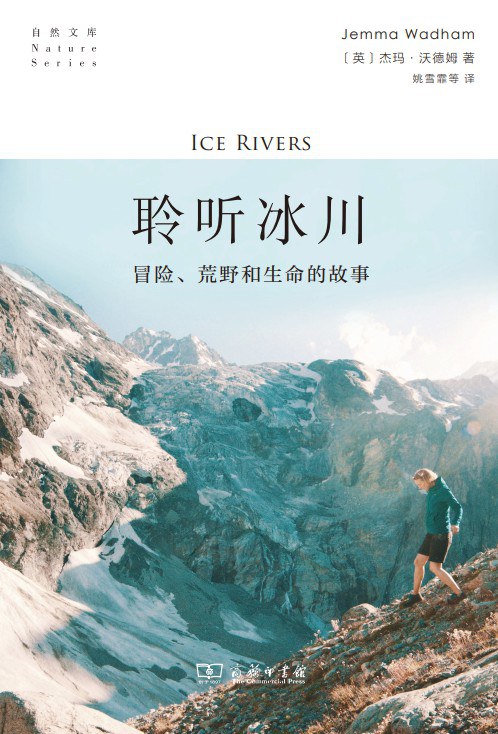
《聆听冰川:冒险、荒野和生命的故事》书封
喜马拉雅是除了极地外冰川覆盖面积最广阔的地区,也经常被称为“第三极”。与格陵兰和南极洲不同的是,这里巨大的冰盖覆盖下的是山峰和低谷,有超过5万条山谷冰川,从8848米几欲刺破天空的珠穆朗玛峰,一路蜿蜒向下。这些亚洲的“水塔”是该地区至关重要的资源,它们把水这种最基本的物质以冷冻的形式储存起来。
春天来到,覆盖山脉的雪毯慢慢融化,到了夏天,一旦积雪消失,冰川融水又继续稳定地汇入河流。在喜马拉雅中部和东部,夏季季风带来的暴雨不仅增加了该地区山坡的降水量,而且在冰川高处变成雪,帮助冰川维持储量。融水和降雨也会深入地表,土壤像海绵一样吸水,再在山腰以泉水涌出。因此,雨水晚到的时节,可靠的冰川融水会持续流淌到下游。
就这样,喜马拉雅山脉像一系列“水龙头”一样,在不同时间开开关关,流出的水量最终汇聚在一起,供养穿过整个区域的10条大河。印度最醒目的是印度河、恒河,还有发源于中国的雅鲁藏布江,这些河流滋养了世界上最广阔的农业灌溉区,让最偏远地区的人们也得以存活。在喜马拉雅地区,水是其他一切的基础,这里包括农业、政治,甚至灵魂与宗教,而冰川正是这些的核心。
但是,过去50年来,喜马拉雅冰川的气温每10年上升0.2度——看似不多,但如果21世纪持续如此的话,最终会打破201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的承诺,到达预期升温的上限。
这片山区生活着大约2.5亿人,如果算上生活在平原中的,会超过10亿人,他们某种程度上都依靠融水生存,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喜马拉雅……
从默纳利开始,我们印度—英国团队的所有10个人都钻进了卡车,背包和板条箱晃晃悠悠地绑在车顶上,加入了痛苦缓慢的军用车辆和卡车队列,缓慢地驶向海拔接近4000米的罗塘垭口(Rohtang Pass)。那里只在夏天开放一两个月。剩下的时间,天气太恶劣——也许这就是这个垭口名字的由来,在波斯语里它的意思是“死尸堆”,这冷酷地提醒着人们曾有累累冰冷尸骨。罗塘垭口是一道文化上的分水岭,南边是古卢山谷(Kullu Valley),印度教繁盛之地,北边则是信仰佛教的斯碧提和勒劳利山谷(Spitiand Lahaul),我们的目的地是北边。
垭口处飘扬着鲜艳明亮的藏族祈祷用的经幡,暗示着这种转变——不只是宗教性的,还体现在空气变得更稀薄了,我第一次感受这种变化是在穿过碎石地,想拍一张没有叽叽喳喳拥成一团的游客的照片的时候。从卡车上下来走了几步而已,我就喘不上气了,干冷的空气哽在喉咙后部,我开始咳嗽。过了罗塘,道路险恶之极——一连串的急转弯,大部分时候只是仅靠着一侧的悬崖,路上凹凸颠簸,我们在车上亦摇摆颤抖。2018年的斯蒂芬冰川之旅结束后,我在回程的飞机上晕倒了。而一年前,在这里,在卡车猛烈的摇晃中,我的头开始剧痛,好像被什么从左猛地砸向右边。
……
过了河,又经过了短暂而痛苦的爬坡,我们终于到了乔塔希格里冰川上的大本营,就在山谷边,是拉马教授建立的研究冰川的永久性小型研究站。乔塔希格里冰川在勒劳利方言里是“小冰川”的意思。其实也不小,大概有9公里长,是瑞士上阿罗拉冰川的两倍,与喜马拉雅最长的冰川之一巴拉希格里冰川(Bara Shigri,意思是大冰川)相邻。这两条冰川的融水都汇入了钱德拉河(Chandra River),就是我们之前在铁箱里摇摇摆摆跨过的河。
两条冰川北边正对着克什米尔争议区。作为科学家,你需要印度的外交和内务部门的双重许可,才可以前往。(在实际操作中,如果获得了许可你会接到通知,如果被拒绝了你却无从知晓,不管怎样过程都是漫长曲折又隐秘的,所以很难做什么计划。)莎拉和我,显然是被允许前往的第一批西方女性……
正是乔塔希格里冰川水的传说激发了我的兴趣——它的漫长迂回。钱德拉河吸收了冰川融水,然后汇入杰纳布河(Chenab River),越过国界,进入查谟(Jammu)和克什米尔,最后灌入巴基斯坦的旁遮普(Punjab)平原,注入伟大的印度河。印度河十分壮观,它养育了巴基斯坦那些无法自行解决供水的地区——这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地区之一。印度河为印度河盆地的上部提供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灌溉系统,与巴基斯坦建造的多座大坝相连。杰纳布河的水源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脉印度段,但根据1960年签署的《印度河用水条约》(以下简称《条约》),它由巴基斯坦调节。这个条约是国际水资源分享的早期样板,规定了印度控制三条东边的河流,巴基斯坦控制包括印度河和杰纳布河在内的西边的三条河。这处理方案并不完美,想想就知道,水无时不在流动,很难去规定其边界。
在这个地区,水资源控制权的政治斗争更引发了其他数不清的冲突。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争议地区冲突的原因之一就是水。因为这里的河流是巴基斯坦珍贵用水的源头。巴基斯坦在杰纳布河上建造了很多水力发电的大坝。印度也计划要建更多,这种行为《条约》是允许的,只要不影响下游巴基斯坦的供水就行。建大坝,是解决人口增长和水资源短缺的一种策略,但这个策略也有政治上的潜在影响。如果印度在杰纳布河上发展水电项目,那么它就能控制的克什米尔争议地区的供水,因此也就会对巴基斯坦形成辖制。
多亏了拉马教授和他的团队,乔塔希格里冰川是上印度河流域唯一拥有后勤设施的冰川,科学家得以有条不紊地研究这里的水流。这条冰川和它冰冷的邻居们共同成为该区域供水争夺战的关键,很多伟大的亚洲河流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其中印度河最仰赖于冰川融水。在这个被盛行西风掌控的区域,当雨水稀缺时,上印度河流域中高达40%的流量,一些高山支流的90%的流量,都是由春夏季的冰川融水组成的。恒河流域大部分受季风控制,雨水更充沛,所以只有10%的流量来自于冰川融水。所有源自喜马拉雅的河流中,海拔越高的地方,冰川融水所占河流供水的比例越大。值得注意的是,最脆弱的那些人,那些夹在喜马拉雅高山中偏远陡峭的山谷村庄里勉强谋生的人们,也最依赖于冰川融水。
喜马拉雅冰川储量丰富,形状规模各不同,表现也各不一样。有一些冬季时会把雪困在冰体中,有一些夏季时会通过季风存雪,还有一些(比如乔塔希格里冰川)两季皆可。有一些冰川最后终于陆地,其他一些则让冰舌浸于湖泊。跟大部分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不同,喜马拉雅冰川的表面极脏,通常覆着一层从上面滚下来的粗粒碎石。而且,这些冰川分布在绵延3000多公里的山带上。
我们的野外工作要应对严峻的气候和麻烦的后勤保障,所以研究喜马拉雅冰川也显而易见地充满挑战。
亚洲季风会携带满溢的水汽从南边过来,而冰川坐落在季风的雨影区(通常是山脉背风坡的干燥区域),因此乔塔冰川的降雪通常是随西风到来。尽管如此,季风仍然对这个小冰川的健康情况影响重大,因为它在夏季带来间歇性降雪,会形成一条反射毯,减缓冰川的融化。乔塔希格里冰川是一条温冰川,河床处水流充足,基本上是在夏季融化,有点像阿尔卑斯的上阿罗拉冰川。自从20年前在阿罗拉工作后,这是我第一次研究小的高山冰川——从各种角度来说,我感觉回到了家。
不过,第一次尝试爬上乔塔希格里冰川——一次被尼泊尔向导响亮的吟诵声点亮的短途跋涉——就让我深刻意识到这次任务的艰难。我们从海拔4000米左右的大本营迎峰而上,几乎花了一整天,向上爬了1000米到冰川中段。冰川的岩面前缘善意地提醒我们:前面可都是石路了,大片的石海里有一些石头大得跟汽车一样,把好几公里形态模糊、脏棕色的冰川前缘武装得严严实实。
之所以有这么多石头和岩屑,是因为喜马拉雅山脉有着世界上最快的侵蚀速度,从5000万年前就开始了。那时候,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撞击在一起,把中间的一切都碾压碎了,也推挤出眼花缭乱的峰峦,这些山脉每年长高一厘米。风、雨和雪共同调节着这种生长,剥除掉一层层的岩石,把沙砾、岩屑都冲刷进冰蚀山谷,其中一些混在移动的冰川中,并最终出现在冰舌的下部,积聚成厚厚的岩层——有点像冰碛,但是形成的是碎石之海,而不是明显的细长的一溜(即冰碛)。这些岩石毯盖住大概喜马拉雅冰川四分之一的表面,在冰川融化并消退时似乎还会增厚。
……
关于喜马拉雅冰川个体的生长和退缩的很多研究,都是最近几十年做的——但是这些冰川本身差异甚大,以至于报告常常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政府间气候变化影响评估专家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评估冰川过去和未来的健康情况。该评估由联合国发起,一个全球性科学家网络来推进,差不多每6年一次,把目前已有的气候变化信息综合起来。而喜马拉雅冰川被归在常规的“高山地区”类,这意味着它们是跟世界上其他的高山冰川,如阿尔卑斯山脉冰川、安第斯山脉冰川、非洲热带冰川等冰川绑在一起的。
直到2019年,一个位于尼泊尔的区域性政府间研究机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ntegrated Institute of Mountain Development,简称ICIMOD)才撰写了喜马拉雅及其冰川的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响评估报告,该报告历时5年编写而成,涉及的主题包括生物多样性、气候、能源、食物安全和水资源,将多样的发现综合成一份独立的区域性评估。结论是:喜马拉雅冰川的退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亚洲季风袭入,越往东冰川的质量损失越大。对那些因季风获得雪量的冰川来说,变暖尤其倒霉,主要是因为,降雪本来会形成了一道反射性的保护毯,减缓融化,但变暖后降雨取代了降雪。
一些科学家好奇,为什么这些喜马拉雅冰川的这些碎石盔甲——在我们行进在乔塔希格里冰川时阻碍我们的石海——可以防止它们继续融化,拯救这些冰川。最近用卫星图像进行的研究似乎表明,基本上,被碎石覆盖的冰川情况并不比干净的冰川好,部分是因为所有的碎石都累积在冰川表面,冰川的流动最终会慢下来,顶部会形成湖泊,边缘上会出现大型的冰崖,这些都会变成融化的热点区域。所有这些额外的融化抵消了碎石层的延缓融化作用。对这些覆着碎石的冰川来说,这些加减法着实很难算清,科学家们还有大量问题有待研究。
还有一些比较孤立的地点,比如喀喇昆仑山脉东部和青藏高原西部,冰川赫然呈现全面的退缩趋势。很多这类冰川既大又高,会达到海拔8000米以上,一年四季都会有降雪。这些地方夏季气温更低,持续的盛行西风带来了更高的降雪,这些好像可以让冰川暂时维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不过科学家并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原因。最可能是一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包括气候变化导致亚洲季风强度的改变,还有一些当地独特的因素,比如中国西部平原更大规模的灌溉,往大气中蒸发了更多的水汽,导致了高山上的更多降雪。但这里冰川的发展趋势似乎也不可持久。
本来高山上的冰雪表面可以把太阳光反射回天空,但现在的变暖(就像北极一样)把这个反射层给剥除了。于是,在21世纪未来的日子里,几乎可以确定,喜马拉雅山脉比其他地方都要更快地变暖。即便奇迹发生,所有国家通力合作,把全球变暖的温度控制在《巴黎协定》中那个艰巨的限度(前工业化水平以上1.5摄氏度),喜马拉雅也会升上2摄氏度。最好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把全球平均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喜马拉雅大概三分之一的冰川在21世纪末会消失。而最可能的情况是:我们继续按照现在的速度燃烧化石能源,到时候大概三分之二的冰川会无影无踪。
至于喜马拉雅区域几百万人的命脉之源,那伟大的白色冰川河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短期来说,我们认为大概在2050年前,会有更多冰川融水汇入河流。因为冰川目前覆盖的区域非常广阔,未来的变暖会加快它们冰雪表面的融化。但21世纪中期之后,因为冰川变小,无法保持大量融水下流,即使融化速率还是一样高,融水量肯定会下降。
最终,在一年中的特定时期,河流水量会大规模减弱,影响国内供水、水利工程,从而进一步影响农业和能源利用——对河源上游来说这种情况尤其突出,比如在干旱的夏季极大依赖于冰川融水的印度河。白色的大河们会枯竭。你可以想象在季风性雨带,随着冰川融水减少,雨水相应地变得更加重要——而问题是,雨水并不会像冰川融水那样平稳持续,而是会不可预期地猛然爆发,当地的人们并不知道水龙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
在乔塔希格里冰川大本营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直想着冰川融水作为生命之源的重要性。不管我在哪儿,我总能听到河水从营地旁流淌而过时低沉的轰鸣声,最终奔腾着汇入印度河。在这条窄窄的生命线之外,沙子、沙砾和大的石块组成了冰碛和巨大碎石堆,或者只是一堆堆杂乱散布着,在它们之下,土地正贪婪地渴望着水分。水孕育了生命,缺水生命将熄——这个简单的真理印刻在此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正因此,水和冰川对喜马拉雅地区的人们有如此重要的宗教意义。
恒河大概是世界上最热的河流,通常被印度教徒称为母亲河,是他们神话中的女神,相信恒河之水能洗掉他们的罪恶。这条河源自甘戈特里冰川(Gangotri Glacier)前锋裂开的冰穴,就在印度和中国西藏的接壤处——一处神圣的印度教场所,每年成千上万的教徒前来沐浴在圣水中。不久之前,印度河是印度教最尊贵的河流。事实上,“Indus”这个词是从古梵文“Sindhu”衍生来的,这个词就是“河流”的意思——还生成了“Hindu(印度人)”和“Hindustan(印度)”这两个词,然后从古希腊语中演变出了英文的印度“India”。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之后印巴分离,因印度河主要流经巴基斯坦,于是印度人对水的信仰转移到了恒河。
这种灵魂与水的难分难舍的纠结让我着迷。我十分相信冰川和泉水由生命女神掌管,它们有力量净化和赐予生命——因为最近在巴塔哥尼亚的风暴中艰难跋涉的时候,我开始发现自己在思考,有没有更大的,超越我所见、所触、所感的存在?在这些荒凉冰川,我有时候感觉到离一些不是人类也不生于此地的生命很近——那是云团攀升或越过高耸山巅时阵风中的嬉闹;太阳升起驱除黑暗冷冽的阴影时的片刻温暖;或(时而)一种潜伏在冰川边缘的有生命的存在。有一些一闪而过的瞬间,持续了只有千分之一秒,但足以让我灵光一闪,感觉也许这其中有更高的存在。
我是一个科学家,这些并不难理解。自然界中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存在。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我个人生活中也是一样。2013年夏天,母亲去世后一周,我还跟她有过一次不寻常的对话。我当时被悲痛淹没,坐在一个灵媒昏暗的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甜美浓厚的焚香味。一个灵体出现了——我看不见,但是灵媒能看到——说出我母亲的名字,准确地描述了她的疾病,她临终前的感受,甚至还知道我戴着她的婚戒。想到在她的灵魂出现的那一瞬间之前,我的世界观一直都是一维的,我略有不安,想到人们可能会从一个世界移动到另一个世界,我便晕乎着离开了。
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喀喇昆仑山脉北部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Gilgit-Baltistan),人们把冰川视为生命体,还有性别的区分。男性冰川颜色深,移动缓慢,水量很小(科学家称为表碛覆盖型冰川,debris-covered glaciers),而女性冰川则是闪烁着白色或蓝色微光,水量很大(干净的冰川)。当地人还有一种传统习惯,会把两种冰川的冰混合在一起,然后把冰块放在山洞之类的隐蔽处,上面堆一些装满水的葫芦,冬天水冻结时,这些葫芦会裂开,水会冻到冰块里。这些混合冰块上还会铺木炭和树枝、木条等其他材料,用来隔热,减缓融化。男性冰川会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女性冰川“受孕”,在接下来的冬天里,会诞生一条新的冰川。
在印度北部干燥寒冷的拉达克地区,工程师索南·旺楚克(Sonam Wangchuk)用这种繁殖冰川的方法,发起了冰川的制作,夏天把融水存储起来,到冬天时水沿渠道流入山谷,产生的高压会使之喷射入寒冷的空气中,形成一种球形的冰金字塔叫作舍利塔——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形状很像佛教徒供奉佛舍利的地方。这些舍利塔一般靠近村庄,春天时经常出现水量短缺,冰塔会比冰川先融化。这种人工冰川必须每年都人为添加冰量,但确实解决了一些供水短缺的问题。
在乔塔希格里冰川前缘的岩石区域,也有类似典型的干旱特征。在如此高的海拔上,地质如此不稳定,我们的营地却惊人地结实,一座看起来无菌的白色活动房,两旁排列着睡觉的铺位,一座坚固的石头棚就靠在后面起伏的冰碛石上,我们围着棚子搭起一圈帐篷。我把之前去巴塔哥尼亚的那顶昂贵帐篷也带来了,这顶帐篷之前在我的头部制造了自己的夜间液滴喷雾系统,而在高高的喜马拉雅山,这小小的圆顶石棺[我的一个学生马修·马歇尔(Matthew Marshall)这么叫它]却绝对完美。所有凝水问题都消失了,一旦太阳落山,刺骨寒冷就会横扫冰川底端,而这顶帐篷现在变成了一个舒服的庇护所。
即使如此,我到乔塔希格里冰川后的那几周也极少能睡着。我总是能感觉到需要深深呼吸才能吸入足够的氧气,而且后脑勺的钝痛也纠缠着我。黎明到来时,深色的夜幕开始变成灰色,我感到周身一股深深的欣慰。我会爬出帐篷长管状的内室,进入稍微大一点的门廊,然后赶紧套上尽可能多的衣服——这绝对是“两件羽绒服”地区。接着通常我会先去看一下乔恩·特林,他不跟我们一起,而是在我“石棺”10米外的地方,一块巨砾侧翼下的缝隙处,自己单独搭帐篷,然后用卡其色的拉脱维亚军用迷彩睡袋保暖,他发誓这比任何帆布帐篷都好——虽然一天早上他承认他前一晚感觉有点冷。不过我们俩都比彼得·尼诺的睡眠装备要好——他从我们的印度朋友那边借了一顶帐篷,这帐篷已经扛过了许多个四季,最后在一个风雨之夜不敌疾风,夸张地倒塌在他鼻子上。印度代表团明智地选择了活动板房,通常在我们从帐篷里出来的时候已经起来活动了。还有一位欢乐的尼泊尔向导总是带着冒着热气的锡杯,里面是甜美的柠檬茶。我会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吃早饭,看着太阳逐渐地用柔软的金光照耀这块岩石区。
印度同事们好像有点担心怎么招待我们——他们显然尽心竭力地捣鼓出了各种可以吃的西式早餐,从薄煎饼到燕麦粥到鸡蛋卷应有尽有,不过在我们的反复劝说之下,终于接受了我们对豆餐和印度薄饼相当满意这件事(我们习惯了在营地自己准备食物,所以能得到这种奢侈的服务对我们来说已相当不错了)。他们也非常关心我们女性的生活是否舒适,还不辞辛苦拖来一个陶瓷的卫生设备,有完备的水箱和冲洗功能,安装在营地下游一个很小的帐篷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一天早上,我在营地漫步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件神奇无比的事件,一个用篱笆围起来的一两米宽的围栏,里面萌出一大簇四季豆豆苗。尼泊尔营地主管阿迪卡里(Adhikari)解释说,他种了一些豆子,想看看如果有山羊和绵羊粪便滋润的话,能不能真长出豆子来。这让我心头一颤。这些豆子长在冰川沉积物上,这些沉积物曾经是乔塔希格里冰川下的大片岩石。我记得,从格陵兰冰盖释放出的冰川岩粉包含了磷和钾这些元素,有一些漂浮在阳光照耀的海面上的微生物因此获得了营养。在远离海洋处的高山山脉上,这些从乔塔希格里冰川释放的岩粉也能从碎石和巨砾中脱颖而出,给四季豆提供养分。我在想,如果带一些冰川岩粉回家,我也能种一些作物吗?
莎拉有一种罕有的对植物和冰川的热爱,一年后,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在布里斯托大学生命科学大楼的楼顶接管了一间温室。很快,成百上千的大豆就郁郁葱葱地从盆里发芽了,土壤是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沙土和一两克乔塔希格里冰川岩粉的混合物。
(冰川学遇见植物学,谁能想到呢?)这些粉粒似乎就跟传统的化肥一样促进大豆的生长,而化肥却会引起农田的退化和地下水和河流的污染。植物一般在有土壤有机质的地方长得好,但在某些时刻,也需要额外的营养来促进生长,特别是在要收获植物作为食物时,而不是让它们死亡、分解,形成珍贵的有机质。
冰川岩粉能提供来自岩石的养分。问题是,岩石并不含氮。这也是冰川融水造成了巴塔哥尼亚和格陵兰峡湾的浮游植物问题的原因——没有足够的氮。但是,如果种不需要氮的植物,比如像大豆这样的豆科植物,它们能巧妙地利用大气为自己固氮,然后加入水分还有一点点如山羊粪便这样的有机质,就能茁壮生长。我在想,冰川岩粉能不能用来给贫困偏远的喜马拉雅地区退化的农田增加肥力呢。
这个想法扩展一下的话——如果冰川在退缩,是不是会露出新的土地表面供植物甚至农作物生存,并得到冰川岩粉的滋养?事实上,当你看看冰川边的土地里,就有这种迹象。任何冰川的附近,你都会看到不久前还被埋在冰下,现在已经暴露出来的磨碎的沉积物。很少有什么能在这里生长——没有足够的有机质和氮。
但从冰川到冰川岩粉,则有了新的可能。更强健的生命形式,比如微生物、地衣、苔藓类,能驻扎进来开始生长,在生命和死亡的循环中,慢慢地在土壤里形成有机质。有些微生物能从空气中吸取氮形成自己的细胞,它们死亡后,这些氮就进入了土壤中。时光飞逝,小的植物们也来了,然后是大一点的植物,然后是灌木和树。这叫作自然演替——随着生态系统的成熟发展,一种生态系统代替了另一种。
在冰川边贫瘠的土地上,这种新地表的自然殖民一直都在发生,而且随着冰川前锋继续退缩,这种情况还会更加频繁地发生。对尼泊尔及其高山的卫星图像分析已经表明,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林线和雪线中间的陆地带,已经有了一条“绿化带”。从1993年发生的这些变化——我就是在那时成为了一位冰川学家——意味着植物开始在此前太冷的地方生长,而且可能已经在吸收冰川岩粉里的氮。如果植物能在高海拔地区自然生长,那么像豆子这样的作物怎么就不能人工培育呢?看起来可能性很大——过去50年,气候变暖使得喜马拉雅地区的生长季,以每10年长5天的速度增长。
不过,供水仍然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我们所见,21世纪内,这个区域内流入河流的冰川融水会越来越弱,会减少河川径流,而且越来越无法预料河流未来的走势。要防范这个危机,亚洲多国政府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他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主要河流上筑坝蓄水、发电。印度就发起了宏大的“国家河流连接”项目(National River Linking),将用9600公里长的运河,把跨越印度次大陆的45条河流,甚至包括喜马拉雅的那些河流,都连接起来。筑坝、建水库的好处是它们能像水槽里的塞子一样——即使冰川融化和雨水减少成细流,水也能被存起来供干旱时期使用。
不幸的是,就跟在巴塔哥尼亚一样,这些巨大的人工湖也累积了沉积物(比如冰川岩粉),沉积物对各大河流冲积平原上的农业是至关重要的。整个文明都建立在绵延不断的富饶的河流冲积物上——古埃及就是一个好例子。因为有大坝,如今尼罗河里几乎没有任何沉积物——要是法老们还在,也得吃苦了。在这些大坝里,也可以积累一些沉积物供下游使用——但你得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一开始就不建大坝会更好。喜马拉雅山脉在变绿,也许会开发出新的区域开垦农业,但解决水的问题是很难的。冰川融化是一个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巨大的人道主义定时炸弹,会极大地影响脆弱的当地居民——讽刺的是,这些人并没有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回到平坦的德里之前,在乔塔希格里冰川的最后几天,我们再一次拖着笨重的箱子和背包们越过钱德拉河。我的心情很沉重,仿佛是失去了什么。挂在绳子上要返回河的另一边时,我是最后一个爬进哐当的铁箱子里的。这次,我只是轻松地融入了这种晃动。
我们的箱子们像钟摆一样,在涌着白色激浪的水面上,晃来荡去擦过凸出来的岩石,然后被缓慢而颠簸地拖到峡谷的另一侧,而我只是享受着这预料之中的短暂片刻。这一路,我一直盯着磨损的山峰,想把它们独特的形状铭刻进记忆里——峰顶的轮廓,光与影的妙手天成,流连在山壑里的那少许的雪,我想在它们消失之前把它们全部记住。到达另一边之后,彼得有点困惑地跟我说:“杰玛,你有没有意识到,越河回来的人里,你是唯一一个一直面对着冰川的人?其他人都面对目的地方向。”我没注意到,因为我一直在心里向冰川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