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纪事 | 重返乡土:一个漂泊大学生的“寻根”之旅
重返乡土:
一个漂泊大学生的“寻根”之旅
廖雯菲
“还没过二九天,家里就开始下霜了!”奶奶在电话那头细声感叹着福建老家的气温。
我有点错愕,今天是12月26日,刚过完圣诞节,广州满街还是五彩的圣诞树,街上不乏穿着春秋服装的上班族,我也难以想象此时老家的寒冷极致。我下意识翻开手机日历,一眼扫去,日历的农历时间上确实有个“二九天”,是这个月的31日。“二九天”来自民间谚语,所谓“二九下雪寒,九九惊蛰暖”。
“毑1(奶奶),那你冷不冷啊,要多穿衣服,注意保暖啊!上次给你买的……那个热水袋可以用。”我一时不知道怎么用家乡话说“暖手袋”,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好在奶奶还是听懂了。
奶奶从不会说普通话。她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山里农村的女子没有几个上过学,也不识字,她们只是遵从着老一辈的指示,跟着一头牛到男方家里,早早成为了“童养媳”。算起来,我奶奶已经有91岁了,这两年奶奶抱上了重孙,也渐渐能听懂小孩嘴里嘟囔的“奶奶”,跟重孙慢慢地笑着哄:“一起吃饭……吃饭……”。
半年前,奶奶在路上摔了一跤,进了医院做手术,听说是脑出血,整个人昏迷了。或许是碍于我在备考,家里没有人主动告诉我。那天偶然点开家族的微信群聊,才发现奶奶已经住院好几天了,大伯、二伯和我爸妈在群里讨论着轮流照顾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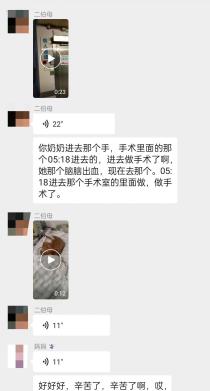
我不忍点开群里的视频,但又迫切想知道奶奶的状况。视频中,奶奶的头发全部削落,脑袋上插着一根充满血液的导管,额头上裹了一层意外洁白的纱布,衬得奶奶那样黯淡苍老。她孱弱地躺在床上,睁不开眼。我从未看见那样一动不动的奶奶,我不敢想象,不敢想象那个“万一”。
“那个手术室,五点十八分进去的,五点十八分,六点,啊六点就出来了。没事啦没事啦,你们放心,这边我在帮忙阿妈照顾吼。”一向乐观开朗的二伯母在群里发了一连串很长的语音,习惯转文字的我还是连上了蓝牙听。依然是熟悉的闽南腔调,依然是她习惯性的重复,好在,听语气,一切还是抱着希望,奶奶的身体也在伯母的悉心照料下恢复向好。
距离总能让人的焦虑多了一点安放之地,但也让心中的愧疚多了生长的空间。长期在外考学的我,不仅脱离了在广东潮州打拼的爸妈,也脱离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福建小山村。考试结束后,我借着难得的空闲,买了一张回老家的大巴票,从广州奔赴回福建长汀,探望留守家里的奶奶。
返乡的大巴,流动的乡村
习惯了高铁的速度与整洁,我对9个小时长途大巴的行程总是抱有一点畏惧。印象中难闻的皮质座椅、时不时的呕吐声都在提醒我回家路途的不易。坐车前,我买了几个橘子、备了几个干净的口罩,往上面喷上了一点香水,试图让自己在封闭的大巴车里能够更好地“存活”。
中午十一点,凭票过完安检,我照着座位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便收拾好东西坐下。后面陆续上来的乘客都是中年的叔叔阿姨,个别的手上还抱了小孩。还未出发,熟悉的乡音就开始在前前后后划破了汽车的发动机轰鸣:“今年高铁票盖2(这么)难买嘅呗!”“喂嘢,伊3(这)架车窗户都莫得开”……
我默默在心里点头,如果不是买不到高铁票,我也不会选择坐长途大巴了。想起以前坐大巴的时候,还是我上初一那年。我跟着爸妈、带着我弟,一家四口就挤在大巴的前后座,在车厢的摇晃里逐渐东倒西歪。妈妈的晕车情况很严重,总是祈盼在熟睡中抵达终点。而爸爸总是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是哪里,什么时候过梅州、什么时候过上杭路口……这条路,他领着我们走过很多遍。
小时候,他试过亲自骑摩托带我们回家,行李箱摞在摩托车尾五花大绑。我们就靠着一辆红色的机动摩托在泥泞的国道上飞驰,但颠簸之下也难免会有行李突然松开,洒落路边。

为了省钱,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打工家庭,都选择这样冒险的行驶方式回家,成为电视上报道的“春节返乡摩托队”。但这样的方式,并不安全,出过一次意外的车祸后,爸妈的返乡方式就变成了搭便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
返乡的路一直很艰难,爸爸也总是记得格外清楚,但我天生差劲的方向感从来不记得他标记的地方。不过,现在的手机地图导航已经很发达了,我也能大概知道,我到了爸爸说的何处。
“你到哪块?”随车的检票大哥开始问刚上车的阿姨。
“我去长汀,这车有没有经过上杭高速啊?”阿姨试图确认大巴的行驶路线。这好像是父辈们坐车的一个下意识习惯,甚至有点像自带的天赋,总能瞄准某个路口、某条道路来确认自己的行程与时间。
“你也去长汀啊?有过的有过的,你跟我一起吧!”突然,我后座的叔叔开始搭话。
“喔,这么巧,我第一次坐,不太清楚。我是长汀涂坊的,你在广州做生意啊?”阿姨礼貌地回道。
“没有啊,生意不好做啊现在……”叔叔叹气。突然间,我对面靠窗坐着的爷爷抬起了帽檐,也开始聊了起来:“谁说不是呢,不过我现在在海珠做的那个猪肉生意还可以。”叔叔听到这话,兴致一下就起来了,从后座挪到我隔壁,和爷爷隔着车厢过道也不减热情,到了中午该吃饭的时间,也没歇着,话茬一轮接着一轮。
我惊讶于家乡人们的社交之道,没有那么多猜疑,只是一句话就可以成为“缘分”之辞,车厢上的陌生人也能瞬间变成邻里乡亲。但我又有些落寞,在习惯于城市“互不打扰”的默契中,我们保持着体面,但似乎也有些冷漠,即便听到了一些求助、知晓其答案,也会选择沉默,避免唐突与冒犯。
阳光渐弱,我们的大巴在穿越了好几处长长的隧道以后,雨丝开始在车窗外织起水帘,外面的山连绵成一团黑影,清肃得很。晚间的灯光投在车窗玻璃上,涣散成一道道眩光。我抬手去拉窗帘,才发觉我靠窗的右手袖子已经浸湿了。原来,玻璃窗内也结了一层水雾。我知道,外面的气温已经很低了,我也估摸着快到家了。

正当我思索时,我有一个龙岩的朋友打了电话过来,问我在不在长汀,她正好刚从瑞金游玩结束,等会就可以过来找我聚聚。
正好,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在赣闵交界处,两地相邻,开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我欢喜地告诉她,我正在回去的路上,让她与我同住,不必再订酒店。她如今在厦门大学读研,我们自从大二见面后就再也没见过。虽然长汀就是龙岩市的下属县域,但细究起来,还是相距两个小时的车程。相见不易,这起电话让我兴奋不已,更期待回家的旅程了。
“长汀的!长汀的!下车了啊!”大巴停了下来,我终于能有机会摘下口罩透气了。一出车门,湿冷的空气侵入皮骨,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身后的叔叔阿姨结伴打电话让家里人来接,我则拉着行李箱往预订好的民宿走去。
老院新居,冬去春来
“游家大院?怎么看着那么熟悉呢?
还是店头街?”我看着我订的民宿位置陷入沉思。我的家乡长汀以汀州古城、红色小上海为名,吸引了不少游客。店头街则是长汀的一处旅游景点,也算是商业化的古街。以前在县城读高中时,偶尔会和同学来店头街走走,但也不曾记得这街上还有什么民宿。不过,仔细想想这两年的发展,长汀确实在旅游服务上越做越齐全了。

长汀虽叫“古城”,但主城区不大,往来顶多一两公里。我循着记忆走到了古城墙“济川门”,再往前两百米便是店头街了。没想到,还没完全到春节,城里早已灯笼高挂,祥龙花灯也倨傲城墙之上,洋溢着新年的喜庆。
我刚想打开导航确定民宿的位置,就被人群中的声音吊住了——“菲菲!菲菲!这里!”我追着声音寻着来源,终于看见一个小姑娘在卖冰糖葫芦的小哥旁挥手,于是和我朋友顺利碰面了。
街上的人意外地多,摩肩擦踵,以前我从未见过如此的场景,连走路都是“人堵人”。我忍不住开始吐槽:“哎,其实长汀也没什么可玩的,怎么那么多人呢现在。”
朋友笑了:“或许是大城市的人待腻了,就想来小镇的地方看看。以前小学我也来过长汀玩的,只不过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人。”

时间已是晚上八九点,我突然想起自己还没吃晚饭,又询问朋友要不要一起吃,朋友摆摆手:“哈哈哈哈不用啦,你发给我那家砂锅粉挺好吃的,我傍晚没事就去吃了。”我有点心虚,其实那家店我没有吃过,刚好刷起小红书,看见店主女儿在长汀旅游的帖文下留言评论说他们家开了十几年,实惠好吃,才想着分享给朋友试试。谁能想到有一天,我回家乡吃饭也要靠小红书这些平台推荐了呢。
“菲菲你家在哪啊,怎么住起酒店了?”朋友开始疑惑我的行程。我解释道,我老家在长汀县下辖的南山镇,大巴没有直达镇上,只能坐到县城的车站。爸妈没有在县城买下房子,我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虽然有姑姑住在城里,但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人家招待,才想着订起酒店来了。刚好住一晚,缓缓坐车的不适,第二天再坐小班车回南山。
“那好辛苦,那我们先回去放东西,再出来吃个饭,晚上早点休息。”
“没有没有。”我急忙回应,“你从龙岩过来,又去瑞金,晚上又过来这里,你也很累啦。”说着说着,我们到了游家大院。我仔细一瞧,噢,原来是这里。这是游氏的家庙,保留了古建筑的样态,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供游客参观用。以前路过这儿,都不敢进去,没想到今天我竟然以一个游客身份住进了这里。

抬脚迈过门槛,院子里一棵侧倒的柳树唤着些许生意,旁边的石桌石凳与地上的鹅卵石也留了几分闲致,除了行李箱的轮子不太方便,这里还是蛮惬意的。踏进大堂正门,满屋的木制墙面、窗户,散发着一阵古香,天井里的青花瓷鱼缸在丝丝雨滴里奏着一点弦音。
民宿老板娘见我拉着行李箱,一边让我拿身份证登记,一边介绍说,民宿有送一张长汀的古城墙和卧龙书院的景区联票。我忍着笑意,本想用家乡话说我也是长汀人,最终还是没说出口,礼貌性地用普通话说了谢谢,把票转给了我朋友。
这间民宿看着不大,但穿过天井,路过正堂,后面有好几道门,一个个小天井连着一间间侧厢房。虽然这里大部分保留着传统民居的装潢,但为了运营便利,房间门换了新式的现代合成门,挂着一个个房间门牌号,屋内也装了新式的墙板、空调。民宿的阿姨还给我们开了抽湿器,在床被里放了一个热水袋。
“这里真的好像小时候住的老房子啊。”朋友突然感叹。我也附和着,感慨着许多老房子的消失:“其实老房子冬暖夏凉,有时候也比水泥房舒服,但大家都盖新房子了,都会想盖个小洋楼,长面子。”
那一晚,我们两个躺在床上聊了许多,直至凌晨三点才渐渐睡去。我睡不着,一部分是因为没习惯老房子的隔音问题,隔壁住客的呼噜声总叩醒我的脑子,另外一部分则是因为我开始困惑未来的就业选择问题——走?还是留?
朋友她说,她想留在龙岩,和家里人待在一起,毕竟生活在外面的世界还是没有那么容易。我起初想劝她再看看,因为我觉得老家的生活虽然安稳,但是也少了很多乐趣,能看到的世界也有限。但转头一想,老家始终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地方,她能在这找到满意的工作,能和家人常在一块儿,又是多么难以奢求的幸福呢。
人们常说,福建的孩子恋家,不是留在福州、厦门,就是漳州、泉州。我一度想逃出小山村、逃出省内,去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但回过头来,却又无法否认,自己听见乡音的亲切、吃上煎薯饼的幸福。这种拉扯感一直缠绕在我心头,我早已适应在城市里喝咖啡逛书店的日子,我可以过好自己,但我也不可能舍弃脱胎于山村的家庭。作为村里人满怀期待走出去的大学生,又该做什么选择呢?
“被卖掉的孩子”
第二天,我在超市里挑了一些新鲜的菜,买了奶奶爱吃的油豆腐块,就往车站赶去,准备回南山镇。坐了一小时车,可算到了。我一下车,发现路边的店铺门面都改成了统一的红色招牌,挂着几个星星,矮房的墙面也刷上了新的墙画。
再往里走,便是镇上的中央路口了。那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我们一般叫“墟日”。镇上的路边摆满了水果摊、菜摊,还有辆小货车,拉着一头野猪肉,吆喝着人们抓紧买了。不过,老家的人们总不会轻易相信便宜的东西有好货,当家的她们总会在菜摊边徘徊,货比一条街,再兜回来放心地把手帕里的毛票花出去。

从镇上到我家还有段距离,一般来说,从镇口到村里,我可以坐私人的面包车,花3块钱,就可以和叔叔阿姨们一起拼车回家。但等了很久都没有合适的车,我只能选择坐12块钱的摩的回家。这要是换了我爸,估计他又得跟摩的司机还价一趟,细说油钱的成本多少。
刚到家门口,就看见我奶奶又坐在大门口等着,想必是我妈妈把我回家的事提前跟她说了。奶奶总是这样,就一个人坐在门口等,等着谁回来。
我高声喊着“毑!捱4(我)系菲菲啊!”她笑着站起来缓缓走着,迎着我回来。没一会,她又问我坐摩托车多少钱。我如实说了,奶奶嫌弃道:“喂嘢,盖贵,以前唔系捌5块钱吗?”我笑着解释道,现在一直都这样,涨价很久了,没办法。看她还有精力计较这个,看来身体恢复得确实还不错。
放下行李,我便开始调试电视。因为前段时间妈妈跟我说,奶奶又按不到电视看了。我想着,这次回来正好可以帮奶奶调一下频道。我一边调试,奶奶就在一边咕哝着:“就是怎么按都按没有,一下子能看了,喔没一下子又跳没了。”我一开始还不明白为什么会跳走,后来发现是电视的会员广告弹窗。广告一弹,不识字的奶奶不会操控遥控器关闭弹窗,只能乱按一通,最后作罢。
还记得前段时间,广电总局整改电视会员套娃收费,没想到如今我也亲自感受了什么叫做“花钱还要买罪受”。调试半天,我终于帮奶奶设置好了长辈模式,方便她开机就可以看直播。
“弟弟在哪读书啊现在?”奶奶突然问。
“他在武汉,在湖北,很远的。”
“怎么要去那么远,不能在城里读书吗?”听完这话,我无奈地笑了,毕竟,小县城怎么会有大学呢。
“他一走,把我的电视都带走了。”
我一时不知该觉得奶奶的形容可爱,还是该心疼她孤苦一人。奶奶听不懂普通话,也不识字。以前我教过她用遥控器,甚至画了指示图。无奈她年纪大了,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最终还是没办法操控电视,只会开关机。自从弟弟出去上大学,家里便只有奶奶一人。原本住在隔壁的大伯一家,也都为了带孙子出去厦门生活了。没有电视能打发时间,奶奶就只能坐在门口,等着哪位邻居,或是老朋友上来跟她聊聊天。
“你们啊,一个个都跑那么远,跟被卖掉了的一样。”我不敢正眼瞧她,因为我知道,她的脸上必然淌下了浑浊的泪珠。
但我没想到,奶奶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我很想反驳她,但又不知该如何说起。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的选择,有多少是情愿如此的呢?父辈期盼儿女能够走出深山、出人头地,儿女背井离乡无可奈何,祖辈又嫌弃儿女不能常伴左右。我不知道这样的循环要持续多久,在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里,我们这代年轻人要怎么去做出选择。
我时常想起《山海情》里的老书记面对吊庄移民,最终劝慰了村里的老人们,说:“人嘛,毕竟不是树,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哪儿了,哪儿也就能再扎根。”
是啊,人又不是树,树只能在土里扎根,而人可以找到更好的土地,甚至把瘠土改造为沃土。在如今的乡村发展之下,在那些一线的基层工作下,我作为流动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应该让自己的小山村,成为更好的家园?
家乡的雨下了很久,持续了一个多月都是阴霾昏沉。渐近年关,大伯一家、二伯一家、还有我爸妈也都陆续回来了,唤醒了旧日的喜庆与热闹。炮竹阵阵,久违的艳阳竟也出来了,引得小狗们在鞭炮纸碎上打滚嬉闹。小孩搬出了角落的学步车、大人把茶几搬到了院子里,享受独有的阳光。但不一会,待久了,又觉得发热甚至发烫,人们终究回到了屋檐下的阴凉处,看着几个小孩在阳光下追赶嬉笑。
山连着山,连着我们。年青人因为祖辈的牵挂,总会在某个节日重聚一堂,也会因为节日的结束,曲终人散。但不变的是脚下的土地,如何让乡土留住人、留住人心,我想,这是我们新一代人的使命。
注释:
1毑,意为“奶奶”,汉字读音为jiě,客家方言中发音为jià。
2盖,音译,在福建省长汀县方言中意思为“那么”,表程度副词。
3伊,音译,表“这个,这”,代词。
4客家话,意为 “我,我等”,读ngai ,正字为我,“捱”是白水字。
5客家话,意为“八”,读bie。

本文系2024年“新青年非虚构返乡纪事”第一季优秀作品。
原标题:《返乡纪事 | 重返乡土:一个漂泊大学生的“寻根”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