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自然 | 食物森林作为一种替代性社区经济模式
每到周末,大理的柴米多农场就人声鼎沸。
一群自发形成的志愿者前来共建“食物森林”。

这是一个两亩多大的农场试验地,不大的面积内种满了大大小小、高矮错落的各类可食植物,自2023年底以来,由志愿者们营建管理而成。“我们想先以一亩多地来做实验,然后扩大至整个农场。未来的整个农场将会成为一座食物森林。”发起人瓜瓜如此解释这片可食地景的存在。

2024年4月中旬初具雏形的柴米多食物森林,分为7个层级。(1)最高的主冠层,用于遮挡紫外线。(2)4至5米高的次冠层,可由苹果树、梨树、石榴树、枣树、柿子树等各种果树组成。(3)1至2米高的灌木层,可由蓝莓、树莓、覆盆子等浆果类,以及无花果树、柑橘类树木组成。(4)草本植物层,可由小麦、水稻、玉米、秋葵、花卉、美人蕉等较高植物,以及番茄、茄子、辣椒等低矮植物组成。一般来说蔬菜瓜果都属于这一层级。(5)地被层,紧贴地面,主要功能为覆盖土壤,以帮助微生物躲避紫外线。生菜、香菜、小青菜、菠菜等蔬菜,以及三叶草、野花、草坪等花草均属于这一层。(6)根类植物,可由山药、红薯、土豆、葛根等植物组成。(7)攀缘植物,可由丝瓜、黄瓜、牵牛花、紫藤、炮仗花、风车茉莉等植物组成。摄影 天心;资料提供 瓜瓜
除了种植与日常维护,自四月开始,志愿者自发形成了“食物森林共生社区”,社区设置了若干小组,分别负责香草育苗、酵素制作、食材开发、自然教育及市集运营等方向,并将所得收益以一定比例返还给社区资金,形成了某种社区小规模经济的雏形。

左图为印在宣传册页上的柴米多食物森林的志愿者福利规则。累计参加一定的志愿者共建活动后,志愿者均可以从食物森林中获得物产。其初衷旨在于建立自给自足的依托食物森林而生的社区。图片来源:食物森林共生社区群
在瓜瓜眼中,这是一个“青色组织”,社区成员就像植物一样,可以自然而然、自由生长。
何为食物森林?
食物森林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富于生物多样性的农林系统,包含7个不同层级的植物层,具有提供食物、生计、环境服务(如栖息地、散热、碳储存等)以及娱乐、教育和社区建设空间的潜力。许多食物森林的存在,目的是完成“自给自足”的使命,而并非依托于任何正式组织或受到专业机构认可。
实践者们认为,在自然中放任一块土地,最普遍的方向是形成森林。因此,通过对可食植物的分层,种植者可在一定区域种植更多植物,这片土地也会朝着健康的生态系统的方向迈进。其中,人与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可以达成一定的动态平衡。例如,不同层次的结构复杂性可以吸引栖息和筑巢的鸟类,而花朵的多样性则扩大了传粉者的栖息地;更深的根系能提高保水性;植被还可提供遮荫并调节温度,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都意味着更强的恢复能力。
食物森林还可通过吸收大气中的碳来缓解气候变化。与其他粮食系统或土地利用(如每年耕作的农作物或草坪)相比,食物森林的众多植被层,可以在其生物量与土壤中储存更多的碳,尤其是木本植被的固碳能力超群。由于排除了每年耕种的弊端,食物森林往往根系深厚,可在土壤与地下植被中储存大量碳。此外,食物森林还能让社区拥有丰富的本地食品,有效减少食物从种植地到食用地的距离,从而减少因食物链运输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无论对缓解气候变化还是提高社区韧性,食物森林均具有积极的作用。
“模仿自然”是食物森林贯彻始终的理念。事实上,它也是地方/传统农业生产系统中寻常的形式。尤其是在热带地区,“模仿自然”的传统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而欧洲的“森林花园”概念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大约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开始了永续农业运动,其中“食物森林”是其主要成果,还对此进行了更为专业化的努力。在美国,第一座公共食物森林是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华盛顿卡弗博士可食公园(the Dr.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Edible Park),1997年开放;目前,根据Community Food Forest网站,这样的食物森林场所扩张为160余处。
许多文章认为,“森林花园”和“食物森林”在研究与实践中几乎没有区别。二者都被定义为,以可食用的多年生植物为主的多层生态系统。根据“森林”的定义,食物森林的最小面积理应为1英亩(0.5公顷),并至少拥有10%的树冠覆盖率,以提供类似森林的生态系统服务。但由于实践中大量存在较小规模的有趣案例,在现存的学术研究中,面积更小的“食物森林”也往往被纳入考察范围。
根据Albrecht与Wiek(2021)的研究《食物森林:其服务与可持续性》(Food forests: Their services and sustainability)对现有食物森林研究的总结,食物森林在改善水循环与土壤形成、储存碳、调节微气候、增加生物多样性并创造生计机会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其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过去的研究汇编了不同类型食物森林的实用知识、文化转型、营养价值及生态恢复潜力,甚至认为其有助于公共空间规划与管理实践,但较少关注经济维度,即如何稳定、可持续地运营一个食物森林。因而,食物森林衍生出的生态社区经济模式,也成为部分研究者关注的新话题。

食物森林的典范之一。新西兰南岛的里弗顿(Riverton)小镇, Robert Guyton夫妇建立了一座31年历史的 食物森林,形成了一个繁荣的生态系统。(图片来源:https://www.nzgeo.com/stories/the-future-of-food/)
在“大理福尼亚”构建食物森林
大理是这个时代诸多新兴思潮与社群的集散地。
柴米多食物森林共生社区的发起人瓜瓜,并非柴米多农场的员工,而是携带食物森林梦想的实践者。
瓜瓜原名芮小云,毕业于苏州大学生物系,曾留校任职。因痛感被规划为“工业城市”的苏州远离自然,以及大学期间缺乏实践,瓜瓜萌生了返乡念头。
回到老家,面对家人邻里的不理解,她尝试以生态农业的方式耕种被化肥、农药污染的土地,并发现过去村里的农业方式中存在很多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做法。问题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单一化种植导致植物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被剥离;同时,惯性农业又极大破坏了土壤的微生物多样性。
在改良土地的过程中,她观察到,野外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糖分,并将糖分储存在根部,与微生物交换养料。因此,只要土壤中的微生物多样性高,植物就能生长好。而惯性农业的方式破坏了土壤中的微生物多样性,导致农作物只能依赖化肥,最终其营养也变得单一。
进行种种尝试后,瓜瓜深刻认识到,种菜的本质是养地,或者说是养微生物。“要让土壤中有活的微生物”。关键在于,土壤需要保持潮湿,富含有机质,且不能被太阳暴晒。
后来的实践让瓜瓜验证了施用酵素与做好覆盖对于养地的重要性。“把酵素的微生物加入土地活化它,无论什么植物都能长好。不需要管植物,只需要管土,以及把覆盖做好”。
直到去年,一个偶然的契机,来到大理的瓜瓜与柴米多农场一拍即合,尝试构建可食植物能够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

柴米多食物森林共生社区用厨余垃圾制作的酵素。摄影:大宏&柴米多食物森林共生社区群
年底,食物森林启动,由当时的柴米多农场员工刘珩与瓜瓜共同发起。刘珩是生态农业爱好者,过去曾在有机果园工作,厌倦了果树单一种植,对更具多样性的食物森林跃跃欲试。
正式种植之前,他们先测试了土壤,检查其中的微生物是否丰富。柴米多农场提供的土地,过去荒废了好多年,没有化肥农药的污染,但其中微生物还不够丰富。于是,他们选择将苍山上的土著菌进行扩培,加入土中,同时加入酵素微生物、EM菌、枯草芽孢杆菌以及农场牛马粪的堆肥来提高土壤的微生物多样性。
同时,场地上持续了割草覆盖的工作,用以维持土壤潮湿,为微生物提供良好的繁殖环境。土壤中还加入了蚯蚓,用于将粪便分解为有机质,以便为土壤直接吸收。
就这样,养地过程经历了两个月,微生物多样性大幅提高。瓜瓜认为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而在养完地的基础上,瓜瓜与刘珩规划了食物森林七个层级的种植细节,并在日后的志愿者活动中,带领大家从高到低进行种植。

在营建食物森林之前,先在旁边的花坛中尝试建设了一个mini版本——共生菜园。摄影:大宏
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刚开始的主冠层。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大树挪动容易导致死亡。他们选择趁冬天大树休眠时种植,以便春天生发时不再受到不良影响。刘珩认为,如果时间足够充裕,最佳的操作方式应当是,让如合欢(乔木)、木豆(灌木)这样的先锋树种从小树苗开始演化生长,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三年。但现实不足以提供那么充裕的时间,或许是项目的遗憾之处。
为了让大树挪移后更好地适应环境,他们在树坑下加入微生物的“营养肥料库”——苍山的土著菌、草与厨余等微生物快速消耗的食物、树皮及树枝等微生物消耗较慢的食物。此外,有机质与堆肥也被加入;为避免烧根,上面覆盖了一层厚土,与大树根相隔。大树移植后,每天要给其叶面喷洒酵素水。“大树扎根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期间很难吸收营养,因此需要在叶面提供营养”。这就是喷洒酵素水的原因。
不同层级的植物,在志愿者帮助下持续种植了几个月。到了四月中旬,食物森林初具雏形。
社区如何共生?
每周临近周末,大理食物森林共生社区的志愿者,都会收到类似如下的群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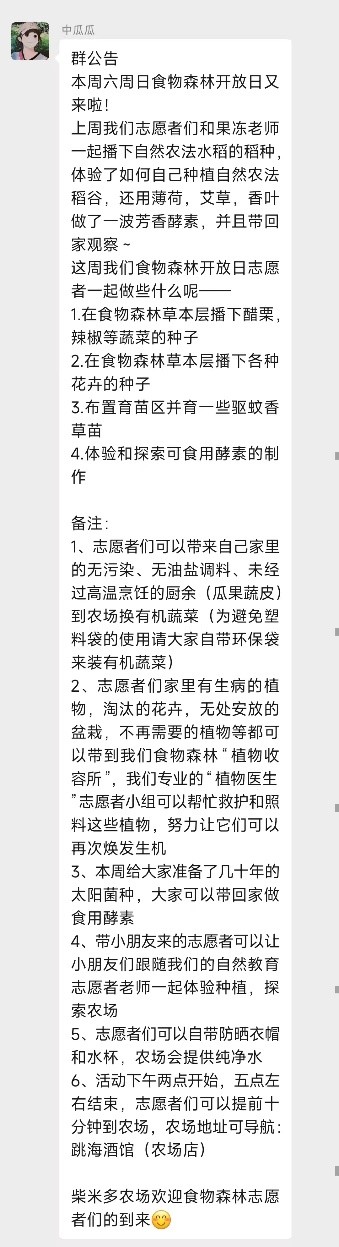
于是,周末活动日,许多志愿者会将家中蔬果为主的厨余垃圾带到农场,由垃圾分类小组统计每位志愿者带的公斤数,并以每3公斤厨余换取1公斤农场蔬菜的方式回馈,鼓励大家回收利用厨余垃圾;而酵素制作小组则拿这些厨余垃圾制作植物用酵素,这些酵素除了用于食物森林的日常维护,还可以在市集上售卖。

志愿者活动日合影。第二排左五为瓜瓜。摄影:洋洋
“可持续、零废弃”大概是志愿者最大的共同标签,爱好DIY以及废物利用是主要表现形式。利用废弃木板,志愿者DIY了农具收纳架。利用废弃竹竿,志愿者DIY了植物标签。利用社区成员家中不需要的/生病的盆栽植物,又在食物森林中不断加入新的植被。甚至利用自家果园闲置的水果,有位志愿者尝试开发制作了不同种类的饮品,供应在劳动中有补水需求的其他社区成员,并将收益的20%反哺回食物森林社区。

利用废弃木板DIY的农具收纳架。(摄影 / 大宏)

小朋友们为植物制作的竹标签,兼顾了环保与趣味。摄影:洋洋
发起人瓜瓜善于发掘社区成员的爱好与优势,并鼓励其在社区充分表达。例如,开发水果饮品的志愿者杨能,曾谈及这段经历。“家里很多水果没人吃,摆着就坏了。很多人不喜欢单纯吃水果,我就想可不可以做健康饮品。一次偶然机会,我带给瓜瓜尝了一下,她说很好,并询问我是否可以在志愿者共建活动上制作,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健康又解渴的东西。”
首次水果饮品的售卖,在共建活动上大获成功,也为食物森林共生社区产生了首笔来自内部成员的资金,然而,盛放饮品的容器成为无法再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杨能尝试在后续共建活动中用搪瓷杯代替塑料杯。这一举动获得了社区其他成员的认同,并成为了持续的社区行动,也为新加入的志愿者传播了环保理念。

志愿者共建活动中制作水果饮品的操作台、搪瓷杯柜,以及其余赠送给志愿者的食物森林物产福利(右图为肉桂叶)。摄影:天心
杨能很乐意把收入的一部分捐赠给食物森林共建。他认为,自己的每一次捐赠都可以为食物森林增加新的植物,让这个生态系统更加完善。这样的图景让他产生成就感。
回到自然而然
“我们可以将食物种植的方式,转变为保护地球的方式。地球会越来越好,人类也会越来越健康”。瓜瓜认为,食物森林可以让人与食物都回归自然规律。这一道理在工业文明之前便为人类古老的智慧所诠释。
另一位志愿者可仔,则在劳动中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她在自媒体中写道,“在练习发酵的时候,我发现不同的菌种可以在漫长的时间中演化出跟此前全然不同的形态,而如果在新酿造的酵素中加入长时间发酵之后的菌种,后者则可以带动这样的变化朝向不同的方向……有时,我感知自己正从它们身上生长出一种与以往全然不同的依恋关系。如果时间足够长,我便能从任意一罐涌现出的新生命中,觉知到一种深厚的古老——正是这样广大的时间,使我对日常的重复感到敬重”。

“从土地到餐桌”。食物森林共生社区志愿者聚会,大家自己用土地物产制作生机饮食。摄影:食物森林共生社区群
刘珩则是社区构建的关注者。他心中的理想,是“基于食物森林,最后形成一个在地的生态社区,自给自足的同时,又能分享有余,并与外界交流互动”——人类社群也可以像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生长。他坦言,这是对工业化、机械化的时代背景的反思,目前单向度的社会分工太过细碎,导致人的思维方式也过于局限,而食物森林及其所衍生出的生态社区,则代表了另一种更为整体性的系统视角,是一种不止于批判的“建设性实践”。
柴米多农场的食物森林还在继续生长。围绕它的共生社区也在自由生发,或许代表了这个时代某种朴素的追寻。
这种追寻其实一直流淌在人类的血脉里,既是一种超越,更是一种回归。
(作者天心系媒体人、独立研究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规划与生态修复。感谢王婷博士为内容、图片提供修改意见。王婷系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后, 从事湿地景观与环境人类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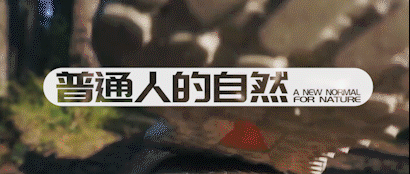
个人能为环境做什么?普通人如何在自然中自处?
“普通人的自然”(A New Normal for Nature)专栏记录普通人与自然相遇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