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2》热播,在猫腻访谈中,解读范闲等角色承载了什么样的历史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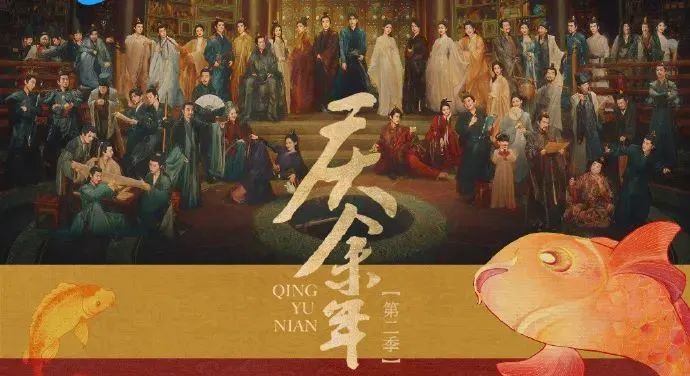
时隔五年,《庆余年》第二季(以下简称《庆余年2》)终于带着原班人马播出。《庆余年2》5月16日在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开播后,瞬间爆上热搜!CCTV电视剧的官微透露《庆余年2》首晚实时直播关注度峰值破2;在网络端,该剧播前预约破1800w,开播仅57分热度值破30000,成为历史首个开播当日进入腾讯视频爆款俱乐部剧集,同时成为历史最快进入爆款俱乐部剧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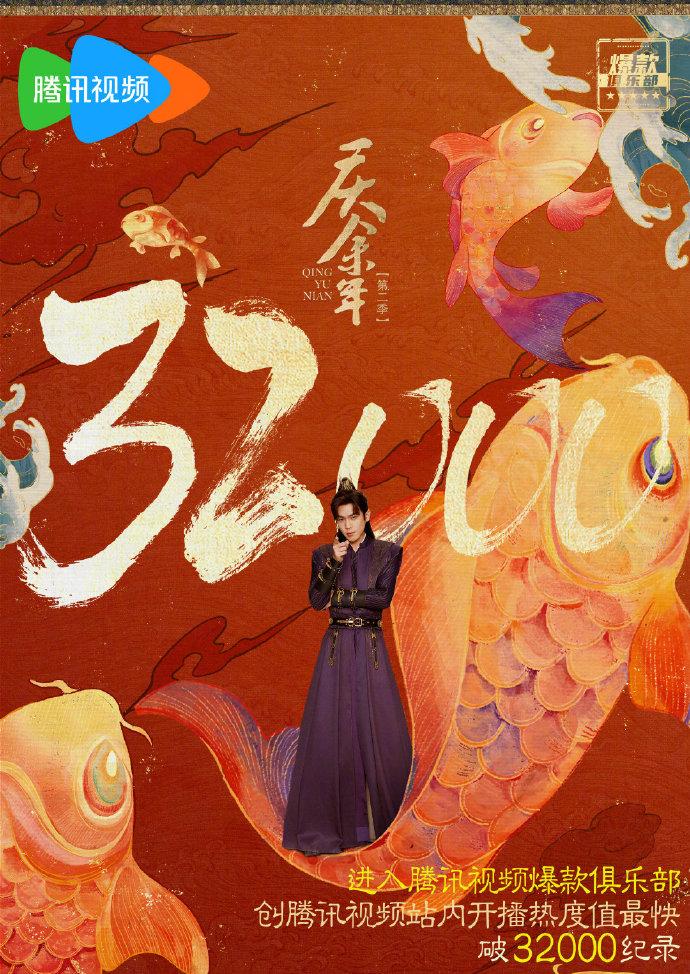
《庆余年2》开篇快速揭晓了上一季结尾留下的范闲的生死谜题,迅速将观众带入范闲假死回京后面临的新局面与新变化。熟悉的轻喜剧风格,生动的人物塑造,依然是剧集吸引观众的不二法宝。在后续剧情中,范闲所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会带来更多的看点,此前的路演中,主创团队也表示,“第一季是鲜衣怒马少年闯江湖的感觉,但是现在它更现实、更深刻地进入这个世界的本质了。看上去好像厚度重了,但范闲本身的理想、追求并没有改变,在重重压力之下,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本心。”
与此同时,期待五年之久的观众也吐槽起了片中大量贴片广告与原著改编问题,五年前第一季《庆余年》的精良制作令人眼前一亮,五年来国剧质量的逐步提升也让观众在品质方面有了更高要求,而期待与批评,都是推动国剧更好发展的必要市场推动力。今天,我们重新推送本报此前对《庆余年》作者猫腻的访谈,当部分观众不解《庆余年》主角究竟是穿越到古代还是未来,又为何始终坚持理想时,或许通过猫腻的分享, 会更多理解《庆余年》的写作背景与借主角抒发的历史情怀。

猫腻:我只有“希望作品常在”的情怀
访谈
文 / 郑周明
(刊于本报2015年7月)

猫腻,知名网络文学作家,当他近几年进入网络文学财富榜前十的时候,在网络写作环境里,他身上有两个标签显得尤为特别,一是“70后”,一是“情怀”。
最初猫腻从芸芸网络作家跃入读者视野里时,他被贴上的标签便是“情怀”。在当下,这是个被用到泛滥的词汇,却很能够用来形容网络文学作家中的“另类”。2003年,猫腻从川大肄业,初入网络文学世界,开始连载《映秀十年事》,他一开始便主打东方玄幻这个拥有庞大作者群和读者群的大类型,此后至今,他的创作进一步细化为仙侠和武侠。然而这部首作最后未写完便无疾而终,这让猫腻停笔想了好一阵子。2007年,当他开始写作《朱雀记》时,他说,这部作品让他确立了做一个作家的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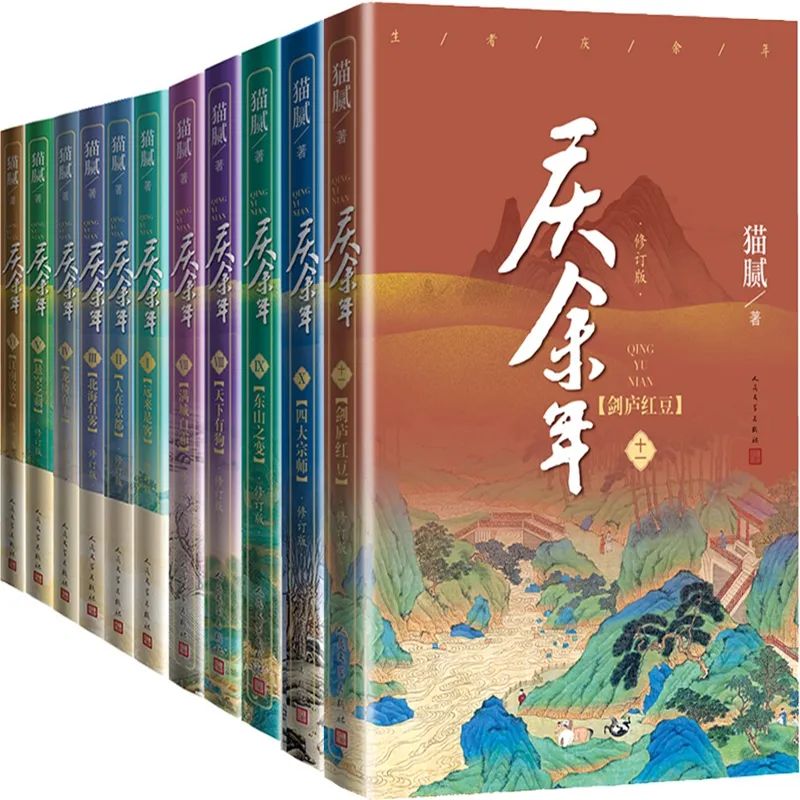
《庆余年》《间客》《将夜》《择天记》……这些作品一次次打开了读者对猫腻的新认知。在几百万部网络文学作品里能够被读者发现并追捧,这里面有几分运气,更多的则是依靠作者身上的“不同”。猫腻的作品不仅受网络读者喜爱,也引起许多圈外人、专业文学评论家的注意,注意到他和其他网络作家写作的不同,注意到他比别人自觉多一些的东西———这可能源自他的阅读和阅历,也可能是他希望在模式化的网络写作里增加一点“理想”,也可能是他有心把传统文化里的一些哲学问题、个体意识、启蒙意志加入到了角色的人生桥段当中。
有许多因素让猫腻变得有“情怀”,变得“另类”,但他却表现得颇为谨慎,他信赖网络写作与读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也会反思自己这种“不同”给今后的写作带来的是优势还是背离。他同样清楚,当下的网文IP开发热潮会让他获得更多跨界的读者,但他也偶或怀疑,目下的写作方式是否能满足越来越期待他的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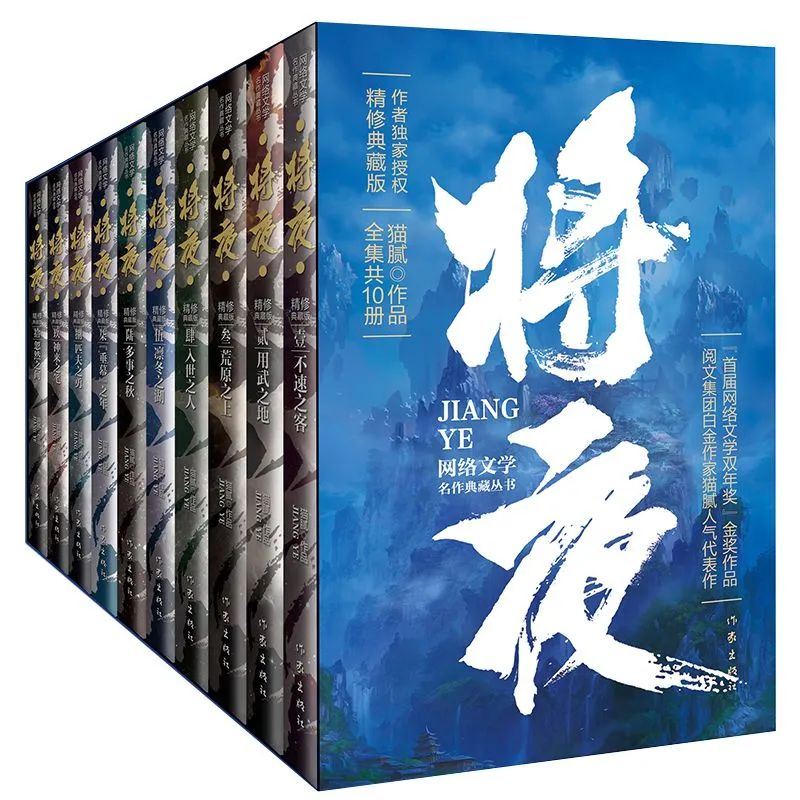
在猫腻之前对读者的调侃式自白以及记者对他的访谈里,能够感受到他像任何一个热爱阅读的文学青年,曾捧读港台武侠小说,幻想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与偶像比肩。多年后,这个可能性在逐渐放大,他会珍惜,会适应,也会去调整。
在通俗文学这一文学史的大脉络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懂网络文学中的各种类型书写,也更能理解作者的初衷、读者的收获。重要的是,猫腻的写作也在表明,网络文学像任何文学形式一样,正在筛选出自己的代表作家、作品,并试图在商业模式之外,努力把作品留下来。
网络写作是一门手艺活
记者:从2003年以来,你创作了《映秀十年事》《朱雀记》《庆余年》《间客》《将夜》《择天记》共六部小说。回顾这些作品,你认为哪部作品是确立了自己成为作家的自信?
猫腻:应该是《朱雀记》。因为准确来说,正是从这本书开始,我才正式走上商业小说的写作道路,并且凭借写作这个曾经的自我娱乐方式,获得了足够维持相对轻松的生活的报酬,能够靠写作养家,才能往“作家”这两个字靠吧。
记者:在这个写作过程里,你觉得从事网络写作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猫腻:网络小说无论被称为类型小说还是商业小说,本质就是为广大读者服务,那么想要从事网络写作,首先你必须清楚地知道,大多数的读者,他们真正想要看的是什么,想要获得什么样的阅读体验,对这种娱乐方式有怎样的要求?知道这些并且认真践行之,便是从事这个职业的基础。清晰明确的表达方式、尽可能稳定的更新节奏,都是其中一部分。

记者:这些之外,现在的网络作家都比较认同类型小说很依赖技术训练。
猫腻:写作肯定与天赋有关,但我确实支持说商业小说或者说类型小说,更重要的还是技术方面的训练。唯手熟尔,从古至今的类型小说写作,归根结底都是个手艺活儿。就我个人而言,不外乎是多读多写多思考多总结,这里的对象不仅限于网络小说本身,也涉及到我能够接触的大众流行文化领域里的所有审美对象。
记者:当你想明白这些基础问题后,是否会想起第一部作品《映秀十年事》当初未写完而放弃的经历?
猫腻:《映秀十年事》只是因为本来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看的小说,商业性方面先天不足,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过太多商业方面的考量,没有利益回报,单纯凭爱好,当然没有办法一直持续下去。应该说,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网络写作本来就分为两个方面,自娱和娱人,自娱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自乐。

记者:你的写作应该说很顺利,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获得很大反响,不仅仅是名利上的,创世中文网曾给你写的推荐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文风细腻、辞藻华丽,铺排考究于当代网友无出其右者。”你的作品还受到很多传统文学评论者的好评,说在你身上能看到“思想性与娱乐性”、“文学性和故事性”的兼并,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些评论?
猫腻:我一直认为我的文笔有问题,尤其是对于商业小说来说,至少在某些时候是不恰当的,所以每每听到赞扬文笔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妥。至于思想性和娱乐性、故事性与文学性这方面,我以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面,而应该是天然统一的纸的两面。我也没有刻意地想去做些什么,只是觉得小说就应该这样写,如果因此而得到了一些好评,只能说是意外之喜。
记者:在欧美高校教类型写作时,都会告诉学生秘诀是坚持阅读、坚持写,你会给新人些什么建议?
猫腻:还是坚持阅读、坚持写、坚持思考与总结,不要忘记在本子上记下你想到的每个桥段。
情怀是我的意外收获
记者:回到写作这件事上来说,无论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写作对自己都存在一种内在的自我实现,也导致许多人把你的写作放在大环境下,看作是有情怀的。这个词现在有些泛滥,但的确你比别的作家加入了更多个人思考的东西,比如《朱雀记》通过佛宗来揭示“苦中有乐,人应该好好活着”的命题;《庆余年》借范闲重生向人们解答“人为什么而活着”;《间客》以一个小人物的愤怒,展现强权主义对个体生命的践踏,回应了“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
猫腻:我总以为一个故事写上两三百万字,我要为之付出两三年时间,总是希望在付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之后,能够留下来一些什么,无论是一个特别瑰丽壮观的画面,一个人物阳光灿烂地离去,还是一个哪怕最简单的道理,就像小时候学语文时的中心思想,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故事能够有自己独特容貌的最简单实现手段。而且有时候也是我自己没想明白的事,想与读者聊聊,找些共通的感觉。如果这就是情怀,每个人都有,并不需要太过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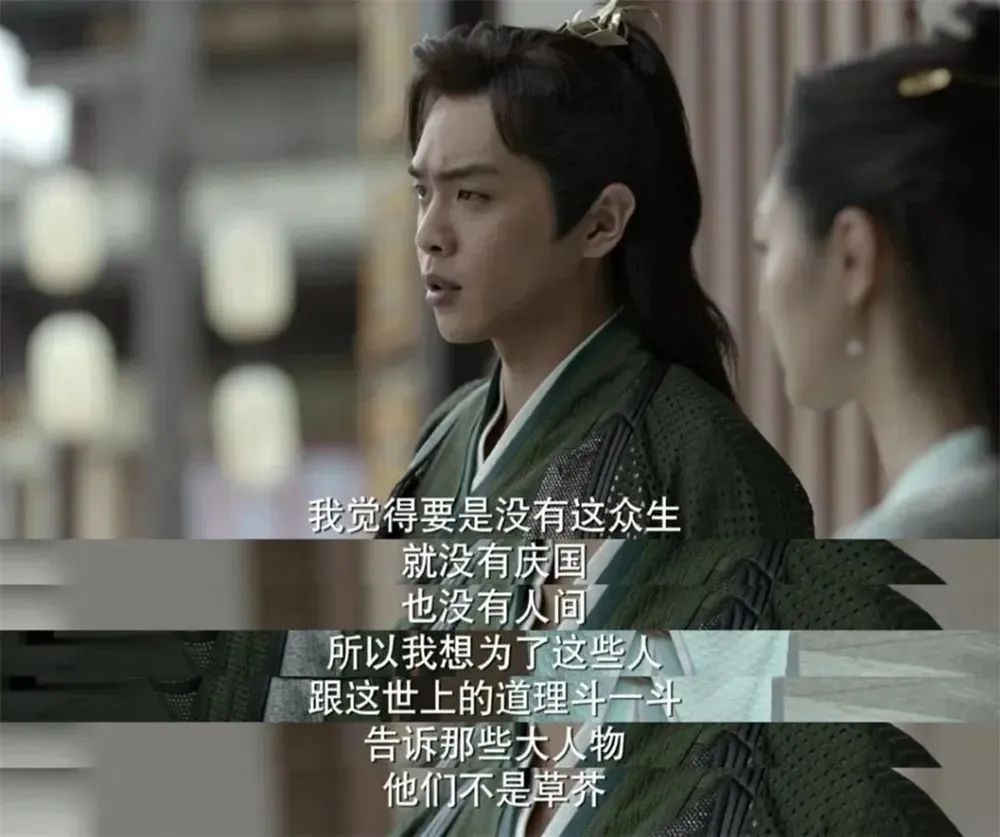

记者:的确,你和读者互动的过程里,也在呈现共同成长的样貌。《间客》出来时,有读者说机甲题材不是你擅长的,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武侠小说,之后《将夜》好评如潮,却也有许多“包袱”最终没有解决的遗憾。在粉丝反馈和自己写作方向把握上,你如何考虑?
猫腻:《间客》的确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武侠小说。对读者的这种意见,我没有任何意见,因为这就是我写这个故事的目标。读者反馈的意见,如果是直指要害的,那我当然要认真接受,但如果是读者的口味偏好,那我就没有办法了,终究不可能满足所有的读者,某些时候还是需要坚持一下自己。
记者:这让我想起最新的《择天记》,开篇气势恢宏,到打斗场面节奏慢了下来,绵延好几章节去渲染气氛,有点赶着写赶着更新的感觉,叙事节奏和以往不一样。
猫腻:是的,《择天记》可能是我写的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世界架构相对较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延续从《将夜》开始的一种尝试,即把长期连载的网络小说与日日剧这种娱乐方式对应起来,有更多的平缓叙事、家长里短、真切一些。而且《择天记》是一个关于青春热血的故事,我对这四个字并不是太熟悉,一直在寻找怎么能够青春热血又不自以为是的方法,现在看起来,虽然还不是很完满,但有所获得,相信会越来越好。

记者:《择天记》连载到现在来看好像剧情发展还不到一半,你预计这个小说完成的体量和时间跨度会多大?
猫腻:就像上面说的那样,这会是我写的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时间跨度会比大家想象中要短,但体量会非常大。
记者:《择天记》之后,下一部新作有设想过吗?
猫腻:下一部作品现在有三个故事备选,题材也是完全不同的三种,至于最后选择哪一个,时间还早,我自己比较倾向没有写过的。
记者:但凡涉及武侠题材的,一般都会视金庸、古龙、黄易等香港武侠小说宗师为偶像,这也隐含了一种写作上的仿造和延续。你有没有期待自己能与前辈们并肩而立?这也需要自己对写作有更多的思考和沉淀。
猫腻:理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花心思和沉淀当然是必须要做的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经常被很多人忽视的一方面就是修改,不停地修改,就像金庸一样,这个需要以后拿充裕时间来仔细做。
尊重网文IP是集体创作
记者:现在网文IP开发热火朝天,你的作品也是很受改编欢迎的,像《择天记》有动漫和游戏版,近日也发布了动画,你会对改编版有所参与吗?为了作品质量的统一性。
猫腻:在游戏计划之初便有参与,动画也是如此,只是限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参与程度没有办法太深。如果说为了作品的质量考虑,我始终有种看法,无论电影、电视、动画还是游戏,这些和小说不同,小说更多的是私人创造,这些项目则是商业项目,涉及的人与事太多,我不愿意因为我的意见让一个集体项目做出太多的调整,因为那确实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我尽可能地保持尊重与安静。

记者:如今看网文发展方向,大约会像日本ACG产业那样,成熟的团队进行周边打造,对作家的索取会很“饥渴”。IP用户与读者之间,有时候重合,有时则对你的作品需求不同。
猫腻:哪怕把眼光投向日本,卖得最好的那些作品———我指的是所有周边———当然就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抵触。事实上,好的IP,当然就是读者最喜欢的,也当然是读者优先。
记者: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梦,有理想也有很实际,到今天你回望会明白自己的梦具体是什么?
猫腻:我的梦想,其实一直都很具体,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想写一本很好的小说、想拍一部很强大的电影,还有一些更遥远的。我对读者也隐讳地提过,我就是想不停地写,以此确保读者会一直记得我,然后会回头去看我以前写的故事,直到很多年后,还有读者在看那些故事,更多年后,我这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些故事还存在,还有读者在看,并且通过那些故事,知道我这个人,记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电视剧照

原标题:《《庆余年2》热播,在猫腻访谈中,解读范闲等角色承载了什么样的历史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