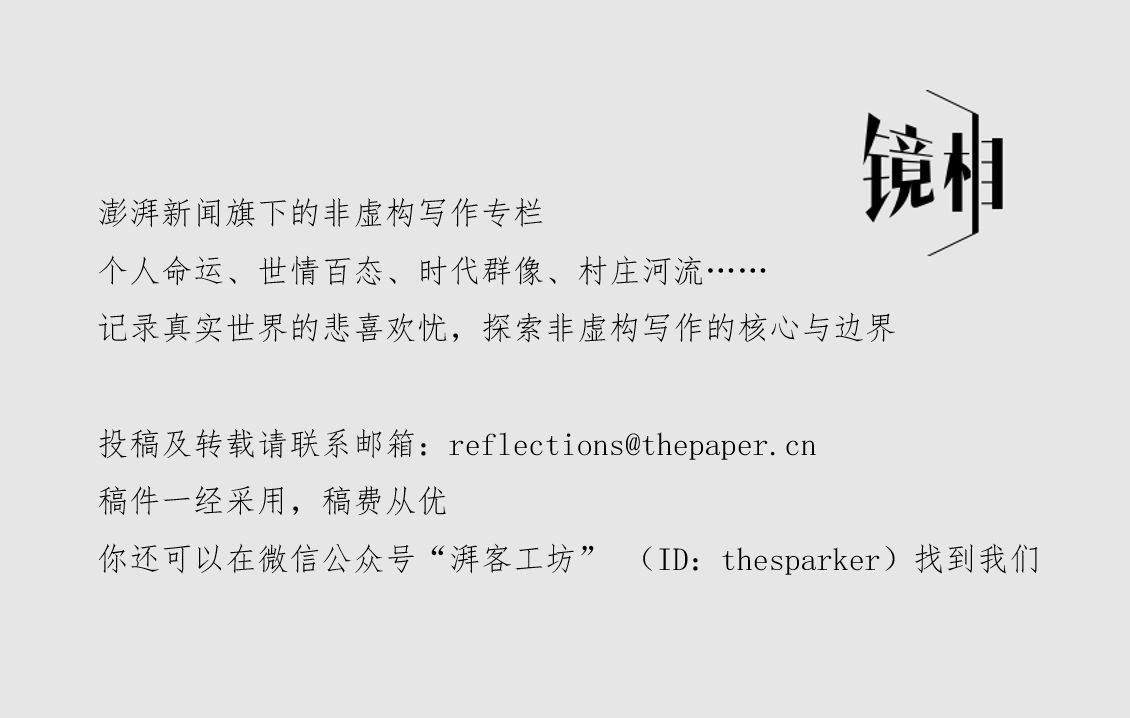“盲目”的爱:失明41年,寻找“第四条出路”丨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丨杨海滨
编辑丨柳逸

图源:娄烨电影《推拿》
“所有盲人的职业,就我的经历来说,只有三条路能走,一是上按摩学校,毕业后当按摩师,也是最好的出路;二是在民间跟着懂易经的师傅学八卦,之后蹲路边算卦,是低级的出路,这两者的前提条件是家庭经济要好,能拿出数年学费才行。第三条路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出不起学费,他没有任何方面的一技之长,也就只能窝在家吃喝等死。而这样的盲人占整个盲人群体的百分之六七十。”
这是丰望在2024年2月23日焦作市民主南路他所在的“中医推拿”店对我说的话。在我还没来得及向他提问前,他首先定义了盲人的职业范围。我正思忖怎么接话时,又听到他反问:“在今天的社会,像我这个年龄段的正常人是如何生存的?”
我明白像他这样天生失明的盲人,都伴随着天生的敏感,我怕随意的一句不妥的话伤害到他,便在大脑里飞速选择着合适的词汇。我稍许的迟疑果真被他敏锐察觉出来,他安慰似的又说:“我经历的事多了,你把我当个平常人就好,没必要顾虑什么话会伤害我,我抗打击能力很强,这也是我们盲人在社会上生存的最基本的技能。”我心里又一惊,小心翼翼地说:“不仅是你这年龄段的人,而是所有人都在奋力挣扎。”说话时我一直看着他的表情,见他双眼快速眨动,似思考着什么。我继续说:“我说挣扎这个词,本意就是热爱,热爱就是不停地挣扎。试想一下,如果连挣扎都没了,那不完全失去对生活的热爱了吗?”
他点头说:“这说法有道理!”然后用语速急促的北京腔调说:“盲人肯定比正常人付出数倍的挣扎才能勉强地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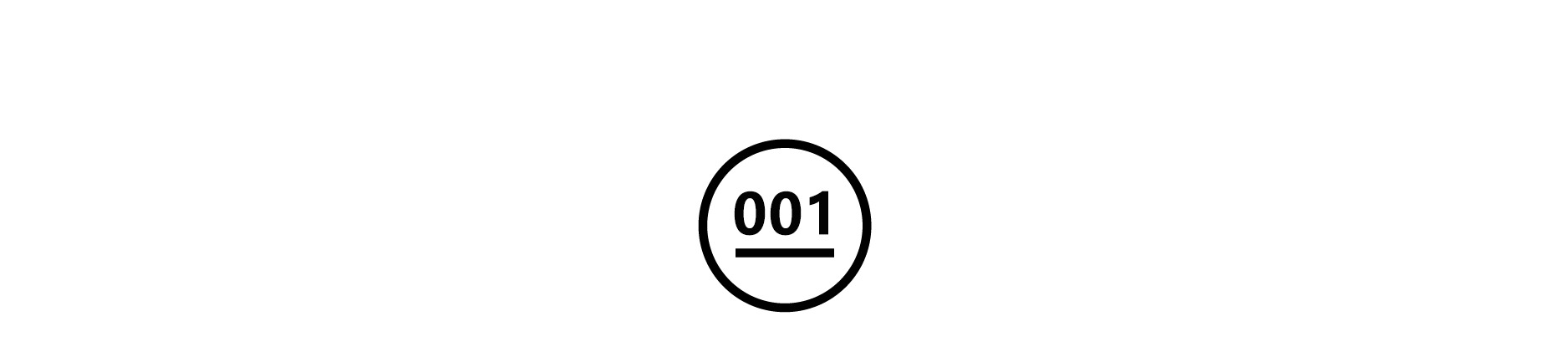
“盲人为什么不能上学呢?”
丰望出生于1982年12月的修武县郇封村,父母都是没上过一天学的纯农民,一直希望丰家能有个传宗接代的人——在已有两个妞的情况下超生了丰望。但没想到盼来的儿子却是个先天性盲人,之后,他们对丰望的哺养方式几乎是自生自灭。到他该上小学的年龄时,也没人想起他能不能上学,平时的生活由比他大十一岁的大姐负责。大姐去上学时,他便由父亲带到一个砖瓦窑的坯场上,让他自己跟自己玩,父亲去背砖,天黑才带他回家。因他不熟悉环境,常跌倒在一边的沟壑或泥潭,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水成为他这个时期的记忆。

主人公丰望,在河南焦作一家推拿店给顾客推拿(受访者供图)
有天,正当他与小朋友玩得高兴时,伙伴们忽然被他们的父母叫走,把他一人孤零零地留在那,后来才知道,人家父母怕他这个瞎子没轻没重,给他们的孩子造成伤害。还有天下午,邻居俩小孩来找他,这可是他童年里小朋友仅有两次主动找他的一次玩耍,结果也只玩了一会,就爬在小凳子上写作业。丰望听着文具盒和翻书声,一种失落油然而生。自己为什么不能上学呢?从此孤独成了他童年永恒的状态。
丰望的大姐从小去哪都带上他,仿佛他是她身体的延伸部分。尽管家庭经济条件差,手里有了零钱就给他买能买得起的食物,一般小孩吃厌了的方便面,就是他生日最美味的蛋糕。所以他对大姐的感情甚至胜过和母亲的感情,有什么心里话就对大姐一人说。大姐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在他12岁这年,大姐在广播里听到焦作特殊教育学校招生的消息,立即告诉了父亲。丰望儿时就被小伙伴的翻书声吸引过,早有上学的念头,但也知道自己拖累了家庭,家里数年来被村委会评为贫困户,以政府每月发的几百元救济款过活。父亲觉得他这样的盲人上学没什么用,能吃上饭不饿死比去上学更重要,一直拒绝他去上学。恰好这时,已二十来岁的大姐某次外出打工挣了数百块钱,她拿着这钱交给父亲,说:“如果不送丰望上学,将来他就是一个文盲加瞎子,一辈子只好窝在家吃喝等死,如果现在送他去上学,学个一技之长,再让他去讨生活也许还有出路……”这话驱散了父亲原本的犹豫,丰望的命运因大姐的话得到改变。
父亲咬着牙拿出家里的钱,加上大女儿的钱,凑齐了丰望的学费。他被送到焦作特殊教育学校。他在学校用四年学完小学课程,初中只读一年就毕业了,接下来面临的就是高考。对于盲人来说,高考的面很窄,他也只能考专收盲人的河南省针灸推拿学校,结果以较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他再次被父亲和大姐送到洛阳这所学校读大学。
可在入学的第一年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崩溃,甚至想退学。这个学校除了盲人学生外,还有健全的学生。有天有个健全学生把烟头弹到他的保暖瓶里,他在喝水时喝出烟味,就把这个瓶里的开水倒到另一瓶里,可那个恶作剧学生,又悄悄把尿尿到他的保暖瓶,他在无意中喝到了,虽然愤怒,可不知道是谁干的,没有证据,就忍下没报告校方。不久后的某天,他再次喝到尿到他保暖瓶里的尿,忍无可忍,报告了老师,老师也很愤怒,要揪出这个没有道德的坏学生,由于没有证据查不出是谁干的,而且这个学校以教技术为主,对学生道德甚是无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下文。他知道这是个不能破的案件,也就不了了之。在盲人的成长过程中,承受这样的羞辱是常见的代价。
从此他基本不再用保暖瓶,而是托大姐买了一只容量很大的塑料水杯,随时带在身边,这习惯一直保持数十年,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喝水。

再见姐姐,亲爱的姐姐
大学期间,丰望格外认真地学习推拿技术,同时还进修中医理论,学习养生,终于熬到毕业季。
学校和全国各地的推拿店都签有实习合同,每年毕业季前,北京东城某家推拿店的老板就来洛阳,挑选几名最优秀的学生到北京实习。丰望名列其中。他也想趁机实现自己的抱负,回报家庭一路来的支持。
丰望到了北京的店里才知道,在他们之前,老板已在北京推拿学校招了六人,每当有客人来总是先安排北京的学生上,甚至北京的学生轮到第二圈了,也没他们上场的机会。他们接待不上客人,就提不了成,而他们的工资都是按推拿次数提成的。这样的现实让丰望有了被欺骗的感觉。
洛阳的同学围着他商量咋处理。也许他生来就是个有智慧的人,在学校也这样,同学有拿不定主意的事都会找他商量。他说:“我们要联合起来给老板提意见,既然都是实习生,那就要公正,所有人都要排队,轮到谁谁上,否则我们就要求回洛阳,拒绝实习。”他领着五个同学找老板提意见。起初老板并没在意,直到七天后丰望和同学要离开北京时,他才引起重视。老板怕他们回去让他名誉受损,向他们道歉说忽视管理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丰望尽可能把自己在学校所学的技术施展出来,没事就给北京盲人出版社打电话买业务相关的书籍,进修并提高理论水平,还给客人讲养生之道。
没想到的是,他们与老板因伙食问题再次爆发了冲突。老板觉得这些外来者在他这干活挣钱,有碗饭吃就不错了,并不顾及他们的要求。
通过这两件事,丰望明白了这个社会并不会因为你看不见、是个盲人,就同情、宽容你,你必须要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尽管他自小就明白这道理,但在踏入社会之初,还是遭受了超出想象的残酷。
在北京,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他就会在晚上给大姐打电话诉说。这天他也照常把这事跟大姐说了。不料几天后,大姐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面前。
他想都没想她为什么舍得花几百块钱专门来北京看他,以为她是担心自己的生活。大姐对他说,“这个社会可不像大姐那样心疼你,你在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之外,还要勤快,把推拿技术再提高一截,让自己变成店里的招牌,才能更好地发展。”
他“嗯嗯”地答应着,然后告诉大姐:“等我实习结束后,想考郑州或是北京的大学,学心理学专业,当心理咨询师,那样就能挣到更多的钱。”
大姐说:“那就靠你的奋斗了,大姐可能再也帮不上你的忙了。”
大姐的口气充满了伤感,他虽然听出来了,也没在意,然后她就回了河南。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当丰望再次收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时,他才得知,大姐回焦作后,喝农药死去了。大姐为他今后的生活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也为自己帮不上丰望而自责,她自己的生活也出现问题,一切让她更加绝望。
得知这一消息时,丰望正给一位客人推拿,顿觉天雷轰顶,不顾形象也不顾客人反应,蹲在地上大哭起来:“你怎么这么傻,你让我替你死呀,你为什么自己去死?我是个没用的人……”
他在那时觉得,原本坚实的大地突陷沼泽,他深陷其中,快要窒息死了。至亲离世的痛苦,时刻袭击着他的头脑,让他无法集中精力。他决定不再实习。2002年6月5日下午,丰望坐上火车,回到修武郇封村那个用土坯垒起的、简陋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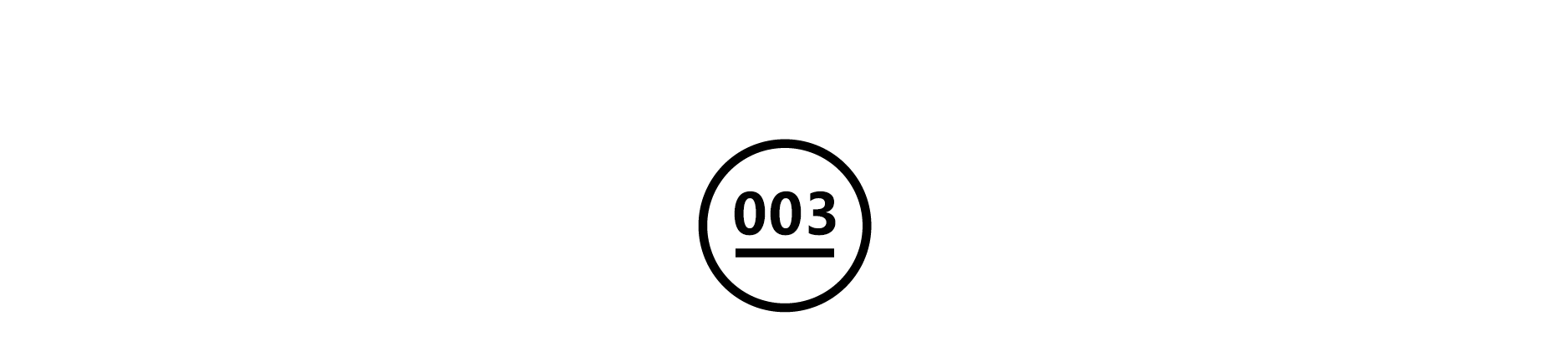
再出发
丰望回到老家后,忧郁得像腊月里阴沉的天气,这样的心绪延续了一年。他曾经考大学当心理师的计划,因为大姐的去世碎了一地。他常能听到老父亲的唉声叹气,尽管他不说什么难听的话,但丰望也明白,父亲也年近八十,自己不能再啃他的老。他这才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决定到焦作闯荡一下,改变一下阴沉的气象。
他和同学们在微信上一直保持着联系。盲人们用的微信软件是触屏式的,在买手机时会花数百元下载这套软件,手指头就是盲人的眼睛。那天,他听说他在焦作的小学老师目前正在焦作市内开一家大型推拿店。他便给老师打了个电话,还没等开口,老师就大声说,“我正四处打听你呢,你藏到哪去了?一年也不见你,我这正需要你这样的专业人才,明天就来上班!”
2002年十月,丰望一个人拄着盲杖从郇封村搭班车到了焦作,当他穿上白大褂开始为客人推拿时,终于感到自己从阴沉的天气中走进了有阳光的社会,也算在社会上站下脚了。他格外珍惜这份工作,对待每个客人都尽心尽责,一般推拿半小时的他都会延长五六分钟,以博得客人好感,并在推拿过程中分享他在前一天听到的最新的保健知识。客人很喜欢他的这种服务态度,许多人办了数千元的长期卡,就是冲着他的手艺和态度。
这样一干就是八年。他也从一个盲人学生成长为推拿师,甚至在入岗第四年拿到了推拿师的资质证书,工资也逐渐升到了他所期望的数字。
终于,他在职业上有些顺风顺水了,但与初恋的女友却出了问题。女友原是他在洛阳推拿学校的同学,毕业后一直在南方某市做按摩,2000年春天,丰望邀她回焦作一起工作。可恋爱中的卿卿我我到了漫长、艰难、琐碎的生活中,很快就化为泡影。
丰望在感情中的强势,和他在成长中受大姐、母亲、姑姑们的宠爱有关。他认为别人对他的照顾都是应该的,不自觉就有了唯我独尊的大男子主义意识,把女友当成了大姐,对她指手画脚。
失恋让他像失去大姐一样痛苦,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要打一辈子光棍了,这才是他最焦虑的。为转移注意力,他给北京盲人出版社打电话买盲文书。由于他这些年常打电话买书,出版社的人都知道他。巴金、高尔基,加上多年前买的《红楼梦》《西游记》,他一本一本地看,或是听《静静的顿河》等有声书。半年后,他终于悟出一个道理,生活就是要奋斗,爱情就是要奉献,即便在社会上拼搏得遍体鳞伤,也要为爱人、为家庭挺身而出,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懂索取。
他想起大姐在北京对自己说过的话,说他业务上还需要再提高,以往几年里他虽积累了一些中医理论,但还需要加强对西医的学习。于是他又买了盲文版的《内科学》《病理学》《药理学》等基础书,和《生物力学》《微生物与寄生虫》等专著自学。
一年后,丰望感觉自己在理论上有了积累,心里也有了底气,便重新回到焦作,准备自己开一家推拿店创业。这时距失恋已过去一年。

“盲目”的爱
2018年初,丰望和同学们在焦作合伙开起了推拿店。但由于门店选址的问题,有段时间推拿生意很不好。于是,他便在QQ上搞起副业:教不会操作电脑的盲人如何上网。因盲人的空间感较差,常常不知道鼠标在哪,用的也都是组合键,丰望给他们讲具体的操作细节。
这天,有一位女生顾客在网上问了他许多问题,他俩聊得很投机。“几天后,我有了一种半天不聊就失魂落魄的感觉,就直接向她要了微信号。她很大方地给了我。”她叫阿莲,湖北荆州人,原本有正常视力,可1987年,她从武汉船舶学院毕业那年,患上了‘一过性’失明症。起初是左眼失明,后来是右眼,然后是双眼失明。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眼病,2014年,阿莲完全失明。
丰望大胆地向阿莲表明,自己有想跟她交男女朋友的意思。没想到,她答应了。“看来她也是在寻找男友。我俩属于网恋,网络成了我俩花前月下的地方。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和她聊天。”她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就像皲裂的大地饱饮暴雨的甘露。丰望第一次明白了爱情的滋味。

阿莲未失明前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有天我在微信里随口说,我要去荆州看她。她肯定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想表达感情,郑州至荆州这么远,没人护送怎么可能成行,当即她就将了我一军,她说可以呀,那你就一个人来吧。然后又强调了一遍,那你就一个人来吧!当时我特别惊讶,哪有这么大方的女生?”丰望不明白她是开玩笑还是真诚邀请,反倒一时没了主张,随后几天,他想了又想,她两次说让他一个人来,肯定是想考验他有无远行的能力,于是决定,去荆州看望她。
2018年8月,那时正是豫北最炎热的季节。丰望没告诉阿莲他的计划,自己偷买了郑州东至荆州的高铁票。在买票的同时,他向郑州东站打电话预约申请了重点旅客乘坐高铁的帮助服务,“他们派人按我到郑州的时间和地点来接我,还开玩笑说,你视力不好,走这么远的路,还要带着大包小包,去相亲啊?我想,一个人的幸福肯定能被别人看出来,就告诉他们,还真是相亲。”丰望在祝福声中被送上去荆州的高铁。
“这个社会有很多善良的人,一路上,有人见我需要帮助都会伸手。坐公交车也很顺利。几经辗转就到了阿莲家附近。”他打开导航,用盲杖摸索着前进。当他准确无误地来到她家门口,预备举手敲门时,却被内心涌出的激动冲得一哆嗦,不自觉放下手,平息情绪。他想着见到阿莲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想好后又举手,可还是没敲。“我发现自己的喘息过快,做了几次深呼吸才去敲门。”
是阿莲开的门。当丰望说“我来看你来了”这句话时,他虽看不到她惊讶的表情,但从她的喘息声中能知道,她很意外。阿莲花了点时间才确定,丰望就站在她面前,故作镇静地说“你真的一个人来了!”同时,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肩膀。丰望明白,她这是在摸他的身高。阿莲这才把惊讶换成一种平静,说“你到底还是来了!快进屋!”
进了屋,她又摸了摸丰望的脸,“我这才确信了她在微信上说的,她是全盲”。
丰望把带来的焦作土特产一一拿出来,她马上给正在上班的哥嫂打电话,说焦作的丰望到家了。丰望早在微信上听她说过,她父母已去世,她跟着她哥生活。她哥嫂回来后见他一个人,迷惑地问“你一个人来的?”口气充满了不信任,又强调了一句“没人送你来吗?”丰望淡淡地说,“多年来我就是一个人走南闯北的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
当晚,他住进离她家一公里的连锁酒店,第二天早上在附近小吃店吃了早餐,又多买一份,给阿莲带过去,在陌生的环境里,他都是用盲仗摸索道路。他俩聊到中午,丰望邀阿莲外出到饭店吃饭,却被她拒绝。像她这样后天失明的盲人没有空间感,不像丰望这样的天生盲人,有平衡感。连续三年,阿莲竟然没出过一次家门。平时吃饭都是靠哥哥,或是亲戚们帮忙做饭。
“我见她这样自闭,反复给她讲,一定要融进社会、不能被生活淘汰这类鼓励的话。还说,你看我,到哪都可以自由行走,你要不相信,就和我一块下去感受一下,看看我在你家前面的街道上是怎样行走的。她这才第一次跟我到了街上。我们去一家饭店吃炒粉。我能感觉出她的兴奋。”
后来五天里的每日三餐,都由丰望去街上买回,再送给阿莲,然后坐在她家聊天。第六天一早,丰望要返回焦作了,这也是向她哥展现自己有无远行能力的好机会。哥哥主动帮他买了客车票,看着丰望上车,当天就回到了焦作。

图源:娄烨电影《推拿》
在他离开阿莲那天,她用无意的口气刻意说,她想离开这个家。这话让他明白她在家里的处境。到焦作后,丰望立即在微信里商量起接她来焦作的事宜,同时开始找房子。
丰望的二姐听说此事,陪他又去了一趟荆州,请阿莲的亲戚们吃了顿饭,正式确定丰望和阿莲的关系。“她哥把我和我二姐的身份证拍了照片,我知道他们怕我诈骗,然后他陪阿莲来到焦作,看了我租的房子和我的推拿店,才放心离去。”
两人同居后,每天早上7点前,丰望吃过早餐,带着阿莲去店里上班。一个月后,丰望尝试让阿莲自己摸索着一个人走。但有天正好下雨,阿莲站在十字路口将近一小时,不知去向,发着呆,当丰望找到她时,她失声痛哭。晚上趁丰望做饭时,她独自在楼下的院里徘徊许久,差点不辞而别坐火车回荆州。她为不能很快融入崭新的生活而发愁。
“她后来说,她觉得我为了她来焦作,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她要是真走了怕我不能承受。心想既然如此,那就结婚吧!”
2019年12月25号,阿莲和丰望在焦作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丰望在河南焦作一家推拿店给顾客推拿(受访者供图)

丰望在河南焦作一家推拿店给顾客推拿(受访者供图)
丰望在给我讲述他的故事时,一直坐得笔直,挺着上身一动不动,我看他很累,就说:“你把身体调适到你觉得舒服的姿势坐着,不用这么正式。”他却说:“这样的礼仪还是必须有的,我是个很注重礼仪的人。”他这话让我想起介绍我来找他的李玉萍对他的评论:“许多盲人由于看不见,穿戴也就不讲究,自然就邋遢,不是他们不想注意卫生,而是看不见没法讲卫生。但丰望却是例外,爱干净,皮鞋每天早上都要刷一次,穿的衣服从来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关键是他还娶了个老婆,这和他有文化、懂业务、素质较高也有关。”
丰望自己开的推拿店一年多就关门了,经营和管理是个难题,他不会经营,也觉得不会的东西硬做是自找苦吃,索性找到如今的老板李总,焦作的推拿圈很小,李总早就知道他,就让他来自己店里干活了。这不,一干就是四五年。
阿莲走的却是盲人的“第三条路”——在家待着。她如今生活在丰望的老家郇封,丰望每月回郇封看她。
我问丰望:“你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说:“盲人没今后,不知道今后的打算。有句老话叫随遇而安。”
这时一位顾客走进店里,点名要他推拿,他说这是他的老顾客,不敢懈怠,马上停止对我的讲述,进入工作状态。我站在一边看着他工作。这时已是晚上近十点,街道上的灯光早已亮了起来。
(除丰望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文中图片皆获丰望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