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霁安丨评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
摘
杂书是明代图书市场上流通较为广泛的一类书籍,内容涵盖猜谜、戏曲、农桑、法律、蒙学等诸多内容,“凡人世所有,日用所需,靡不搜罗包括之”。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即以杂书为切入点,展开对明代书籍史的论述。该书创造性地发明“识书”概念,以回应阅读史中识字率的议题,同时熟练地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书籍史研究结合,展现了晚明动态的文化与社会。
关
稗贩之学;杂书;识书;书籍史
作
蔡霁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2020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发于。
书籍史是近年研究的热门方向,它发端于西方,20世纪80—90年代传入中国。这一新研究取径在国内首先要面临本土化问题,即是否可以采用书籍史视角研究中国历史。在欧美书籍史学者笔下,传统中国惯用的雕版印刷,犹如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的象征,意味着在文化领域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进行中国书籍史研究无疑可以反驳这一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在实际研究中,学者多把目光聚焦于明清,尤其是晚明。这一时期由于技术的进步、原材料获取的便利、识字率的提高,书籍日趋大众化。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就诞生在这一背景下。作者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明清书籍史、文学文化史及人文地理,正是浸淫于中西两大文化环境之故,才有了如此精彩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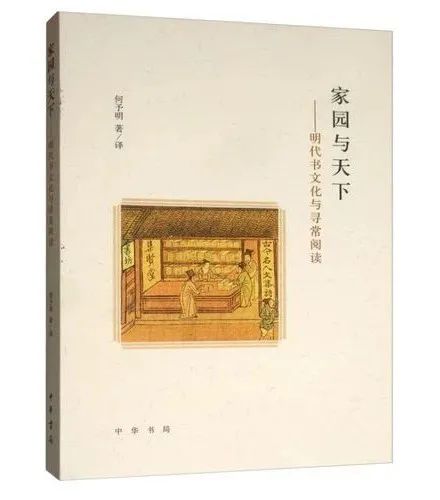 本书由绪言、正文、结语、附录、参考文献五部分组成。绪言从四库馆臣对明书的不屑说起,指出“明人刻书而书亡”“明人不知刻书”,刻书过程中荒谬绝伦,抄撮庞杂,乃是“稗贩之学”。作者认为,若转换视角,“这些类书……却是最能体现其文化活力的刻本书籍类型之一”“不屑之词本身恰恰为我们了解明代书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线索”。本书正是从“稗贩之学”入手,一是借“稗”字对杂芜不经的明代书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二是借“贩”字了解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诸过程。以下四章分别关注某一类书籍或某本书籍,试图了解它们产生及意义生成的过程,以此构建明代书文化的图景。
本书由绪言、正文、结语、附录、参考文献五部分组成。绪言从四库馆臣对明书的不屑说起,指出“明人刻书而书亡”“明人不知刻书”,刻书过程中荒谬绝伦,抄撮庞杂,乃是“稗贩之学”。作者认为,若转换视角,“这些类书……却是最能体现其文化活力的刻本书籍类型之一”“不屑之词本身恰恰为我们了解明代书文化提供了有力的线索”。本书正是从“稗贩之学”入手,一是借“稗”字对杂芜不经的明代书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二是借“贩”字了解书籍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诸过程。以下四章分别关注某一类书籍或某本书籍,试图了解它们产生及意义生成的过程,以此构建明代书文化的图景。第一章聚焦杂书《博笑珠玑》。全书由行酒令、谜语、笑话、诗文等编排而成。因《博笑珠玑》内容庞杂,作者节选行酒令、《古文珍宝》、集中集《皇明诗选》进行解读。行酒令要求行令者依次赋诗,内容主要是典故诗书,既博涉经史子集、蒙学读物、戏曲,更涵盖法律条文等,要求行令者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通过对这些权威文本的断章取义,并进行情境重构,就生成了另类的意义。“古文”是《博笑珠玑》中常使用的概念,由于现代读者与明清书籍有天然的距离感,难知其义。“古文”实指《古文真宝》,成书于宋末元初,在明代书籍中地位重要,曾流传至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影响力经久不衰。围绕《古文珍宝》,明人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文坛“古文”的概念。“前七子”以复古为旗帜,号召改变“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明代文风,提倡“文必秦汉、诗必汉唐”。《古文真宝》与之相反,反映的是一种迥然相异的古文世界,它通俗、日常,甚至低俗,又广为人知。正是这样一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书籍,上至万历皇帝、下至寻常士大夫均会阅读。集中集是明代坊刻书中的常见形式,它反映了编写者力图将尽可能多的材料往一本书中塞的努力。书籍每页分上下栏,各栏文本独立,为集中集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条件。《皇明诗选》位于《博笑珠玑》卷4上栏,内容自上而下,展现了从宫廷到民间的明代生活图景,语言简洁通俗。本节以《太祖晓行》与《正德游宣府》为例进行解读,展现通俗与雅正之间的对话。整章告诉读者,明代杂书是如何通过戏谑的方式与正统书籍进行勾连,形成读者与天下的连接。
极具商业特性的戏曲杂书是第二章讨论的重点。这类书为吸引读者眼球,从形式、内容、书名、书题等方面进行了全新包装。戏曲杂书页面设计通常采用三节版,上栏下栏是戏曲,中栏杂收笑谈、酒令、俏语等。“一页多栏的技术处理,将阅读经验重塑为一种视觉上的愉悦与新鲜感。”书名的选定以激发读者的购买欲为目的,多强调新刻或是曲调新、腔调异。书题需醒目,最好能从戏曲中感受到对人生的极乐追求,引发多重想象。戏曲杂书中栏的创用是本章关注的重点,如加进中栏的方情密语。它是一种市井隐语,流行于风月场所。这类语言与官方文化有鲜明的对立感,尤其从官员被称为“孙”“姑儿子”中看出对官方文化的不屑。将它放在戏曲杂书中和戏曲一道构成了一个与官方迥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充满了戏谑、市井情趣。日用类书同样会出现在中栏。它相当于一本百科全书,对地理、时令、人际关系等方面有诸多介绍,这些书的书名最后都有“不求人”三字,告诉读者买了日用类书,日常做事、行为准则毋需向人低三下气地讨教。日用类书出现在戏曲杂书中显然是出于商业盈利的目的,买了一本戏曲书,同时能获得一本生活指南。全明地名亦是戏曲杂书中出现的一个文本,这些地名先列出两京十三省名,再按府、州、县依次列出,渐渐地还包括各省土产、水陆路程,表现了明人对人文地理的关注。戏曲杂书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展现帝国气象的“天下”框架,也将读者与其他方式的空间感知,如地方知识、区域文化传统等,和身份认同更强烈地联系起来。
第三章围绕雕版印刷的再生产过程展开。所谓再生产是指明代刻本书籍复制过程出现的异变现象,即书籍出于环境、印刷目的的不同,在印刷过程中发生了改变,具体表现在使用插图、分栏等,这构成了“文本获取意义的过程中的活性成分”。晚明作曲家王骥德用“机熟”概括这一变化,如今已成为书籍史家的关注点。本章通过六本书——《玉谷新簧》《妙锦万宝全书》《田家乐》《罗江怨》《西厢记》《藩王来朝》各书版本变化,试图证明这一再生产过程。以《玉谷新簧》与《西厢记》为例。《玉谷新簧》原名《玉振金声》,这一题目意指文章道德之胜,传统的礼乐教化构成本书主要内容。经过雕刻名工刘次泉的翻刻,本书外貌大变。封面扉页图变成了男女相戏之景,其中琵琶、太湖石、男女身躯均象征色情世界,标题中“玉”谐音“欲”,“调簧”含戏谑之意。经过一番改造,《玉谷新簧》从传统礼教走向声色犬马,改造迎合了市场需求,刺激了图书生产和消费。《西厢记》中“张生跳墙”显示出“刻本中传播的文本与图画在互相指涉、复制和异变所构成的意义网络以及其营造出的阅读环境中参与、干预文化流行样态的生产与消费,并为读者提供了个体阅读的多样可能性”。得益于《西厢记》的知名与广为流传,戏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能引发读者无限遐想,于是“张生跳墙”一幕中出现的崔莺莺、张生、红娘、书房、花园等在文本再版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如崔时佩、李日华版在跳墙一节中加入了莺红下围棋。在《摘锦奇音》中收录的《张生跳墙失约》中,张生遭到红娘的多次为难,还出现大段对白。另外,各改编本出现了张生跳墙的插图。环翠堂本《西厢记》中墙体高耸如云,闵奇伋本《西厢记》采用套印技术,在插图中呈现出三个张生:墙上、地上和水中,效果极佳。文本和图画交错叠加,“加宽了文化记忆的色域”,更体现文化再生产的力量。
第四章着眼于明代流行书《臝虫录》的生产传播史。《臝虫录》以国为单位,对亚洲、中东、非洲、欧洲等地之国进行图文并茂的介绍。书以“臝虫”为名,有天朝上国对四周居高临下的蔑视,蕴含民间对化外之国的戏谑。本章以《高丽国》《日本国》《匈奴》三条目的编纂为例探讨《臝虫录》的编纂过程。《高丽国》条中的记载多源自《宋史》,书中将高丽历史追溯到武王封箕子,意指其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宋距明已远,这一条目早已过时。为满足当下读者对域外的了解和杂书盈利的需求,编者对此条进行更新,采撷《北史》《后汉书》中内容,形成《高丽国》条杂糅各史的特征,新加内容又因带有异域气息格外吸引读者。《日本国》条目采用了中古史书《旧唐书》的叙事框架,比《高丽国》条少了许多想象,这主要由于明代倭寇之乱让编写者更注重中日实际往来中的不快与战争。《匈奴》条是野史的写作风格,内容自谓引自《元朝秘史》,“秘”即不公开,实际上《元朝秘史》确实不易在市场中得见,多出现于儒臣私宅中。对有猎奇心理的读者而言,自然充满好奇与想象,可见编写者深谙读者心理和市场需求。《臝虫录》在明代广泛流行,不仅引起士大夫关注,琉球使者对它也十分熟悉,意味着它在海外有大量受众。作者对本书流行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臝虫录》以日用类书章节形式的传播非常重要,产生了精彩的副文本,如序与卷首图。序言根植于科举应试中的基本程式,熟悉感扑面而来。卷首图来自职贡图,体现明代天朝上国的威严,表达读者的自我认同和对四夷的蔑视。通过诸多技巧性操作和对市场、读者的分析,《臝虫录》得到了广泛传播。
结语从一幅《货郎图》谈起。图中货郎向三位女性售卖扇子。货郎在文化传播中起着中介作用,他通过售卖扇子,隐喻售卖外面的世界。扇子又分团扇、折扇,折扇在明代社会是作为雅具而存在的,曾风靡一时。团扇是南方女性常采用的器具,随着折扇的流行,团扇逐渐式微。货郎到乡村兜售两类扇子,给买家提供了选择的机会。他作为文化中介联系了都市与乡村社会,引导了消费者的需求和品味。将以两类扇子为代表的广阔天下带到了家园中,成为消费者的居家日常。
书中最具创造性的概念是“识书”。研究阅读史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识字率。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罗友枝(Evelyn S.Rawski)做出了开拓性讨论,她以一百字左右为标准计算得出结论,在18—19世纪的中国,有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30%—45%,女性只有2%—10%,据此便可分为识字者与非识者两个群体。有学者对一结论提出质疑,然无更令人信服的研究出现。在讨论明人阅读时,识字率问题不能回避。同时,这也是要回应目前文化史研究中提出的各种二分法,如划分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许多书籍的受众并非可用这样的划分方式来涵盖,彼得·伯克曾提出“双栖文化”的说法,意指文化、书籍具有广泛、杂糅的受众,以此挑战二分法。具体到中国书籍史领域,作者发明了“识书”。
“识书”意为认识、懂得这个事物。详而论之,“这个概念一方面涵盖了儒士对古今文本的精审掌握这样的学识,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各种‘知道拿到一本书后该怎么办’的见识,而有这种见识的读者未必就有对阅读技能的完全掌握,甚至可能是不识字的(比如绘图本的一些读者)”。这一概念包含原有的士大夫、读书人,并容纳一些仅仅识文断字或者目不识丁只看得懂图画的一般人,甚至涵盖将书作为器物使用之人。“识书”还有更深刻的意涵,以它为切入点,将书籍的物质性这一书籍史的重要话题纳入到本书研究中。因为书籍中的图画、装帧能吸引读者与之互动,如图像的变异、三节版的设置等。
与此同时,“识书”还和本书研究对象有关。本书聚焦明代日用杂书,征引《中国日用类书集成》中的书籍包括《新刻天下全书博览不求人》《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等。可以《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为例了解书中内容。该书由著名书商余象斗出版,共43卷,书中内容多非原创,是从许多书中节选拼凑而成,如目录中的律法门,正文中名为律例门,这反映了明末日用类书出版的现状,即为了能迅速获利,便以牺牲书籍质量为代价。该书另一特点是,图像极多。43卷中仅律例门、民用门、子弟门、养生门、卜筮门、僧道门无图,其他门类多则页页有图,少则每类正文前附有一图提示内容。由此可知,图像成为日用类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以识字率衡量读者,似会遗漏许多不识字却识图的人,尤其书中的农桑门、营宅门只需看图即可,可见作者深刻洞悉明代书籍文化的一些关窍。
本书另一特点是各章采用不同的研究路径。前两章从书籍的物质性入手。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认为,书籍的物质形式决定了阅读方式。《博笑珠玑》和戏曲杂书多采用三节版设置,每栏独立成书。这类书于一本书中给读者提供几类书籍阅读,达到购一本而能阅多本的效果。戏曲本身融合了俚语、方言、酒令、人文地理等内容,与中栏内容互相参照,能促进对戏曲的理解,使杂书的杂并不突兀。一页多栏的技术处理,将阅读经验重塑为一种视觉上的愉悦与新鲜感。晚明戏曲杂书的流传创造了一种巧妙的文本地理,将书页转为雕印技术、视觉印象、剧场与社会表演等各种实践活动之间互相碰撞、彼此影响的一个场域。第三章中的图像分析是艺术史的常用方法。艺术史家多对画谱、图像感兴趣,其研究关注书籍物质性的一面,只不过多侧重纸张、插图颜色等,对书籍内容或副文本缺乏关注。本章在关注图像变异之时,对书中扉页、书名的挖改进行了文本分析,有效弥合了艺术史研究与史学、文学研究的罅隙。
第四章是书籍的交互史研究,这是近年书籍史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交互史关注的是两个甚至多个文化与社会之间有意无意间交流的历史,聚焦的是真正存在直接联系的各个主体。交互史现有研究较多,如《东亚出版与社会》杂志曾设有《中国小说在近代世界:〈好逑传〉在韩国、欧洲与日本的阅读》专刊探讨《好逑传》在日本、韩国、欧洲的阅读与接受。东亚之外,大卫·卡特(David Carter)探讨了19世纪末澳大利亚书籍进入美国市场的轨迹,显示出澳大利亚的出版业绝非仅仅依赖英国,文本、作者具有跨越殖民、国家与帝国的非凡流动性。《百年孤独》《骨人》在全球背景下取得的成功证明了不管在过去还是当下,文学代理人、出版商以及其他为书籍创造市场的参与者的重要性。在书籍传播过程中,只有迎合接受者的特殊品味、兴趣与偏好,才能使文本适应读者需求,达到在地化目标。同时,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共同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
当然,书中存在一些可供商榷或有待补充之处。从杂书受众看,上供帝王一乐,下供四民日常之用,几乎涵盖了所有群体。现有对它的研究大多认可这些书在明清之际流通全国,受众面广泛。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杜新豪认为,晚明日用类书的生产刊刻绝大多数在福建建阳,其销售区域集中在以江南地区为核心的南方地区。换而言之,尽管读者受众广泛,却存在地域性。他以日用类书中的“农桑门”为例进行论证。豆类作物被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可能是这个时期豆饼被视作一种重要的肥料应用在江南农业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蚕用浴法,唯嘉、湖二郡”,可见日用类书中提及的技法是嘉湖平原的独特技术,间接佐证了晚明时期日用类书的主要销售市场是以嘉湖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又如花卉产业、蔬菜种植方法,均以服务江南为主。其他门类亦可证之,明代好讼之风以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为甚,在很多地方和明人笔记中都有关于好讼之风的描述。江南地区在明中后期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说。好讼之风的盛行,促进了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明代的综合性通俗类书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需求,辑录了大量关于法律特别是诉讼的知识,明后期几乎每一部综合日用类书中都设有专门介绍法律知识的门类,或称“律法门”,或称“状式门”,“体式门”“文翰门”中也有关于诉状写作常识和技巧的内容。商品经济发达使得纵欲之风兴起,本书附录二以《嫖赌机关》为例,介绍明代青楼指南。其中对狎客的指导和告诫处处以苏样为目标。所谓苏样,就是以苏州地区为中心所代表的文化、品味和情趣。明代中后期的苏州虎丘确是娼妓发达之地,《玉谷新簧》中太湖石、勾栏、竹木可证之。至于日用类书中的“琴学门”“棋谱门”等,不仅与色情业兴盛有关,想必也与当地如常熟虞山琴派的传播大有关系。
这些类书的价格多有不同,每册从三钱至一两不等。如《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此书34卷8册,定价银一两正,这应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最为真实的日用类书价格。这个价格相对而言是较高的,不过这类书籍仍被不断刊刻,更可见士农工商对此书的需求量较大。明中后期,商业繁荣,形成许多新兴的市镇,出现大量的市民阶层,新思想奔涌,对书籍的种类和数量要求甚于前朝,此时雕版印刷技术趋于成熟,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出现新兴城镇最多的地区是江南地区,市镇发展最引人注目。以苏州为例,明中后期,苏州下辖吴江县弘治年间仅二市四镇,嘉靖年间增为十市四镇,明末又增为十市七镇,增长一倍之多,嘉定县亦是如此,致使苏州税粮名列全国第一。随之兴起的市民阶层,成为购买日用类书的主力军。这些人未完全脱离农桑,又想享受都市生活,杂书的编目正迎合了他们的需求,价格在他们的承受范围内。然而,这些杂书为迎合市场需求和牟利,品质之差成为了清人口中的稗贩之学,正如贾晋珠(Lucille Chia)所说:“就大多数建阳本的内容来看,我们很难通过翻阅它们来判断当时哲学和知识界的趋势,以及医学和技术上的新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商榷有吹毛求疵之嫌。实际上,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所言:“她(指本书作者)对明书的内容、版刻特征、话语体系和那个时代的历史框架做出了缜密分析,下笔之处言之有物,眼光独到。要想做到这一点,没有对中国古籍长期研究和对东西方两大学术话语体系的精确把握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本书足可谓中国书籍史研究的佳作,它的学术价值和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原标题:《蔡霁安丨欧美中国书籍史研究的佳作——评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