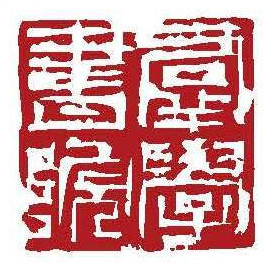陈冲:我的姥姥

题图:演员陈冲(右)与她的姥姥史伊凡
史伊凡(1908-1989),原名史人范,江苏溧阳人。1922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与吴健雄等同学。1926年积极参与北伐战争,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麾下任职。1927年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翌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曾加入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奔赴抗日战场。此后曾自费举办现代医学出版社。1935年12月,与史良、罗琼、沈兹九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1938年赴伦敦大学留学。1949年后任上海科技出版社编审,主要从事医学卫生科普出版工作。著有《科学饮食法》《吃的科学》,译有《苏联区级医务人员手册》等著作。
我的姥姥
文 | 陈冲
我从六岁开始跟姥姥同屋,一直都喜欢和羡慕她那股潇洒劲儿和享受生活的能力。我记忆中总是有很多年轻人来找姥姥补习英文、修改文章或者闲聊,有时聊得高兴了她还点上一根烟。姥姥是一个让年轻人喜欢的老人,有许多忘年交。
文革期间姥姥下放到“五七干校”,虽然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她的信上讲的都是她找到了什么上海吃不到的东西,我记得让她特别兴奋的好像是一种叫臭芦梗东西。她在干校跟人说,毛主席是“两论起家”,我是“两精起家”(味精和糖精),结果让人给抓了小辫子,批斗了一通。姥姥没跟我说她挨斗的事,这是她的个性,说这种倒霉事有什么好玩儿的?挨斗的事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为了让我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几十年以后,也是从母亲那儿知道,我的那位热爱生活的姥姥原来在文革初期挨整时曾经自杀过。我至今都无法将那种悲哀和绝望安在我心目中的姥姥身上。

陈冲在姥姥怀中

陈冲与姥姥、父母
从干校回来后,姥姥还停着职,不能从事她热爱的出版事业。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政治待遇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但是姥姥却决定乘没事干带我去旅游。那个年代没有人旅游,只有人出公差。我妈觉得很诧异,我却兴奋得跳起来。当时家里钱很紧,姥姥和妈妈又都不太会过日子,到了发工资前几天,总是缺钱买菜。为了不影响家用,姥姥取出她全部的积蓄,就带我上路了。那时我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姥姥为我请了两周假,用的什么借口我不记得了。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写南京长江大桥的,姥姥就把大桥作为我们的第一个景点。站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我感受到无比的骄傲 ——并不是因为建桥的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完成了这座壮观的大桥,而是因为全班甚至全校只有我一个人亲眼见过它。
1977年我主演了谢晋导演的《青春》,78年又拍了《小花》。在那之后,经常会有一些人上门来要认识我。据姥姥说,他们都是“高干子弟”。不管我当时在家或不在家,姥姥一概不让我出面,我总是拿着一本书待在厨房或待在厕所。姥姥照常倒茶递烟,冬天点上炭炉,夏天递把扇子,天南海北地跟人聊。来的人虽然不能满足初衷,走时也不觉太失望,有个把还回来看过姥姥。

陈冲在《小花》中剧照
刚开始留学那阵,我隔好久才能见姥姥一回。那个年代,如果从美国回家探亲,总是要带一台电视机什么的,那些所谓的“四大件”。可是姥姥不要大件的,也许是不舍得我花钱,也许是真的对大件不感兴趣。当我坚持要带东西给她时,她让我带一块美国最“臭”的奶酪,姥姥喜欢一切发过酵的“臭”食品:臭芦梗,臭豆腐,臭奶酪。还有一回,她问能不能带一个有点儿波浪的假发套。最让我惊讶的是有一次姥姥居然让我为她买一个在前面扣扣的文胸,让我在电话里开怀大笑好一阵。在美国拍戏后,我有了足够的收入频繁地回来看她。每次回家,我总能从楼下就看到姥姥已经带着头套趴在钢窗框上等着我。
我在世界各地出外景都会在电话里告诉姥姥我的近况,她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姥姥是一个富有强烈好奇心和探险精神的人,现在回想她一定很向往能到那些异国风情的地方去看看。当年护照签证都是非常难拿到的,如果我邀请姥姥,她未必能去成。但是,我的遗憾是我没曾邀请她。
1989年我到澳洲拍戏,到了就给姥姥打了个电话。跟以前一样,我们嘻嘻哈哈聊了好一阵。但是我渐渐发觉姥姥的反应有些异常,说再见之前我突然意识到她不知道我是谁。挂了电话我大哭了一场,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两星期后我鼓足勇气再打给她一次,跟她解释我是她的外孙女,是阿中的女儿,是陈冲。她笑着说,我知道阿中的女儿是谁,是电影明星。其实阿中比她女儿漂亮多了,倒是女儿当了电影明星。仍然是那位健谈的姥姥,但是她挣扎在失忆深渊的边缘。
最后一次回家看姥姥时她已经得了胰头癌,我陪她一起到医院。有些检查的过程是痛苦的,而且缺乏尊严,姥姥不想做。她不停地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最后跟我说,你让他们停下来。我真想跟医生们说别查了,我们要回去了。但是我没有,我轻轻跟姥姥说很快就会结束的。不幸的是,检查结束后医生让姥姥马上住院。带她回家拿生活用具时,她待在房间半天不肯走,说还要再想想有什么东西忘记了。住院当晚姥姥就动员同病房的病人一起逃回家,护士们只能把她的鞋藏起来。
手术后没两个月姥姥就去世了,她没有能从医院回到她心爱的房间,我也没有在她身边。也许当年真的应该让姥姥留在自己的屋里,也许少活一个月,也许不,但是那是她想待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夜梦见姥姥,有时梦里的姥姥生动鲜活到跟真的一样,我醒来后要好几秒才悟到刚才那只是梦。
我每次回上海跟老朋友们聚会都有人会提到姥姥,我出国后朋友常去陪姥姥聊天,他们每个人都有几段姥姥的故事说来分享。也是在朋友那里,我慢慢知道一些她年轻时代的事。小时候姥姥念的是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到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教育。
现在回想,姥姥带我去南京的时候,我们的确去了金陵女子大学的旧址,也许姥姥不想让她的个人历史给我带来政治包袱,所以没有提及她的过去。姥姥还参加过北伐,1932年“12.8”事件爆发后,她加入了上海医学院组织的第四救护队,奔走在抗日战场上。留学英美回国后姥姥用自己的积蓄和稿费,一个人办起了一家现代医学出版社,外公则利用国外带回的微型胶卷文献资料先后写成了《磺胺类药物》、《青霉素和链霉素》、《现代药理学》等书,这些书填补了国内医学界、尤其是解放区医学方面的空白。1942年,姥姥还随中国远征军在中缅边界当过英文翻译。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姥姥是怎样遇见外公的。姥姥是当年的新女性,跟外公并不是家庭包办的。外公出国深造,姥姥把两个幼小的女儿留在战乱中的国内,跟他去了。如果不是自由恋爱,不是那么喜欢外公,姥姥应该不会这样选择的吧。
THE END
原标题:《陈冲:我的姥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