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单位大院里遭遇讹诈风波|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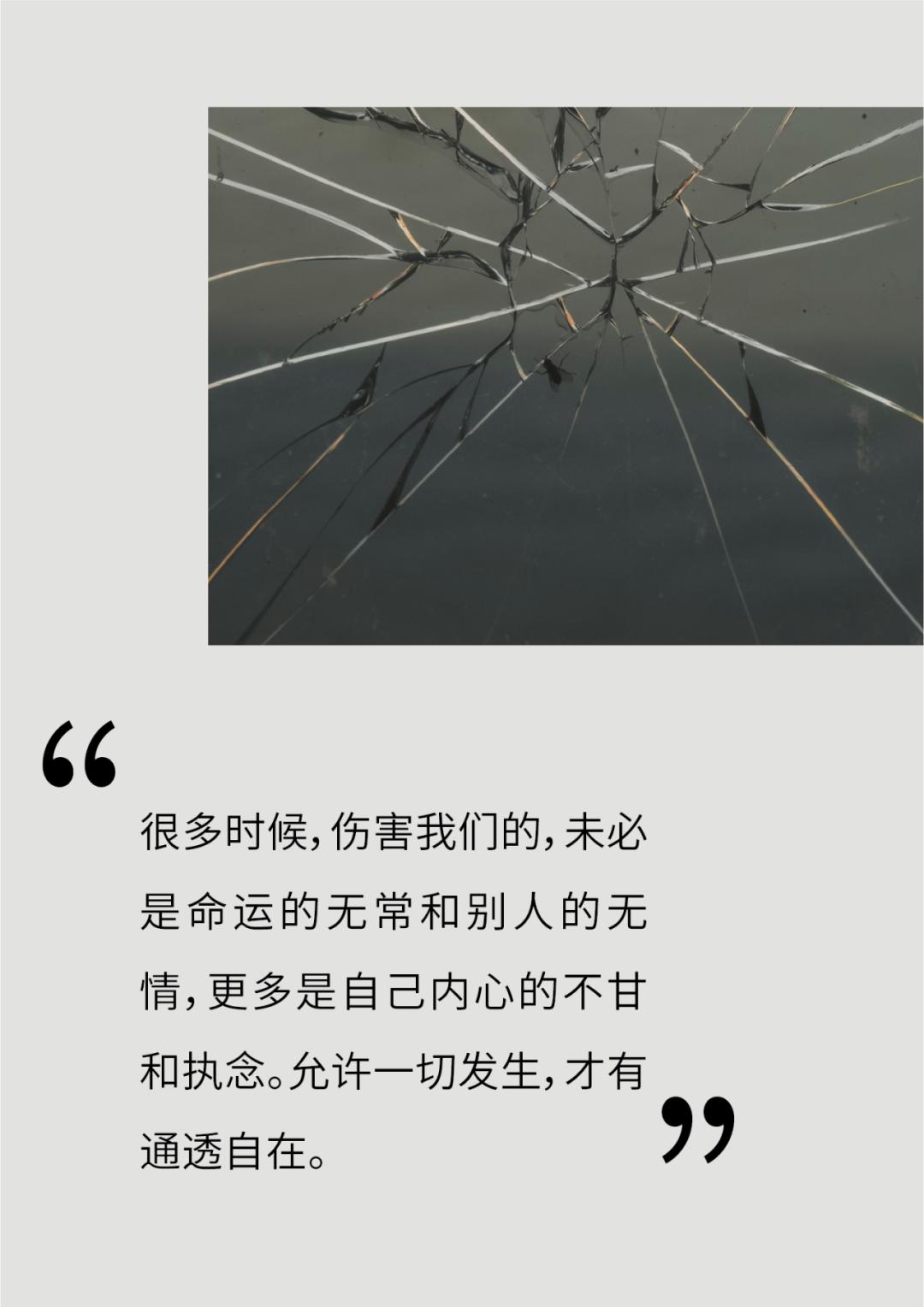
作者|曲奇
编辑|童言
灰蒙蒙的大街,灰蒙蒙的天空,灰蒙蒙的房屋,灰蒙蒙的人群,这些我都无暇顾及,因为我心急火燎在赶路,为了把自己安放进售票点前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中。
队伍缓慢挪动着,突然,身边多了个小伙儿,不容分说挤在我前面,我刚要询问,他恶狠狠地蹬了我一眼,又推了我一把:“怎么了?我就站这怎么啦?”。
一股怒火直窜我脑门,我漂亮地甩给他一耳光,他毫不客气地回了我一脚,顿时两人扭打成一团。身边人似乎见怪不怪,继续排着他们的队。
......
我气喘吁吁地醒来,咳,原来只是一场梦。一场经常出现的梦。
还好,只是一场梦。
但,暴力和冲突,在我的生活中很少出现的主题,为什么却常在梦里遇到呢?
我咨询过心理老师,她说:“梦境中人和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
“愤怒。就像有一团熊熊怒火在心里燃烧。”
那这个愤怒从何而来?

我生活在一个内部单位大院,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忙于工作,孩子相互认识,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干“坏事”。这个大院里除了办公区,还有大片家属区和活动区,住了近千户人家。生活设施也很齐备,有图书馆、游泳池、文化活动中心,生活服务超市等等,人员多而杂。孩子们可以互相串门,尽情撒欢。在外人眼中,大院长大的孩子通常比较“野”,对口小学的老师也抱怨:“你们大院的孩子啊,特别抱团,特别调皮。别人刚上一年级谁都不认识,你们倒好,都已经在一起六年了。”
很庆幸,在城市中,我还有这样的空间,让孩子撒野。我的孩子属于放养型,放学后,书包一扔,先到楼下撒欢。小宝正是“七八岁的男孩狗都嫌”的年龄,胆子大,动作猛,脾气爆,平时没少为他操过心。
一个普通的秋日下午,南方的天气还是炽热如夏,孩子们如往常一般在楼下玩耍,傍晚我赶去参加一个聚会,结果中途接到先生的电话:“小宝犯事了,你快回来。”
本来只是孩子们普通的戏耍,没想到演变成战斗,一个不小心,小宝手中玩具扔到了小朋友P的嘴唇上。
事情发生时,现场只有孩子们,小宝躲在一边不敢吭声,P在路边哇哇大哭。围观的大人们越来越多,我们家长才得知消息。P的妈妈先送孩子去了医院,我先生和P爸爸一直在现场了解情况。先生把病历和孩子现场的照片转发给我,看到病历上写着“唇裂伤”,已进行清创缝合处理。当时,我的大脑“嗡”地一声。
匆匆赶回家后,P已经从医院回来。我和先生带着礼物上门道歉。虽然住在一个大院,但是住户太多,我们两家完全不认识。
这是我们第一次处理这类事情。我没顾上回家换衣服,先生就在大门口焦急地等着。我还穿着聚会的旗袍,踩着平日里难得穿的高跟鞋,我悄悄擦掉嘴上的口红,彷佛做了坏事等着老师惩罚的学生。
我们小心翼翼走进P的家门,我尴尬地询问是否需要换鞋,尴尬地放下手中的礼物,尴尬地坐在那个孩子身边,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结。
P的妈妈全程黑脸。在对方灼灼目光烤炙下,我们再三道歉,表示承担所有诊疗费。对方表示再去医院复查,治疗完结后将费用一并告诉我们。
第一次会面还算顺利。没想到啊第二天下午,我就接到孩子妈妈的电话:“我们谈谈赔偿事宜吧。”

第一次交锋,我们约在大院图书馆。图书馆是我选的地点,这里公开又私密,不仅有多个阅览区,还有独立会议室,平时人也不多。
这次我们专门带上小宝一起去道歉,还提前给P准备了一个玩具。
在电话里我已经感受到来自P家凛冽的寒气,于是我们在家把道歉的话演练又演练,把小宝批评得哭了又哭,我把自己也埋怨了一次又一次。
但躲也躲不掉,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对方来的是外婆、妈妈和P。外婆让我挺意外的,浓艳的妆容,很明显的医美脸和一身紧身黑蕾丝裙,那扑闪扑闪的假睫毛自然地加强了我的防备。
我犹豫了几秒钟要不要奉承一下外婆很显年轻,没等我虚情假意的话出口,外婆先开始了表演。
那对精心纹过的柳叶眉拧到一起,浓密厚重的睫毛下方闪出两道凶光,保养得很好的手从精致手袋里取出一瓶药,“啪”地一下拍到桌子上,略带嘶哑的声音大声道:“我告诉你们,我是要吃药的。这件事我已经好几天睡不好了(此时是事发第二天),你们把我孙子伤成这样,我和我女儿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太生气了,我今天倒是要看看是谁对我孩子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我一下子就被震住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该怎么办?吵架是我最不擅长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P妈妈制止住外婆的表演,一脸寒气地步入正题:“今天主要谈赔偿,孩子的伤害以及对我们娘俩的伤害你们都看到了,我已经查过法律条款,这已经达到轻伤2级标准,赔偿起步XX万。你们什么意见?”......
“what?”有这么严重?
这方面,我一直是个神经大条的母亲,我家小宝曾被小朋友用砖头砸破过头,被足球踢到鼻子出血,但我觉得既然是玩耍,这种磕磕碰碰是难免,我小时候被同学摔骨折过,我的父母也没有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
我想到小宝被球踢到鼻子那次,对方家长主动联系了我,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说不用吧,止住血就好了。
那位家长后来专门和我聊起这件事,说,你真的太好了,换其他家长都会不依不饶。
这就是我日常的解决方式啊,孩子都不是故意的,遇到类似事情后,我都会及时与孩子沟通、分析,鼓励孩子思考下次如何避免危险,如何做得更好,从而将风险变成学习成长的机会。
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不就是关系吗?一定要把对方打倒才算胜利吗?
但是看到对方如此强烈的反应,我有点能理解,也有点不能理解,更多的是在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平时太大意了?
当我的孩子受伤,我怎么都没想过要去找对方家长?
我是不是太软弱了?!
我是不是之前都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所以对方的气急败坏一下把我搞蒙了,也把我唬住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伤情评定,也不知道如何反驳,我和先生只能不停地道歉,希望对方平复情绪。外婆没有罢休的意思:“对不起有用吗?我告诉你们,我给你们录像了,我要发到网上去,下次出门,你家孩子小心点......”听到这些我内心的愤怒、焦灼、不知所措、难堪、沮丧开始翻腾,复杂的情绪最终冻在脸上变成了面无表情。我面无表情地看着P的妈妈,看着那双喷火的眼睛,看着那张变形的脸,也好过外婆的张牙舞爪。
P妈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就要让你们出钱出到肉疼,你们才会体会我的难受,要么选择让同样的伤害出现在你儿子身上,我才能解气。”
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楼下听到了上面的动静,见外婆情绪激动得又叫又跳,要把这个外婆请出去,我才清醒过来,此地不宜久留,谈不拢就走。
我说:“两个孩子都在这里,请不要对孩子造成再次伤害。”
我们不欢而散匆忙离开。
回到家我先安慰了孩子:“没事,爸爸妈妈会保护你。” 等孩子睡后,我独自下楼打电话咨询律师。律师告诉我,伤情等级评定只在于成年的刑事犯罪,对于未成年人伤害,只能进行伤残鉴定,而目前孩子的伤势绝对不会构成伤残。
那天晚上,偌大的操场只有我一个单薄的身影,阵阵秋风,偶尔的虫鸣,秋天真的来了。

打架事件过了一周左右,我在操场偶遇了小P,他独自和小伙伴们在开心打羽毛球。
我先过去询问孩子的伤情,当看到孩子伤口愈合得很好,我稍微安下心来,至少P妈妈原本担心留疤变得像唇裂儿童,这个顾虑可以打消了吧。我甚至不断地往好的方面去想:孩子伤口慢慢愈合和康复,P家长的担心和愤怒也会慢慢缓和吧。
我们主动和P爸爸联系,了解孩子的伤情恢复情况,希望坐下来再好好谈谈,事情发生三周后,我们等来了第二次交锋。
因为有第一次的前车之鉴,我们邀请大院安保部门参与,他们帮我们约定在社区居委会进行。
P家长落座后,冷冷地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沓资料,摆在居委会主任面前。我的心“咯噔”往下一沉,来者不善。里面不仅有普通医院的诊治,还有高端私立医疗机构的修复,精神损失费误工费营养费,包括后续可能的各种费用,一张长长的单据......最后还附上孩子各个时期的照片和受伤当天的照片对比。
居委会主任首先打破沉默,她问P家长:“因为涉及金额比较大,你们咨询过律师了吗?”
没想到一句话就把对方惹怒了,P妈妈直接拍案而起:“凭什么要我咨询律师,难道你对我们的资料有质疑,难道不是应该对方找律师吗?”
主任见她气势汹汹,缓了缓说:“我们小小居委会也没有那么大权限,金额太大可能调解不了。”P妈妈继续叫嚷道:“调解不了你叫我来干嘛,浪费我时间干嘛?”现场一下子就僵在那里。
我拿过那张索赔项目表,觉得有点好笑又可悲,更多的是愤怒。对方是真的不懂法,还是他们明明懂但还要讹诈我们? 很多项目都是对方想当然的诉求,我提出疑问:“这些赔偿有依据吗?依据是什么?” P家长就一直是“我觉得”“我就要”的口吻。
经历第一次交锋后,我从容很多,我告诉对方:“该我付的一分不少,但是想狮子大开口,没门。你们的赔偿数额和我们预想的确实差距太大,我们还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吧,这样对双方都公平。”
又一次不欢而散。

两次交锋下来,我感到心事重重加心力交瘁。交涉的过程会不断在我脑海中闪回,每次闪现,内心就像划开一道口子。先生就比我想得开很多。他安慰我,不过是赔钱多少的问题,没必要这么难受嘛。
而我却忍不住地陷在负面的想法和情绪中,想法就像一条条毒蛇缠绕着我。
我害怕对方的暗箭难防,我害怕孩子间又因为打闹而误伤。我从神经放大条放养式一下子变成小心谨慎看护式,有时觉得自己象一只惊弓之鸟,任何关于孩子伤害的话题都让我心惊,每次走在院子里都让我担心,更可怕的是网络大数据推送,一旦它发现我关注这个话题,就不断给我推送。
我发现我的不安里有很多的愤怒和害怕。这种感受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吗?我一边码字,一边思绪荡漾开来:
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很小开始,家族就有纠纷。有一次,对方人多势众找上门来,对着我母亲就开始拳打脚踢,我当时应该才4、5岁,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死死地抱住母亲的大腿,大声喊道“不要打不要打。”母亲用力甩开我,喊道:“快跑,躲起来”。
脑海中还出现这样一个场景:还在读幼儿园的我,已经自己独自上下学,但是我要时时提高警惕,因为“仇家”会骑车故意在路上追赶着用车撞我,我只能飞快奔跑,躲进附近的商店“避难”。
记忆中,外人都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无所谓,我和外婆在“仇家”砸门破口大骂时,相拥在一起瑟瑟发抖。那种深深的绝望恐惧,刻在我最深最深的记忆里,那时的我就像个溺水的人,恐惧象潮水一样将我吞没。
其实写到这里,我痛哭了一场,这是我这段时间来特别渴望做的事,却一直没有痛哭的理由。
有一次在咨询室,我和老师探讨过一点过往,我哽咽了,但还是节制地表达了情绪,但这次,面对真实的自己,我哭得好开心好痛快,哭完之后好像卸下千钧重担,我感到很平静,很平静。
也许就是因为童年的经历,我比别人更敏感,情绪容易被点燃,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提醒我:小心哦,有危险了。同时敏感也让我能感知到细微之处,对他人的同理心更强,对事情的思考也更深入。
但当时的我实在太弱小,我只能是选择逃离和躲避危险。
长大后,我也一直在逃避各种我“以为的危险”。

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我发现了逃离之外的方法。
我去参加一个心理工作坊,课堂上邀请了某著名高校心理学教授,教授针对现场案例得出一个结论:导致这个案例困扰很大的来源是,中国由来已久的重男轻女问题。
但是,他话锋一转:“中国重男轻女的不是我们男性而是你们女性。你们中国女性.......”当他斩钉截铁地吐出这几个字时,教室氛围些微有些异样,在座的20多人,只有3名男士。所以他也察觉到不妥,转口说:“我们中国女性,不仅是重男轻女的受害者,更是重男轻女的施害者。”
然后教授走近我们,挨个问道:“你认不认同我这个观点?”其他学员都笑而不语。
我旁边一位女生大声回答:“我不是这样的。”这句话象一记响亮的耳光,扰动了整个课堂,本来都昏昏欲睡的教室,瞬间清醒过来。这位教授很惊诧,他指着那位女生,问道:“你确定你不是?”
那一刻,我察觉到内心一股强烈的不满喷薄而出,我接过话题:“教授,我也不认同这个观点。”战火成功地燃烧到我身上,教授转移了方向,问道:“你不认同?那请问你有孩子吗?”
“有!”
“多大了?”
我开了个玩笑:“和您家孩子差不多吧。”
教授一愣,接着问道:“男孩女孩?”
我敏感的“杏仁核”开始拉响警报,我猜测教授的话中有话,他想根据我孩子的性别去推断我是否重男轻女吗?我们继续下去会变得难堪尴尬吗?
我不想发生冲突,此刻我只想结束这个话题:“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教授咱还是回归到主题吧。”
教授没有罢休的意味,继续追问。
我为了缓解尴尬,接着开了个玩笑:“您猜?”
“我猜不到。”
“你是心理专家,肯定猜得到。”
“我猜不到。”
当然,我并不想为难他,我就是希望尽快结束我们的对话。
但也许是教授从来没有被如此质疑过,或者他真的很想和我探讨,他选择了继续追击:“你不回答我的问题,说明你就是重男轻女。只是不敢承认罢了。”
那一刻,我好像被逼到了墙角,“太过分了,怼他!怼他!”警报器在身体中持续拉着警铃。
“教授,“我深吸一口气不紧不慢道:”您刚才说的——你们中国女性,不仅是重男轻女的受害者,更是重男轻女的施害者。这个观点我觉得太绝对了。而且在心理学当中,口误和笔误都是潜意识的反应,请问您是不是曾经受到过重男轻女的创伤呢?”
课堂上本来还有一些窃窃私语,这一刻,突然安静下来。教授一愣,继而有点气急败坏:“我是个男的,我怎么可能受到重男轻女的创伤呢?”
我继续追问:“我记得您刚才说过,当年您生了女儿后,有人要把孙子过继给您当儿子,这是不是一个伤害呢?”
他扶了扶眼镜,喃喃自语道:“这......这算是一个伤害吧,但不能算是创伤。”教授还要保持最后的倔强。
但他终于放弃了和我的论战,开始顾左右而言他。当他刚一转身,我就被身边小伙伴赞爆了:“你说出来我们的心声,你说得太好了!”
“你的气场强过他十倍!”
我从最初被冒犯的愤怒转为打算迎战的紧张,再到平静输出的愉悦,过渡至最后的逐渐冷静,我意识到今天我和教授的对话全都用的“您”,而“您”,并不是我习惯对人的称呼,为什么今天会用到这个听起来尊敬,说出来冰冷的“您”?
愤怒?嘲讽?不满?距离感?
同时我发现这很不像“我”,现场有人笑而不语,有人为我喝彩,他们到底怎么看我?
我和心理老师谈论这件事,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当时参加一个德国老师培训时,老师让大家去表达对课程的意见,有个同学讲了很多不满,事后,这个同学有些懊恼,觉得自己不应该。德国老师说:“中国人比较内敛,喜欢隐藏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但是你的表达让我看到了你的力量。”
我的心理老师肯定了我的感受后说:“要不要去挑战权威,要不要勇敢地表达自己?这对每个人都是抉择,有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攻击性的一面,它也是体现我们有力量的一面。”

我仔细回味老师的这段话,对自己有了更多的理解。
不知是因为幼小的我经历了太多的暴力,还是因为我天生就是典型的“高敏感”特质,我有时像一块”情绪海绵“,能很快“吸收、共情”他人和环境的感觉。
我容易焦虑,容易预知和发现危险,然后做大量准备对抗危险。
我容易愤怒,我会把别人的一些言语行为看成是对我的攻击。
我容易自责,事情发生后我最先想到的是“肯定是我不对,肯定我有责任。”
我容易压抑,我在意别人的感受,有时宁愿委屈自己,而把一些可能破坏关系的话语咽回去。
我容易害怕,童年的暴力深深影响着我,冲突的情景让我不堪。当关系出现紧张或分歧时,我直接缴械投降。
这些情绪反应在工作上的困难时,我会“主动迎战”,因为我相信“我可以。”但在处理人际关系纠葛时,我却没有缺少这样的自信,“勇敢反击”这个行为会直接Pass掉,“没事啊,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没有办法把握好冲突的方向和力度,那就干脆选择做“好说话的人”。
我不喜欢提意见,我不喜欢反驳,我不喜欢说不。我喜欢沉默,我喜欢逃避,我喜欢自我安慰。
但我发现,忍一时,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一步海阔天空。我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平静和安宁,内心压抑的愤怒在梦中向我发出警报——“你要还击,你不要逃避!”
和这位教授的论战,让我看到自己能够漂亮地应对攻击,化解愤怒。锋芒未必就代表伤害,它也能保护我。
和P家长的几次交锋后,我也不断复盘。以前遇到类似事情我容易被激怒,但行动上会回避,最后只落得独自难受。但这次,我选择静下心来,把注意力放在搜集证据上,放在学习法律法规上,放在寻求朋友帮助上,我一直在勇敢面对,积极行动。
当然我还是会焦虑,还是会担心,这些情绪是在提醒我要提高警惕,但我不再急于摆脱它们,允许情绪在我脑海中升腾又落下,允许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造访,我去感受情绪带来的各种感觉,我更细致地观察了我的身体,有时候生气时我乳房会隐隐作痛,这也提醒我,万病源于心,虽然生活中总有不顺心的事情,但要找到让自己心情舒畅的办法,比如做做运动,聊聊天,写写日记都是很好的方式。这次参加三明治短故事写作,就是一次很好的情绪梳理和自我疗愈。
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说过:“在刺激和回应之间,我们还有选择如何回应的自由与能力。”不去纠结刺激本身,接纳自己的各种想法和情绪,看清后再采取行动。忍让逃避是一种,猛烈回击是一种,绵里藏针也是一种,没有一尘不变的回应,关键要选择最合适自己的一种。这次,我选择维护我的合法权利,不卑不亢斗争到底。
很多时候,伤害我们的未必是命运的无常和别人的无情,更多是自己内心的不甘和执念。允许一切发生,才有通透自在。

这件事情也让我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每每想到自己有可能走上法庭,我忐忑又难堪。朋友安慰我:“人生嘛,体验而已,总有第一次。“在这个过程中,朋友们给我许多许多的支持和帮助,有人安慰我,有人出主意,甚至有朋友说:“需要钱你就说话。”我,一个平时不爱社交,一个喜欢沉浸在自己小世界的人,感到巨大的爱意和温暖。
在孩子养育上,我和先生有很多反思。回想小宝头被砸破的那次,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孩子调皮,也没有去找过肇事孩子的家长,先生也没有太多参与。而我,自责背后更多是害怕,是我担心破坏家长间的关系,是我担心引发更大的矛盾。“没必要吧,反正也没有受太大伤,下次注意就好。”我就这样一次次安慰自己,安慰孩子。
我把这些事情和小宝一一谈论。
小宝说:“妈妈,我觉得没什么啊。”
“你觉得受伤了没关系是吗?”
“是的,因为就疼一下下就好了。”
我发现小宝平时处理同伴冲突的方式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旦他受到攻击或挑衅后,他会选择奋力还击。而且被打了,他不会哭,也不会选择求助。即使遇到一个比他强大的对手,他都会选择“勇猛出击”。而我,在孩子的小打小闹中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性,没有教会他好的情绪管控,也因为一次次受伤后的忍让,让孩子觉得打闹受伤都是小事,所以在玩耍时没有真正弄清伤害的边界。
我和他专门学习了情绪绘本,情绪是千百年来人类进化中的自我保护机制,愤怒是划清底线,焦虑是未雨绸缪,每种情绪都有存在的意义,在什么情境下会出现什么情绪,每种情绪都会什么表现,我们又可以怎么办。
我告诉他:“当有人取笑你,当比赛失败,当感到不公平,都可能会生气,生气是一种强烈的热血沸腾的感觉,你可能想要吼叫或者打人,不过想和做是不一样的,要考虑会不会伤害别人,会不会给自己惹上麻烦,无论谁受伤都是不好的,都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你可以先尝试深呼吸让情绪平复下来,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让自己生气,然后选择一个更恰当的方式去处理。比如找家长找老师,或者用言语去沟通,可以倾诉可以聆听,有时是自己需要改变,有时是别人需要改变......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方法应对生气这个家伙。”
我和先生达成了更多的一致。我们制定了更明确的课后计划,有了更多的亲子时光,爸爸也放下工作更好地陪伴孩子。
儿子似乎一夜长大。以前的他,喜欢大喊大叫,容易激怒,这件事之后,他小心谨慎了很多,对于孩子们之间的冲突推搡,他会选择远离或者劝解。有一次,他在给小朋友劝架正好被我听到了:“你要考虑一下C的感受啊,你这样做不对的。”
我很惊喜他居然用到了“感受”一词。
在面对同伴冲突时,孩子该回避忍让还是勇猛出击,如何把握好度,我不能简单给出结论,也是接下来要思考和处理的问题。我想,这就是人生吧,不断和环境发生碰撞再不断调整方向,慢慢成熟成长。就如同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件好事,在摸索和尝试中,深入了解自己,不断改进方式方法。真正做到吃一堑长一智嘛。
和P家的纠纷目前还在司法流程中,审理结果还是未知数。我没有再专门联系P一家,既然已经站到了对立面,就让法律去裁决一切吧。

巧的是,前几天我又做了一个梦。
还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去参观,进门时,工作人员禁止携带手机入内,而且要求每个人留下自己的开机密码,我询问工作人员:请问这是哪里的规定?工作人员直接忽略我,喊道:下一个。
如此的无理,如此的蔑视,那一刻我又体会到熟悉的愤怒,但这次,我没有争执,没有理论,我径直进入了展厅......
醒来后,我很好奇,按之前的“剧情编排”,我应该和对方争论啊,干架啊,我变了吗?
或许变了,或许还是最初的那个我,那个一打电话就有银铃般笑声的我,这个笑声是真正看清生活仍然对生活充满热情,发至肺腑的笑。
原标题:《当我在单位大院里遭遇讹诈风波|三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