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有多美?八百多年前他这样写……
东
古籍里的
阳

东阳本是佳山水,何况曾经沈隐侯。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此诗,被称为东阳旅游的最早“广告”、最美文案。然而,事实真相是,此诗是诗人根据画工为东阳岘山涵碧亭所绘之图而作的“看图说话”。
刘禹锡和东阳人冯宿关系甚笃。《全唐诗》记载,冯宿在河南为官时,曾作诗《酬白乐天刘梦得》,诗末提到“每春,尝接诸公杏园宴会”。冯宿在洛阳为官时,每年春天都要邀请白居易、刘禹锡到自家的杏园里宴饮。后来冯宿离京到河南赴任,白居易和刘禹锡赋诗相赠,殷勤问候。虽然私交笃厚,刘禹锡却无缘东阳。因此当好友于兴宗为东阳令,寄来此画请他作诗时,他把对东阳的满腔好感融于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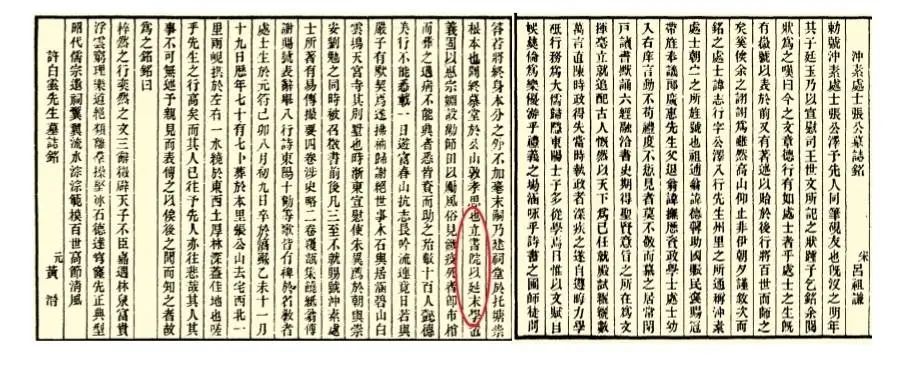
光绪《浙江通志》记载张志行办书院之事
虽然东阳文旅“宣传”工作早在唐代就已发轫,但是唐代东阳乡贤中,至今未发现主动在诗文中推介故乡美景者。首位真正从旅游角度推介东阳景观的东阳人,当数宋代的张志行。其被收录于《全宋文》《全宋诗》《康熙东阳县志》《东阳托塘张氏宗谱》的10篇诗文里,有7篇是游记类。这些游记记录了他的出游“打卡点”,基本上处于城区周边,又仙又美,高级感满满,堪为宋代东阳文人首份Citywalk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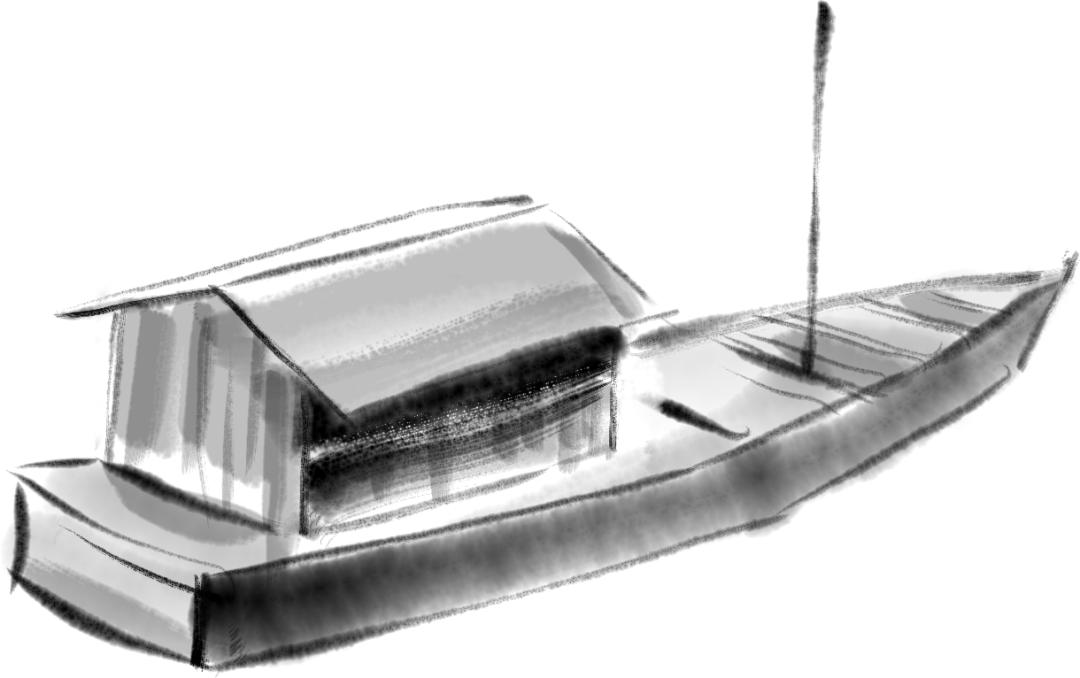

他隐而不仕美名传扬

东阳城区有一处叫“托塘”的地方,这里是东阳城西张氏的发祥地。后晋天福五年(940),籍贯河南开封的张潮任东阳县令,开运二年(945)七月,括苍“魔寇”侵扰东阳,张潮率长子天贤迎战,不幸殉职,全家八十余口均被杀死,妻子鲍氏抱着幼子天宥潜于此塘内,以吃莲子为生,躲过一劫。1099年出生于托塘的张志行就是张潮后人,字公泽,号八行先生。

西岘峰,当年曾留下张志行的履痕。
也许是出生后即听着张潮的事迹长大,张志行幼有大志,聪颖过人,入读乡学时,他更显示出其才思敏捷的一面,写文章洋洋洒洒,倚马可待。如此一路考到举人,却因在殿试时直陈时弊,被当时的高层执政群体忌恨,于是返乡归隐。
回到东阳后的张志行建祠堂、立书院、置义田,并作《东阳十劝歌》,劝世人敦行孝悌、和睦乡党、莫持刀杖、莫兴讼词、莫相报雠、莫务兼并、莫作教唆、莫相斗殴、随田受税、莫为赌盗,以此敦睦风俗,感化民众,跟着他学习的士子络绎不绝,他也被人称为“南阳进士”。
获悉东阳有这样一位“卧龙”,当局者自然屡屡征召,但张志行均坚辞不赴。宣和年间,知州刘安上等人具奏朝廷,褒扬张志行“甘贫乐道,虽老不倦”。
绍兴三年(1133),浙东、福建路宣谕朱异上奏朝廷,称张志行“力学有行,乡里推服”。虽然朱异三次征召张志行出仕,他依然不为所动。朝廷于是赐号“冲素处士”。
这一年,张志行仅34周岁,他作诗《辞聘》记录此事:“纶音旁午下宸州,三使征贤礼甚优。杰异始堪膺物眷,迂疏岂可玷勤求。敢将钓石垂竿卧,漫说公孙复觅侯。自有夔龙熙帝载,山中容我作巢由。”在此诗中张志行的心态很清晰,他是决定隐居山中,永不出仕。

他曾伴邑宰同游岘山

回到家乡后,张志行开启了Citywalk模式。他以西甑山的白云洞为中心,在洞中建书院育学子,教学之余则沿着岘山漫游,从天宫寺到涵碧亭,甚至屡次陪同当时的邑宰游览岘峰。

白云书院
位于西岘峰中兴寺(今法华寺)边上的涵碧亭,建于唐宝历三年(827),因为刘禹锡题诗,宋代已成为“网红”打卡点。张志行不仅屡屡来游,还在现场即兴“涂鸦”《游白云山过涵碧亭题壁》——由此可见,涵碧亭在当时砌有墙壁。
诗共有两首。其一:“梦游还解洗尘劳,一日堪来一百遭。有眼石泉声更细,无心亭竹节犹高。洞中意寂含千古,世上名轻等一毫。此乐要知天付与,未宜轻话与儿曹。”只能说,张志行对涵碧亭是真爱,恨不得日日梦游,一日百回。只要来到这里,听着山泉细细流淌声,感觉世间名利都轻如鸿毛。只可惜,这样的乐趣还不能与晚辈说道!
其二:“岩洞阴阴绝众嚣,白云流水暮还朝。算来混沌分时妙,枉说丹青巧解描。杖履润如涵沆瀣,衣裙清似御扶摇。遨游且纵诗兼酒,分外何曾著一毫。”在张志行看来,游涵碧亭,最好的时候当在早晚之际,此时朦朦胧胧的意境,即使是丹青妙手也难以描绘。此时,他的状态是放空的,曳杖寻幽,身轻履轻。当然,这个时候,面对白云流水,宜携酒,宜吟诗。
位于西岘峰的天宫寺,也是张志行喜爱的打卡地。淳熙五年(1178),同为东阳人的曹冠在《刘崑侯庙记》中提到:“东阳,婺之望县,地广民繁,……吾邑西乡之祠,唯崑侯为盛。谨按梁将军刘侯讳崑,东阳人也。受命征伐,屡立奇功。天监五年,舍宅建天宫寺。天台智者大师七世之孙,尝尸是刹,衲子云集,是为七祖道场,今之般若寺也。”可知天宫寺建于梁天监五年(506),由东阳人刘崑舍出自家宅院所建,天台宗四祖智者大师的徒孙即七祖慧威,曾经住持此寺,僧众云集,因此天宫寺被视为慧威大师的道场。

西岘古道
张志行经常沿山径行至天宫寺,再返回白云洞,《山行至天宫寺归洞中感赋二首》即记录了这种出游状态。其一:“鲁瓢聊借乐吾天,衰病逢途倦直前。千树好花空照眼,数茎新雪已垂巅。常饥穉子啼难遏,厚禄交朋信懒传。输却醉乡游烂熳,解貂换酒日绵联。”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山顶还有新雪飘落。处于半醺状态的张志行面对千树繁花,行于烂熳花途,想起自己多年隐而不仕,屡屡辞请朝廷征召,虽时光虚度且生活困窘,却另有一番乐趣。其二:“抱树遗踪识问僧,才逢佳处便身轻。云藏好岫飞应懒,石障寒泉泻未平。静坐肺肝俱澡雪,高谈齿颊亦澄清。翻思六月长安道,谁管尘沙积满缨。”冬日的涵碧亭格外清幽,坐于亭中观流泉飞瀑,心境澄明。这样的意境,又岂是长安道中竞趋名利者所能享受到的呢?
独游,是张志行的常态。但作为名人,张志行也摆脱不了偶尔的应酬。他曾作诗《邑宰同游岘峰》:“胜境追游岂易寻,公余喜得共登临。攀萝缥缈云霄兴,夹道琮琤玉石音。置酒但教呼我辈,题名何必刻碑阴。篮舆归去敲明月,盛集应堪继竹林。”这是一次高级感满满且宾主俱欢的聚会,酒馔佐诗赋,邑宰喝得酩酊大醉而被竹轿抬回,颇得魏晋名士风流。
邑宰为何人?张志行还有3首《次韵周邑宰同游岘峰怀旧》。查《康熙东阳县志》,宋代东阳周姓县令仅有周思,其于政和五年(1115)上任,重和三年(1121)卸任,此期张志行正值壮年,他与周思诗酒唱酬。周思赠诗给他,或想请他出仕,张志行于是和韵回复,其中一首直陈心迹:“宠辱纷纷不到峦,云无心出鸟知还。因思宦路千钟乐,未博浮生一日闲。细想何如周梦蝶,重游却是祐寻环。更添三十年华后,不省予犹住世间。”
张志行对周思是真心拥戴。政和六年(1116),笃信道教的宋徽宗下令各地建造祠宇供奉玉皇。周思潜心寻访,将城北已经倒塌的栖真观重建焕新,建起昊天殿。张志行不仅前往打卡,更欣然为之作记,借百姓之口给予周思高度评价:“邑之父老相与聚议曰:‘东阳素以难治称,领承宣者多不敢就。自周侯之来,政有条理,宽猛适中,游刃虽微,错盘肯綮,如土委地。未踰累月,争讼衰息,四五万户安居乐业,费无秋毫。我属今德其惠,正如食蔗而入佳境。’”北宋末年的东阳,还是属于难以治理的地方。但周思到来之后,施政手段宽猛相济,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纷纷瓦解,各类讼诉也因此平息,四五万户百姓安居乐业。私心里,张志行非常期待周思日后可官至尚书,代他实现报国之志,“他日粉闱中性字,不宜同在碧纱间”。

他“开创”东阳记游母题

当然,张志行的履迹不会局限于城区,但因他的著作如《易传撮要》《涉史略》《冰壶集》《覆瓿集》等均亡佚,对于他的更多行踪,后人已不得而知。唯有一篇《东白山禅林重建大殿记》,让人可推知他的足迹曾远至东白山巅。
应该是在绍兴十一年(1141)的春天,张志行历尽艰险,登上了太白峰。他极目远眺,却见“钱塘大江,茫然咸在目围”,于是他终于相信东白山是“浙东群山之雄”。再放眼前后左右,凡目力可及八百余里的范围内,“草木花卉,含芳孕秀,四时不凋”,在这神奇的仙境里,他邂逅了被陆羽写进《茶经》的东白春芽,“又土产春芽,名在茶谱,与壑源顾渚共播天下”。
其实,张志行此次出游,更多是冲着修竣重光不久的东白山禅林而来。他对寺院“襟山带水,岧峣衍迤”的地理位置赞叹不已。寺院周边遍植修竹茂林、折柏病桧,高森映蔽,如此茂密的植被,堪为天然园林,即使三伏天暑气如蒸,也难以侵袭这清凉胜境。
在寺中,张志行拜访了住持稠公大师,听他讲述宣和年间寺院毁于兵燹的情况,又听闻大师历时20年,于建炎二年(1128)重建大殿的经过,感佩不已,于是应邀作记刻碑以铭。此记可谓字字珠玑,夹叙夹议,移步换景,情景交融,堪为上佳的游记!
正是张志行这些看似无心的感赋、题壁、怀旧以及作记,东阳山水借其心迹而广为传播,让更多人窥见东阳佳山水的细节深处,那番摇曳多姿的美好。与此同时,张志行的这番举动,开启了东阳文人咏东阳山水的新篇章,东阳山水真正成为东阳文人的创作母题。
就此而言,张志行堪为宋代东阳文旅宣传“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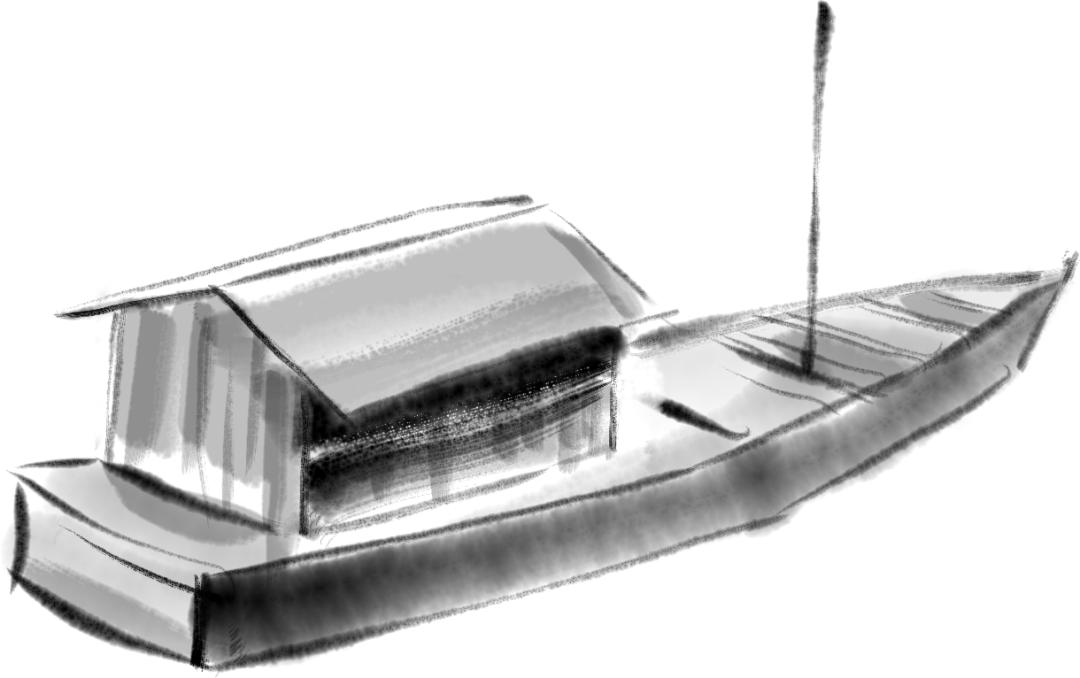

记者丨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吴旭华
通讯员丨陈林旭
原标题:《东阳有多美?八百多年前他这样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