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乡村史、气候史及年鉴学派——勒华拉杜里教授访谈录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2023)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新史学”的推动者之一,研究领域包括乡村史、气候史、城市史、宫廷体系、君主制度等等。他于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为他带来世界性声誉,并标志着年鉴学派的“人类学转向”。作为历史学家中气候史的创始人,近年来,他先后出版三卷本《人类气候比较史》,将气候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这篇访谈是中山大学周立红教授于2008年在巴黎人文之家从事“二战后法国一代历史学家”的博士后研究时对勒华拉杜里所做的访谈。在访谈中,勒华拉杜里讲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从乡村史研究上说,他的《蒙塔尤》一书的成功在于他受到美国以村庄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的影响,从而得以从一个村庄的角度解读《雅克·富尼埃宗教审判记录簿》;作为最早从事气候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他注重探讨气候变化与革命等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并主张对不同国家的气候进行比较研究;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唯物论者,继承了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关注物质现象这一传统。访谈原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的第一部著作《朗格多克的农民》脱胎于您的博士论文,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是您的论文导师,那么您是否遵循着拉布鲁斯的路线,即“抽屉理论”(le plan tiroir),认为社会是由五个层次构成的:经济的、人口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心态的?
勒华拉杜里:没错。我的著作保留了这个体制的物质特性。农业生产,渗透着马尔萨斯观念的人口学,然后是分配运动,它会因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贫困化,然后是局势、稳定、税制、政治,捐税也很重要,最后是宗教问题,探讨的是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就是这些不同的层次。拉布鲁斯也是价格史专家,这是另一回事。
您这本书以大农业周期为背景,您写农村史时,为什么对历史分期感兴趣?
勒华拉杜里:这就是说,在11世纪大规模土地开垦浪潮的刺激下,人口数在1320年、1330年和1340年达到最大值,这是第一个中世纪周期的顶峰。随后,黑死病、百年战争先后爆发,人口下降;对于法国来说,人口达到2000万,很快在1450年降到1000万。随后,一个周期又开始了,自15世纪末起,经过16世纪上半期,直到1560年代宗教战争,法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人口急剧增长周期,人口数从1000万回升到2000万。然后,从1560年到1715年或1720年,人口保持在2000万,这是第二个周期。18世纪是人口增长的第三周期,1715年,路易十四时期人口有2000万,大革命爆发前夜达到2800万。1870年达到4000万,然后一直保持在这个高度。这就是三个周期。
您在《历史学家的领地》一书中说过,弗朗索瓦·西米昂的贡献在于把5个以上的历史周期统一起来。
勒华拉杜里:的确如此。西米昂现在是有点过时了,但是他认为价格增长运动常常伴随着由需求发展以及贵金属的出现而导致的经济增长。16世纪价格上涨,这既是人口增长导致的,也和玻利维亚白银的流入有关。然后价格走跌:17世纪价格保持稳定,这并不必然是一场危机,而仅仅是持稳,然后18世纪,受制于巴西黄金、墨西哥白银和人口猛增的影响,价格又开始飙升。
对您来说,历史周期是不是类似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
勒华拉杜里:没错,如果您这样认为的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有几层含义。有百年的长时段,例如16世纪价格上涨,或拉布鲁斯在《18世纪的价格和收入运动纲要》中研究的18世纪的价格上涨,还有17世纪价格的稳定。然后还有非常长的长时段,布罗代尔或许有些仓促地把它与地理等同。最后,农业结构相当稳定,地中海的农业结构延续了几个世纪。
布罗代尔和拉布鲁斯两人您都认识,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性,分歧又体现在什么方面?
勒华拉杜里:拉布鲁斯是研究价格史的计量史家,他很关注18世纪的价格上涨,这实际上是繁荣造成的。我们以1693年饥荒为例,2000万法国人中有30万人因此丧生。我们再看1788-1789年的生计危机,这发生在大革命前夕,虽有人在街头煽动闹事,却没有人死亡,说明这个国家取得了很多进步。拉布鲁斯是伟大的价格史家,在他关于大革命前夕危机的著作中,他研究了酒价危机。当时,这个短期的危机是由于天气连续四年炎热,使酒增产造成的,但把这说成大革命的起因,则不一定正确。因为这场危机发生在1778年或1781年,大革命却来得有点晚,无论如何,这说的只是酒的情况。实际上,法国的经济在大革命前发展态势良好。真正的危机是1788年的生计危机,我在《人类气候比较史》中解释了这个现象。布罗代尔呢,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计量史家,至少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第1卷中,只有1页,他写道我们可以做个图表;在第2卷中,有很多图表来自他的学生,因为他让学生帮了不少忙,我也帮了些忙。我认为,布罗代尔首先是个唯物论者,换句话说,他对宗教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小麦、黄金、白银和人口。例如,有一天,我对他说,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经济成就上有所差异。他对我说,不,我对这不感兴趣。总之,他对宗教不感兴趣,或许在他的晚年有些变化。我呢,我是天主教徒,但在历史研究上,我是唯物论者。我当然相信观念的作用,但我更对物质现象感兴趣,比如气候、人口等等。我年轻时和孚雷很要好,他当时在宗教问题上也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他变成了唯灵论者,注重研究观念史。我知道这也重要,但这是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的确如此。您与居伊·勒马尚和卡林娜·朗斯在一段对谈中曾这样说过,这篇对谈发表在最近的《法国大革命史年鉴》上。
勒华拉杜里:没错。我和老马克思主义者走得有些近。我可以与他们对话,我认为孚雷做了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很有意义的研究。老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如此,尤其是对生计问题的研究,这一点,孚雷根本没有看到。他对精英、自由派贵族和政治感兴趣,却从来没有看到生计问题,相反,索布尔对此有很好的研究。至少,索布尔关于无套裤汉的论文是建立在档案基础上的一篇杰作。当您翻开索布尔的论文,阅读那10页关于生计危机的描述时,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从档案中爬梳出来的。至少,如果您看看让—皮埃尔·巴尔代(Jean-Pierre Bardet)这样的人的著作,他固然右倾,却也对生计危机感兴趣;还有英国的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和E.P.汤普森,这些人都看到了“生计危机”这一面,孚雷却根本没有看到。孚雷的贡献在于让左派接受右派的观念。
您和孚雷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上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勒华拉杜里:我是唯物论者,他是唯灵论者。我承认他天资卓越,但他却对年鉴学派有敌意。我呢,我认为年鉴学派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好的一面,这就是对物质生活、对人口的关注,这些都不是纯粹观念。孚雷才华横溢,但他的学生们却有迹象在背离他,去寻求观念史的共性(la stratosphere de l’histoire des idées)。
孚雷与年鉴学派是有些疏离。
勒华拉杜里:没错。他有他的方式,他有他的道理,但我仍然忠于年鉴学派。实际上,我并不敌视宗教史、观念史与学校史。它们都很重要,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我的第一使命,尽管我也做了一点这方面的研究。
您的乡村史无疑也涉及宗教方面的内容。
勒华拉杜里:对,这就是我那本庞大的农民史——《法国农民史:从黑死病到大革命》。我在其中谈到宗教,的确,这很有意思。根据一种有些过头的表述,这是“静止不变的历史”。实际上,如果我们以1320年的法国为例,当时有2000万人口,如果看1715年或1720年的法国,同样是2000万人口,从表面看,任何变化都未发生,但从本质上看,许多事物都不复原样。其实,这之间出现了一个裂缝,一场黑死病使人口降到1000万,然后再次攀升,所以才会保持稳定。在这片六边形的土地上,虽经历动荡,但终归于平稳,很多事物都处于稳定状态:村庄的数目几乎稳定不变;从社会结构来说,总是有工人、散工和农夫;宗教状况无甚改变;新教徒总是少数地方语言同样如此,阿尔萨斯语、奥克语、布列塔尼语、北部法语久未改变;政治体制虽然有所变化,但总是有王国,也总是有贵族。因此,您看,很多事情都是稳固不变的。人口很明显是往城市、往资本主义出现的地方流动,但以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也就是1700年为例,10%的人口住在城镇,我认为在14世纪是8%,这就是说要养一个城里人,总是需要9个乡下人,其中8个是农民;这个比例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但相当稳定。人口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结婚年龄推迟到24或25岁,但更重要的是有流行病爆发,饥荒也不时出现;人们不会饿死,但饥荒引发的流行病却会令人丧生。冬天也会有大批人死去。人口增长受到限制,大体上也可以这样解释,即一男一女结婚后,从原则上说能生8个孩子,但往往丈夫或妻子会在女方的生殖期结束前死去,他们实际上有4个孩子:一个长不到1岁就夭折了,还有一个活不到20岁,这样就剩下了两个孩子,这叫简单再生产。那么,到了18世纪,再生产稍微扩大了一些,但这个体制相当稳定。自1715年或1720年起,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道路修建和文化变迁,这种稳定性被打破了。
正如米歇尔·伏维尔《从地窖到顶楼》一书的标题所示,在1970年代,您这一代历史学家大多脱离了经济—社会史领域,而转向心态史和文化史。对您来说,有这样一个转向吗?
勒华拉杜里:多少有些。我也写了《蒙塔尤》(在某种程度上是两者的结合)。我也写了法国史,这很经典,其中就有心态史的内容。但是,我忠于基础(infrastructure)观念,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这一点,但这根本不是共产主义。我对宗教史、文化史持开放态度。孚雷很有才华,但他有点使人忘了年鉴学派的历史。还有记忆史,我并不想触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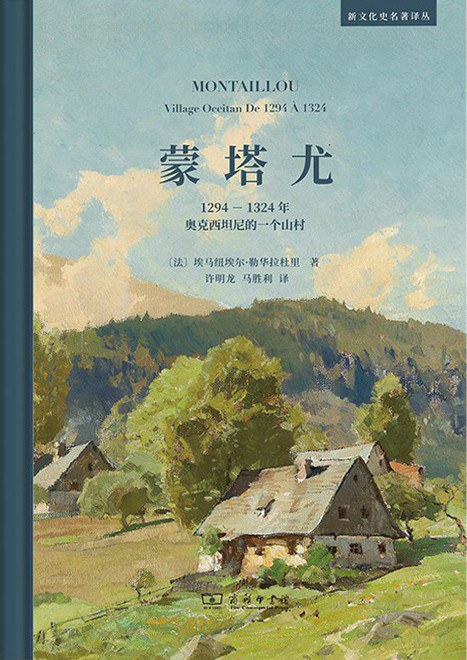
《蒙塔尤》
《蒙塔尤》在中国很有名。实际上在您之前,已经有些学者使用了雅克·富尼埃(Jacques Fournier)的审判记录,为什么只有您才写出如此精彩的一本书,来重构一个乡村的生活呢?
勒华拉杜里:的确,关于蒙塔尤的历史,曾有两本宗教审判记录簿,一本已经散失,另一本跟随教皇伯努瓦十二世(Benoit Ⅻ)到了阿维农,后来被保存在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随后,一个反对教皇至高无上地位的德国神学家,叫德林格(Johann Joseph Ignaz von Dllinger),他是天主教徒,在1880年发现了这本记录簿,然后一个教士和南方的几位历史学家曾经利用过这些资料。再后来是让·迪韦努瓦(Jean Duvernoy,法国电力公司的律师),他为了建电坝,参与淹没了一个村庄,但却复活了另一个村庄,这就是蒙塔尤。他出版了《雅克·富尼埃宗教审判记录簿》。随着《蒙塔尤》的成功,有人出了(审判记录簿的)法文版,很不幸,一部分被销毁了。但实际上它仍存在,或许保存在某地的一个图书馆,或许就在中国,这也有可能。我呢,我的贡献是理解到这是一个村庄的历史。对其他人来说,这仅是宗教裁判史。我说这里面有一个村庄,正是这个观念有价值。迪韦努瓦是有才之人,他发现了不少东西,但他并未领会到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村庄的历史。
在发掘《雅克·富尼埃宗教审判记录簿》之前,您是否想过要写一个村庄的微观史呢?
勒华拉杜里:的确,我有过这种想法。我做过关于古贝韦尔老爷(Sire de Gouberville)的乡村史研究,然后我在美国短期逗留过,接触了研究村庄的人类学,比如,研究墨西哥村庄、法国村庄的人类学,我看着这些东西,着迷起来。随后,我回归村庄史研究,写过几本书。我又回到了我的导师布罗代尔称做的“大历史”(Grande histoire)。实际上,布罗代尔在结构史、长时段史与事件史之间做了区分,他把事件史称做“大历史”,“唯历史的历史”(l’histoire historisante)……或许有点出于妒忌,布罗代尔不喜欢我关于蒙塔尤的书,因为里面有性史。但我仍旧忠于他,我敬仰他。我认为我找到了其他领域,比如说气候史。
您在《蒙塔尤》中使用了“社交性”(sociabilité)这一术语,描述了男人、女人和年轻人不同群体内部的社会交往。实际上,这个术语在当时还没有流行开来。
勒华拉杜里:并不是我发明了这个词。即便我也发现了家庭住所(la maison-famille),即使不是的话,也是一些年轻的牧羊人,过的是一种家庭生活。我竭力挖掘其中不同的方面。幽灵、死亡笼罩着村庄。有牧师这一人物,他是山里的一类领导人,相当粗暴,极具诱惑性。您知道,蒙塔尤的镇长也叫克莱格(Clergue),但不是他的子嗣,而是一个侄子,因为教士没有后代。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领主的社会,这些小人物对领主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有一个贵妇,城堡夫人,她有点权力,但并不很重要。这是一个农民的世界,一个农民领导和小民构成的世界。最近,我读了另一本书,讲的是南部加尔省一个城堡里的男仆,书名是《皮埃尔·普里翁的日记本:朗格多克的一个村庄(1744-1759)》。在这个村庄中,城堡是一个大企业,就像一家工厂,有很多地产和仆人,这并不是封建剥削,但却养活了很多人。这是叠合在村庄上的一个统一体。这本书在法亚尔出版社出版,我帮了不少忙,但作者是让—马克·罗歇(Jean-Marc Roger)。
您也做过一座小城市的微观史——《罗芒的狂欢节:从圣蜡节到圣灰星期三(1579-1580)》。写小城市的历史与写小村庄的历史,经验有什么不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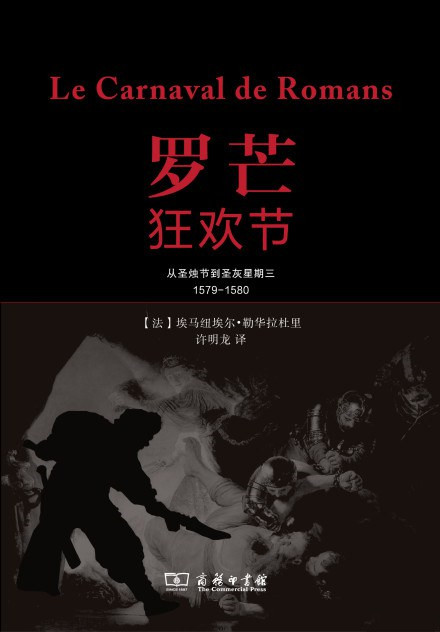
《罗芒的狂欢节:从圣蜡节到圣灰星期三(1579-1580)》
勒华拉杜里:没错,我尝试的题材多种多样。它们之间是否有共同点?毫无疑问,它们之间是有共同点的。我也做过《圣西门或宫廷体系》。实际上,我的观念来自路易·迪蒙(Louis Dumond),法国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印度。我把路易·迪蒙的心智类别应用到路易十四的宫廷,换句话说,就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神圣的一面,纯静的和邪恶的,妇女的“上嫁”(hypergamie)。妇女如同鳟鱼或蛙鱼,窜到宫廷,换句话说,女人凭借美貌与财富可以嫁入门第更高的人家,因此她们是社会流动的因子,有点像向河流上游游奔的鳟鱼或蛙鱼。最后是路易十四的派别和团伙。我在《狂欢节》中没有触及路易·迪蒙提到的倒错问题,我在其他地方对此做了研究。于是,我被邀请到印度,就此书做了几场报告。
您成为一位乡村史家,这是否同您的父亲雅克·勒华拉杜里有关?他曾是一位农业工团主义者。
勒华拉杜里:没错。我父亲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发起农民工会运动。我对气候史感兴趣也是如此,因为我曾在诺曼底生活过,那里雨水很多,常常使收成毁于一旦。
周立红:我知道您很早就开始研究气候史。1962年,您就被邀请参加在美国阿斯彭(科罗拉多州)举办的“11到16世纪气候史”国际研讨会。您关于气候问题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于1967年。因此,您是当之无愧的气候史的创始人。
勒华拉杜里:没错,在历史学家中间,我是气候史的创始人。最近,我出版了两卷本大部头著作。我还想出版关于回暖问题的第3卷著作。第1卷从中世纪一直到1740年,第2卷从1740年到1860年,第3卷是关于回暖问题的。
布罗代尔曾鼓励您进行气候史研究,并给与资助。
勒华拉杜里:没错。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首次谨慎地触及气候史,因为法国历史学家对此并不看好。法国有固定论、稳定论传统,比如,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拒绝进化理论,这与达尔文恰恰相反。法国传统认为气候是一成不变的。
您说过,当您最初进行气候史研究时,您最好的朋友有时还拿您的研究取笑。
勒华拉杜里:没错,但他们错了。现在气候史被接受了。
您曾强调气候史的重要性,难道一个原因是气候对乡村史尤其是对生计史很重要?
勒华拉杜里:没错。从短时段看小麦价格的变化,很明显在有饥荒时,价格飞窜,这时会爆发生计骚乱,然后是革命,一场革命的爆发有心智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生计危机的出现,1788年、1789年、1846年、1847年就是这样的情况。1846年,土豆染病,气候干燥,小麦、谷物、土豆一概歉收,这已经很严重了,法国死了20万人,这是导致1848年革命的众多原因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和气候毫无关系。这就是历史的因果关系问题,是有好几个参数的。
为什么在《历史学家的领地》中,您谈及的是“没有人的气候史”?
勒华拉杜里:没错。最初我小心翼翼,因为它没被看好。我想做纯粹的气候史,但现在,一方面,这是没有人的历史,反气旋,降压,它们并没有考虑人;但另一方面,这却对人有影响。例如,如果出现撒哈拉反气旋的话,如果它持续得时间太长的话,将会出现干旱天气,随后就是歉收。如果低压持续时间很长,且过头的话,会出现类似于1709年那样的漫长的寒冬。1709年的寒冬导致60万法国人丧生。如果出现雨水天气,且气压低的话,则会造成130万人死亡。最后,如果出现干旱天气,夏天酷暑当头的话,比如1846年,则会爆发生计危机。
您为什么在近年出版的《人类气候比较史:13-18世纪的酷热与冰川》中用“比较”一词?
勒华拉杜里:“比较”,是因为我在法国、英国、德国之间做比较,多少还和美国、非洲、澳大利亚、阿根廷的情况做对比。一个叫乔丹(Jordan)的美国黑人历史学家研究了1315年的那场大饥荒,那场因雨引起的饥荒……我认为,马克·布洛赫的比较史学思想很重要。应该对可比的事物进行比较。对于气候史来说,我们有能力这样做。对于20世纪来说,在《欧洲历史统计》中,可以找到欧洲所有国家每年收成总量。例如,您可以看到,1998年,欧洲所有国家——从芬兰到西班牙——各种农作物都大获丰收,甚至酒也如此。如果您知道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德国、希腊的情况的话,就可以做比较史,研究欧洲45个国家酒的生产。

马克·布洛赫
在您看来,气候史是环境史的一个分支吗?
勒华拉杜里:我研究的是气候史,不是环境史。环境史对我来说是很宽泛的一个问题,气候却很具体。具体说来,有酒的历史,炎热、干燥的夏季适合生产好酒。比如,有一个单子,写着死前应该喝的100瓶酒(好酒总是在炎热、干燥的年份酿造而成的)。我研究乡村史,这说到底是环境史的一种。
您在《历史学家的领地》中写道,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认为,经济史首先应该给职业经济学家提供资料根基。气候史家首先应该给地球和大气科学专家(气象学家、冰川学家、气候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提供档案资料。
勒华拉杜里:的确。我认为科学家应该寻找一些历史资料,我们不擅长气候学,他们则对历史一无所知,因此,两者应该多交流,但我太老了,不能去参加学术会议了。
您研究气候史的方法是什么?难道这和研究乡村史不是一回事吗?
勒华拉杜里:的确有些关联。我研究葡萄收获时间的历史,气温史,冰川史,饥荒史,缺粮——仅仅是缺粮,还研究一点树木(年轮)的历史,然后是事件史。
计量方法对您来说总是很有价值吧?
勒华拉杜里:没错。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了电脑,但是做计量史学的却越来越少,这是悖论。本来,他们拥有的计算机越多,就应该越多做些专业的计量史研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身上有1968年5月的反叛精神。
您有一句话在中国学界很流行:“[在当时的法国]谈到1980年代计量史学的实践前景时,有这么一个预言:明天的历史学家将是程序设计员。”您仍持有此种看法?
勒华拉杜里:不管怎样,很多人是这种情况,我也这样认为,很多人用电脑,即便是定性史学也需要电脑。
您的研究主题非常广泛,涵盖乡村史、气候史、城市史、心态史、君主制度、宫廷体系等众多领域。
勒华拉杜里:现在我要写一本关于19、20世纪气候回暖的书。您知道孚雷,当他写共产主义史时,说他“进入了20世纪”。我或许也伴随着这本气候回暖的书进入了20世纪。实际上,我已经打量过20世纪了。大致说来,我是一个研究第二个千年的历史学家,或许也研究点第三个千年的初期。这么说吧,我有一种理论与中国有关,我知道微生物引起世界的统一,我已经将其写在了《历史学家的领地》中:欧洲与亚洲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因马可波罗、成吉思汗、无数传教士和商人增多起来,到一定时期,“星球的小循环”出现了。这也就是说,中亚带有鼠疫的跳蚤附在老鼠身上窜到了克里米亚——这可能要归功于蒙古帝国的统一和丝绸之路。黑死病几乎使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发现美洲后,同样的一幕重演了,征服者们把他们的病菌带给了一个不具有免疫能力的人群,引发了一场比黑死病更可怕的大屠杀,(海地、古巴的)一些岛屿上的人口迅速消失,墨西哥人口急剧减少,出现了异种交配。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348-1700年之间出现了由微生物引发的世界的统一。我在《历史学家的领地》中写了欧亚之间这段统一的历史。
您是否有一种意愿要做总体史?
勒华拉杜里:没错,有点儿。我们可以做一个村庄的或一个广阔空间的总体史的深入研究。美国人称之为“大历史”(Big history)或“全球史”(Histoire globale)。比如,我们可以做气候的总体史。
您出版过一本书叫《在历史学家中间》,收集了您多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很长时间以来,您扮演的是双重角色:杂志记者和历史学家。
勒华拉杜里:的确,30年来我一直是一位杂志记者,我为《世界报》《新观察家》《费加罗报》写过稿子,现在为《宗教世界》写些东西。
我觉得这或许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您的朋友孚雷、德尼·里歇、奥祖夫夫妇都扮演着此类双重角色。
勒华拉杜里:对,对,这就是说我们利用媒体,上电视,在电台录节目,为杂志写稿子,而现在,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了。我觉得,首先私人电视台的频道对此不感兴趣,而公共频道比较独特,他们对历史感兴趣,人们有必要吞下(听)它。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阶段的现象。有段时期涌现出有意思的绘画,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也会出现有意思的历史学著作。这或许会持续下去,但不再那么引人关注。
您怎样看待皮埃尔·诺拉的路径,他集编辑与历史学家于一身。
勒华拉杜里:他对记忆史感兴趣,这有些危险。他一度明白不应该走得太远,因为应该通过历史来学习和控制记忆(但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实际上,最先对记忆史感兴趣的是菲利普·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他考察了法国南部清教徒的记忆。皮埃尔·诺拉主编了《记忆的场所》,但最终应该通过历史掌控记忆——这才是严肃的记忆。
对您来说,《巴黎—蒙波利埃》是一部“我的历史”(ego-histoire)吗?您没有参与诺拉主编的《“我的历史”论集》,是因为您在这之前已经写了些东西吗?
勒华拉杜里:没错。我在诺拉的《“我的历史”论集》出版之前已经写了“我的历史”。我是第一人。在我看来,我做的是最好的,因为我写的是一本书,其他人的只是文章。
您曾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工作过,但那时,大学里的人很不喜欢第六部,有时甚至鄙视它。这里是个死胡同,培养的人不能去外省院系或索邦当老师。那么,您怎么看待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对20世纪下半期史学史的贡献?
勒华拉杜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当时有些远离大学体制,后者的重要之处在于可以和年轻人保持联系。的确是这么回事,无论是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还是在法兰西公学,都缺少这种氛围。在布罗代尔时代已是这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现在是降格以求(De la poésie à la prose):这是一种自我维系的运动,但是在我那个时代却是创新。无论如何,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一直在扮演一个角色,大学同样如此。
您还有一句话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军事技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内,并不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在1930年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
勒华拉杜里:我认为,年鉴学派的确有些贡献,具体说来,它超越事件史,关注结构、长时段和大众,当然,它也对事件感兴趣,因为后者曾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了历史学的方向。如今,(如果您翻翻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国的期刊的话,会发现)年鉴学派已普及开来。年鉴学派的许多历史研究已经超越了《年鉴》杂志的范畴。长期以来都有回归事件史的趋势,这尤其对当代史来说是正当的。年鉴学派的历史学最终随着这种“大规模”的历史带来了一种新因素,这好比一棵硕果累累的树,枝干四面伸展然后又返回树干;但年鉴派史学仍旧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发展着。
您知道有些时代产生了出色的画家、杰出的作家。这或许是一种情感……一种因世界大战而导致的历史的悲剧意识,一种与过去的疏离感,一种顿感过去破裂的悲怆之感。吕西安·费弗尔说道,做经济史是为了避开战争的恐怖。我想是在寻找一种慰藉,在历史中,在对这段历史的审视中寻找一种安慰,尽管悲剧重演,历史仍旧滚滚向前。我想战争过后,人们有一种国破山河碎的悲怆,尤其是世界大战让人们经受了历史的震撼: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存在。
现在还有一个系谱问题。20世纪初,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开创了法国地理学派,吕西安·费弗尔向法国地理学派借鉴了这种方法,完成了《菲利普二世与弗朗什—孔泰:政治、宗教与社会研究》,它成为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式的历史或地区史的样板。但同时,“菲利普二世”一词又让我们想到了布罗代尔,想到了地中海。因此,我认为这本书的确是史学史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它出版于1902年,所以我认为还有系谱问题。
马克·布洛赫是基督徒一类的人物,他被德国人枪决。他的书,一本写乡村世界,一本论封建制度,还有一本涉及的是君主制(《国王的触摸》),考察神圣与政治、农村世界和封建主义问题。马克·布洛赫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对此很感兴趣。正是从那时起,费弗尔投入到心态史的研究,写就《16世纪的不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此书并不完全成功,因为他假设在16世纪,人们不会成为无神论者,金兹伯格的研究表明这是错误的。总之,战后很多年轻人聚集到年鉴学派的麾下,拉布鲁斯在索邦任教一定帮了忙。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