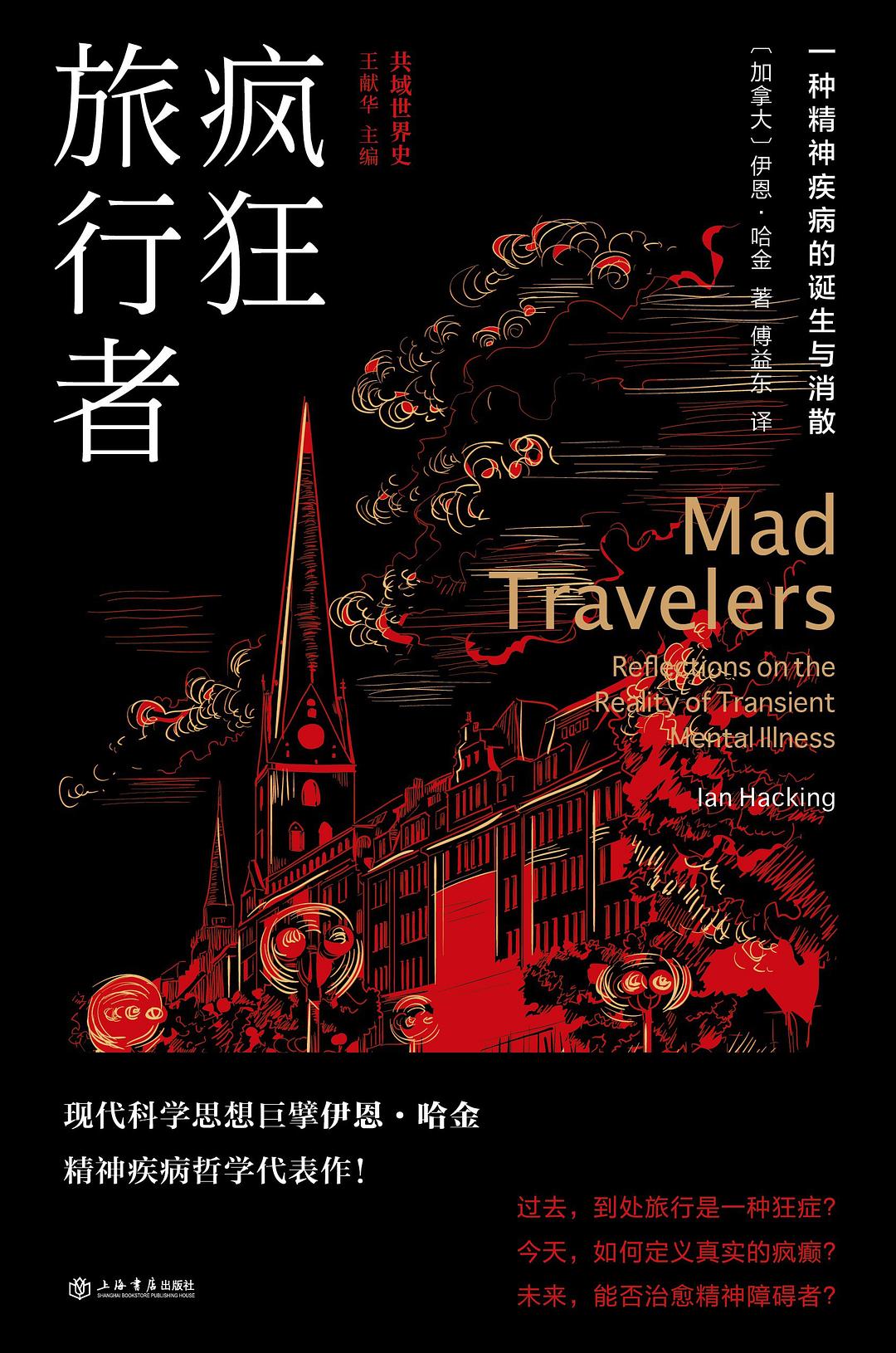疯狂旅行者:德国的“游荡癖”
《疯狂的旅行者》一书出版于1887年。1888年,夏尔科发表了对送货员的研究。1889年,意大利医生开始发表神游症类型的诊断分析。意大利受法国的影响很大。德语国家的精神病分类学发展很快,声势盖过了法语国家,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传统。神游症渗入德语国家,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我想简明扼要、不揣浅陋地描述发生的事情。因为政治、地理方面的状况,德语世界中的医学文化是分散的,甚至在德意志帝国内部也是如此。德意志精神病学文化从奥匈帝国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国。在讨论热烈的1898—1914年,最富影响力的中心或许是位于苏黎世的布尔格赫茨里医院(Burgh.lzli Hospital)。然而,我在那里找不到任何关于神游症诊断的蛛丝马迹,尽管很多说德语的神游症患者确实到过瑞士。
一切都开始于1898年,当时恩斯特·舒尔策(Ernst Schultze)在波恩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关于意识的病理性紊乱论稿》。舒尔策写道:“我没有带来太多新事物,因为夏尔科已非常清晰地阐述了漫游自动症的‘症候群’……但如果你继续阅读文献,你会发现这种疾病在德国非常罕见,至少很难被诊断出来。看看1894年法国的考察吧,书中引用了四十部作品,只有一部是德语的!”
只有当人脑洞大开时,他才会将以下病例归入漫游自动症。这个故事写于1880年,讲述了一个病情很重的未婚牧羊人的故事。1857年,他被送入精神病院,留院观察。此人于1860年去世,年仅40岁。他有过很严重的惊厥失神,在发作前后,他会不由自主地前后或绕圈踱步,总是沿顺时针方向。他秉持一种偏执的信念,认为应该把整个世界、天堂和天使都记在脑中,放在心里。 尸检结果显示,他的大脑硬化严重甚至已经萎缩,尤其是右脑半球。这位男子并未患夏尔科所说的潜伏性癫痫,这一点在了解他的神经病因之前便已显而易见。不管怎样,在主治医生看来,癫痫的症状过于明显。简而言之,这种踱步类似于癫痫发作后出现的“前奔”,即一种漫无目的的来回踱步。牧羊人被关进精神病院,不是因为他的踱步行为,而是因为存在于脑海中的对世界的虚妄幻觉。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当舒尔策开始研究时,德国医生并未发表过任何相关病例。
这并非全然正确。此前当然有过符合诊断标准的病例,尽管这个诊断标准当时还不存在。这些病例出现在逃兵群体中,比如火枪手J.M.,他未经请假便擅自离开多次,每次都是步行离开且难以抑制。他第一次上军事法庭的场景并未给人留下太多印象:被告人总是回家,声称他难以克制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但在上诉过程中人们发现,这名火枪手从青春期开始就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并且有强烈的旅行欲望(流浪、驾车、旅行)。被告人没有癫痫病家族史,也没有任何癫痫发作的迹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被告人的精神活动受到了短暂的病态干扰,在此期间,他擅离职守。根据德国第五十一条军规,火枪手无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精神病人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除非行为人是故意为之且具备自由意志。
这一指控事件发生在1880—1882年,该报告发表于1883年。当时德国不存在神游症或漫游自动症的诊断。人们充其量只能说,他的精神活动受到了暂时的病态干扰。 因而,我们可以说,这是在神游症诊断(“歇斯底里神游症”——甚至将癫痫排除在外)出现之前的病例。但在德国,歇斯底里症是存在问题的,那里针对男性的诊断并没有得到夏尔科式的推动。弗洛伊德觉得歇斯底里的诊断不错,将其引入他在维也纳的资产阶级心理咨询室,主要用于治疗有明显“神经质”的病人。维也纳的医疗机构最初是拒绝弗洛伊德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男性歇斯底里症的坚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性病因学的热情。对于年轻的士兵来说,情况更为糟糕:1883年,歇斯底里症并不属于被迅速普及至第八十七步兵团的诊断类型。
直到1898年,当舒尔策着手填补这一空白时,漫游自动症才被引入德国。他提出了三个新病例,并在1909年又增补了第四个。他坚持认为德国医生需要建立一个病例目录库:我们绝对不能落后于法国人!他描述的病例极为有力。其中每个故事都可以作为小说或电影的提纲,但在此处,我必须省略多余的轶事。
X是军中一名年轻的志愿兵,一名优秀的战士,正计划延长服役期。但他突然走了,前往伦敦,在那他乘船去了纽约,然后再到辛辛那提。直到那时,他才完全意识到自己身处异乡、孤身一人,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稍微恢复了点意识,知道自己是谁,甚至写信问父母要钱。
Y,一个37岁的奥地利裔男子,有一天出现在舒尔策位于波恩的诊所。从服兵役开始,他就有开小差神游的经历。有一次,他从布拉格旅行到的里雅斯特,最后带着他的老仆人和一只鹦鹉回来;而当他回到布拉格的家时,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忘得精光。10几年后,在与妻子争吵之后,他来到了马赛,这段10—12天的经历从记忆中消失了。在巴黎,他经过外籍军团的征兵办公室,便应征入伍,被送到奥兰后又被送至摩洛哥的一个堡垒。于是他从军中逃离,回到巴黎。在巴黎他进入一家医院,接受了电疗和冷水浴疗法。突然有一天,他到了荷兰并试图加入殖民地军队,但是被拒绝了。此后他成了一个耽酒症患者,即酗酒狂。他会狂饮一个星期左右,然后间隔三四个月再来。他饱受眩晕、昏厥折磨,并有惧旷症,这导致他常被警察送回家。
Z,一个23岁的化学工作者,对任何事情都浅尝辄止,从不深入精进。他在理工学院时,刚开始化学和物理学得不错,但转而学习法语、俄语、英语、波兰语和梵语。他也会外出旅行,伴随着阵阵失忆,他完成旅行的效率和完成学业的效率同样低下。他的确去了普利茅斯,计划从那乘船去美国或加拿大,但他不太确定具体的目的地及通过何种方式前往。他也认真考虑过参军,但总是优柔寡断,未能付诸行动。
舒尔茨的第四个案例来自他的同事。病人是一个37岁的木匠,他经常感觉自己被恶魔力量追杀,遮天盖地,无处遁形。他因偷窃两块表而被捕。当发现有两块不属于自己的手表时,他表示没有任何印象,且认为既然违反了法律,便愿意接受惩罚。原来,他曾多次被人发现从部队擅离职守,受过入狱两天、三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惩罚。在新一次疾病发作之前,他头痛欲裂,持续了一两个小时,感觉有把刀正从脑中拔出;他眼冒金星,然后就开始漫游。一段时间后,他回过神来,感觉就像刚睡醒。然后他开始问自己:“你现在都干了些什么?”在故事的结尾,他找到了一份马车夫的新工作。
在舒尔策的叙述中,这些故事是令人恐惧的19世纪末欧洲心理剧。前三人中的两人有自杀冲动,他们拿着左轮手枪四处走动,并不时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我已经省略了大量细节;舒尔策,像许多研究神游症的学者一样,是一位擅于讲故事的人。他在 1898年那篇论文的结尾处写道:“我更倾向于把这三位病人都当成癫痫患者。”X有过类似于癫痫发作的症状。Y有眩晕和昏倒的症状。此外,克雷佩林(Kraepelin)在他1896年版的教科书里指出,耽酒症是癫痫的一种后遗症。Z在旅行刚开始时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之后他的记忆逐渐消失,乃至失去了言语能力。自杀倾向甚至也成为癫痫诊断的依据。舒尔策在每个病例乃至论文标题中,都提到了心理的混乱状态——“意识紊乱”(Bewüsstseinst.rung)。
在分析的结尾,他对治疗提出了疑问。夏尔科提倡使用溴化物疗法。有人尝试过,但未取得明显疗效。舒尔策写道:也许我们会沦落到使用一位父亲的处理方式,他15岁的儿子总是不停在外流浪。这个小伙子最后被父亲安置在一艘游艇上,无处可逃。
就这样,神游症被引入了德国医学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重述法国论战的要点,尽管直到1903年为止,问题更多集中于“是癫痫还是其他什么疾病?”而非“是癫痫还是歇斯底里?”。舒尔策面临的第一次挑战发生在 1899年,不是源于歇斯底里,而是源于癫痫的外延拓展概念。尤利乌斯·多纳特(Julius Donath)描述了另外三个病例。第一个是38岁的木工大师,他骑马赶往最近的火车站,然后从那出发,去了布达佩斯、维也纳、莱比锡、汉堡和纽约,却完全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第二个是一位49岁的店员,他的神游症经历非常简单明了;他艰难跋涉,睡得简陋,从不感觉饥饿。第三个是一位19岁的裁缝助手,他宁愿做一个马车夫,这是其挚友的营生。他喜怒无常,长夜难眠,伴随着难以预料、稀奇古怪的外出神游——在此过程中,他会追逐女孩,追赶军乐队。这三位病人都会有头痛、偶尔失忆的症状以及一种难以抗拒却毫无目的的旅行欲望。多纳特将这些病例诊断为癫痫,并为关于旅行的癫痫性强烈冲动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旅行狂热症。但他特意强调:“对于我来说,癫痫性旅行狂热症是一种特殊的癫痫心理当量,和其他常见心理当量不同。在特殊的心理当量中,意识紊乱要么是完全没有,要么是由于未发育完全的天性而居于次要地位。”颇具争议的词汇是“意识紊乱”。舒尔策进行了反驳,他把失忆症看做意识紊乱的病征。他也认同多纳特的观点,即癫痫性漫游自动症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但这是因为,癫痫本身就是千变万化的。
比抨击舒尔策更引人注目的是多纳特对歇斯底里神游症的鉴别诊断。在癫痫概念已经扩大的情况下,歇斯底里神游症会出现在患者被一个固有的想法困扰或具有双重人格的病例中。神游症通常发生在“第二状态”。多纳特目睹了这种情况,为此他在1892年将其作为确切证据加以描述。这是一位受淋病折磨而接受治疗的妇女,她从未接受过催眠治疗。女病人极富魅力,聪明伶俐。在谈话过程中,她会毫无征兆地开始玩耍,用孩子气的声音说话、歌唱,
通过这种方式,她不再感到痛苦,甚至可以起床奔跑,而平时她几乎常年卧床,足不触地。她母亲说这是种“发作”。多纳特实际上并没见过任何一个歇斯底里神游症患者,但他会想当然地把自己所遇之人当作神游症患者的替身。
在布达佩斯的医院病床上发现典型的双重意识患者是非常罕见的,直到你知道了病人的母亲是法国人。当多纳特引用她口中的“Krise”这个德语单词时,她一定指的是法语里的“Crise”。在这种情况中,德语不常用该词,而在法语中该词是标准的多重人格探讨用语。这个双重意识的病例是从法国输出的,不同于近年来,多重人格从北美输出到澳大利亚和荷兰。
癫痫仍然是神游症的基石,这一点未受挑战。尽管出现了“旅行狂热症”这个名词,但常见的“游荡癖”是这种疾病的医学名词并变得根深蒂固。自杀的想法和实际行为如此之多,令人震惊。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患者来自萨克森、西里西亚和匈牙利,这些地区的自杀率比西欧要高得多。对于西里西亚人或匈牙利人来说,自杀是一种人生选择,但在巴黎人中不存在这种选择,更不用说加斯科涅人了。
歇斯底里症此时已羽翼丰满,蓄势待发。它被纳入关于“游荡癖”的大讨论中,大概反映了德国医疗实践对于相关疗法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德国第一篇研究神游症的文章出现在 1903年。海尔布隆纳(Heilbronner)描述了他的十二个新病例,他把这些病例编制入表,总计共有五十七个病例——他称之为“神游症和类神游症状态”。表中有三十人是法国人,混合了典型的歇斯底里诊断和癫痫诊断。海尔布隆纳在他恰好能得到的资料中做了严格的挑选,添加了一些之前未被列为神游症的癫痫病例(以其他名词指称)。但是他忽略了典型的法式综合征,该综合征于1895年由菲尔让斯·雷蒙在讲座中提出,皮埃尔·雅内将之记载。他的结论是,最多有五分之一的病例无疑是癫痫,但出现歇斯底里症状的病例占绝对多数。
他还强调,神游症通常是由某种“焦虑”(dysphoric)状态引起的,这种焦虑状态可能源于癫痫发作,可能源于事故造成的创伤性歇斯底里症(身体创伤,但不一定是头部损伤),也可能源于一些家庭或工作环境。“焦虑状态”(Dysphorische Zust.nde)成为德国神游症文献的一个标准短语,因为它似乎表明了某种原因、某种病因,尽管事实上它的意义宽泛,可以用来表示任何郁郁寡欢的状态和忧心忡忡的感觉。
海尔布隆纳还给出了神游症研究史上最有用的意见。神游症的发作最初是不由自主的,以癫痫、歇斯底里或其他某种可能的形式展现出来。但他写道,对逃离的心理偏好可能会成为一种习惯,长此以往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件可能也会引发神游症发作。在我看来,这种观点适合很多神游症患者,包括阿尔贝。海尔布隆纳并没有质疑神游症是伪造的。它足够真实,包括真正的失忆症和其他疾病。但是,它代表了一种心理习惯。在法律上,类似的习惯可以被用来免除责任。事实上,只有在有充分证据表明神游症已经成为习惯的情况下,司法鉴定才是适用的。
自此以后,这个领域的涵盖范围就扩大了。同年,即1903年,舒尔策发表了关于九个新病例的重要演讲,其中很多都具有典型意义,精彩纷呈。舒尔策宣称自己和海尔布隆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看法相同,但在某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是的,虽然有些医生在诊断癫痫时,显然过于自负了;但如果认为只有五分之一的“游荡癖”病例是癫痫,那就大错特错了。必须对舒尔策的新病例加以仔细衡量:它们是不是真的与歇斯底里症状无关。光是这些病例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各种病症间的数量比例!
次年,即1904年,德国医生发表了一篇类似于1889年法国论文的文章,这也是相关领域的首次尝试,标题为《一个歇斯底里病例中的神游症》。1895年雷蒙提出的综合征引起了德语世界内科医生们的注意。作者后来又观察到了另一个在异常状态下的歇斯底里症病例。 可以据此指出在德语世界范围内歇斯底里诊断的一个问题。夏尔科为男性歇斯底里症消除了女性化特征的污名,但德语世界的研究者接纳了这一污名,并且暗示它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不同学派的建立。在此过程中,大人物作用巨大。认为所有的神游症都源于癫痫的学说,现在被称为“克雷佩林学说”。
另一位研究者,通过对病理的详细临床观察,向多纳特提出了质疑;并且对三个新病例做了“显微镜”式的精确检查,发现了一个意识紊乱病例。一直以来,军队系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不穿制服的人在服兵役时擅离职守。1906年,大概发现了十八个新病例,每一起擅离职守事件都来自海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神游症不是一种成因简单的疾病。在1907年的一项研究中(针对三个强迫力引导的新病例),尤利乌斯·多纳特犹豫不决,他在考虑是把“旅行狂热症”最终限制在癫痫类中,还是将其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名词,与 1895年雷吉斯对法国式“旅行狂热症”所做的定义分类有所区别。
男人、男人、男人,无休止的男人!我们稍后还会看到很多儿童病例。难道德国医生从来没有在成年女性中发现“游荡癖”吗?多纳特的第二篇论文包括了一个女性病例,但是细节缺失。斯特凡·罗森塔尔(Stefan Rosental)描述了一位63岁妇女的悲伤往事。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伴有游荡癖和偏执行为的抑郁症》。施女士(Frau Sch.)在42岁时结婚,在此之前她常年独自生活。施女士的丈夫把她的毕生积蓄投资在一家被烧毁的锯木厂上。丈夫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他的亲戚便能够继承他所有的财产。施女士只能从维也纳的哥哥那里获取一点微薄的生活费。她住在柏林,有一次搭火车去波美拉尼亚拜访亲戚,她在一个小站下了车,漫无目的地游荡,当地警察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施女士说自己不想活了,她恨那些医院里的护理者。然后她被放了出来。施女士也曾先后五次去维也纳看望哥哥,但几乎每次都被借故打发走了;只有一次,她被允许待上两个星期。施女士最后一次看望哥哥,是在他和一个年轻女子结婚后;她连和哥哥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施女士在回柏林的途中半道下车,偷偷回到了维也纳,并在那里住院治疗。她很清楚自己有一种乐观妄想的倾向。这算偏执狂吗?这是一个关于病理学的故事吗?
至于儿童,当你仔细观察海尔布隆纳的表格时,你会发现很多神游症患者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的旅行。其中十四位患者首次神游的年龄在8—15岁。事实上,威廉·施利普斯(Wilhelm Schlieps)于1912年写道,虽然发现成人神游症是法国医生的贡献,但发现儿童神游症是德国精神病学领域的一个标志性胜利!恐惧法国、排斥法国、超越法国的心理,在舒尔策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都存在。但施利普斯声称的民族优势站不住脚。雷蒙在 1895年详细描述了一个男孩的经历,我称这个男孩为“汤姆·索亚”。施利普斯没有谈及第一批病例,只是宣称发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神游症,即儿童神游症。1909—1910年,贝农和弗鲁瓦萨 尔——一个隶属于警察总局的精神病医生团队,颇有影响,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过——发表了至少三篇关于儿童神游症的论文。 当时的医生想把儿童神游症诊断为自动症,就像现在的医生试图把儿童多重人格症纳入下一版本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手册》一样。
施利普斯的三个病人包括两个女孩,分别为11岁和12岁。她们确实是第一批有相关病历记录的女孩。施利普斯指出:只有男孩会去旅行,而女孩骄奢淫逸甚至在性生活方面放纵堕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男孩会去林间和田野漫步,而女孩则会说她们“一直在镇上散步”。让我们从退化的角度来看流浪儿童。他们被认为智力低下,且通常会在旅行中患上失忆症。
施利普斯研究的两个女孩从小就逃学,在外漂泊神游。其中一个女孩得有监护人陪伴她上学放学。两个女孩都患上了淋病,种种迹象表明,至少第一个女孩遭遇过强奸。人们该做些什么呢?施利普斯并没有帮到什么忙,尽管他提出了简单慎微的意见,至今仍在流行——让她们的父母擦亮双眼!看看是什么让孩子堕落如斯!去给孩子安排些心理咨询吧!护送你的孩子上学、放学,即使你不能做到,也请雇个人陪护她们!
总而言之,1898—1914年德国的游荡癖研究,类似于1887—1909年法国的神游症研究。军队在德国病例中的影响,甚至比在法国病例中更大。然而,人们对两国病例的看法,不尽相同。差别不只在于这一点:流浪的犹太人的形象似乎根本没有出现在德国。我认为这种说法苍白无力。法语和英语中的“流浪的犹太人”,在德语里是“永生的犹太人”。而神游症患者,是不能永生的。
更为重要的区别是,流浪对德国研究者来说,并不构成问题。是的,流浪是同一时期的普遍社会问题,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流浪问题的著作便不断出版。但在德国,与神游症相伴而生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军队的逃兵及帮助年轻的逃兵走出困境。比之重视军队士兵还是流浪者,其他的区别不太明显。我们讲述的德国故事不仅发生在十年后,而且地点转移到了中欧。这些人可能会西行,去英国、荷兰、法国或美国,故事字里行间所渗透出的,不仅是病人自身的悲伤,还有他周遭的整个外在世界的忧郁沮丧。在阅读了几十个病例的故事后,你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其中的每个人都带着左轮手枪旅行,并且时不时地用枪口对着自己的脑袋。但这不只是那些有游荡癖的人的真实情况,也可能是很多正常旅行者的真实情况。
事实上,德国的游荡癖并没有大肆流行。有具体病例为证。德国的医生们出于民族情感,不希望落后于法国同行。因此,他们想要找出诊断方法来拯救年轻的逃兵,使其免受残酷的惩罚。但在德国,神游症并没有生存的生态位。让我们来重新看一下之前提出的四个矢量。游荡癖甚至不符合当时德国既有的疾病分类法。它与当时受人关注的疾病无关。同样,它也没有文化极性和善恶二元的矢量,在此类矢量中,疯狂的旅行是可以悬浮的。没错,逃兵是可观察的,但他们是逃兵,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神游症患者。游荡癖本身没有社会性目的,也不附带其他的东西,它无法成为宣泄释放的一种方式。我提出的四个矢量,在此都未能造成明显影响。因此,在德国,有一些医生试图将神游症发作当作一种诊断方式来推广。但游荡癖本身,在德国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彻底但短暂的精神疾病。
(本文选摘自《疯狂旅行者:一种精神疾病的诞生与消散》,[加]伊恩·哈金著,傅益东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