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展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他一辈子只带了我一个研究生”

编者按:2018年是陈子展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9月29日,复旦大学中文系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要联合召开陈子展先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暨《陈子展文存》首发式。复旦大学中文系徐志啸教授是陈先生唯一带过的研究生。我们特此发表徐教授关于陈先生的回忆口述,以为纪念。
早年经历
陈先生出生在湖南长沙县青峰山村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后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师。五四运动后,陈先生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两年,后来因病辍学,回到湖南,寄住在长沙船山学社与湖南自修大学。此后,相继在湖南多所中学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在湖南一师,他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如李维汉、李达、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毛泽东等。我听他说起过,他曾跟毛泽东一块儿踢过足球,毛泽东踢前锋,他守门,其时毛泽东比他年长五岁。
1927年“马日事变”,他被卷进去了——作为“共党嫌疑分子”,遭到反动派通缉,长沙待不下去了,他逃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应田汉之邀,陈先生进入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授。1931年,陈先生旅居日本一年。1932年,他应谢六逸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开始是兼职教授,1937年起被聘为专职教授,同时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院系合并,他卸任系主任一职,郭绍虞先生当了系主任。之后,陈先生便一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八十年代曾由陈先生介绍,到北京拜访过廖沫沙先生,廖先生告诉我,他是陈先生的“三代学生”——小学、中学、大学,都是陈先生的学生,这大学,就是上海的南国艺术学院,他们师生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
杂文写作
陈先生三十年代在大学教课,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的开支,他就开始写杂文,主要为了赚点稿费,补贴家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骗饭吃”。陈先生的妻子过世后,曾又娶了一个,但时间不长,考虑到孩子关系,这段婚姻很快就结束了。他的孩子都是前妻所生,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他的后半生,都由小儿子陪伴照顾。
陈先生的杂文大多短小精悍、刺中时弊,辞锋之犀利、讽刺之辛辣、识见之广博,在当时文坛堪称翘楚。这些杂文发表时,多以楚狂、楚狂老人、湖南牛、大牛等笔名行世。他笔名中的这个“牛”字,很能体现湖南人的个性:脾气有点倔。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在《申报·自由谈》合订本“序”中曾写道:如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要论述《新青年》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不能不写,它对杂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陈子展先生正是这个报纸副刊的经常撰稿人。陈先生在《申报 自由谈》发表的杂文数量,堪与鲁迅比肩。
学术研究
陈先生早期在复旦任教时,先是研究近代文学,先后出版了两本书——《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这两部书集中阐发了1898年至1928年三十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及其演变,在当时很有影响,即便从今天看来,这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也依然具有开创性意义,为近代文学研究界所称道、引述。在这两部近代文学史中,陈先生专门论述了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所忽视,而在近代时期曾出现的旧体诗词创作及其作者群——宋诗运动、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四大词人等。在陈先生看来,1898年应是“近代文学”的真正开端:原因在于,甲午战败对中国的刺激太大了,警醒了中国人,文人们才从八股文中解放出来,接受外来影响,开始倡导“新文体”,从而产生了“诗界革命”乃至文学革命。
这以后,陈先生开始教中国古代文学,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讲话》上、中、下三册,以及《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后合编为《唐宋文学史》行世)。另外,陈先生还曾专门开设过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并专门编写了讲义,此讲义在时间上要早于国内不少著名文学批评史家的批评史论著。
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陈先生开始涉足《诗经》语译——将《诗经》译成白话文刊登在报纸上,发现读者反应不错,颇受欢迎,由此,陈先生对《诗经》产生了浓厚兴趣,结合教学,他开始着手对“诗三百”作逐一的注释、今译、评论和研究,他的《诗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问世于三十年代的《诗经语译》;第二阶段,五十年代出版《国风选译》与《雅颂选译》;第三阶段,八十年代集大成的《诗经直解》出版,此后,又有《诗三百解题》问世。可以说,陈先生毕生用力最多、体现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首先是《诗经》研究,其次是晚年的《楚辞》研究。

陈先生认为,《诗经》三百多篇作品从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反映表现了上古时代的社会生活,它是上古社会和历史的一面镜子,堪称上古社会的百科全书。对历来争议较大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孔子删诗说、采诗说、诗序作者、风雅颂定义等,陈先生都旗帜鲜明地表述了个人看法。为了解析诗篇本义,特别是其中可能涉及的历史与社会的多学科广博知识,陈先生都会予以详尽的引证,而这些引证的材料,很多要涉及天文、地理、历史、风俗、生物、考古、农业、军事、经济等多学科、多层面,他都不厌其烦地引证各种资料予以阐释和说明,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有:《曹风·蜉蝣》《小雅·信南山》《小雅·宾之初筵》《周颂·良耜》《周颂·潜》等诗篇。我见过他的一个笔记本,记录了各种古代史料的原始资料,全部用毛笔小楷手抄。与学界其他《诗经》研究学者不同的是,陈先生特别注重对最新文物出土考古资料予以发掘与利用,及时地将这些资料运用于他的《诗经》诠释中,从而对这部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尽可能地作出切合历史和时代的准确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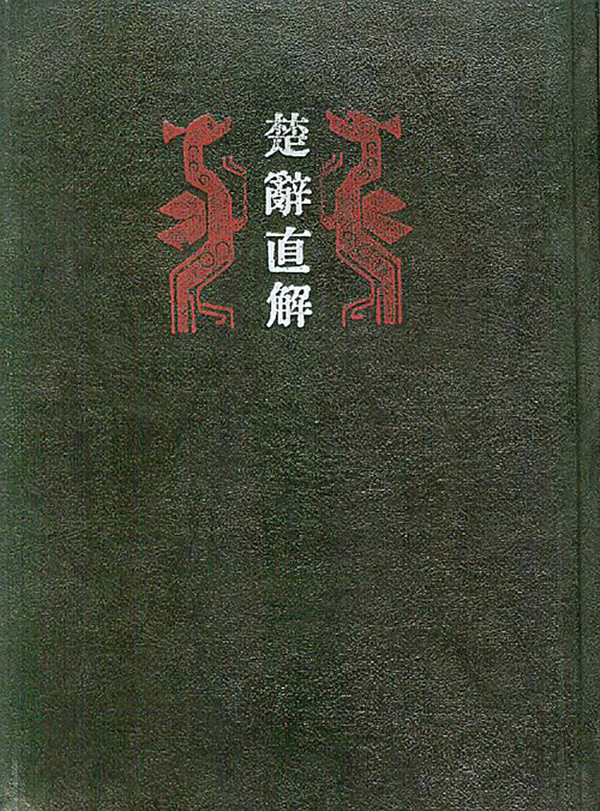
陈先生的《楚辞》研究开始于六十年代。他说自己搞《楚辞》,是既和古人“抬杠子”,也和今人“抬杠子”,他要爬梳、澄清历来在楚辞研究上笼罩的迷雾。我记得他当时明确说,他不赞同武汉大学刘永济教授的观点。由此,他下决心对楚辞作系统全面的梳理,对历代和现代的各家注本作逐家评述,而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陈先生翻遍了历代的《楚辞》注本,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恩和西方许多理论家关于人类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论著,参考了大量的上古时代的出土文物资料和历代文献,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待和阐释楚辞中表现的上古社会的历史与文化。
政治运动
陈先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起因可能与他的“湖南牛”倔脾气有点关系,他老人家为人正直、说话直率,绝不对人阿谀奉承。他根本不可能反对共产党,只是对基层领导有些不当做法表示不满,说了些实在话。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当然不到学校上课了,蓄须以示抗议。后来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他当年的朋友和学生,知道了他的这一情况,都觉得很奇怪:陈子展怎么可能反党?他是党的同路人啊。由此,他成了全国最早一批的“脱帽右派”。
脱帽以后,陈先生基本不上课了,所以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怎么波及他。但“文革”他还是被卷入了,参加了集体劳动,吴中杰老师的文章里曾提到,他和陈先生是一个战斗队的。那个时候,复旦全校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都被卷进去了。
学人交游
和陈先生来往比较多的中文系老教授,我知道的有赵景深、贾植芳、杜月村等,王运熙当时属于他指导的青年教师。赵景深先生曾经这么评价陈先生的近代文学史著作:“这本书是我极爱读的。坊间有许多文学史的著作,大都是把别人的议论掇拾成篇,毫无生发,而造句行文,又多枯燥。本书则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且时带诙谐。书中文笔流畅,条理清楚,对文学大势说的非常清楚,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陈先生跟周谷城先生关系很好,他们都是湖南人。我七十年代末到陈先生家里上课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辆三轮车停在他家门口,进门以后才知道,原来这是周谷城先生的包车,其时两人相谈正欢。两位先生因友情深厚,经常来往。不过,周谷城先生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后,陈先生就主动不和他来往了。陈先生这个人就是这个特点,他绝不主动逢迎巴结身居高位者,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他根本没想到去找那些已是国家领导人的早年朋友和学生。
同辈或晚辈的学人里,陈先生很欣赏湖南的杨树达和上海的杨廷福、范祥雍。他多次在我面前提到杨树达先生,说他学问好,是湖南人中的杰出学者。杨廷福是做隋唐史的,在上海教育学院任教,陈先生和我多次讲到他的学问好,杨廷福一直没离开上海教育学院,据说是因为教育学院领导对他太好了,杨觉得离开有点对不住领导。陈先生的《楚辞直解》一书扉页上有“范祥雍、杜月村校阅”,这是陈先生这部著作,曾请范、杜两人共同参与校阅。陈先生在我面前,曾多次提到范祥雍,说他学问很不错。
师生情谊
我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生,恢复高考之后,1977年末考上了复旦历史系,1978年初入学,属于七七级本科生。入学后,第二年跨系跳级考上了中文系研究生,从此拜到了陈先生门下。在我看来,陈先生的名望和学问都是最好的,我后来才知道,他一辈子只带了我一个研究生。他当年招我的时候已经八十一岁了,比我整整大五十岁,属于我的爷爷辈。
刚入学的时候,陈先生家住长乐路,我每周星期六下午去他家上课,他开了书单让我读书,包括《说文解字》《尔雅》《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以及涉及先秦两汉时代的文史典籍,我读后写读书报告,向他汇报。平时我也会按照他的吩咐,帮他买书,做些协助他研究工作的杂事。当时钱锺书的《管锥编》刚出版不久,他对此书评价很高,特意让我帮他去买。
陈先生有几件事情让我特别感动。“文革”后楚辞学界第一次在湖北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湖北方面专门给陈先生发了邀请函,当时陈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不可能亲自与会,但他很郑重地写了两封推荐信,一封答复湖北方面,一封给复旦中文系——推荐我带着当时已基本完成还没参加答辩的硕士论文,代表他参加会议。但这事最终没成功,因中文系认为,研究生代替导师参加学术会议,系里从没此先例。1984年,成都召开楚辞研究国际会议,批驳日本学者对屈原的怀疑否定,陈先生又一次接到邀请,也又一次嘱我撰写论文,推荐我代他参加会议,当时我已毕业留系工作,任他的助手,他老人家又一次郑重地用毛笔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成都邀请方,一封推荐信写给中文系,但中文系还是没同意,理由是成都太远了。陈先生这两次主动热情推荐,让我这个还没出茅庐的学生十分感动,陈先生这是有意识地在推我走向学术界。
我读研时,学校规定有一笔研究生科研经费可以去外地访学,陈先生专门给我写了多封介绍信,让我去拜访一些学界专家,其中包括殷孟伦、常任侠、廖沫沙、林庚等,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或学生,有他的介绍信,我肯定不会被拒之于门外,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求教机会。我毕业留校后,先做陈先生的学术助手,后来陈先生正式退休,他建议我到北大继续深造,特别推荐我到北大林庚先生门下,攻读博士。
陈先生和林庚先生父子都比较熟悉,林庚先生的父亲林志钧老先生是清华的名教授,也曾是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之一,曾受梁启超生前所托,负责整理编辑《饮冰室合集》。我是带着陈先生的推荐信,专程北上,到北大林府拜访林庚先生的,林先生看了陈子展先生的推荐信后,对我十分热情,在全面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生。入学后我才知道,林先生招我时就想要我毕业后留在北大,当他的学术助手。但遗憾的是,我妻子执意不肯北上,我不得不忍痛割爱,离开北大,离开林先生。这方面情况,我在怀念林庚先生的专文中曾详细写到。
陈先生晚年一直想回湖南,和我讲了多次,那个时候他已年近九十。陈先生是1992年去世的,当时我已经从北大重回复旦了,但不巧的是,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好不在上海,回到上海后才得悉噩耗,很遗憾没能为他送行——他没让举行任何辞世仪式,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符合他的性格和愿望,他去世前就早定了“四不”原则: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不留骨灰,不发讣告。
当然,最后一条是肯定做不到的,复旦还是按惯例发了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