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上任:清朝知县构筑人际关系“指南”
知县与“官”
对知县而言,“官”当中,特别是从知府以上到督抚为止的上司,毋庸置疑乃是重要的存在。知县时常要接受来自上司的考核(被称为考成),其评价的好坏不只是吏部知晓,有的时候,也会直接传到皇帝耳里,对于知县日后的官僚生涯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知县在赴任之际,若有机会与上司接触的话,是绝对不允许失败的。除了《福惠全书》以外,其他的官箴书也提到了许多与上司应对的方法。我们来看其中的几个例子。
首先,与黄六鸿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潘杓灿在其官箴书《未信编》里,针对赴任之初与上司应对的方法,有以下的建议:
亲管上司乃系仕途中祖父伯叔,安得不速请见。同城者,到任三日,例俱禀参。即不同城,如本府本道,三日亦应次第晋谒。院司驻节省会,与本治相远者,三月之内,定须往谒。断不可惜费这巡。盖一官初至,在上司亦欲观其才品。苟或愆期,不怒其怠慢,则疑其猥懦。难前而厌心生矣。其相见仪注,着礼房开送,依例遵行。其举止应对,务必舒徐周到,敬慎大雅,傲谄俱非所宜。嗣后不时相见,应将钱粮刑狱以及紧要之事,开一小帖,携带观览,以便陈白答问。
针对与上司的日常交际,他也有以下建议:
交际之礼,居官必不可缺。凡庆令节,上下同寮,例用馈送。同城者,只开揭帖亲送。远者上司宜大启,同察宜小启,差役呈送。其献新祝贺谢候等事,必周旋以图和好。慢事惜费者多致参商也。
从以上内容可知,潘杓灿特别强调:即使是形式上的礼仪,也不可轻忽。又,大约在黄六鸿所处时代的100年后,汪辉祖针对与上司应对的方法,留下了较多的文章:
获上是治民第一义,非奉承诡随之谓也。为下有分,恃才则傲,固宠则谄,皆取咎之道。既为上官,则性情才干不必尽同。大约天分必高,历事必久,阅人必多。我以朴实自居,必能为所鉴谅。相浃以诚,相孚以信,遇事有难处之时,不难从容婉达,慷慨立陈,庶几可以亲民,可以尽职。
天下无受欺者。翔在上官,一言不实,为上官所疑,动辄得咎,无一而可。故遇事有难为及案多牵室,且积诚沥惘陈禀上官,自获周行之示。若诳语支吾,未有不获谴者。苍猾之名,宦途大忌。
事有未惬于志者,上官不妨婉诤,察友自可昌言。如果理明词达,必荷听从。若不敢面陈而退有臧否,交友不可,况事上乎。且传述之人,词气不无增减,稍失其真,更益闻者之怒。惟口兴戎,可畏也。
关于与上司应对的方法,我们已知《福惠全书》建议知县要克制傲慢的个性,用尊敬与忠勤的态度与其应对,并且留意不要做出失礼的行为,这才是获得上司好评的秘诀,而诸如此类大同小异的注意事项屡屡出现于清代的许多官箴书中,特别是从强调要获得上司信赖的这一点来看,共通点极多。反过来说,如果未能获得上司信赖的话,就代表着地方官无法实行地方行政。
不过,虽然汪辉祖认为“既为上官,则性情才干不必尽同”,但是,官箴书所说的“上司”相对来说指的就是“耿直的”上司,在官箴书里,会歧视他人的上司,或毫无责任感将自己的失败推卸给部下的上司,或找借口勒索财物的上司几乎不会登场,甚至是滥用权力来骚扰下属的上司,官箴书亦未触及他们的存在。以这种恶劣的上司并不存在于世间为前提,建议知县要如何与“耿直的”上司正面应对的正是官箴书,若是如此的话,对于上司的“待人法”可说是告诉知县要从官僚道德规范的延长线上来进行应对。但是,对于实际赴任后将一己之身置于官僚社会当中的知县而言,尽管官箴书耳提命面地提醒知县“惟在敬与勤而已”或是“毋过谄”,但是,这些或许都只是华而不实的乌托邦吧。
知县与“吏”
对于“吏”只字未提的官箴书可说是完全不存在,几乎所有的官箴书都提到了与胥吏或衙役这类衙门里的下级官吏应对的方法。如同宫崎市定所言:“如果士大夫想要诚实地进行有责任的政治的话,就必须要通晓胥吏政治的实际状况。为此出现于世人面前的正是种种官箴书。”这是因为所谓官箴书乃是畅谈应付胥吏方法的书籍。《福惠全书》建议知县对“吏”要以信赏必罚为基本,即使是尘埃般的小事,也要用毫不妥协的坚定态度去应对。若是如此的话,其他的官箴书又是如何建议的呢?这里仅列举较有特色的例子。
首先,潘杓灿有如下的建议:
吏书之弊,古今通患。其人不可缺而其势最亲。惟其最亲,故久而必至无所畏。唯其不可缺,故久而必至于奸欲。其畏而无弊莫若严于自律。而常加稽察,勿使主持事务,说事过钱。门子须择慎实者,一月换班,上堂令远立丈许,机密事情,勿使觇知,以防漏泄。皂快、民壮两傍分立,不许杂乱拥挤。凡事不许代禀,以防谁骗。冗役宜汰。盖少一人,即少一民耗。
接着,孙铉在其官箴书《为政第一编》里,则是指出:
官有盘役,如书之有蝉,木之有蛀。残蚀既久,书破木空。一官而遭群盘,其官箴有不速坏者乎。书役之弊,卷内诸条言之极详,其弊也,皆其盘也。知其弊而驭之以法,弊无由而生,盘亦何由而入。诚恐奸胥滑吏或蠹我国,或蠹我民,平时不觉受其欺瞒。设一旦上台风闻,或被告发,则投鼠而碎其器,批枝而动其根。蠹虽万死,何足为惜。大之连累本官,小之亦必受上台之戒饬。百口谢通,难骂失察之愆。故平日之待此辈于趋承奔走之下,孰为老成而谨饬,孰为少壮而殷勤,孰为似信实奸,孰为大整积滑。其败乃公事者,固必锄而去之。即有恶贯未盈,蠹形未著,或亲有所试,或别有所闻,亦必先之以戒词,继之以革役。不待上宪访拿,士民越控,以几先之哲,而免事后之嗟。幸毋明知故纵养虎以自害也。慎之,慎之。
又,汪辉祖亦有以下的建议:
宽以待百姓,严以驭吏役,治体之大凡也。然严非刑责而已,赏之以道,亦严也。以其才尚可用,宜罚而姑贷之,即玩法所自来矣。有功必录,不须抵过。有过必罚,不准议功。随罚随用,使之有以自效,知刑赏皆所自取,而官无成心,则人人畏法急公,事无不办。姑息养奸,驭吏役者,所当切戒。
接着,田文镜在《钦颁州县事宜》当中写道:
官有胥吏,原以供书写而备差遣。其中虽不乏勤慎之人,然衙门习气,营私舞弊者居多。苟本官严于稽查,善于驾驭,则奸猾者亦皆畏法而敛迹,否则纵恣无忌。虽勤慎者亦且相率而效尤。此胥吏之不可不防也。
赴任之初,迎接跟随,皆是窥探之计。即任之日,左右前后,无非伺察之人。家人亲友,择官之所亲信者,而先致殷勤。举止动静,就官之所喜好者,而巧为迎合。官而爱财,彼则诱以巧取之方,而于中染指。官而任性,彼则激以动怒之语,而自作威福。官而无才,彼则从旁献策,而明操其权柄。官而多疑,彼则因事浸润,而暗用其机谋。官喜偏听,彼则密讦人之阴私,以倾陷其所仇,而快其私您。官好慈祥,彼则扬言人之冤苦,以周全其所托,而图其重贿。官恶受赃犯法,彼则先以守法奉公取官之信。官喜急公办事,彼则先以小忠小信结官之心。官如强干,彼则倚官势以凌人。官如软弱,彼则卖官法以徇己。官如任用家人,彼则贿通家人以为内应。官如听信乡绅,彼则联结乡绅以为外援。舞文作弊,则云一时疏忽,出票催规,则曰历年旧例。凡此皆不可不严防者也。
至于办理文案,则防其抽换按捺,经管钱粮,则防其侵收吞蚀。捕役缉盗,则防其私拷诬良。件作验尸,则防其匿伤混报。一役有一役之弊,一事有一事之弊。在胥吏惟思作弊,故无一事不欲瞒官。而官首在除弊,故无一事不可不防胥吏。盖胥吏之作奸犯科,全视乎官之性情所贵。喜怒不形,使彼无所揣摩,嚬笑不假,使彼无所倚恃。而最要者廉以律己,严以执法,明以烛奸,勤以察弊。
如点经承,点柜书,断不可因仍陋规,收受分文。换头役,出差票,断不可纵令家人,索取丝毫。否则不但有欲无刚,不能禁其作弊,亦且立身不正。何颜与此辈相对。苟能遵而行之,则官无纵容失察之愆,民无恐赫索诈之累。而此辈之心思才力,亦皆用之于办理公事之中,为我所用,而不为其所欺,则胥吏亦可收臂指之助矣。

田文镜像
知县执政之际,于衙门负责实务的下级官吏堪称知县的左右手,而这些皆是对付下级官吏的方法,往往会大量出现在官箴书里。这些官箴书的共通点乃是,与“吏”相关的内容自始至终都是一贯的,例如,必须对下级官吏抱持猜疑的态度,或是如何不让他们有机可乘,并且压制他们,不让他们从事不当行为,甚至是如何才能免除自身监督不周到的责任。对于“吏”的应对方法,很明显地,与对于身为上司或是同僚的“官”有所不同,其中,对在同一个职场一起进行业务的人,官箴书并未要求知县有身为工作伙伴的连带意识,而是劝告知县要心怀紧张和警戒,与他们保持距离,并且强调所谓“吏”乃是与知县这种知识分子处于不同世界的存在。因此,对这种处于不同世界的集团,若是搞砸应对方法的话,就代表知县所主导的县政业务将会无法实施。因此,许多官箴书都详细地记载了与他们打交道的方法,新科知县也是最想知道其中诀窍的人,在这个情况下,官箴书成了实用的信息来源。另外,官箴书被视为对付胥吏的参考书,其理由也可说是出自这一点。
知县与“士”
最后是关于“士”的部分。关于17世纪的官箴书,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其中的待人法,特别是关于“士”的部分,官箴书花费了许多笔墨在这里。知县执政的时候,必须重视的不只是官僚机构的官吏与胥吏,还有在当地拥有固有发言权的现任官僚,以及具备官僚经验的乡绅和与此相联系的生员,也就是本地知识分子(“士”)。他们不论好坏都对地方行政拥有影响力,因此,一方面,他们既是辅助知县为地方行政提供建言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利害不一致的状况发生的话,他们同时也是容易转化为抵抗知县的势力。以下,我们将再次检讨其具体应对方法的内容。
有关于此,孙铵认为:
士为四民之首,原宜刮目相看,重之者非独贡监青衿,即赴考儒童,潜修墨士。凡平时接见,或讼案干连,皆须宽容培护,勿得概以凌贱加之。优之以礼貌,徒施要结之文。或绅士钱粮,催征得体。或屡空学究,周济无虚,季考观风,花红不吝。丁忧事故,勒指无加。凡可作兴之处,无不尽情当理。身受者,既感隆恩,闻风者亦衔雅意。
平时隆重,门色咸知,一旦有抗粮玩法,及把持官府,起灭讼词等一切不肖劣行,尽法申究,绝不容情,以向来之雨露为此际之雷霆。虽遭修辱,犹戴恩勤矣。万勿因一二豪绅劣士遂谓此辈不堪作养,令其怨望,腾作谤声。学校之口甚于没字之碑。传闻不实,有碍官箴不浅。况文运盛衰,关系地方隆替。重斯文,正所以培国运。又乌得视同末节而不急为留意乎。
又,汪辉祖认为:
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朝廷之法纪不能尽喻于民,而士易解析,谕之于士,使转谕于民,则道易明,而教易行。境有良士,所以辅官宣化也。且各乡树艺异宜,旱潦异势,淳漓异习,某乡有无地匪,某乡有无盗贼,吏役之言,不足为据。博采周谘,惟士是赖,故礼士为行政要务。
“士”扮演着衔接官与民,并且将行政渗透至民的角色,因此,为了获得他们的协助,一方面,汪辉祖认为必须礼遇“士”,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有以下看法:
第士之贤否,正自难齐,概从优礼,易受欺蔽。自重之士,必不肯仆仆请见,冒昧陈言,愈亲之,而踪迹愈远者,宜敬而信之。若无故晋谒,指挥唯命,非中无定见,即意有干求。甚或交结仆胥,伺探动静,招摇指撞,弊难枚举。是士之贼也,又断断不可轻假词色,堕其术中。故能浚知人之明,始可得尊贤之益。
要将乡绅及与此相关的生员视为地方行政的协助者,拉拢至我方,抑或将其视为地方行政的抵抗势力,对其进行压制?这对知县而言乃是极大的课题,不过,拥有官僚经验的人们都深知:选择后者的话,其代价太大,并非合理的选项。因此,就算是不肯合作的“士”,还是要特别关照,才是上上策。
从以上内容可知,拥有官僚经验的前辈们透过自身的经验总算领会到官僚们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后,对于那些挥舞着观念上的正义旗帜,结果往往在人际关系方面尝尽苦头的年轻后辈们,将自身经验整理为文章,传授给这些后辈们的实用忠告正是官箴书所提倡的待人法。
话虽如此,对于实际即将赴任的官僚而言,他们心底真正想要知道的究竞是什么事情呢?《儒林外史》有与此相关的情节,也就是身为南昌知府前往当地赴任的王惠向前任知府蓬太守的儿子景玉询问当地状况的情节,如下:
须臾,摆上酒来,奉席坐下。王太守慢慢问道:“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蓬公子道:“南昌人情,鄙野有余,巧诈不足。若说地方出产及词讼之事,家君在此,准的词讼甚少。若非纲常伦纪大事,其余户婚田土,都批到县里去,务在安辑,与民休息。至于处处利薮,也绝不耐烦去搜剔他。或者有,也不可知。但只问着晚生,便是‘间道于盲’了。”王太守笑道:“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而今也不甚确了。”当下酒过数巡,蓬公子见他问的都是些鄙陋不过的话,因又说起:“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筒刑清,所以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都也吟啸自若。还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王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息却也有趣的紧。”蓬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样?”蓬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由此看来,官箴书所阐述的世界或许只是一种理想吧。
官箴书所示的待民观
以上,关于官箴书对于“官”“吏”“士”这三种“围绕在知县身边的人群”所提倡的应对方法,我们已经进行了概观了,那么,对于与这三种人群性质迥异的“民”,也就是一般民众,官箴书认为要采取何种具体且有效的方法呢?只要知县标榜着自己是“亲民之官”“父母官”的话,官箴书的待人法里,出现与其相关的言论,也就绝非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我们先看结论的话可知:如前所述,官箴书极为详细地描述了知县与“官”“吏”“士”应对的方法,但是,相较之下,关于民众的部分自始至终皆为抽象性、观念性的描述,就这个意义来看,可说是欠缺了足以作为实用信息的具体性描述。其理由为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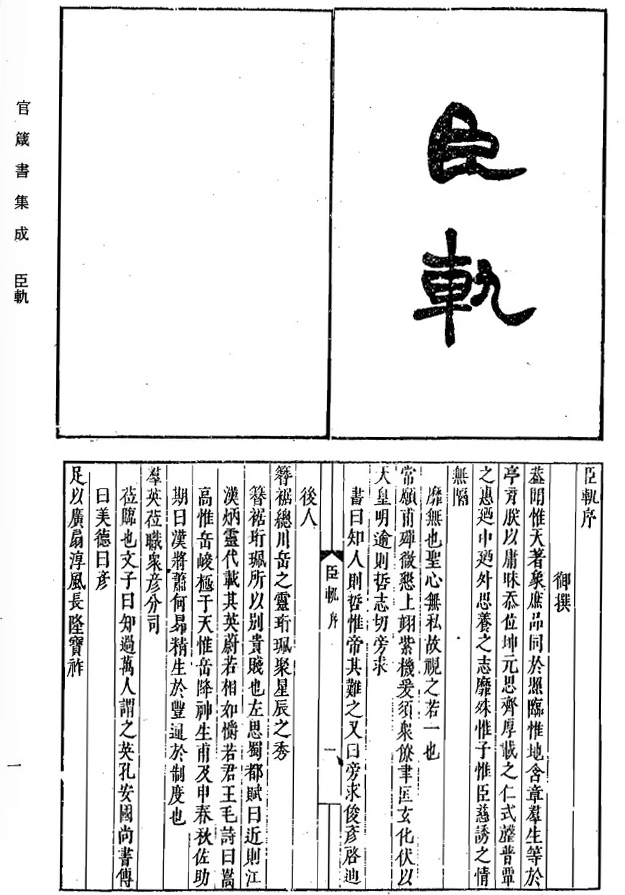
《官箴书集成》
官箴书往往不会将与民众的应对方法放进所谓“待人”的范畴之中,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理由。就笔者所知,针对待人法设立了特别的篇目(如“待人”或是“接人”等)且进行相关议论的清代官箴书,其多数重点在于与执政现场的人们的应对方法上面,但是这些自始至终都是绕着上司、同僚、下属、胥吏、衙役、长随、幕友、乡绅、生员打转,毫无与民众相关的内容。唯一的例外乃是《图民录》,其中可见与民应对的条目,不过,这个记载仅仅引用了圣人言论的官僚道德规范而已,并未脱离观念性描述的领域。至于《福惠全书》则是完全没有设立与民众相关的条目。
话虽如此,官箴书并非完全省略了与民众应对的方法。但是,其所提到的民众多限于特定的范畴之中,我认为这是第二个理由。例如,汪辉祖有如下看法:
剽悍之徒,生事害人,此莠民也。不治则已,治则必宜使之畏法,可以破其胆,可以铩其翼。如不严治不如且不治。盖不遽治,若辈犹惧有治之者。治与不治等,将法可玩,而气愈横,不至殃民罹辟不止。
这里的所谓“莠民”乃是与“良民”相反的存在,意味着他们是一种扰乱秩序,对“良民”带来危害,亟须“治”,也就是予以处罚的存在。这种民众也被称为“奸民”“刁民”“猾民”“黠民”等,其中特定的民众更是被称为“棍徒”或是“地棍”。不过,这些民众若是出现于官箴书的话,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妨害知县行政的存在,因此,官箴书认为必须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统制,甚至要求知县必须毫不留情地处分违反者。但是,他们说到底也是“民”,于是,这和先前官箴书提倡必须对万民普遍施予仁爱的教诲之间,可说是出现了矛盾。
以上诸点也许是官箴书对于所谓“良民”并无太大兴趣的证据吧。
对于仅仅三年的任期结束后,就必须调动至其他地方的知县来说,应该重视的人群乃是以上司为首的“官”,协助行政实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吏”,以及实质上支持着地方行政工作的“士”,短期间的任务必须建立在他们的协助和支援之下,才能够圆满完成。因此,知县在这期间实在没有必要为了贯彻“亲民”这个理想,而采取对他们不利的行动,也无必要让他们与自己为敌。若提到知县对于“民”的关心,应该集中在那些对知县的统治和安稳的官僚生活带来威胁的“莠民”身上,只要学会彻底管理“莠民”的技术,这样就足够了。这乃是实际担任知县后才能各自体会到的心境,而官箴书正是抢先一步将这种心境传授给即将担任官僚的后辈们。官箴书鲜少提到一般民众的这个特征应该也是受此影响不少。
这种官箴书的特征可说是官箴书整体的共通点。因此,刊行于宋元时代的官箴书也具备了这种特征。不过,正如“洁己”“正己”“尽己”“省己”等条目所示,宋元时代的官箴书在强调身为儒家精英分子的地方官必须律己的同时,也提到了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的“爱民”或是“亲民”等概念,这些概念纵然是一种观念性道德规范,不过宋元时代的官箴书往往将其置于较为中心的地位。相较之下,随着时代的更迭,比起道德规范,明清时代的官箴书更加重视实践性、具体性的执行任务须知,特别是《福惠全书》或是《学治臆说》等,这些大获好评且广为流传的官箴书更是强烈拥有这种倾向。方大混在刊行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官箴书《平平言》里,列举了即将担任地方官的人们必读的书籍,其中官箴书的部分就有十种,分别是《实政录》《五种遗规》《福惠全书》《图民录》《牧令书》《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节钞》《庸吏庸言》《蜀僚问答》。这些都是重视具体实践方法的实用书籍,特别是方大混完全没有提到宋元时代的官箴书,这一点饶富深趣。这可说是如实反映了清末的知县究竞希望透过官箴书获得何种信息吧。透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隐约窥见官箴书究竞是何种书籍。一方面,针对即将担任知县的儒家精英分子在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应该遵守哪些戒律,官箴书展开了一种可说是“理想”的道德论。另一方面,官箴书也提示了不少儒家精英分子以知县的身份实践“地方统治”之际,必须遵守的注意事项,此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则是一种可说是吐露了“现实”的待人论。官箴书原本就同时具备了这两种面貌,这乃是官箴书的特色。当中要求知县必须扮演“亲民之官”或是“父母官”,正是为了强调前者之故。但是,即将担任知县的人们之所以需要官箴书,反倒是出自后者的动机。在清代大获好评的官箴书都巧妙地传授了这种“现实”。
顺道一提,乾隆年间出身于江苏省松江府的朱椿有以下看法:
州县官职在亲民。境地宽广,人民散处,官住衙门,除审事比较外,不能与民相见,焉能与民相亲。甚有审事则惟了结本案,比较则惟按欠责比,何曾有一语教训乡民。屡奉上谕,训饬州县巡历乡村,所以尽亲民之职守,行亲民之实政也。凡踏勘田山,相验人命,所到之处,不妨停骖稍坐,招集士民耆老咨询慰间。僻地不常经过者,不妨迂道一行,到任数月半载之后,必须处处皆到,处处之民皆得与官长相见听话,乃不负巡历之行,克尽亲民之职。常见有在任数年而足迹未历四境者,名日亲民,实同遥制。如此那有善政善教。
就地方官的规范而言,朱椿的意见也许是一种“主流”。但是,从他必须重申上述意见的这一点来看,现实中,多数知县其实是不愿意与“民”有太多接触的,因此,要他们成为“亲民之官”实为天方夜谭。
如前所述,雍正帝在上谕里,期待着知县们能够成为“亲民之官”,委托他们于各个地方执行王朝国家理想中的对人民的统治。不过,如果“亲民之官”在现实中只是“理想”的话,那么,所谓皇帝的统治也不过是理想之下的一种产物罢了。

(本文摘自山本英史著《新官上任:清代地方官及其政治生态》,魏郁欣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