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钱穆的《国史大纲》
一
近来,钱穆研究如火如荼。2020年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逝世三十周年,学界将相关论文汇集为《重访钱穆》(上、下)一书,于2021年由秀威资讯出版。两年后的2023年7月,台湾商务印书馆推出《重返〈国史大纲〉:钱穆与当代史学家的对话》(以下简称《重返》)。由于本书试图吸引普通读者,就其体例而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集,除了个别文章外,大都没有多少脚注。《重访钱穆》集结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等地60位学者的论文,涉及钱穆研究的方方面面,而《重返》的撰稿人均为在台湾地区任职的学者,主题相对集中,即解读钱穆的《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钱穆在抗战初期完成、由商务印书馆(上海)于1940年初版的一部通史,影响深远。该书在一些地区曾作为高等院校的历史教科书,启迪了一个时代的莘莘学子。实际上,在台湾地区的中国通史课程上,迄今仍然可见《大纲》的影子。而且,《大纲》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颇受欢迎,长期出现在畅销书榜单上。也就是说,《大纲》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之间基本上被奉为一部经典。如今,北京、台湾和香港的商务印书馆都有各自的版本。2022年春天,台湾商务印书馆策划了有关《大纲》的系列讲座,本书大体就是在11位学者12场讲座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重访》分两个部分,其一是“钱穆的思想世界”,由前七篇文章组成,主要着眼于钱穆的学思历程,侧重于整体上把握《大纲》的意蕴;其二是“《国史大纲》的历史世界”,由后五篇文章组成,基本上是根据断代和专题来品鉴《大纲》。该书目次如下:
历史时间是延续的吗?——钱穆与民国学术(王汎森)
需要一种新的国史——钱穆与《国史大纲》(王健文)
开放性思考的历史叙事——《国史大纲》与通史精神(阎鸿中)
如何阅读《国史大纲》——经典·学说·史料(游逸飞)
情的融合?——《国史大纲》与域外思想(孔令伟)
士之自觉——能动性问题与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国史大纲》(徐兆安)
钱穆与余英时(王汎森)
从文献中抽绎时代精神——《国史大纲》的上古史(高震寰)
大时代的气运盛衰——《国史大纲》的中古史(傅扬)
立基于社会治理——《国史大纲》中古代至中古的宗教(许凯翔)
以政治为走向的书写——《国史大纲》的宋元史(郑丞良)
专制下的经济与学术——《国史大纲》的明清史(丘文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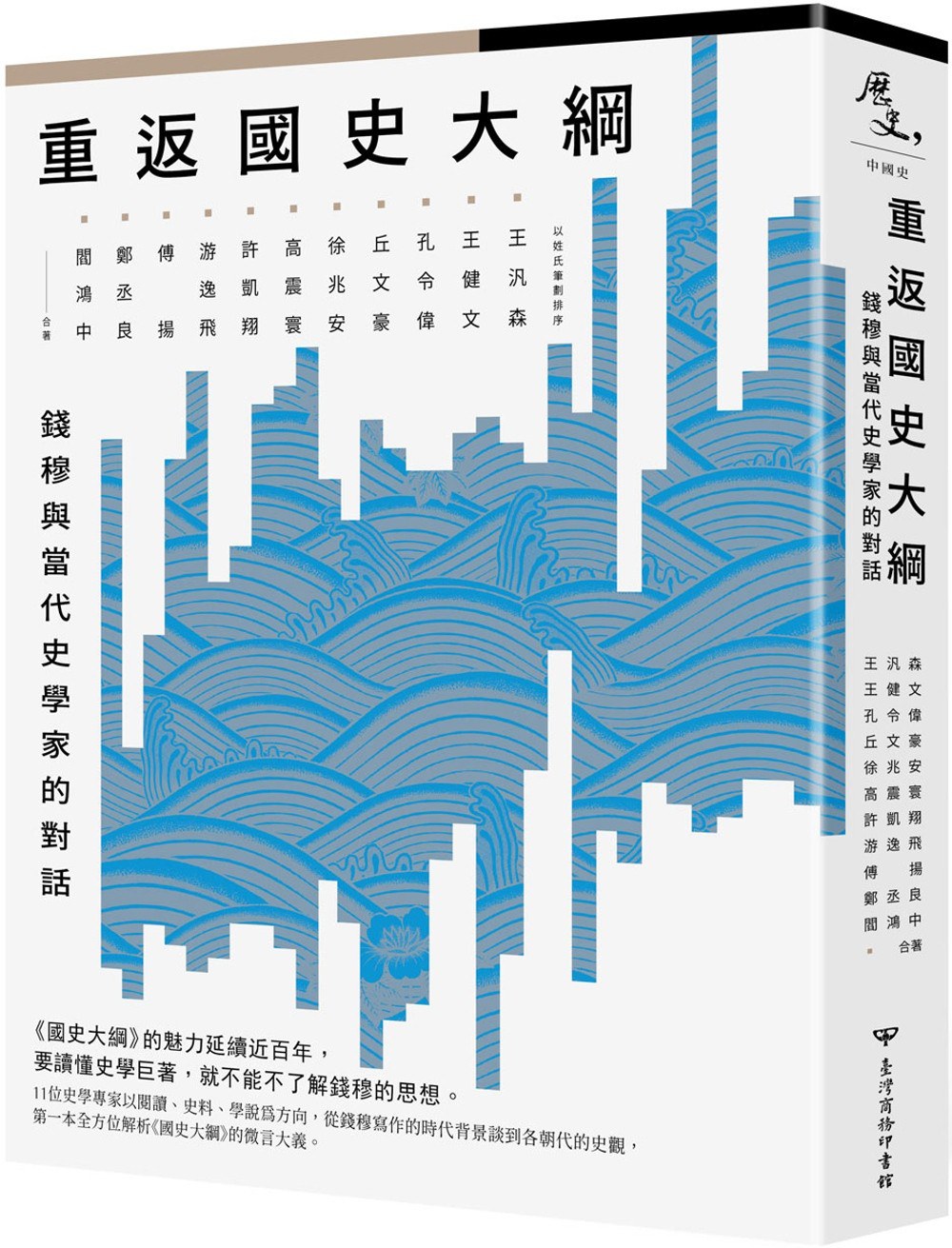 二
二下面,对各章内容稍作介绍。
第一编“钱穆的思想世界”第一篇和最后一篇都是王汎森撰写的。王氏师从余英时,属于钱穆的再传弟子。其实,王氏此前写过一篇《钱穆与民国学风》(收入氏著《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可与本书两文对照阅读。《历史时间是延续的吗?》(下文简称《历史时间》)一文认为,《大纲》的写作与民国时期的七个学术思想议题不无关系。该文就从这些议题入手,讨论钱穆与民国学术的关系。这七个议题分别是:①在乡的新知识分子,②1930年代的三种历史观(即《大纲》引论中所说的三个派别——传统派、宣传派、科学派),③评判历史的视角(内部抑或外部),④文明与文化的态度,⑤新通史的写作,⑥历史时间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⑦中国历史的“本质”。
王健文主要从“国族”的角度探讨《大纲》的形成及其意义。为此,作者从近代中国的“新史学”运动谈起,强调历史书写与国族形塑的关系,进而指出《大纲》如何克服意义危机和技术危机,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通史”。作者认为,钱穆“身处地理空间、文化场域、知识分子身份的多重边缘”,“是一个在潮流中逆风而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55页),强调钱穆的边缘性和反潮流。另外,作者一方面引用余英时的“一生为故国招魂”界定钱穆史学的意义,另一方面强调《大纲》的“未来预言书”性质,这不期然之间与王汎森《历史时间》一文结尾所述“历史新天使”的姿势(身子向前、头却往后看)相映成趣(36-37页)。
如果说王健文着眼于“国史”,那么阎鸿中重点关注“通史”。当然,该文也涉及“国史”。阎文通过梳理近代中国的“通史”和“国史”的脉络,认为傅斯年、钱穆等人都优先考虑历史知识的客观性(98页)。接着该文列举了近代流行的中国通史的代表性作品,指出其共同趋向,然后重点考察《大纲》的“国史”观念。作者认为,《大纲》具有两个特质,一是肯定传统史学,一是强调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回应了现实中许多关键而难解的问题”(106-107页)。接着,主要通过政体演进和立国形势等讨论钱穆如何处理中国政治的疑难。
游逸飞一文,如副标题所示,是从《大纲》的典范地位、该书涵摄的各家学说及其所征引的史料等三个方面,讨论钱穆此书的价值。首先,该文以台北大学和东华大学两位教师的中国通史课纲为例,证实《大纲》迄今仍有生命力和影响力(131-133页)。接着指出,“士人政府”是钱穆稳健的史论,“中国式民主”则是激烈的政论(156页)。作者大致认为《大纲》基本上以士人政府为主线,讨论中国政治史的演进。在史料方面,该文指出:《大纲》主要依据正史,但也大量参考了正史以外的文献(163页)。
本书所收各文有两篇在标题上用了问号,其一是上文业已介绍的王汎森的《历史时间是延续的吗?》,另一篇即孔令伟的《情的融合?》。不过,前者的问号不是对钱穆的质疑,后者则颇具批判性质。该文以“域外思想”为视角,检讨近代中国史学界的域外观,接着探察钱穆如何讨论中国史上的“域外”,最后强调突破“中国”与“域外”的二元对立,超越国族主义历史观,建议从欧亚史、海洋史、全球史等角度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中,该文对钱穆划分的三个派别的认识颇有意思。作者认为,柳诒徵、吕思勉等人属于传统/记诵派,钱穆本人大体属于这一派,大体认为秦统一之前不存在所谓域外的问题;翦伯赞、白寿彝等属于革新/宣传派,这一派提倡“自古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即已形成)和“共创论”(中国是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科学/考订派则包括傅斯年、陈寅恪等,主要依据是傅斯年等人提出的“虏学”志在突破乾嘉汉学的传统,以多语种的比较文献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181-183页)论文指出,《大纲》对中国和域外的认识是相互对立的,中国是和平、统一的,而域外夷族会造成分裂和暴力。另一方面,《大纲》主张,周边诸民族与华夏在漫长的历史中经过“情的融合”,最终形成了现代中国。对此,该文以西汉与匈奴、东汉与羌族、清朝与准噶尔汗国的紧张与暴力为例,对“情的融合”论指出质疑。
徐兆安一文试图借助“能动性问题”,在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把握《大纲》的意义。该文指出钱穆“以士人为中心的史观”,牵涉到历史解释的种种问题(215页)。作者特别选取《大纲》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认为这一章与其他章节格格不入(217页),“士之自觉”与全书其他部分有“关键的差异”(219页)。在作者看来,《大纲》大部分章节采取了经学家与理学家的思考方式,而“士之自觉”反映了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的“超历史”的一面。所谓“超历史”,是指身在历史之中,却不为历史所限,反过来寻找改变历史潮流的动力(223页)。该文将“士之自觉”置于清末民国的时代背景下,以胡适、陈独秀、傅斯年、孙文主义的“自觉”作为反衬,认为钱穆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悲欣交集的文化复兴观”(242页)。
王汎森《钱穆与余英时》并不是一个专题研究,而是他根据个人所知加以讨论。作者首先指出:胡适、钱穆、杨联陞三人对余英时影响最大,其中在整体的文化、政治方向上,胡适影响最大;在学问上,钱穆影响最大;在职业生涯上,杨联陞影响最大(253页)。该文一方面指出钱穆在学问上对余英时的巨大影响,一方面也考察了两人在职业选择(留在美国还是回到新亚)、治学理念上的差异。作者强调钱穆与余英时是两代人,是两位取向不完全相同的史学大家,钱穆身上有浓厚的“道学”理想,而余英时是置身于现代学术社群、服从现代学术纪律、追求客观的现代史家(268页)。
其后五篇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各位作者根据其专攻领域,通过介绍该领域较新的研究状况和趋向,与《大纲》的观点相对照,从而形成某种“对话”。
高震寰专研秦汉史,他在文中指出,《大纲》更侧重论述中国这个国家的历史,而当代学者的通史写作更偏向中国与域外的联动发展,强调中国作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意义。上古史的探索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毋庸讳言《大纲》在考古方面是相当欠缺的。作者指出,《大纲》上古史部分,在史前时代到殷商一段,由于当时考古材料的限制,比较不足;而西周以后的叙述,迄今仍有参考价值(299页)。由于新材料大量出土,先秦、秦汉史领域在认识上受到了很大冲击。比如秦政的内容,在钱穆的时代确实“无可详说”,而今各种秦简的陆续公布,给秦史研究提供了各种线索(289页)。汉代史研究也相当注重简牍、墓葬、碑刻、器物等材料的利用,而不只是传世文献,在方法上也不限于文献考察,人类学、考古学等几乎已是秦汉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傅扬考察的是《大纲》里的中古史部分,即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但《大纲》并没有采用“中古”的概念。该文认为,《大纲》最关心的是各个时代的人对理想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追求(307页),中古时期也是如此。所以作者着重从君主、士人、庶民三方的互动出发,探究《大纲》中所展现的中古时期的制度及其精神。《大纲》对四项制度格外关注,即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制、科举制。在钱穆看来,这些制度反映了“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313页)。另外,作者注意到,钱穆对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态度截然相反的——魏晋南北朝是黑暗的,而隋唐是光明的(323页)。
许凯翔着重讨论了《大纲》中古代至中古的宗教,不过这似乎并不是《大纲》特别注重的题目。该文首先从宗教的定义出发,指出钱穆笔下的“宗教”带有折中性质(341页),一方面是传统中国的“教”的意思,即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思想学说,另一方面又吸纳了西方religion的含义。不过,钱穆关注的重点仍是与政治高度相关的宗教,譬如祠神信仰就基本不在其考察范围之内(342页)。作者指出,钱穆评价宗教主要是基于政治关怀,大体有两个标准,一是宗教对“大群体”的关心程度,二是宗教是否经世致用。因此,钱穆对这个长时段内宗教的论述比重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讨论魏晋时期的道教时,侧重其与政治相关的部分,对道教内涵的变迁则很少涉及。对于南北朝时期的宗教,则重北朝而轻南朝;进隋唐时期,则重佛教禅宗而轻道教(346页)。对中古时期传播深远的净土思想也基本未加关注(347页)。总体来说,钱穆坚持的是儒家本位,追求“经世致用”的理想(346页)。
郑丞良通过比较《大纲》中宋元政治史若干议题的见解与当今学界的观点,以观察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趋向。这些议题都颇为重要,且耳熟能详。比如,宋代是否“积贫积弱”?宋代宰相制度究竟是不是“相权低落”?元代的行政制度是不是“中央临制地方”?元代士人“九儒十丐”是否属实?作者指出,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观点可能是《大纲》推出宋代“积贫积弱”说的重要出处(372页),并认为“积贫积弱”说至少可以从国家财政、百姓负担两个角度加以解读,反映了钱穆对“上下俱足”(国家强盛、民众富足)的理想社会的期待(375页)。再则,作者认为宋代“相权低落”说不能等同于“唐宋变革论”的“君主独裁”(378页),强调单纯从权力分配的角度来说相权低落并不符合史实,而应更细致地讨论(380页)。对于元代的行省制度,则引用李治安、萧启庆的研究,认为行省具有中央与地方的双重性质,“看似分权,实则集权”,与《大纲》的论述基本一致(382-383页)。“九儒十丐”之说大体反映了南宋亡国的失落心情,但并不是元代社会的实情(384-385页)。最后,作者认为,制度、儒士、理想社会这三点是钱穆最看重的。
和傅扬一样,丘文豪也注意到《大纲》的历史分期问题。《大纲》设置了“元明之部”和“清代之部”,并没有采用“明清史”的称谓。作者指出,要讨论钱穆的明清史,至少应该将《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三本书放在一起考虑。该文强调在通史的视野下考察明清史,因此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政治是不是专制,二则涉及经济地理和学术思想。作者认为,钱穆考察中古史的基本原则是,以中国自身的标准去理解中国政治和文化,所以钱氏并不同意将专制视作中国政治的本质与常态(398-399页)。接着,该文概述了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和社会学术氛围的兴起与衰弱。

钱穆
三
限于篇幅,评议部分拟着重讨论三个问题。
(一)本书议题的设置
总体而言,本书内容相当丰富,对阅读《大纲》颇有启迪。在阅读本书之后,我也将《大纲》重新翻阅一过,一面叹服其博学宏识,一面也深感其时代的局限。就个人而言,孔令伟从“域外思想”、许凯翔从“宗教”的角度品读《大纲》,是比较新鲜的两个议题,带来很多知识和思想上的刺激。不过,就《大纲》本身而言,至少有三个议题非常值得深入讨论,最终未付诸实施。这里面或有各种缘由,但就结果而论,不免让人稍感遗憾。这三个议题分别是制度史、经济史和历史地理。
钱穆曾致信严耕望,对《大纲》的取向有所说明:
拙著(指《国史大纲》——引者注)侧重上面政治,更重制度方面;下面社会,更重经济方面;中间注重士人参政,于历代选举考试及时代士风,颇亦注意。
可见《大纲》最核心、也最有特色的论断集中于制度史、经济史和士人政治方面。其中,据钱穆回忆,他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盛赞《大纲》“论南北经济”堪称“千载只眼”。本书有多位学者涉及第三方面,即士人政府论(或君、臣、民三方互动论),对制度史和经济史则缺少深入的分析和精到的评判。
另外,书中虽间或论及历史地理,如郑丞良(359、377页)、丘文豪(397-398页),但大都点到为止,似乎谈不上精彩的发挥。实际上,钱穆对历史地理甚有兴趣,且做过专门研究,而且《大纲》配有不少手绘地图,足见其对地理之重视。倘有人从这个角度盘点《大纲》,或许能发现不少有意思的问题。
(二)影响《大纲》的论说及《大纲》的影响
通史写作必然多方参考、利用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钱穆在《大纲》“书成自记”中说:“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亦不备详,义取一律,非敢掠美。”余英时为《大纲》重版作序时指出,《大纲》对时贤的成果不仅仅止于“采获”,而往往有所商榷。余氏特别举了王国维、陈寅恪、周一良等人的例子。在这个意义上,《大纲》不愧为“现代中国史学鼎盛时代的结晶”。
本书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探讨。譬如,王汎森《历史时间》一文指出,《大纲》关于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的说法,源自梁思永的“后冈三叠层”(29页)。阎鸿中则指出,《大纲》援引了傅斯年的观点,认为西周封建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殖民和军事占领(117页)。此外,游逸飞曾撰文指出《大纲》1995年修订版关于女真的一段叙述参考了蓝文徵发表于1953年的《海上的女真》一文(156-158页)。
一方面《大纲》汲取了先行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大纲》也启发了后来的学者对某些问题继续加以探究。傅扬就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学界有些研究跟钱穆的看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甘怀真的“二重君主观”,余英时对汉末南北分裂的考察,严耕望对隋朝财富的探讨,孙国栋对唐代三省制的研究,等等(317-319页)。这种例子大概还有不少。我这次在重读《大纲》时,注意到钱穆对明末遗民生活颇为关注,这使我联想到王汎森讨论遗民的一篇论文(《清初士人的悔罪形态与消极行为——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作者最初留意到这个课题,可能是受了《大纲》的启发。
如游逸飞所说,《大纲》的史源还可以继续探讨。同样的,对《大纲》的具体影响也值得继续发掘。
(三)一些细节问题
本书各位作者专攻领域不一,对钱穆的学术思想的认识也有差别,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呈现截然相反的判断。比如,《大纲》引论所述的三个派别非常引人瞩目,自该文在报纸上发表后,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迄今仍为学界所重视。在王汎森笔下,钱穆认为自己不属于记诵派(19页),而孔令伟明确主张钱穆属于记诵派(173页)。王汎森(19页)、王健文(41、64页)、阎鸿中(91页)大体倾向于强调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考订派之间的隔阂与对立,而孔令伟认为钱穆所说的三派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有所重合的(183-184页)。应该说孔氏后面这个意见有一定道理,但他将钱穆归为记诵派,恐怕并不符合钱氏本意,毕竟《大纲》引论对三派都持批评态度。另外,孔氏将陈寅恪列为考订派(180页),这个看法恐怕陈氏、钱氏都不会赞成,毕竟陈寅恪对科学考订派颇有微词,对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顺带一提,孔氏认为,“钱穆对元朝的历史很熟悉,但对蒙古历史可能并不那么熟悉”(200页),恐怕是高估了钱穆对蒙元史的兴趣。当然,如果将《大纲》与其他中国通史的元史部分相比较,可以更清楚地把握钱穆对蒙元史的熟悉程度。
另外,书中有几处笔误。王汎森在文中提及周一良《论宇文泰的种族》(27页),其中“宇文泰”应为“宇文周”。实际上,游逸飞、孔令伟也提及周氏此文,篇名倒是正确的。再则,丘文豪一文两次提及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但两次说法都不准确,分别误作“《中国思想论丛》”(410页)、“《中国思想史论丛》”(4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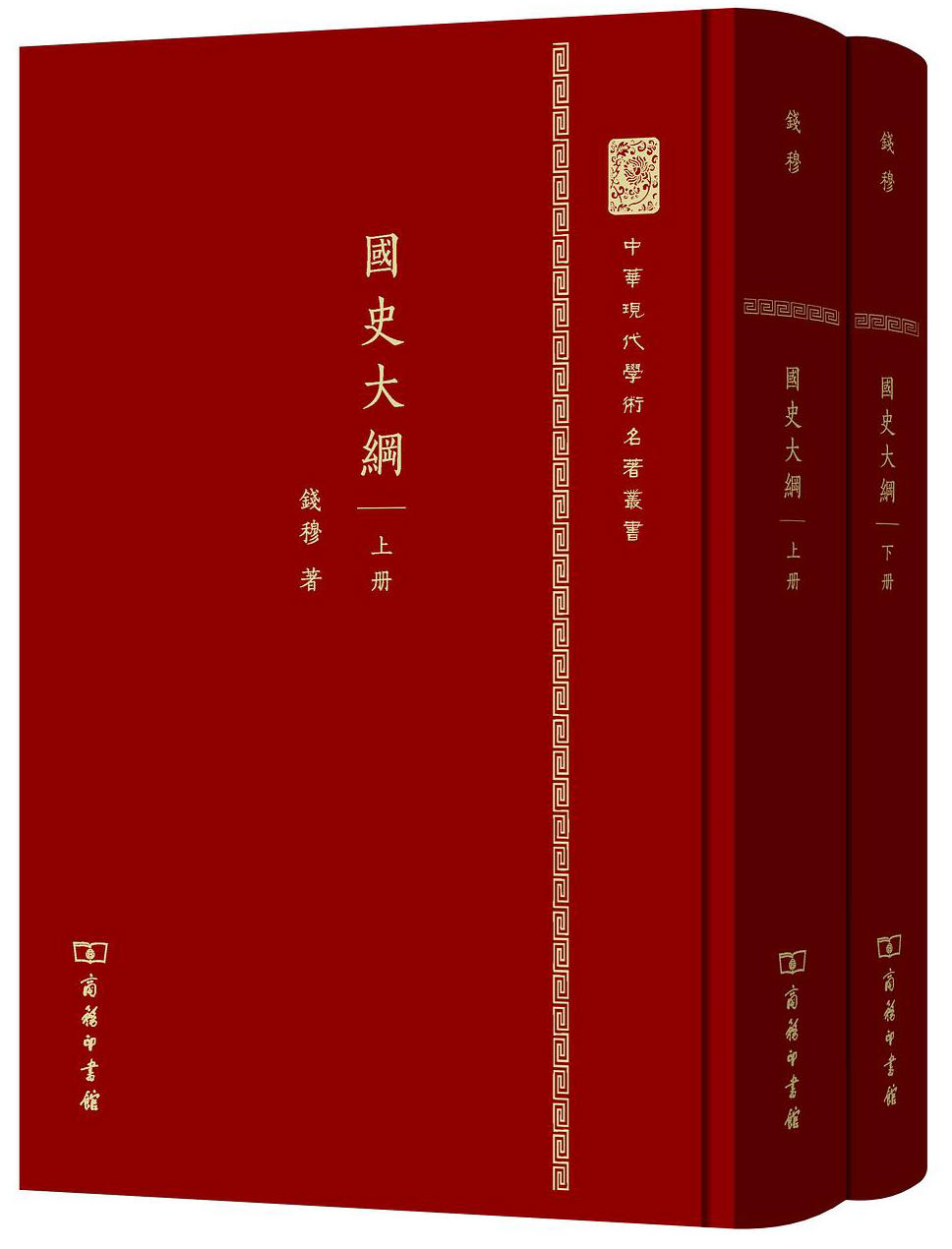 四
四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钱穆《大纲》无愧为一部经典,但这种经典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学界、教育界、出版界共同造就的。毕竟,《大纲》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抗日战争背景下的产物,其历史观是以儒教、大一统、士人为中心的,以今视昔,不免有种种缺陷和毛病。尽管本书各位作者都在努力维护《大纲》的经典性,批评的措辞比较委婉,但通读下来,《大纲》的时代性愈显强烈。此外,相比于日本的中国通史写作,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状况存在相当大的检讨余地。际此时代剧变,重新书写中国通史乃势所必然。汲取《大纲》的营养,而不为其束缚,才可能造就一部新的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