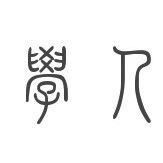逝者|彭国翔:纪念蒙培元先生
 蒙培元先生,2023年7月12日逝世,享年86岁。
蒙培元先生,2023年7月12日逝世,享年86岁。蒙培元,1938年2月9日生,甘肃庄浪人,196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66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访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等。
作者 | 彭国翔 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作者授权发布
7月13日中午,接到学生发来的信息,告知蒙培元先生昨晚去世了。这些年来,老辈相继凋零,接到这一消息,我并没有觉得十分意外。但蒙先生是1938年生人,而治中国人文学的前辈很多都寿至乃至寿过90岁。照此先例和经验来看的话,蒙先生86岁过世,我实在觉得还是早了一些。不过,我之所以要写这篇纪念文章,不仅是惋惜蒙先生作为一位中国哲学的前辈未至耆寿而逝,更是由于我个人和他有过交往、得到过他的鼓励和提携。
收到学生的消息时,我正在旅途之中,无法立刻动笔。不过,这恰可以让我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回忆我和蒙先生的交往。接下来的几天虽然仍在旅途,且不免劳累,但和蒙先生之间的往事,则不时涌上脑海。
第一次和蒙先生见面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至少从2000年开始,蒙先生和我就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那年春天,我获得“中华发展基金会”的奖助,以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到台湾访问,而蒙先生同样在“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下到“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访问。事先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到了台湾之后才遇到。
同在异乡为异客,蒙先生又是中国哲学尤其宋明理学领域的前辈,对于正在撰写阳明学博士论文的我来说,自然是难得的请益之机。我在几次一道活动的场合,都曾有向蒙先生问学的机会。那时年轻气盛,还曾对中国哲学尤其儒家哲学中的心性本体能否以“实体”名之,和蒙先生进行过讨论,对蒙先生的理解提出过不同的意见。
当时客居台湾的还有金春峰先生,他和蒙先生两位都出身于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又都是冯友兰先生的研究生,少不了彼此的晤谈。还记得在中国文哲研究所后面访问学人宿舍蒙先生的住处,就至少有一次是金先生来访,而我恰好也在。虽然我也不时插话,但主要是聆听了两位的交谈。具体内容已不复记忆,但宋明理学应该是最主要的内容。
蒙先生原本只有两个月的访期,后来延至了和我一样的四个月的访期。这样我们彼此交流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台湾学界的朋友非常热情好客,经常邀请我们一起吃饭和游玩。比如现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史甄陶博士,因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便到北京访学,拜访过蒙先生,也在那时和我认识,便多次邀蒙先生和我外出聚餐和游览。还有一次,是当时尚在华梵大学任教的杜保瑞教授,邀请蒙先生和我到阳明山泡温泉。因年代久远,具体情境以及谈话内容,大部分都已经模糊了,但蒙先生温泉出浴之后,清瘦的面庞泛着红光,说话慢条斯理而不失抑扬顿挫的样子,此时此刻却浮现眼前。
由于台北结缘,返回北京之后,我曾去蒙先生府上拜访过几次,那时蒙先生还住在望京社科院分配的房子。我去的次数不多,每次谈话的具体内容也都不记得了,但所谈都是学问之事,这一点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历来不喜无谓的社交,拜访真正学有建树的前辈,自然都是谈论学术。而在我的印象中,蒙先生也极少和我谈学术思想之外的话题。我想,这应该是他将心思大都放在学术研究上的表现。
人的时间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一分一秒都不比别人多,用之于此,便不及于彼。对于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代学人来说,能像蒙先生那样从八十年代初即不断耕耘,写出了《理学的演变》(1984)、《理学范畴系统》(1989)、《中国心性论》(1990)、《中国哲学主体思维》(1993)、《心灵境界与超越》(1998)、《情感与理性》(2002)、《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2004)等一系列著作,在海内外专业学界产生相当的影响,非心思凝聚、用志不分,是难以做到的。也正是如此,蒙先生便不同于那些将心思过多用于社会活动之人,纯粹以其自身的学术成就而非其它赢得学界人士由衷的敬佩。我对蒙先生作为学界前辈的尊敬,也正因此而来。
2001年我博士论文答辩时,蒙先生应邀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委员则有楼宇烈、张立文、许抗生、姜广辉、李中华和胡军几位先生。就此而言,如果借用中国古代科举传统的讲法,蒙先生可以说是我的“座师”了。根据当时北大博士学位答辩的规则,导师只能在开始时介绍答辩学生的情况,中间不能发言,最后也无投票权,所以陈来先生不在答辩委员之中。北大哲学系的张学智先生也是宋明理学的专家,只是当时他正在日本访学,不然也应当是答辩委员之一。答辩时各位先生提的问题,我如今不能一一记得。所幸当时负责记录的许美平博士保存了当时的答辩记录,对我来说是一份珍贵的材料。
根据这份记录,蒙先生向我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你论文中存有论和境界论的区分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那么,存有论和境界论究竟是什么关系,还请你作进一步的说明。”二是“知识之辨是龙溪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龙溪的思想中,是如何论述‘转识成智’问题的。”
我最后的回答不是针对每位委员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而是根据他们所提问题本身涉及的问题综合回答。由于存有论和境界论的区分在我看来是儒释之辨的关键,而在蒙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最后提问之前,儒释之辨的问题已经由张立文和李中华两位先生提出,所以,我的回答是从如何在根本上理解儒释之辨开始,但归结还是解释什么是存有论、什么是境界论。根据美平博士的记录,对于蒙先生的两个问题,我以三点做了回复。文长不具引,我想蒙先生对于我的回答应该是满意的。

蒙培元先生著述《心灵超越与境界》
博士毕业之后,我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和蒙先生成了中国哲学研究室的同事,自然和他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我进入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不久,时任《中国哲学史》常务副主编的陈静女士便邀请我加入《中国哲学史》编辑部的工作,后来又成为副主编之一。我想,这即便不是蒙先生的授意,至少也是他同意的,因为那时蒙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的双主编之一。虽然这份刊物是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刊,但编辑部是放在社科院的。因此,作为身在社科院的主编,蒙先生自然富有更多的责任。
当时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的规矩,是每周二大家只到所一次。午饭聚餐之后,便可以打道回府。至于周二之外,平时都可以在家或自由活动。对于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真是提供了最为难得的时间自由。我因住得较远,单程到所,便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因此,我跟蒙先生和其他同人见面,基本上都是在周二的午饭时间。
2003年夏天的一个周二,蒙先生在研究室专门找我谈话,陈静女士也在场。当时的情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他说:“小陈正在准备评正高职称(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的事有些顾不过来,希望你能接任常务副主编一职。”我因9月赴夏威夷大学客座一年之事已定,且行期在即,便一口回绝。蒙先生知道我性格直率,不以为忤,紧接着说,“你可以先把名义挂上,等回来之后再正式接手。”陈静女士在旁也随之附和。如此一来,我知道此事应是蒙先生和陈静女士早已商量好的。由于我当时并没想到自己后来会离开社科院,便答应了下来。所以,《中国哲学史》2003-2004年的几期刊物上面,副主编一职上还一度有我的名字。这件事,充分反映了蒙先生对我的信任、鼓励和提携。
我在2004年夏威夷大学客座期间,同时收到北大哲学系和清华哲学系的邀请。由于社科院没有附属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而当时我的儿子正面临上学的问题,于是我最终选择了清华。我2004年底回国,2005年1月便转赴清华任教了。如此一来,鉴于《中国哲学史》常务副主编惯例由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担任,我便没有能够按照蒙先生所愿,回来正式接手常务副主编的工作了。后来每次念及此,不免都会觉得有负蒙先生当初的雅意。也正因此,我格外感念蒙先生对我的信任、鼓励和提携。
离开社科院之后,蒙先生和我还有过几次见面。记得有一次是在北大开会时,他亲手送了我一本他刚出版不久的著作。送我时上面已有他的亲笔题字,可见是事先准备好的。还记得当时他说:“我现在的书很少送人了。”我知道,这是蒙先生在向我表示他对我的亲近和看重。其实,蒙先生之前也有好几次亲手送过我他的大著。也正是因此,如上所述,我也才对他心无旁骛、笔耕不辍有着亲证而生的强烈印象和敬意。
离开社科院之后,我也曾有几次专门去看望过蒙先生,那时他已经搬到了较为宽敞的回龙观新居。每次见面,蒙先生兴致都很好。记得蒙先生的夫人郭老师说过,那是他们的女儿为他们购置的。不过,从那以后,我和蒙先生见面的机会就不如从前了。尤其是我2014年移居杭州之后,就没有再见过蒙先生了。
蒙先生2008年七十寿庆和2018年八十寿庆,相关的活动我都是事后才知晓的,主事者事先并未和我联系。不然的话,我是乐意献文为贺的。2007-2008学年我在哈佛访问,但2008年8月我回国听说寿庆事后,即向蒙先生去电致意。记得电话中我自嘲鲜至沪上时,他还调侃了我一下。其幽默的声调,如今依稀耳边。八十寿庆之事我听说之后,因手机更换,找不到蒙先生家的电话,便专门向陈来先生要蒙先生的电话。记得陈来先生当时告我蒙先生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听闻之下十分惊诧,仍然打了电话过去。果然,接电话的郭老师证实了陈先生的话。怅然之余,我和郭老师通了较长的电话,心中惟愿蒙先生能够早日复原,也盼望能再有和他聚首畅谈的日子。
这些年以来,天下多故,每个家庭几乎都或多或少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今年虽渐趋平稳,但一时也很难让人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蒙先生在这个时候离开这个世界,虽然难免让家人、朋友以及像我这样敬重其人其学的学林后辈思念不已,但对他自己来说,也许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安详和乐。

蒙培元先生著述《情感与理性》
蒙先生的学术思想,学界自有公论,无需我置喙。这里我只想表达两点相关的感受。首先,至少在我和蒙先生交往的经验范围之内,我觉得蒙先生总是专注于学术思想的探索,并未有开宗立派的意思。而任何一个学派的形成,也都是积累和传承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所谓“水到渠成”。例如,“现代新儒学”之名,是几代学人承前启后、代代都有真正学术思想上的原创性建树之后,由学界公论而有,非自我标榜而立。事实上,蒙先生在1998年9月《大学生》发表的“学术创新、学术批评与学者良知”(原题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蒙培元教授谈学术创新、学术批评与学者良知”)这篇极有见地的文章中,便不仅为我们指点了治学的法门,更明确指出了“学派”的不易与“宗派”的危害。他一阵见血地说道:“进行学术研究形成学派很不容易,形成宗派却很容易。……由于种种原因,正常的学派很难形成。与此相反,学界的宗派却很不少。有些人打着学术同仁的旗号,在某一个学术机构、组织、刊物、杂志的名义下形成小圈圈,轮流出台,靠互相吹捧扩大影响,一些书评无视客观标准,其内容毫无价值。这种小团体似乎很像学派,但与正常的学术学派本质截然不同。学术研究是件严肃的事,正直的学者并不惧怕孤立,同样,正直的学者也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宗派倾向扼杀学者,扼杀学术。”
至于蒙先生对情感的强调、对生态问题的重视,都是自觉立足中国哲学前贤既有观念、充分吸收西方思想和关怀的表现和结果。比如说,中国哲学的现代学人中像牟宗三、李泽厚等先生,都曾明确指出过情感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重要和特点。至于生态问题,显然当代西方学者更早加以关注并做出了很多理论上的探索。蒙先生对情感、生态问题的阐发,是其善于继承发展、融会贯通以及视野开阔、不断吸收新知的反映。如果把“情感哲学”、“生态哲学”当作蒙先生的标签,非但大大化约了其学术研究的丰富内容,更忽略了其基于细致文献解读而进行思想阐释、不凭空造论立说的治学特色。而细阅蒙先生的每一部学术著作,恐怕都能够让人深切感受到这一特色。
我和蒙先生相识逾二十余年,又曾有过共事的经历。并且,对我而言,蒙先生不仅是中国哲学的前辈,更对我个人有过信任、鼓励和提携。在其辞世之际,就让我回忆与他的若干交往,并略述感怀,作为我个人对他的纪念。
2023年7月20日
原标题:《逝者|彭国翔:纪念蒙培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