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心理学专业的抑郁症患者决定进行意义感研究|镜相
本文由镜相 X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出品,入选高校激励项目“小行星计划”。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写 | 刘蕾岑
指导老师 | 庄永志
编辑 | 吴筱慧
编者按:
2023年7月5日晚,歌手李玟因抑郁症轻生离世的消息令不少人感到痛心。网络上一片哗然,大家难以接受像太阳一样在舞台上发光、温暖粉丝的偶像,也有难以消化的忧伤。但其实抑郁症作为最常见的精神疾病,离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据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我国有将近9500万抑郁症患者,而50%的抑郁症患者是学生。抑郁症患者并不是社会的另类,他们生病的原因、感受以及努力自救的过程值得每个人关注。下文讲述的是一位来自985高校心理学专业的抑郁症患者,曾经的她每天的生活围绕吃饭睡觉、学习做题、考试排名连轴转,可考了年级第一之后,她开始问自己:辛苦和努力到底有没有意义?于是,她将意义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是她和抑郁症斗争的故事,也是她坚持意义研究、探索人生意义的故事。
2023年2月10日,时隔半年再见沈琪,她的皮肤白了不少,大嗓门笑称休学后“天天摆烂在家,胖了好几斤!”
半年间,沈琪因身体原因辞掉了高强度的实习,又发现自己的研究方向“基础心理学”并不适合找新工作,于是她自学编程,考了教资,“实在不行,就去高中当心理健康老师”。
没有科研压力,沈琪自称现在每天能睡满8小时,已在逐步减药。距离复学还剩九个月,虽担心旧症复发,她还是准备重拾落灰一年半的心理学文献,再次面对“意义感”的课题。
2022年3月,南京市部分区域提高疫情风险等级,随即学校管控彻底扰乱了沈琪的看病日程。
她有抑郁症,还有鼻炎,治疗刻不容缓。4月,为方便治疗,她从校内宿舍搬到学校对面的小区。在新租的占地15平米的立方体里,一张双人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一台小茶几,放有调酒用的吧勺和一瓶梅酒。阳台的晾衣杆上,飘着一对洗净的白色衬衫。
沈琪是1998年生人,来自冬天被严寒和海风夹击的秦皇岛,平常戴副625度的酒瓶底,走路一跳一跳,带点模特步的范儿。她是Z大2020级心理学系的直博生,毕业论文和研究方向都与困扰她的“意义感”有关。
她曾向导师发誓,2022年11月,一定参加博士中期考核,争取拿到优秀评级。这需要她高效率地看完75到100篇文献。
由于经常失眠、乏力,她并没看几篇需要正襟危坐、圈点勾画的学术论文。反倒是抱着Kindle把冯友兰的《活出人生的意义》、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和日本推理动漫《名侦探柯南》看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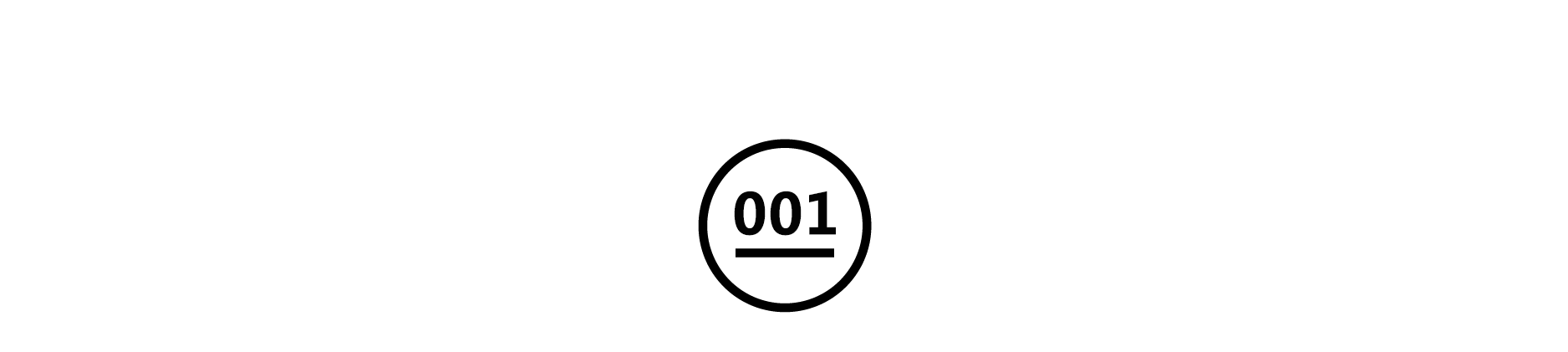
从流水线生产到火山喷发
说起那些让她感到无意义的阶段,沈琪一边大笑,一边掰手指头清算:“初中是枯燥流水线生产,高中是岩浆剧烈涌动,本科是火山连续喷发,直博直接是宇宙大爆炸。”
“流水线生产”期间,为了备战中考,沈琪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绕吃饭睡觉、学习做题、考试排名连轴转,从早上6点一直到深夜11点。她考了年级第一,同时也发现,自己过去热衷的游戏变得索然无味。偶尔想笑一笑,不知该开心什么。
那时她还不知道“无意义感”这个词,也不懂得用心理学术语“快感缺失”(Anhedonia)来描述自己的状态,更不曾想到这可能是“抑郁症”的前兆。
岩浆是在衡水第一中学剧烈涌动的。高考作为一种终极意义,被细化成一个个落实到天的小目标,压力和热血,冰火两重天。为给学习腾出时间,身边的同学省去了睡前换睡衣的环节,直接穿着背面印有“追求卓越”的校服入睡。沈琪身体弱,经常心慌头疼拉肚子,有时捎上习题册跑校医院,喝上两支葡萄糖,猛吸40分钟氧,一边忙不迭地做题。
“这道题首先划去绝对项,用排除法排除A和D,剩下的再看遍材料,关键词圈一下,这块勾出来,好的,选C。”机械化的思维套路让她有些麻木,有时她累得想哭,但比起停下来细想为何要反复练早已熟知的知识点,她还是想先完成眼前这份会影响成绩排名的答题卡。老师说,高考是人生辉煌的跳板,高考成功的人是光鲜亮丽的“人上人”。高中三年来,她一直靠老师的话鞭策自己,但所谓“辉煌”、“人上人”只是脑海中一团意义不明的虚影。
2016年,沈琪考入Z大社会学院,在同为Z大2016级心理系、后来在牛津大学读硕的冯悦的印象里,沈琪是那种“课前争当课代表,上课始终第一排”的优等生。
那年11月,北大心理学副教授徐凯文发表《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演讲,一时轰动。演讲说:在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导向下,中国大学生患有类似抑郁症的“空心病”,不知学习是为了什么。他引用了钱理群教授关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论断,谈了“教育商品化”的问题。
大一下学期,Z大的新生还未分流,在课程《心理学概论》的最后一课,老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意义焦虑”,研究年轻人“担心人生没有意义,因此十分焦虑”的现象。沈琪听着有些入迷:这时的她终于有时间,也有科学手段去质疑——自己长时间来的辛苦和努力,到底有没有意义?
但她不曾料到,在确定将“意义感”作为本科毕业的研究方向前,她先撞上了抑郁症。从大三下学期做学年论文到直博做课题,这三年,是沈琪和抑郁症斗争的三年,也是她坚持意义研究、探索人生意义的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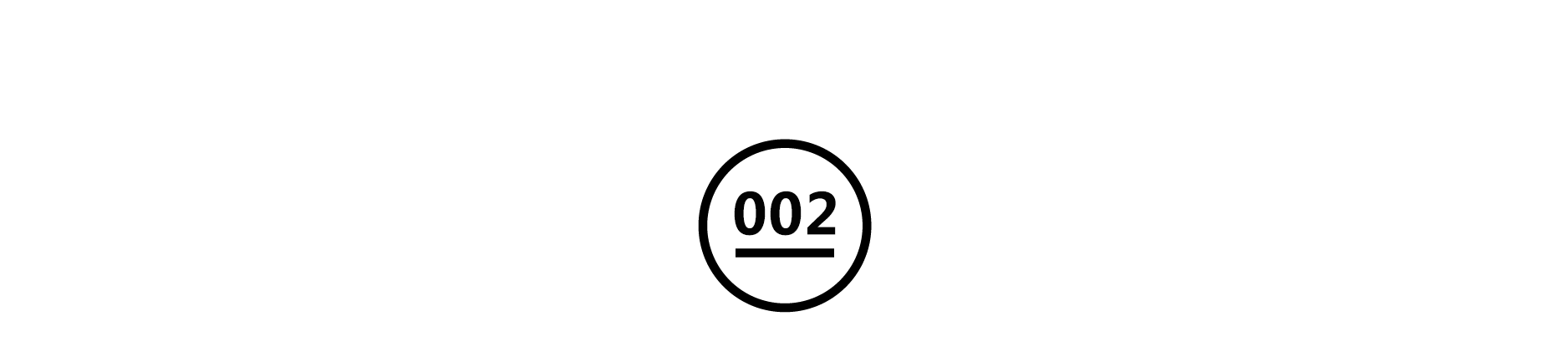
抑郁症来了
自初中起,争吵不断的家便是沈琪排斥的地方,到了大学,家依然时不时刺激她血压升高:
秦皇岛,亲戚聚会。那时沈琪的男友还没念博士,亲戚们认为他配不上保研直博的她,劝她“嫁一个出身大城市的官二代”。
沈妈会将沈琪在初中、高中的所有成就,一一列在一张A4纸上,携着一脸不情愿的沈琪前往各桌,高声朗读纸上的荣耀。
家里,爸妈曾嫌弃她没考上北大。
......
她会用“地狱”形容自己的家庭,也会在每次和家里吵架时首先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孝顺、没人情味。
大一,她时时因为家庭矛盾而失眠,开始尝试通过专业的正念冥想法入睡。正念冥想要求人静下心,调整呼吸、集中精力,可她越是铆足劲强迫自己入睡,越是焦躁难安。
大二,她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换。伯克利的教学不仅让她认识到“有的人天生就在其他人奔赴的罗马”,也让她发现,很多在实验室验证成功的疗法,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能够发挥的效力接近于零。实验室会控制变量,但生活中,身心疾病、阶级、阅历、性格、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影响着个体的治疗程度。这意味着,心灵意义上的疗愈没有可复制的范本,每一个个体对抗精神疾病的故事,都是现在进行时的生命实验。
大三下学期是Z大心理学系压力最重的一个学期,学年论文、升学压力全都压在这一段。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入学式的致辞在国内走红,“你们应该都是抱着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来到这里,可是等待你们的,是一个努力也未必有回报的社会。”这句话在沈琪的心里砸出一圈圈涟漪。
不久,沈琪的手里多了一张显示中度抑郁状态的诊断单,她还记得确诊时,医生“嘶”的一声:我第一眼看你,感觉挺开朗的呀?
确诊后的那段日子,失眠的不仅是沈琪。男友是大她一级的河北老乡,名字里带一个“鹤”字,沈琪喜欢叫他鹤先生。2016年,鹤先生带领同乡的大一新生熟悉Z大,人群中一眼看见开朗自信的沈琪,恍惚间一见如故。得知女友确诊后,鹤先生辗转反侧,第一次意识到爱情不止甜蜜。
2019年秋天,沈琪进入大四,已获得直博心理系的资格。她享受阅读文献、摄取知识和自由思考的过程,年级第一的成绩也让她期待做出一番漂亮的研究成果。她进入Z大社会学院教授王飞的课题组,导师研究年轻人的“无意义感”。沈琪也选择“自我控制与意义感”方向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研究自律为何会给人带来意义感。
如果翻看沈琪的QQ空间,她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赛博剪影是这样的:
2019年 大四上学期
10月18日 图书馆 知道自己最近精神不好,特地选了短小精悍的论文进行阅读。结果对电脑屏幕发了两小时呆,于是去操场上狂跑5公里发泄。
11月26日 宿舍 做噩梦,梦见自己浑身扭曲,怎么呐喊也发不出声音。引用曼玫《抑郁生花》的句子,“我不想再害怕你、抗拒你、逃避你、消灭你。”
12月5日 教室 前夜睡眠差影响记忆,下午两点和导师讨论学术,居然把一篇文献的研究结论完全记反了。但吃安眠药会让第二天头疼。
......
2020年 大四下学期
3月25日 因疫情隔离原因 居家 早上六点自然醒,起床这会儿总算没头疼了——昨天一天基本没学习,我以为今天的状态缓过来了。结果才看了半个多小时的论文,我又偏头疼,颈椎也疼。这是条件反射吗?!
......
这样的状态断断续续,直到她完成本科毕业论文。
时间来到2020年6月,沈琪即将本科毕业,17号这天,Z大2016级心理学系12个学生在食堂将三张四人桌拼成一个长桌,当作毕业聚餐。沈琪聊到自己在吃抗抑郁药,坐她右边的冯悦为了安慰她,搭了一嘴:“其实我已经吃了半年的弗洛西汀和喹硫平”。还有位童姓男生透露,一天吃三片富马酸喹硫平。患了抑郁的同学知道,他的抑郁症已经非常严重。
大家数了数这届心理系的抑郁症患者,合计有四五位。

沈琪的抗抑郁药物
这位童同学本是天文系的,但因为总来旁听心理系的课,也被算作心理系人。童同学曾向冯悦坦言心理疾病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学习,放眼四周,一些挂科的同学其实也是如此。于是他邀请冯悦一起向学校学生代表大会提交提案,呼吁加强对学校心理治疗的重视,但最后由于繁忙,提案无疾而终。

作为直博生,我似乎不喜欢搞研究
读博两年,抑郁症不止不休。
整夜失眠。
凌晨,宿舍,安眠药依然不管用,沈琪听信某公众号声称蓝莓的花青素可能有抗抑郁功效,于是花费一百多元购买蓝莓提取物,辅以收听冥想APP,但仍无法入眠。她当然知道保健品无法医治疾病,还是试了——这是心理专业的她干过的最离谱的事。
不是没有尝试过心理咨询。接受咨询师干预时,她会不由自主地识别咨询师此时向她使用的治疗策略:同感、矛盾性提问、自我披露、与来访者建立长期的情感联系......沉浸感全无。曾有位咨询师过多输出观点,她则在心里默默回忆课程内容:心理咨询师应该注重使用倾听疗法,而不是“三分听七分说”。

沈琪在宿舍,借助插花、喝茶助眠
她一直在等候“减药”的时机,如果某天状态不错,临睡前有点困意,晚上就会少吃半片安眠药。减药一旦失败,病情便会恶化,会比现在任何一刻还难熬。但她在意的是“我在吃药,说明我这个人是不正常的,是精神残疾。”
代替药的是烈酒。在放任自己一口气闷了四两40度的波本威士忌后,她糊里糊涂地用香熏蜡烛将手中用来调酒的壶烧了个洞,清醒后当作笑话讲给别人听。
波本威士忌,加柠檬或不加柠檬,加气泡水或加白开,按1:1和1:2.5兑,都是不同的口味,若是兑上红石榴糖浆,会变幻出渐变色。沈琪仰头干完一杯梅酒,麻溜地从床头柜里掏出护肝片,抠一片扔嘴里:“酒喝太多了,需要护肝。”和着水一骨碌咽下去。

沈琪调的渐变分层酒
酒不比药管用,但酒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需要依靠药物入睡的病人”。
由于直博需要上研一、研二、博士的课程,她的博一课表很满,还好周末跳拉丁舞可以将她暂时拽离现实。舞步踩上音乐节拍,她伸出手,是全班最柔缓的姿态。向朋友介绍拉丁舞步和模特一字步的区别时,她会在嘈杂街区旁若无人地轻轻跃起。
至于研究——只要状态不错,学习都是她的优先项。可她一看文献,看一句忘一句,没两小时就犯困、胸闷。严重时呼吸急促,手不自觉地微微发抖,需要躺床上歇好一会儿。
她分不清,如今做研究的低迷状态,是受抑郁症的生理影响多一些,还是根本就是因为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有时她回望,忍不住揣测也许自己更适合曾经反感的应试学习模式:每天完成被安排的任务,每件事都有标准答案。相形之下,研究生之路则空洞而遥远,大多数是“几年之后要发一篇文章”式的一声令下,往后每一步都要自主探索和设计。
社会学院的书记劝她,“学习”是向内输入、学习知识的过程,而“研究”是向外输出、生产知识,你在本科阶段喜欢学习,并不代表你适合做研究。导师也常问她,你是不是潜意识里并不想读博,只是迫于家里的升学压力,已经将家人对你的学业期待内化了。
她回答不上来。
学不进去的大部分时间托付给了励志动漫,主题关乎梦想、斗志与羁绊。有时她深受剧情鼓舞,有时又黯然伤神。看动漫就像去做了一场心理咨询,咨询结束后的即刻感到疗愈和动力奋发,可回到现实,再次面对一地鸡毛仍束手无策。
我到底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有拼尽全力也想达成的目标吗?我有赌上自尊的事业吗?挥之不去的问号。
2021年8月,南京疫情反扑,城市情绪低落。医生新开的处方要求她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时,最好有半天能室外活动。可当时拉丁舞课程正因疫情停课,户外运动更是难以开展;作为一名直博生,在书桌前久坐是基本。这种反差让她觉得荒谬。
被迫在宿舍隔离的日子,每天盯着确诊数据上爬,睡醒一刷手机就是有关新冠疫情的通告与新闻,她没来由地感到不安全。“没有意义”的感觉,又一次渗入了生活的缝隙。
12月,沈琪的博导邀请她参与课题项目“大学生无意义感的内容及其形成”。她的任务是把学界有关的经典文献阅读、整理一遍。
然而没多久就读不下去了。沈琪和鹤先生的双方父母见面了,沈妈要求女儿在家乡办正式婚礼,因为如果只办订婚宴的话,“没啥亲戚来,来了也不咋给钱”。那晚,沈琪多吃了两片安眠药,她很伤心,自己的终身大事“被爸妈当作回钱的工具” 。
状态又掉了,经常是当房间地板上明亮的方格子轮转成忽明忽暗的夜色,她才从床上爬起来,陪鹤先生吃当天第一顿饭。直到2022年3月初忙完结婚,整顿好心情,她才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准备11月的研究生中期考核。
想在中期考核拿优秀,不仅要求博士生交出一个完整的实验方案,最好还做出一个证明方案没有硬伤的阶段性成果。
可是,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容易投入多但最终难以对数据进行合理的解释,这在沈琪看来如同白干:“不应该讨一个结果吗?”她的本科论文就遇到数据难以处理的瓶颈,到了博一,她仍在反思该如何解释那些数据。
沈琪本科论文的假设是,人们在努力的过程中更有意义感,就算目标没实现,人也会感到很快乐。经过反思,她发现自己对学术名词“Procedure”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误将其翻译成“纯粹的过程”。实际上那篇外文文献对此的释义是:“Procedure并不是纯过程,而是每一步都能看见目标进展的‘阶段性结果’。”这个逻辑是,人无法从纯粹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如果在过程中没有一点结果实现的话,人还是开心不起来。
博士期间,她总在阅读文献时琢磨论文里提到的理论、方法等是否可以用作于自己的论文研究,本科期间那种不为研究结果而读文献,纯粹求知、自由思考的享受感逐渐不复存在。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她的研究方向“意义感”并非学界主流。即使她确实是适合做研究的人,这个方向未必容易发文章,未来就业也难。天平的另一端,她已经24岁,理想生育年龄仅剩6年,对她而言,这意味着自己需要在6年时间里顺利毕业并找到稳定工作。
这一串焦虑的因果缠成她绕不清爽的线团,又像是在走钢丝,偶然发现自己可能并不适合脚下的赛道,却又不敢退回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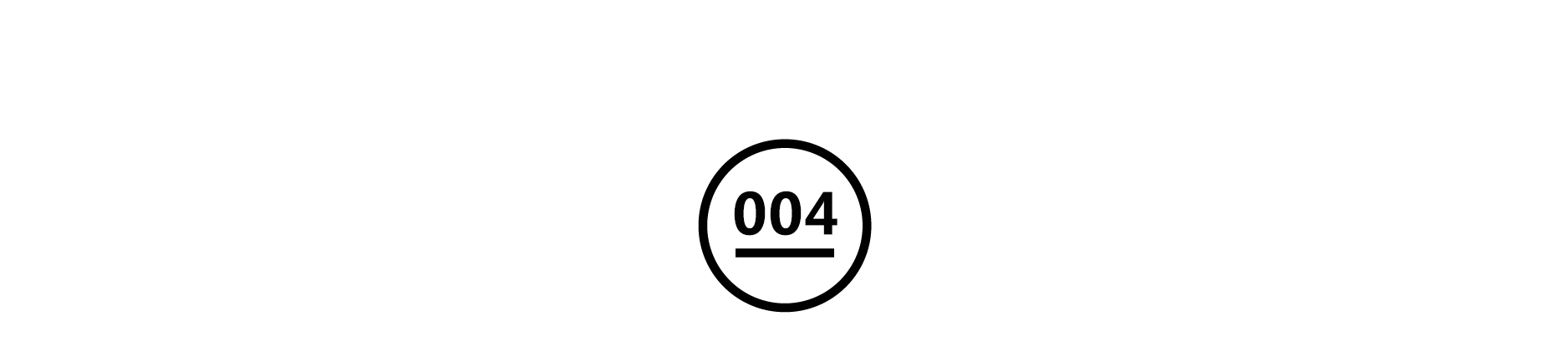
鼻腔手术
2022年4月初,柳絮纷飞的春末,沈琪的慢性鼻炎复发,但这一次比往年更严重。
从单纯鼻塞到偏头痛到整个头都痛,从微微钝痛到尖锐的跳痛,变成下楼梯颠一下都会痛,再到炸裂般的长时间头痛。早晚气温较低时,鼻子堵塞,在快要窒息时,她感觉死神在身侧一闪而过。
考虑到疫情期间外出学校看病要走诸多流程,她和鹤先生搬至学校对面的小区租房。
鼻腔镜的检查结果显示,沈琪偏曲的鼻中隔与鼻甲挤压在了一块。手术通知单赶着4月的尾巴来了。
术后清醒过来,疼痛从咽鼓管区域逐渐蔓延到耳朵,连吞咽唾沫都费劲。一般止痛泵的流量开到5档,她要求开到8档。止痛泵停后,护士几分钟内没现身,她不顾鹤先生的阻拦,一边哭一边拍好几次呼叫铃。换泵时,护士说,之前有个20岁出头的男生,在术后嚎了一晚上。
第三天凌晨清醒,她猛然想起,整整两天,自己常吃的抗抑郁药、抗焦虑药都没有吃。她很心慌,鹤先生也醒了,护士让她吸了氧。
凌晨两三点,濒死感达到顶点。她斜躺在床上,双手抓住鹤先生的手放在胸口。在鹤先生看来,她的眼睛一半睁开,像在做梦,嘴里嘟囔像说梦话。而她当时的感觉,正陷在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既不是疼,也不是痒,像缺氧。整个人轻飘飘的,灵魂似乎正在逐渐离开身体。她把手举起来:我有没有在发抖?
鹤先生急忙按铃唤人,医护人员匆忙的脚步声渐近,他在她耳边一遍遍重复“没事的”。。
四周声音渐弱,世界摇摇晃晃,力气从指尖流出,沈琪失去了意识。
2022年5月1日清晨,沈琪从术后痛感中苏醒,护士拔掉鼻腔海绵的一瞬间非常疼。鹤先生告诉她,前一晚的她,神志不清地交代后事,说她有哪些财产在哪儿,说他离开她的时候要带上些什么。鹤先生调侃她:“你说这么多,却没把银行卡密码说出来。”
熬过了“生不如死的术后恢复期”,为庆祝健康和自由,她穿着病号服在医院四处游荡,又在日记《病痛、濒死感与未来一年的选择》中写道:“憧憬痊愈后的美好生活,是支撑我挺过术后恢复期的强大精神动力,但是,这是很认真的思考,不是单单为了麻痹自己。我经受了这种痛苦,是为了什么?为了之后继续回到大学,继续抑郁焦虑没有动力,不知道该做什么研究吗?显然不是。如果我的人生真的戛然而止,我回顾这24年的人生会后悔什么,是没有读完博士吗?显然不是。”
初中,尤其是高中以来,她被灌输的价值观是,要努力学习,实现阶级跃升。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将人做事的动机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类,从外部动机向内部转变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如果不做此事,担心受到惩罚;第二阶段是如果不做此事,会感到愧疚和后悔;第三阶段是一种认同感;最高级的是同一感,即感到所做之事理应是我的一部分。“我很好学,但从衡水一中到Z大985本科,我努力读书的动机都是处于第二阶段。”
高考已过去6年,时间的卷尺一天天舒展开,她无数次站在高光底下,但也一直啃食着抑郁症长出的恶果。
这一次,她想把从小到大,为了“追求卓越”“成为优等生”这些目标而错失的机会,都补回来。
她决定休学一年。

逃避可耻但有用
学心理学这些年,沈琪越来越能理解爸妈,越来越疲于和他们争辩。她认同一个观点,人在加工信息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父母的爱不可能是无私的。我不敢说他们不爱我,但比起爱我,他们更爱自己,更爱自己的面子。”面对爸妈下达的要求,她学着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他们用爱的名义对我造成伤害,我就是不舒服,也许没有必要太自责”。
至于理解自己:沈琪看过奥地利精神病学家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书中提到,人天生会有一种不足感,终其一生,人都在试图超越这种自卑。
在从本科到博士的心理学研究实践中,她逐渐发觉,屡次失灵的正念冥想法,其核心要义并不是形式和仪式,而在于对周围的觉察和对自我的无条件接纳,“了解自己对于‘烦’是如何具体化的、如何去拆解和描述此刻正困扰我的烦躁,然后接纳自己睡不着、学不好”。
刚确诊中度抑郁症那会儿,医生说这个病不太好治,心理学这个专业让沈琪觉得自己很可能属于好治的那一批,但她不是。后来,她又了解,80%的抑郁症患者会不断复发。她自认为性格开朗,又在努力改善病情,有望成为那痊愈的20%。
“事实证明,其实我就是那治不好的80%。”沈琪歪一歪头,嘴角向下一撇,顺手将手边玻璃杯里仅剩的柠檬水一气喝光——鹤先生将她的烈酒藏了起来。
休学后,她新找了一份实习,想试试学术外的工作,2022年7月底早上9点到岗。“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可我又不觉得我这是逃避。”
也许是一种新的选择。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沈琪、冯悦、王飞、童同学皆为化名,照片均由沈琪提供)
实习生:方益
欢迎继续关注本期“小行星计划”专题:

海报设计:周寰
目前镜相栏目除定期发布的主题征稿活动外,也长期接受投稿。关于稿件,可以是大时代的小人物,有群像意义的个体故事,反映社会现象和社会症候的非虚构作品等。
投稿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
(投稿请附上姓名和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