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讲坛︱高田时雄:法国汉学与汉僧西域行记
二战前的欧洲诸国之中,汉学最昌盛者无疑为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有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与旅居巴黎的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1783-1835),两人相互切磋,对法国汉学的勃兴作出了莫大贡献。此后,法国又陆续涌现出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大师,继承发扬了法国汉学的优良传统,贡献良多。上述前贤,即为法国汉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雷慕莎之前,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曾开法国汉学之先河,为之奠定基础,但其水平仍然停留在汉学的萌芽期,难与雷慕莎及其之后的学者相较。

自雷慕莎开始的诸位法国汉学大师,对汉僧西域行记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汉僧西域行记从而成为法国汉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关于伊斯兰化以前印度及中亚的广袤地域的社会、文化等信息,只能从这些中文文献中获得,因此,这些材料自然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幸运的是,自清康熙年间起,在北京的宫廷中活动的耶稣会士皆为法国人——其因由据说是,康熙患疟疾时,由法国耶稣会士诊病开处方,使用了刚带来的奎宁而痊愈,因而康熙就对法国耶稣会士信任特重[参看白晋(Joachim Bouvet)《康熙帝传》(Histoir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海牙,1699年, 第106-107页)],他们定期与身处法国国内的学者联络,不仅提供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测量数据,还寄去为数不少的中文书籍。雷慕莎在法兰西学院教授的就职演说中曾特别强调,这些中文书籍无疑为推进法国汉学家学术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欧洲汉语研究的起源、发展及其功用”(Sur l’origine, les progrès et l’utilité de l’étude du chinois en Europe),雷慕莎《文集》正编(Mélanges Asiatiques)第二卷,巴黎,1826年,第4页]。
在汉僧西域行记中,最为浩瀚、信息量最大的,当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尽管其重要性已经为学人所知,但在雷慕莎与克拉普罗特的时代,法国国内尚未可得见《大唐西域记》。雷慕莎出于无奈,只能先将法显的《佛国记》翻成法文。在当时的欧洲,法国王家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可谓首屈一指,而其中却没有《大唐西域记》,着实不可思议。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唐西域记》一般被收入于大藏经中,并未摘出作为单行本流传,而当时王家图书馆中并未收藏大藏经,自然也看不到《大唐西域记》了(其实明末万历年间曾有过歙县吴氏西爽堂刊本,但此书极其罕见,不太可能传到欧洲)。
1834年10月,克拉普罗特在柏林地理学会做过关于《大唐西域记》的讲演,但此时他也只能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所引片段章节,无缘得见《西域记》全书[克拉普罗特《玄奘旅行的概要》(Aperçu du voyage de Hiouan Thsang….lu a la séance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de Berlin le 15 Novembre 1834),《旅行与地理学年报新编》(Nouvelles Annales des Voyages et des Sciences géographiques),巴黎,1836年,第35-44页]。
雷慕莎所译之《佛国记》法文译注题名如下:
Foĕ Kouĕ 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dans l’Afghanistan et dans l’Inde, exécuté, à la fin du IVe siècle, par Chy Fa Hian. Traduit du chinois et commenté par M. Abel Rémusat. Ouvrage posthume revu, complété, et augmenté d’éclaircissements nouveaux par MM. Klaproth et Landress. Paris. Imprimé par autorisation du Roi à l’Imprimerie royale, 18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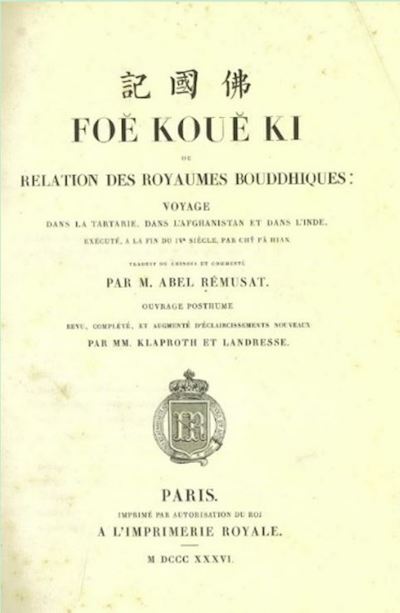
正如題名中所提到的,此书在雷慕莎殁后的1834年方才正式出版。法文译文部分,在雷慕莎生前已经由其本人完成,而注释部分,全四十节中雷慕莎仅完成前二十一节,剩余部分则分别由克拉普罗特及朗德雷斯(Ernest Clerc de Landresse,1800-1862)两人补上,前者撰写的注释注明“KL.”,后者则注明“C.L.”。此书作为法国汉学界第一个汉僧行记的译注本,值得铭记。自此之后,翻译汉僧行记成为了法国汉学的传统之一。
而在汉僧行记中最为重要的《大唐西域记》的法文版,则直到1857年才得以出版。其年,儒莲作好准备后,出版了下文所引的这部书(两卷本):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traduits de sanscrit en chinois, en l’an 648, par Hiouen Thsang, et du chinois en français par M. Stanislas Julie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7-58.
该书作为《大唐西域记》最早出版的一个欧洲语言译本而名声甚著,对后世影响颇深。为正确翻译《西域记》,儒莲还对梵文的汉字音译法进行过研究,其研究成果后来作为《解读和转写中文书籍中梵文名词的方法》(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Paris, 1861)一书出版。且儒莲在完成《西域记》法文版之前,已经翻译出版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慈恩传》共十卷,儒莲的法译本将前五卷全部译出,但后五卷仅有提要),题名如下:
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 et de ses voyage dans l‘Inde, depuis l’an 629 jusqu’en 645, par Houeï-li et Yen-thsoung: .... traduit du chinois par Stanislas Julie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53.
在本书的序言里,儒莲所列举的汉僧行记如下:一、《佛国记》(《法显传》);二、《宋云行記》;三、《大唐西域记》;四、《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五、《大唐求法高僧传》;六、《继业西域行程》。这些著作可能是计划收录于儒莲大规模的《汉僧行记丛书》(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此丛书名见于《西域记》法译本的封面。《慈恩传》是第一种,《西域记》是第二、第三种)中的候选著作。儒莲本人只完成了《慈恩传》和《西域记》,其余著作的译注工作只能留待晚辈学者完成。他的这一构思则发端于更早的时期——1847年发表在《亚洲学报》上的文章中,他已经提及多部汉僧行记,并加以解说(Stanislas Julien, Renseignements bibliographique sur les relations de voyages dans l’Inde et les descriptions du Si-yu, qui ont été composées en chinois entre le Ve et le XVIIIe siècle de notre ère, Journal Asiatique, Octobre 1847)。
如上所述,雷慕莎和克拉普罗特终生无法得见《西域记》全本,而儒莲则充分利用其广泛的人脉,一共得到了三部《西域记》(参看《慈恩传》法译本的序言第10页)。三部中有两部是同一版本,其中一部1838年得自活动于中国内地的遣使会传教士,另外一部得自英国前宁波领事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都是儒莲所说的“钦定版”(édition impériale),但从页数和带有标点等特色的描述来判断,应为嘉兴藏本。至于儒莲何以将这一版本认定为“钦定版”,无从得知。后来他得到了一份四开细长的古老刊本,应为南方刊刻的藏经本之一,从当时的流通情形判断,笔者认为是永乐南藏本。
儒莲的《西域记》法译本确实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欧洲语言译本。然而,在1845年,亦即在儒莲的法译本出版的十几年之前,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已经在北京完成了俄译本。全书十二卷,附有地图,似是马上可以交给印刷所出版的书稿,却长时间埋没在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中,相当遗憾。俄国拥有每十年向北京派遣一次东正教使团的特权,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在获取中国文献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瓦西里耶夫则正是俄罗斯第十二届派遣团(1840-1849)的成员之一。
继承儒莲的事业首先是沙畹。他博赡多识,涉猎相当广泛,包括美术、考古、石刻、宗教、突厥石料等领域,可谓无所不窥。沙畹凭借完成司马迁《史记》法译本的成就为世人所知,而汉僧行记的译注也算是他的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方面。

沙畹所翻译的著作,首先是义净的《求法高僧传》——此书封面第一行标注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汉僧行记丛书》),清楚地表明他的工作继承了儒莲的计划:
Mémoire composé à l’époqu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 sur les Religieux éminents qui allèrent chercher la Loi dans les pays d’occident, par I-tsing. Traduit en français par Edouard Chavannes. Paris: Ernest Leroux, 1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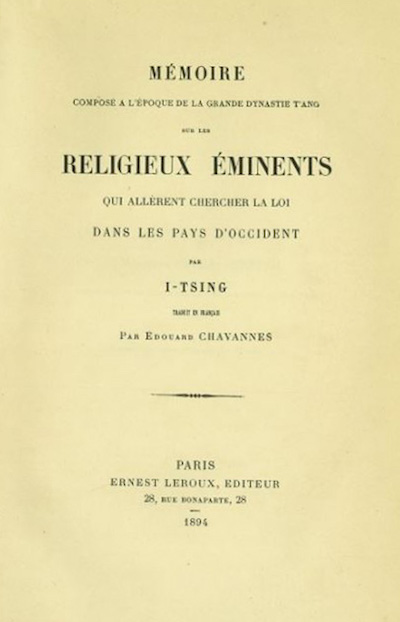
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了《继业西域行程》《宋云行记》《悟空行记》等著作。除这些译著外,沙畹还撰文讨论相关问题,如Guṇavarman (367-431 p. C.). T’oung Pao, 1904, pp.193-206; Jinagupta (528-605 après J.-C.). T’oung Pao, 1905, pp.332-356; Voyageurs chinois chez les Khitan et les Joutchon, Journal Asiatique, 9e série, IX, 1897, pp.377-442, XI, 1898, pp.361-439等):
(一)L‘itinéraire du pélèrin Ki-ye 继业 dans l’Inde. BEFEO, 1902, pp.256-259.
(二)Voyage de Song-yun dans l’Udyāna et le Gandhāra (518-522 p. C.), BEFEO, 1903, pp.379-441.
(三)Voyages des pélèrins bouddhistes.―L’Itinéraire d’Ou-k’ong (751-790), traduit et annoté par MM. Sylvain Lévi et Ed. Chavannes, Journal Asiatique, 1895, pp.341-384.
这些著作篇幅不长,都发表在期刊上。其中最后一种,由沙畹与西尔万・烈维(Sylvain Lévi,1863-1935)合著。身为印度学家的列维虽非汉学家,却精通汉文。他从《法苑珠林》中拾掇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佚文,将之译成法文并加以诠释,题为《王玄策出使印度考》(Les missions de Wang Hiuen-ts’e dans l’Inde),刊登于《亚洲杂志》1900年号上(Journal Asiatique, 1900, pp.297-341, 401-468;另外有抽印本,页码改标为第1至第120页。此文有英译:The Mission of Wang Hiuen-Ts’e in India, translated by S.P. Chatterjee, Calcutta: Ind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67, 80p.)。1990年,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发现《大唐出使天竺铭》摩崖碑残字二十四行,为显庆四年(659)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时途径此地所留,现已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烈维此文当然不能用上这一新发现的材料,然而他亦尽其能事,搜罗当时可利用的一切材料,又求教于沙畹,使论文完备无缺。值得注意的是,《悟空行记》和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两书并不见于儒莲的计划之中,而是沙畹与烈维以两人之力从传世文献的大海中钩沉得来,由此亦可窥见此时法国汉学实力之雄厚。

沙畹和烈维的努力,使得他们在达成儒莲的原计划的基础上,还向学界公布了新的材料。然而法国汉学对这一领域的贡献并未止步于此。最后,笔者需要介绍的是伯希和的奇迹。
自1906年的夏天踏上中亚考察之路的伯希和,在1908年2月11日到达了千佛洞(莫高窟)。他先对洞窟逐一调查,之后说服了王道士,从3月3日起就开始在藏经洞点检敦煌遗书。众所周知,他在洞窟里昏暗的煤油灯下一一拣选带有学术价值的写卷,除汉文以外,尚有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诸语言写卷,总计约五千卷。如今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就是这般由伯希和亲自选出的。
其中有一件写卷,与本文主题关系最为密切:在1908年3月23日,伯希和在无意中发现了惠超的《往五天竺国传》!他在《旅行日志》中说道:“最后,特别是新发现的求法僧的记录。首尾已缺,但其对研究印度尤其是俄属土耳其斯坦、喀什和库车意义重大。这位无名作者在开元十五年十一月(727年末)抵达了安西,我认为此人应为惠超。其所作《往五天竺国传》,在大藏经中被作为注释转引。此注释中提到的‘昆仑’与 ‘谢䫻’,亦见于此写本,用来表示Zabouristan的‘谢䫻’一词,由《唐书》可知仅在武则天即位以后才被使用,即约公元700年以后。”(P. Pelliot, 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 Paris: Les Indes savants, 2008, p.290)
伯希和出发考察之前曾在河内任法国远东学院教授,当时他也涉猎了不少文献。他所说的“大藏经中的注释”指的是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惠超《往五天竺国传》的音义见于其中第一百卷。慧琳《音义》是古佚书,只有《高丽藏》所收录。当时流通于世而一般学者所能利用的版本只有两种:日本延享三年(1746)狮谷白莲社刊本和东京弘教书院出版的《大日本校订大藏经》(即缩刷藏经,1881-1885)铅印本。伯希和在远东学院看到的究竟是哪一个版本,暂时不得而知,但伯希和在藏经洞翻阅写本时,能够凭借如是微末的记载而认出此书,非奇迹而何!
法国汉学对汉僧西域行记的关注和研究,发轫之始为雷慕莎,又以伯希和奇迹般的发现作为收场,诚可谓大团圆结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