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两部小说之后,他将文学才华全数耗尽在这部千页巨作中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代表作《无尽的玩笑》,长久以来在中文互联网上只闻其名不见其身。近日,这部由世纪文景历经十二年引进的作品简体中文版面世,中文读者才得以一窥其真面目。
《无尽的玩笑》是一本没有目录、没有章节,片段之间被神秘符号隔开的作品。它有388个尾注,其中不乏长达数页、仿佛是从正文中裁剪下来的文字。它的语言在不同角色和身份间变换,很多都是街头俚语、小圈子黑话,还有数学、哲学、医学领域的专业术语,因此创造了一种新鲜的和被后来人争相模仿的语言风格;它的背景设定在未来,故事情节是非线性的,结构复杂,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像一个有着奇特构造的未来主义装置……它的出现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威胁,更是一种诱惑。

《无尽的玩笑》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 著
俞冰夏 /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版
华莱士196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市,在中西部地区长大。父亲是哲学教授,母亲是英语教授,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华莱士自幼就对语言及写作充满兴趣。成年后的华莱士尊崇的文学前辈,如约翰·巴斯,托马斯·品钦,唐·德里罗,其中他尤为尊重德里罗,将他视为文学上的父亲,与他保持了多年的通信往来,经常与他分享自己在写作上的思考和困惑。从这些前辈们身上,华莱士学到了反叛精神,不落入陈词滥调的窠臼。他曾表示,巴斯的《迷失在游乐场》是让他下决心当作家的作品;《无尽的玩笑》中用了很多缩写词,这跟品钦有些相似。但他比他们走得更远,后现代主义文学标志性的反讽,到了他这里变成了“反—反讽”,一种极度真诚的行文风格。因为华莱士发现,老一代的反讽由于过度在意反讽的方式,反而忘了真正要讽刺的东西。而他要做的,就是写出一部新东西来颠覆这种观念,这个新东西就是《无尽的玩笑》。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在《无尽的玩笑》之前,华莱士已经出版了两部作品,处女作《系统的扫帚》是一本小说,也是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之一,出版的时候他才25岁。这本小说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贯穿全书,闪耀着天才的光芒,为他赢得了当年的怀丁奖。两年之后,短篇小说集《头发古怪的女孩》出版,那时他还在亚利桑那大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
前两部作品展现了华莱士广博的兴趣和知识储备,但他将它们称为花哨的东西,他真正要写的,是“实现和人情感交流”的作品。1980年代,有些故事已经被他写成了短篇或碎片,到了90年代,《无尽的玩笑》写作计划在他脑海里慢慢成形,一次爱情失意,促使他下定决心开始写这部巨作。在小说里,一部名为《无尽的玩笑》的神秘电影在地下流传,所有看过它的人都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它的致命吸引力将一所网球学校、一家戒瘾康复机构、加拿大分离组织以及美国情报部门都卷入其中,灾难一触即发……在这部有着自己的大脑和心脏的小说里,华莱士挥洒他天才的语言,巧妙构建挑战读者智商的故事结构,于无限放大的细节中,制造出席卷现实与人物内心的连绵不绝的风暴。

《无尽的玩笑》给他带来了名誉和声望,也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意味着他写出下一部长篇将会变得极度困难,于是,他一边构思着小说,一边给各家报纸杂志撰写非虚构报道。当他终于开始投入到另一部长篇小说《苍白的国王》的写作中时,长期困扰他的抑郁症让他几度精神崩溃。2008年9月12日黄昏,他趁妻子外出购物时,在家里的阳台上结束了生命。而《苍白的国王》一部分手稿,就放在他旁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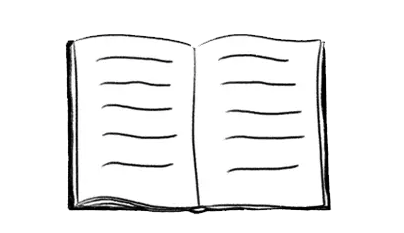
选读
我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周围是各种头与身体。我的姿势有意与屁股底下硬椅子的形状保持一致。这是大学行政部门一间冰冷的房间,木墙板,墙上挂着雷明顿的画,双层窗正对着11月的高温,与外面接待区的办事噪音隔绝。查尔斯舅舅、德林特先生和我最近都是在那里被接待的。
我在这里。
三张脸已分离在夏季休闲西装和半温莎结之上,在这张反射着亚利桑那午间如蜘蛛网一样斑驳光影的油亮松木会议桌的另一头。这是三位主任——来自招生处、教务处、体育处。我不知道哪张脸属于哪一位。
我自以为面无表情,甚至小有愉悦,哪怕我平时受的训练告诉我面无表情总不会错,不要试图做出我自以为代表愉悦或者微笑的表情。

▲ 电影《帕特森》中的书架上有《无尽的玩笑》
我下定了决心希望自己小心翼翼地交叉双腿,把脚踝架在膝盖上,双手放在长裤的大腿上。我的手指交错成了镜中的画面,展现出,于我而言,一连串字母X。这间面试办公室里的其他人还包括:大学的写作主任、大学网球队教练,以及网球学校助教德林特先生。查·塔在我旁边,另外三个人分别坐在、站在、站在我视野的外围地带。网球教练一直在拨弄口袋里的零钱。房间里略微有种跟消化有关的气味。我获赠的耐克球鞋摩擦力强的鞋底与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兄弟晃动的乐福鞋平行,他在这个场合的身份是校长,坐在我认为是我右边的第一个位子上,也面对着三位主任。
左边这位主任是个瘦弱、皮肤泛黄的男人,他脸上一成不变的微笑带着一种拒合作文件上的印戳一样的暂时性特点,这是我最近开始欣赏的一种人格,这种人会不停地从我的角度替我、向我讲故事,以便延迟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回应的需要。他从中间那位头发蓬乱如狮的主任手里接过了一沓打字纸,然后多少是在对着那些纸说话,朝下微笑:
“你是哈罗德·因坎旦萨,18岁,大约一个月之后高中毕业,上的是马萨诸塞州的恩菲尔德网球学校,一所寄宿学校,你也住在那里,”他的老花眼镜是长方形的,网球场的形状,上下都有边线,“你,据怀特教练和[名字听不清楚]主任介绍,是个地区、全国甚至整个北美范围都能排上名的青少年网球选手,非常有潜力的北美组织高校体育协会运动员,怀特教练为了招收你今年2月开始与这里的塔维斯博士联系……”第一张纸被移走,在说话的间歇被整齐放到这沓纸的最底下,“你从7岁开始就住在恩菲尔德网球学校”。
我在思考是否该冒个险,抓一下我下巴的右侧,那里有个小鼓包。
“怀特教练告诉我们他对恩菲尔德网球学校的课程和成绩评价很高,亚利桑那大学网球队曾经多次受益于恩菲尔德毕业生,其中一位就是奥布里·F. 德林特先生,现在也在这里。怀特教练和他的工作人员让我们——”
黄脸主任的措辞整体来说毫无亮点,虽然我也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大家都听懂了。写作主任似乎长着异常浓密的眉毛,右边的主任看我的表情有点奇怪。
查尔斯舅舅在说,虽然他能预见各位主任会倾向于将他所说的话归因于他是恩菲尔德的啦啦队员,但他能保证所有这些都属实,北美排名前30的青少年网球选手,不少于三分之一都在恩菲尔德学习,各个年龄组都有,而这里坐着的我,平时叫“哈尔”,“是我们最好的选手之一”。右边和中间两位主任程式化地微笑着,最左边的主任清了清嗓子时,德林特和教练都点了点头。
“——相信你很可能大一就能给我们学校网球队做出真正的贡献。我们很高兴,”不知道他是自己在说还是在读纸上的字,又移走一页,“这里能有个重要比赛让你南下,给我们机会面对面聊聊你的申请和可能的招生、入学和奖学金的问题。”
“我被要求补充一句,哈尔在非常有知名度的沃特伯格西南地区青少年邀请赛18岁以下男子单打比赛中是3号种子选手,比赛就在伦道夫网球中心——”我推断是体育主任的那位说话了,他歪着的头露出了满是雀斑的头皮。
“在伦道夫公园,万豪征服者酒店旁边,”查·塔插话道,“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这是块真正顶级的球场——”
“还有,查克,查克说哈尔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种子地位。今天早上他以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进入了半决赛,明天还会在网球中心比赛,对战今晚四分之一决赛的胜者,明天早上8点半开赛——”
“尽量在外面出现吓死人的热浪之前开始。还好是干热。”
“——而且显然已经获得了冬天的大陆室内大赛资格,在埃德蒙顿,柯克告诉我——”他头歪得更厉害了,抬头望向左边的网球教练。教练笑着,嘴里一口牙在暴烈的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真的很了不起啊。”他微笑着看着我,“我说得没错吧,哈尔。”

▲ 以华莱士真实故事为原型的电影《旅行终点》
查·塔的胳膊随意交叉在胸口, 肱三头肌在透进空调间的日光下布满了红点。“你说得没错,比尔,”他笑着说,他的两瓣胡子从不对称,“让我告诉你,哈尔非常兴奋,非常高兴能连续三年被邀请参加这个邀请赛,回到他热爱的群体里,拜访你们的校友和教练团队,在这周不能说不激烈的比赛中证明了自己的种子地位,像他们说的,不到戴着维京帽的胖女人唱歌,歌剧还没完呢,而哈尔还没唱完呢,我们打个比方的话。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见到你们,以及参观这里的设施。从他看到的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顶级的。”
出现了片刻的寂静。德林特移动了一下靠着墙板的身子,重新调整了重心。我舅舅面露喜色,试图拉直一根笔直的表带。房间里62.5%的脸都对着我,亲切地期待着。我胸口跳得像烘干机里放了鞋子一样。我做出一个我认为看起来应该会是微笑的表情。我幅度很小地转向这边和那边,有点像朝房间里的所有人投射这笑容。
又出现了片刻寂静。黄脸主任的眉毛变成了抑扬符的形状。其他两位主任看向写作主任。网球教练走到了大窗户前站着,摸着他的平头后脑勺。查尔斯舅舅拍着自己手表上方的小臂。弯曲的棕榈树影子在松木桌上微微移动,某个脑袋的影子是一个黑色月亮。
原标题:《练习两部小说之后,他将文学才华全数耗尽在这部千页巨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