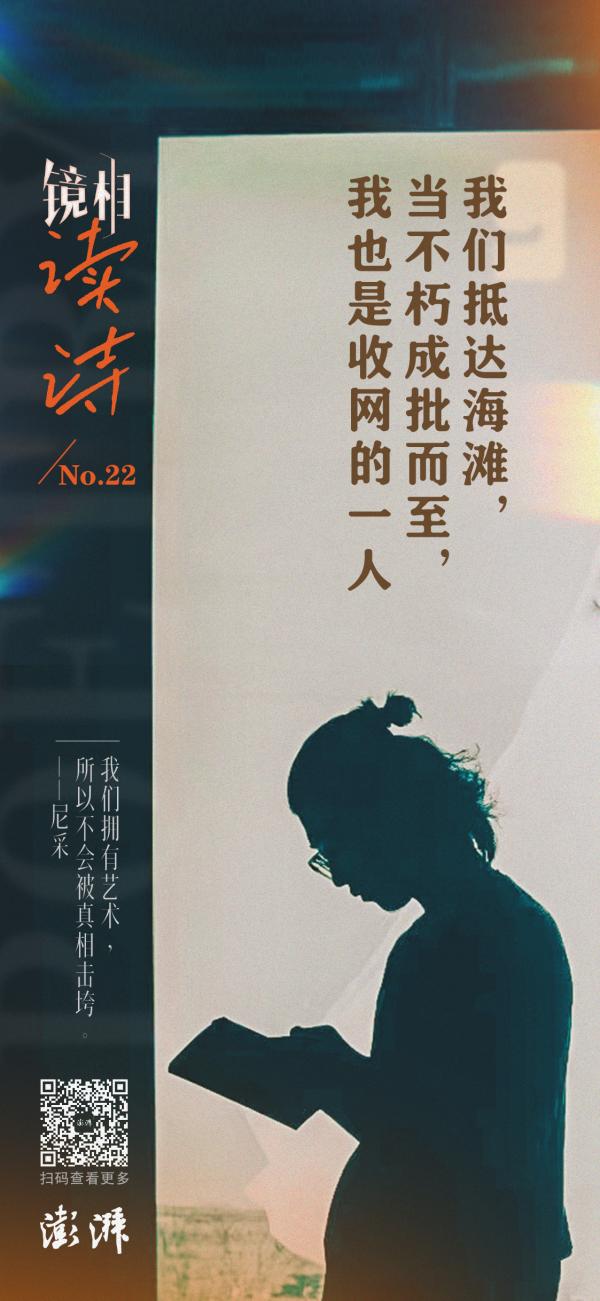镜相·读诗丨我们抵达海滩,当不朽成批而至,我也是收网的一人
编者按:
《镜子》是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自传体电影,其原名《晴朗的白日》取自他的父亲、诗人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塔可夫斯基的母亲后来在《镜子》中扮演了老年的自己,而他的诗人父亲,则在画外音中朗读了大量自己的诗作。他的父亲,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生于1907年,是俄罗斯诗人,也是东方语言翻译家,提倡传统的俄语诗歌风格,并翻译了不少苏联少数民族和波兰、阿拉伯的文学作品。深受父亲影响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后来在《雕刻时光》中写道:“在现实与记忆的邂逅中,两代人的命运叠合在了一起,一边是我的命运,另一边是我父亲的命运。”
周末读诗第22期,本期诗歌皆选自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镜子》,原作者皆为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

本文配图均选自塔科夫斯基《镜子》
我们庆祝每一次天启般的单独相会。
你比鸟儿的翅膀更轻盈,更大胆,一次飞下两重梯阶。
那纯粹的晕眩引领我,穿越潮湿的丁香,进入镜子那端,你的领地。
我在夜色降临时蒙恩。
祭坛的门开启,你的真身在暗中闪现,我缓缓鞠躬。
我醒着,说“有福了”,而我知道,这祝福是冒失的,因你仍在沉睡。
桌上的丁香伸展开来,以天国的蓝色触及你的眼睑。
你蓝色的眼睑安祥,你的手儿温暖。
在水晶的封锁里,江河跃动,山川生烟,大海闪耀。
你手握水晶球,安睡在王座上。
噢公正的主!你是我的。
你醒来,变形,我们的尘世,人类的言辞。
我的喉咙充满了新的力量,给“你”赋予新的意义,现在我称你为“全能”。
万物都被变形,甚至脸盆、水罐。
我们被提升再提升。
魔法建成的城市在我们眼前分开,一如海市蜃楼。
薄荷铺就我们的道路。众鸟护送我们,鱼儿溯流而上,天空在面前铺展。
而命运尾随而至,进入我们的清醒,好似疯汉挥舞着剃刀。
——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

人有一副躯体,如此孤单。
灵魂厌恶这厚厚的外套:耳朵、眼睛、钮扣,
而皮肤只是成片的伤疤,只是骨架的袍子。
它冲出角膜,飞向圣泉,飞向城市,飞向飞鸟的战车。
透过监狱的围栏它听到:树林和草地的欢腾,海水的喧响。
没有躯体的灵魂好似没有穿衣的躯体,不是思想、行为,不是文字和概念。
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谁会回到那没有人跳舞的地方起舞?
我梦见另一个人的灵魂,穿着另外的袍子,
掠过怀疑直达希望,象酒精那样,燃烧而没有阴影,然后溜走,
并留下了纪念品:桌上的丁香。
孩子,不要为可怜的欧律狄刻烦恼,且滚着铁环度过人生,
在你迈出的每一步,你会听到大地的回应,嗓音甜美、单调。
——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

我不相信前兆,也不惧怕凶兆。
我不逃避毁谤和毒害。
没有死亡。
我们不朽。所有人都不朽。
不惧怕死于十七岁,也不惧怕死于七十岁。
世上没有黑暗,没有死亡,只有真实和光亮。
我们已抵达海滩。当不朽成批而至,我也是收网的一人。
我有一所房子,房子不会崩溃。
我随意召唤一个世纪,进入其中,建造我的房屋。
由此,你的妻儿共享我的饭桌,这饭桌侍奉祖先也侍奉子孙。
我们的未来在今天定下。
若我举起手,将有五道光线在你身上停驻。
我的骨头象梁柱,支撑起每一天。
我用尺子测量时间。我穿越时间如同穿越山脉。
我依据我的身高选定一个世纪。
我们南行,在大草原扬起尘土。
野草倒伏,一只蚱蜢碰触着马蹄铁,象个僧侣发表预言,以死亡威胁我们。
我把我的命运紧紧地捆在马鞍上。
我在未来的马镫上站起,如同一个孩子。
我满意于我的不朽,我的血奔流在一个个世纪。
为了一个温暖安全的角落,我乐于交出我的生命。
只要生命的飞针,不要把我像丝线般摆布。
——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

我经常反复做一个梦
在梦里,我好像回到了
我最心爱的地方
那儿曾经有祖父盖的房子
四十年前,我就出生在
那房子里的餐桌上
每次我想走进
总被什么阻挡
这个梦,我做了一次又一次
当我看到那圆木围墙
和幽暗的储藏间
尽管在梦中,我也
能意识到它们是梦
于是快乐消失了
因为我知道自己定会醒来
有时,一点声响把我
从童年房子和松树的梦中惊醒
然后我便伤心不已……
盼望着再做这个梦
这个梦使我又回到童年
重温儿时的欢乐
让我感到一切尚在前方
一切皆有可能......
——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