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从当时的社会来讲,龚自珍是站在最前列的人;从当时的时代来讲,龚自珍又落到时代的后面。这种又先进又落后的特点,突出地表示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性,突出地表现了中国的社会精英与时代要求的差距。这种特征又部分地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龚自珍尚不明自己所处的时代,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精英中,无人觉察到中国面临的时代,那就成了整个中国的悲剧。
我们仅仅用时代局限来贬斥龚自珍和经世致用学说,中国社会就会变得一片黑暗混沌,也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就不能寻觅出中国近代思想的艰难起步,19世纪后半纪的社会改革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中,不能否认其起点很低,以致到今天都不能说臻于完备,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起点,我们才有了后来缓慢且不充分的进步。
*文章节选自《依然如旧的月色:学术随笔集》(茅海建 著 三联书店2023-3)
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一 家世、生平与才华
在 19世纪上半纪,龚自珍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人士。从其家族的谱系来看,完全是官僚与学者结合的完美产物。祖父龚敬身、父亲龚丽正皆为进士出身,分别放过云南迤南道和江苏苏松太道的缺,叔祖父龚守正,更是官至礼部尚书;他的外祖父是清朝著名的学者、《说文解字注》的作者段玉裁,母亲段驯,能诗工画。他的元妻段美贞亦是段玉裁的孙女。成长于这么一个家庭背景中的龚自珍,精于经史,中过进士,做过礼部主事的官。从其人生起步来看,他于仕、学两途似皆可为,或从龚氏先祖,在仕途上谋显达,或从其外祖父,在学术上扬声名。进据退守,都没有什么问题。
脱出其家庭背景,放眼于社会环境,龚自珍生活的乾、嘉、道三朝,“圣朝”的威风依然,而内中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今天的人们从历史的结局很容易看出清朝在当时已经衰落;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感受到康、雍、乾“盛世”风光的人们,不会也不愿将当时已经出现的局部性地区性的问题,当作朝运的根本来思考,他们依旧歌颂赞扬,缩小甚至无视问题的存在。个别极富现实精神的官僚士子,也仅仅把各种问题(如漕运、河工,吏治,武备,冗员)单个排列,谋求单个解决,而不知问题的总合却是要害所在。分项治理,皆无功而返。
龚自珍是个很敏锐的人。他当过小京官,明了上层政治的运作;又随父久居地方衙署,了解民间百姓的生活;且身为文人,与士子们交游甚多,对知识界思想的感受则是更进一层。就是这样,从上到下,从政经到文化,使他有了一个个结实可靠的观察角,因而得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此时的清朝已经是“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相、史、将、士、民、工、商皆为“无才”,甚至连小偷和强盗都“无才”。人才的匮乏,正是“文”“名”“声音笑貌”百般“戳之”的结局。他呼喊:“起视其世,乱亦不远矣。”
龚自珍的这种振聋发聩的呼喊,以及他在一些政论文中对清王朝的激越批评,虽醒目于当时,却不见重于当局,并没有成为清王朝自行改革的助力。但他的议论和对“公羊”学说的探究,却给了当时和后来一部分士子学人以思想的拨动和启迪,使他在倡导经世致用学说时成为众所共认的摇旗呐喊的有力人士。由此,一些士子学人从书斋转向社会,由宋、汉之学转向经世致用,开启了知识界风气的转变。
龚自珍对时政的批评,使他退出了龚氏世代的官宦仕途,而他名士气质的洒脱,也不太合乎当时的官员形象;龚自珍对宋、汉之学的指责,又使他未能退入段氏的治学门径,尽管他在这方面的才学功力,已经得到当时很有分量的承认。社会环境使他背离了家庭背景。以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来衡量,他的这种举动无异于“颓唐”。而恰恰是这种“颓唐”,使龚自珍的名声和社会对他的思想评价高于他的祖辈们,而成为今日学术界所推重且不断研究的人物之一。

龚自珍纪念馆
二 传统意识下的危机感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清王朝当时已经遇到了双重的危机:一是传统的王朝危机,即兴废、治乱、继绝;一是西方殖民主义及其近代化的政、经、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从历史变革的最后结局来看,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最基本的特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尽管前者所显露出的痕迹远远多于后者。
从思想体系而言,龚自珍仍是传统之中的人。他从传统之学中切身感受而体会到的清王朝即将面临的“乱世”,仅仅是传统的王朝危机。从他去世十多年后发生的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内乱来看,不能不赞叹他的先见之明。这种机敏,还可以举他的《西域置行省议》为证。这篇完成于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文章,提出以优厚条件迁内地之民实边,改新疆为行省。就在这年,南疆爆发了长达 8年的张格尔之乱。若联系到同治初年开始的包括阿古柏在内的全疆战乱和 1884年(光绪十年)的新疆建省,龚自珍的预见性可谓高明。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是传统之学中的应有之义,看不出多少时代的新精神。
在龚自珍的文献中,论及西方殖民主义的只有两篇,一是与《西域置行省议》同时完成的《罢东南番舶议》,一是鸦片战争前的《送钦差大臣候官林公序》。前文已佚,仅在龚氏自刻本《定庵文集》中存目。文章的内容今已不可得知,但从标题来看,似乎是要求停止中外贸易。这一种推测,我们又可以从后一篇文章中得到证实。
道光年间的烟毒泛滥,引起了清王朝内部正直人士的警觉。道光十八年( 1838),林则徐奉旨进京,被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龚、林这两位交往已久的朋友,在京有过一次晤谈,龚并当面表示愿随林南下,参予禁烟。《送钦差大臣候官林公序》,正是林临行时龚的赠文。在这篇文章中,龚自珍提出了十项建策——三项“决定义”、三项“旁义”、三项“答难义”、一项“归墟义”。
“决定义”是指应当决而断之不可游移的决策,其分别为:一、严禁白银外流;二、吸烟贩烟造烟者皆诛;三、宜带重兵自随。“旁义”是指应该连带一并解决的问题,其分别为:一、杜绝呢羽、钟表、玻璃、燕窝等奢侈品的进口;二、限期令外国人全部离开澳门,仅留“春馆”一所,供外国商人来船交易时栖止,交易结束即随船离去;三、讲求火器,并从广州带能工巧匠以修整军器。“答难义”是用来对付各种非难的方法,其分别为:一、用禹、箕子的食第一,货第二的言论,说明禁银出海时期减少对外贸易更为有利,以对答儒生利用汉朝刘陶关于食、货旧议论的非难;二、以对外贸易之大利在于米,其余皆为末,国家断不恃海关税收的论点,以对答海关官吏关于禁止呢羽等奢侈品进口必将减少关税的非难;三、以仅仅驱逐外国人,并将不逞外国人和奸民正典刑,而不予之海上交战的做法,以对答迂诞书生所谓宽大为怀、不启边衅的非难。“归墟义”是指总结论,龚自珍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
龚自珍的这篇文章,是其唯一较系统地涉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论著,因而值得细细究察。综观他的十项建策,不难得到以下印象:一、坚决的禁烟决心。这表现在决定义的第一、二项。白银外流,烟毒害民,这是任何一位未坠入鸦片贿赂陷阱的正直士大夫都会痛心疾首的,龚自珍正是其中的一员。他主张用激烈手段力断恶流。但是,他也同当时其他人士一样,没有看出鸦片在中、英、印三角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把障碍仅看为国内“黠滑”官僚、幕客和商人,因而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认为两整年(“两期期年”)即可“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实际上,他还没有看出鸦片的背后站着强大的敌手——英吉利。二、没有意识到禁烟会引起大规模的战争,也无准备大规模的武力抵抗。一些论者引用其决定义第三项、旁义第三项,即劝林多带重兵讲求火器,来说明龚已有用武力抵抗侵略的思想。这其实是误解。龚自珍因为不明林则徐禁烟的具体做法,以为林会远离广州城,以文臣孤身进驻“夷勒”澳门,故建议“重兵自随”,以防不逞之外国人和奸民的破坏。讲求火器也是针对此事。而在“答难义”第三项中,龚还明白声言,“至于用兵,不比陆路之用兵,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非有大兵阵之原野之事”,因而不可能“开边衅”。也就是说,直至此时,他仍没有感受到西方的威胁,也没有发出这方面的警报,他的用兵规模,大抵相当于今日反走私的警察行动,只不过当时的清朝还没有警察。三、保守的封闭思想。《罢东南番舶议》的内容虽不可得知——若从题目来看是要求停止外洋船只的来华贸易,但从这篇文章可知,龚自珍是轻视对外贸易的,至少要求缩小对外贸易的规模。由于当时广东、福建两省产米不足食用,需进口洋米来调剂,龚在此文宣称,“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西方“所重者”,皆中国“不急之物”“宜皆杜之”。由此反映出来的龚自珍的政经思想,仍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重农主义。这一点,我们又可以从他另一篇最能反映其理想社会模式的论文《农宗》中,得到最清晰不过的证明。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
以武力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夷”变夏为基本标志的新时代,即将冲面而来,而龚自珍等社会精英们尚无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龚自珍没有理解他所处在的时代。
龚自珍不是一个政论家,他并未提出改革中国的完整方案。然其枝节零散地提出的改革措施中,无不可看出中国传统的背景,并无新时代的气息。龚自珍只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才气思辨显露在他对社会的批判之中,但这种批判仍是用中国传统之是,来非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人人皆可感受到的浓郁的复古主义味道。在儒、道、法、释糅合羼杂且以儒家为主的龚自珍思想中,他的理想社会,仍是三代之类的境界,仍未脱离中国传统的窠臼。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力图用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方法来解决当时社会中的传统类型的问题,一开始就与时代要求不相合拍。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结局足以证明:清王朝在后来的实践中平定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内乱,可以认定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巨大成功,但对付来自海上的西方列强,却战无不败。
三 社会精英与时代要求的差距
从当时的社会来讲,龚自珍是站在最前列的人;从当时的时代来讲,龚自珍又落到时代的后面。这种又先进又落后的特点,突出地表示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性,突出地表现了中国的社会精英与时代要求的差距。这种特征又部分地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龚自珍尚不明自己所处的时代,只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精英中,无人觉察到中国面临的时代,那就成了整个中国的悲剧。
尽管人们常用预见性作为衡量思想家的标准,但是,当时中国无人预见新时代的到来,又恰恰说明此类预见之难。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没有新的思想资料和新的思路,要对另一种陌生的文明的未来趋势做出判断,无论怎么说也是难以办到的。人们因此而对龚氏及其同辈人并不苛求,予以原谅,表现出一种历史的理解精神。但是,我们又须指出,在这种理解的背后,又存在着多么沉重的历史遗憾。对龚氏一人而言,缺乏另一种文明的思想资料而感到陌生,或许有着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对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子而言,没有收集此类资料而加以分析或供他人分析,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认为是正常的。海通二三百年后,中国士大夫阶层仍然如此无知,正说明了他们的病症。
龚自珍于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去世,没有看到战争的结局和历史的归处。设或天假以寿,他的思想会否有大的变化?人们常常以他同时代的魏源为例,说明经世致用思想之必然归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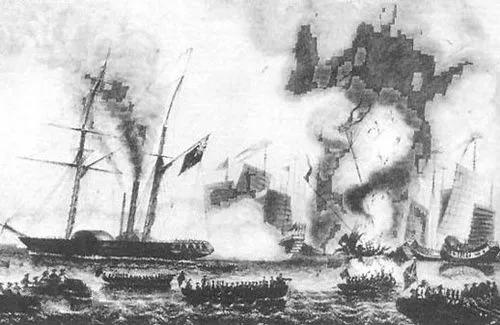
1841年1月7日英军进攻虎门外大角、沙角炮台
魏源是龚氏的好友,除亲身的交往外又别有心交。以魏氏为例,应当说是恰当的。
人们常用魏氏撰刻于鸦片战争以后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遭遇,来说明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来说明《海国图志》所具有的先进品质和历史功能。必须承认,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能否呼喊出学习“蛮夷”的口号,不管它本身是多么有局限性,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日本社会对《海国图志》的接受,得力于它的“兰学”传统,得力于它正处于社会变动的大转机之中,得力于它的众多优秀思想家对外来危机及西方知识的敏感……没有这些条件,仅仅是《海国图志》这一部著作,在日本不会兴起比中国更大的风浪。而且,在日本的变法维新过程中,正如几十年后即洋务、维新时期清朝重新认识《海国图志》的价值那样,这部著作的发挥作用时间和作用力,都是极为有限的。这也恰恰说明魏源思想的功效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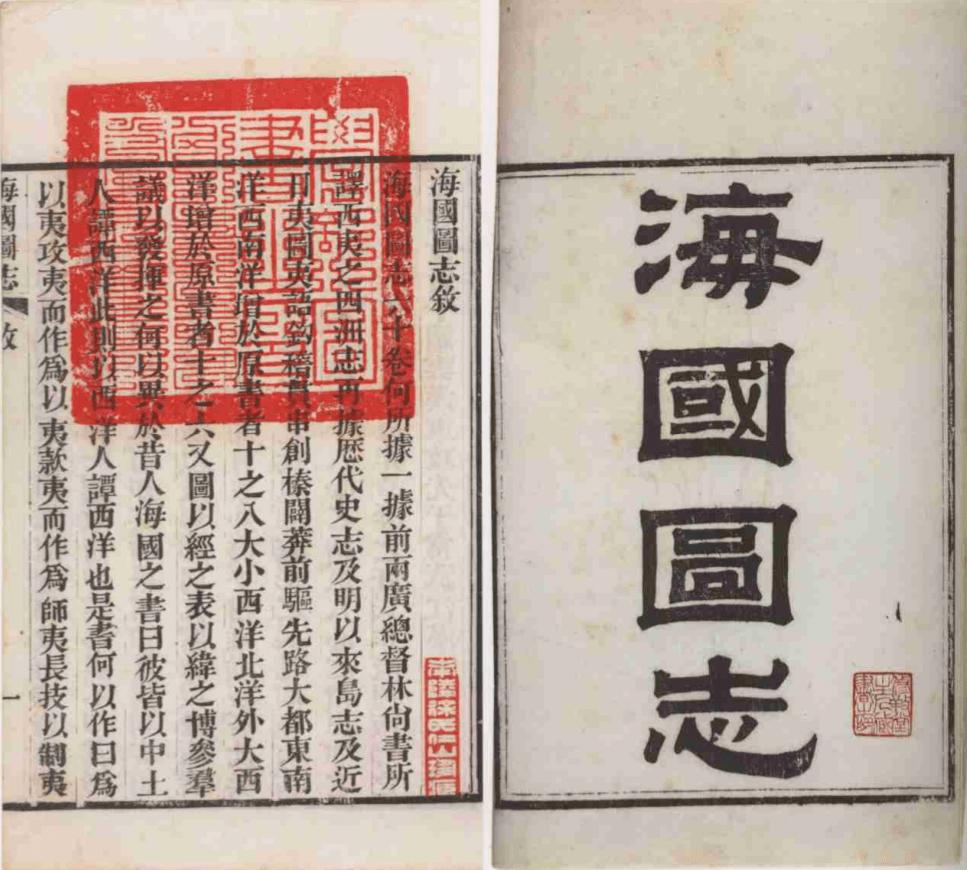
《海国图志》1847年刻本
如果从 19世纪后半纪的历史来看,不难得出结论,经世致用是通往社会变革思想的一个中介,就同龚自珍是处在中国社会和时代要求两者之间的中介那样。我们也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许多反对改革的保守主张也来自经世致用,而并非直接源于宋、汉之学。进步与保守的差别,不在于是否要求改变现状,而是用什么去改变,即用西方的方法还是中国传统的方法。如果我们从这一点去考察经世致用学说的根本实质,很显然,它所倡导的仍然是后者,它并没有导向社会变革学说之必然。
因此,我们绝不应否定龚自珍才学品识之优长,也绝不能低估龚自珍身上的时代局限,因为只强调前者而不认识后者,就无法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为何如此曲折,多灾多难。今天,许多社会科学家们只强调前者而回避后者,使得更多的非研究者误以为:在 19世纪上半纪,中国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文化,已经有了正确的领路人。中国社会的矛盾,只不过是腐败的统治者压制已经正确把握中国命运的先进中国人。似乎只要龚、魏等人当政或他们的主张被当局全盘接受,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难题就可以迎刃化解。实际上,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也等于说,中国的传统方法就可以救中国,西方的方法则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推论无疑是不准确也不可靠的,但在许多人身上,包括我本人十多年前初习近代史时,又实实在在地产生过。毫无疑问,在许多社会科学家的内心中,非为不晓得龚自珍等人的时代局限,但对龚氏等人的偏爱和“善善”“恶恶”的思维模式,有意或无意地缩小了龚氏等人的局限,也就极容易导出上述推论。
同样,我们仅仅用时代局限来贬斥龚自珍和经世致用学说,中国社会就会变得一片黑暗混沌,也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就不能寻觅出中国近代思想的艰难起步,19世纪后半纪的社会改革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中,不能否认其起点很低,以致到今天都不能说臻于完备,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起点,我们才有了后来缓慢且不充分的进步。
由此而知,在龚自珍身上集先进与落后于一体。他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发展的一个最初步的中介,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
刊于《社会科学》(上海)1993年第 1期
▼

依然如旧的月色:学术随笔集
茅海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3
近代史专家茅海建教授的学术随笔集。从不同的侧面记录了作者近二十年习史、治学、思考的学术人生,像散落在海滩上,深深浅浅、寻寻觅觅的一串串脚印。
文章分为四辑。怀人的第一辑如师长学行录,有陈旭麓、黄彰健、卫藤沈吉、朱维铮等活跃在中外史坛的学人、师长,近距离观察其内心追求,亲切温暖,耐人寻味;第二组笔涉学术思潮、学界生态,讨论的问题颇有启发性;第三辑可见其治学心迹的坦陈,对年青学人有垂范的启示;最后一辑有趣味的近代文化生活史事之考察,作者慧眼独具,颇多“看点”。增订本删去了初版中六篇自著的序言,增补了回忆蔡鸿生、章开沅先生等多篇新文章。
对许多熟悉茅海建的读者来说,在 “史实重建、精微考辨”的重大历史命题之外,读读这本书,可以更多地获取有趣味的近代史事,还可以触摸到这位严谨治学的教授内心深处,有着怎样炽热深沉的情感。

原标题:《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