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所有的美丽与血泪》:谁能定义疼痛
谁能定义疼痛
奥斯卡奖项揭晓的这一天,不是只有获奖作品应该被书写。一部记录了南·戈尔丁与止痛药生产商普渡药业斗争的纪录片《所有的美丽与血泪》,虽落败于《纳尔瓦尼》,却仍值得我们的关注。
普渡药业和它背后的萨克勒家族,明知奥施康定(OxyContin)具有强成瘾性,却仍将它推向全球。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奥施康定在1996年上市,三年内就引发大面积药物滥用,1999至2018年间,近45万美国人因滥用阿片类药物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奥施康定。
 ©️ 《成瘾剂量》2021
©️ 《成瘾剂量》2021《成瘾剂量》(2021)中三位试图扳倒萨克勒帝国的检察官并非独行。著名摄影师、策展人、社会活动家南·戈尔丁不惜摧毁自己艺术作品的展台,也要向导演了这一切的萨克勒家族宣战。
戈尔丁用摄影凝固前所未见的瞬间,拿起极具破坏性的武器——艺术,在大都会博物馆的丹铎神庙下、萨克勒家族的资助地,在永久收藏自己作品的博物馆前,投掷药瓶、嘶声呼喊、模拟死亡,以求能破坏身后那个令无数人上瘾的药品帝国,哪怕撕开那么一点裂口。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从1973年在波士顿开幕的首场个展开始,戈尔丁便以摄影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活跃至今。本片选择以戈尔丁某段时期的摄影作品或档案镜头作为章节名——讲述戈尔丁,当然是让她的作品成为叙述者更加合适。
从1973年在波士顿开幕的首场个展开始,戈尔丁便以摄影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活跃至今。本片选择以戈尔丁某段时期的摄影作品或档案镜头作为章节名——讲述戈尔丁,当然是让她的作品成为叙述者更加合适。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她最负盛名的摄影序列《性依赖叙事》(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必然是其中最有力的。这组戈尔丁在1979-1986年间拍摄的照片最初被作为幻灯片展出,后收录在同名摄影集中,不断更新内容,也在不同的节展上现身。
她们横卧,仰躺;或凝视镜头,或毫不在意;有的睡眼惺忪,有的刚结束狂欢;仰赖于沙发床榻,也仰赖于被戈尔丁提炼出来的、80年代纽约下东区的城市生活。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但戈尔丁的创作生涯并非一开始就如此顺利。也是时候邀请出另一位叙述者——是且只能是她自己。我们听到她讲述童年和少女时期被驱逐的经历。学校、社区、父母和寄养家庭,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她停留。声音来自当下,视线却投向过去。在戈尔丁的早期肖像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读出她初才掌握一门语言的羞赧。
对于青年时期的戈尔丁,说话并非必然,她甚至可以六个月不吐一个词,因为拍照才是她的语言。彼时她使用一台宝丽莱,相机成为了她的声带,“忽然间,我有了个性,它带给我一种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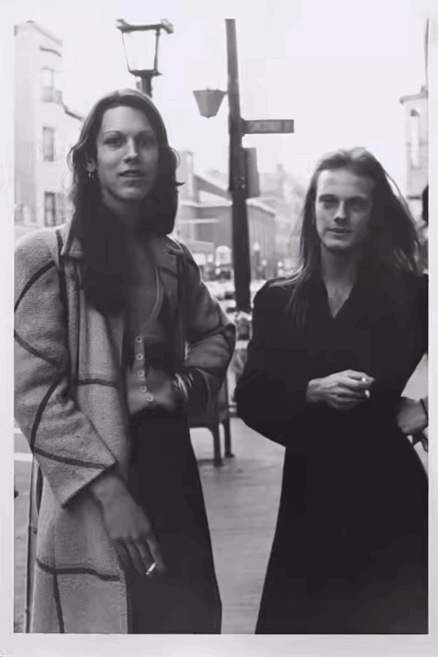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摄影帮戈尔丁熬过恐惧、保护自我、倾诉不同。在认识好友大卫·阿姆斯特朗以后,她很快搬到剑桥,和大卫还有他的变装皇后伴侣一起生活。在此期间,戈尔丁开始学习摄影,为变装皇后们拍摄明胶银盐照片。她爱上女人也钦慕男人,并着手制作人生中第一部幻灯片。
《艾薇穿着秋天》(Ivy wearing a fall, Boston)也是拍摄于这段时期,它如今是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永久藏品。变装皇后lvy(常春藤)是照片主角,一种代表春天的植物也可以“穿着秋天”。在没那么开放的1973年,戈尔丁在创作伊始便挑战了性别固化印象。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在这里,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戈尔丁承认她曾做过性工作者,比起在酒吧扭扭屁股跳脱衣舞,妓女的经历“也太糟糕了”。但戈尔丁必须这样做,“我得靠它来挣钱买胶卷”。
类似的糟糕经历还有很多,但她都可以把它们兑换成影像。她被男友布莱恩打断眼骨,眼睛近乎失明,照片成为了伤愈档案,提醒自己和更多女性去说出被家暴的经历。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在这些由肉体、欲望和虚无主义构成的图像里,戈尔丁用无缝的凝视注销色情的羞耻感,将个人痛苦转化为对文化的冲击,再把私人体验变成政治风暴。
戈尔丁带到画廊和美术馆的作品曾被尽数拒绝,世界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样的作品:她们交媾,他们爱恋,她们和他们虚掷人生,但这一切是彩色的、艳丽的、震撼的。这份震撼由一位女性捕捉,如同风暴一般把大众认知抛进激流,而同时代的男性创作者,不过还在沉迷竖版黑白照片罢了。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八十年代前后的美国,艺术的仲裁权掌握在男性手中。但戈尔丁不管这些,她自知站在风暴中心,但她就是要用手中的镜头破坏系统,止息流云,凝固风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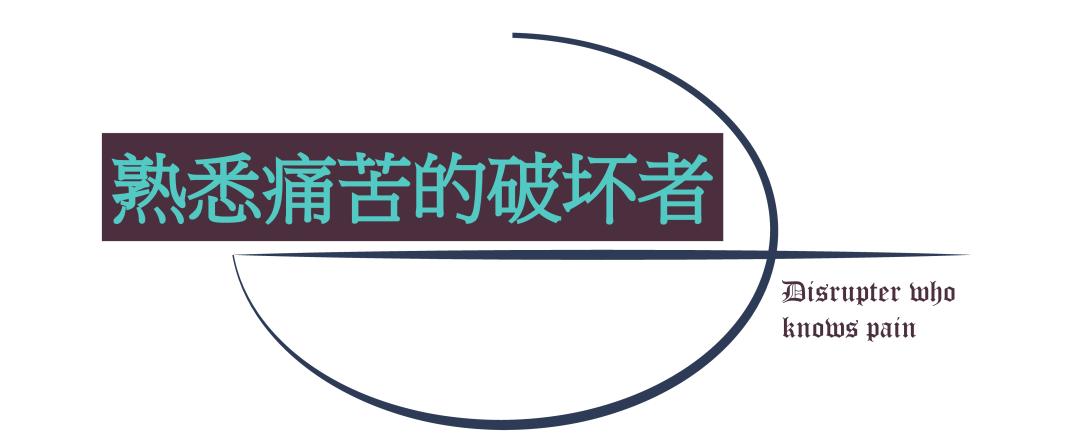 或许连戈尔丁自己也没有想到,对奥施康定发起的抗争会成为一场战役。她因手腕疼痛去寻求治疗,医生给她开了奥施康定,她因此形成依赖,饱受毒瘾折磨。此时她在《性依赖叙事》中拍过的很多友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大多死于毒瘾或艾滋病。为此,戈尔丁在策展《见证:反抗消亡》(Witnesses: Against Our Vanishing)中担任了这些病症的见证者,她想要让他们被看见。
或许连戈尔丁自己也没有想到,对奥施康定发起的抗争会成为一场战役。她因手腕疼痛去寻求治疗,医生给她开了奥施康定,她因此形成依赖,饱受毒瘾折磨。此时她在《性依赖叙事》中拍过的很多友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大多死于毒瘾或艾滋病。为此,戈尔丁在策展《见证:反抗消亡》(Witnesses: Against Our Vanishing)中担任了这些病症的见证者,她想要让他们被看见。 ©️ Nan and Brian in Bed 1983
©️ Nan and Brian in Bed 1983奥施康定当然需要为此负责。《成瘾剂量》详细描述了萨克勒家族将这种药推向世界的步步为营。他们利用“缓释系统”的说辞,给这种第二类麻醉剂做不致上瘾的宣传;创造“爆发性疼痛”和“假性成瘾”的话术,来帮助医生给患者加大剂量、翻倍销售额;资助所谓的“疼痛学会”,只为了让专家为“中度疼痛也需要治疗”的说辞站台;他们甚至和药监局之间缔结了潜规则,吸纳为奥施康定批准特别标签的柯蒂斯·莱特,进入到普渡药业担任高管。
话术并不会改变数据。在奥施康定以前,从未有二类麻醉剂宣称不致上瘾;奥施康定投入使用后的地区,均出现暴力、卖淫、自杀、遗弃案例激增的现象;人们甚至会抢劫处方药店,只为了获得更多的奥施康定。
 ©️ 《成瘾剂量》2021
©️ 《成瘾剂量》2021萨克勒家族抓住了“疼痛文化”的关键。为了推广一种药品,他们不惜制造一种病症。你甚至能在其中见识到一些反本能的景观。在美国,萨克勒家族通过游说“缓解疼痛能让人们重拾幸福生活”重新定义了阿片类药物,那些曾经谨慎使用阿片类药物的医生,甚至落入不给患者开止痛药就不人道的困境。而在德国,奥施康定的推广则遭到前所未有的阻力,人们认为,疼痛是治疗疾病的必然组成部分。你如何看待这种药品,在于你如何定义疼痛的本质。
戈尔丁熟悉疼痛,它贯穿了她的整个人生,从姐姐芭芭拉自杀时就与她相随,2006年的《追魂》(Chasing a Ghost)便是戈尔丁应对这道创伤的方式。年代与家庭掠夺了姐姐的生命,给戈尔丁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也令她成长为系统破坏者。从这段童年经历步入戈尔丁的作品,或许就能理解她作品中的狂热为何总是读来哀伤,她影像里的生命为何每每包藏着毁灭。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于是戈尔丁来到了她的战场。她建立了名为疼痛(PAIN)的反萨克勒家族小组,决定从她事业的前哨站——博物馆发动战役。这里的许多展厅写着萨克勒家族的名字,画作因为萨克勒的资助而能摆在这里,学习中心被收纳到他们的系统中。艺术场因此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黑市,帮助洗去钞票上的鲜血,使得萨克勒家族摇身变为美国最大的慈善家族之一。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旁观了这些战争。劳拉·珀特拉斯的镜头宛若战地记者,穿梭在药瓶、横幅、处方笺和幸存者之中;戈尔丁发起的战斗劈开了金钱帝国在博物馆中搭就的版图,捣毁了萨克勒以艺术之名修建的战壕。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当艺术界开始意识到这一点、选择拒绝萨克勒的捐赠时,世界也就离戈尔丁索求的真谛更近了一步——维持真实的记忆。不管那记忆是关于姐姐的美丽与血泪,还是还原上瘾者的疼痛和麻痹,又或者白色药片下的真实。正如戈尔丁说的那样:“真实的体验是有味道的、肮脏的,并不会包裹在平淡的句号里。”
那是在戈尔丁体内燃烧着的百万只蜡烛,味道刺鼻,蜡油斑驳,烛火可以焚毁一切,也足以摧毁肮脏的东西,只为让我们看见真实。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
©️ 《所有的美丽与血泪》2022来聊
今年你喜欢却没获奖的作品是?
撰文 / 闵思嘉
原标题:《上瘾,导向所有的美丽与血泪》

